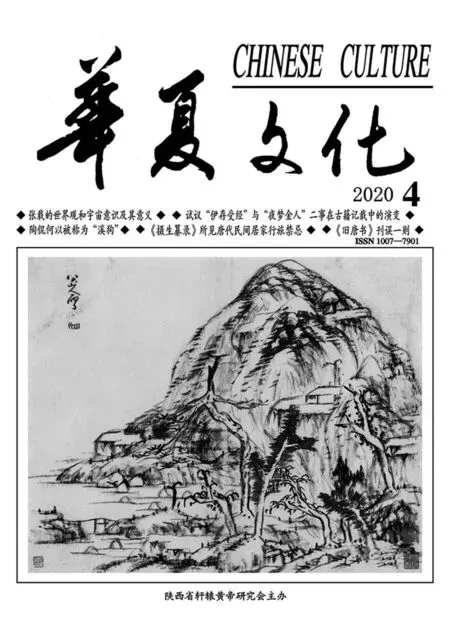《論語(yǔ)》“中庸”觀解析
□袁澤宇
孔子在《論語(yǔ)》中說(shuō):“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yǔ)·雍也》),將“中庸”視為最高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那么隨之就帶來(lái)了一個(gè)疑惑:“中庸”為何能成為最高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筆者認(rèn)為,這需要從以下三方面進(jìn)行分析:第一,“中庸”的來(lái)源是什么;第二,“中庸”的具體表現(xiàn)是什么;第三,“中庸”的最終目標(biāo)是什么。
一、“中庸”的來(lái)源是什么
“中”“庸”二字在《論語(yǔ)》之前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首先解釋“中”字,“據(jù)甲骨文研究的成果,以及早期文字釋義,‘中’可以‘引申為一切之中’”(唐蘭:《殷墟文字說(shuō)》,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1年版,第118頁(yè))。寶雞出土的西周時(shí)期青銅器“何尊”銘文上的“中”,是指方位上的“中央之地”。《周易》里“中”字出現(xiàn)多次,《訟》卦中說(shuō)“有孚窒惕,中吉,終兇”,“中”與“終”相對(duì)應(yīng)。高亨在《周易大傳今注》的解釋是:“筮遇此卦,戰(zhàn)爭(zhēng)中有所俘虜,但須恐懼警惕,其過(guò)程是中段吉,終段兇。”(濟(jì)南:齊魯書(shū)社,2009年版,第86頁(yè))“中”在此代指時(shí)間空間之意。《中孚》的卦辭為:“中孚豚魚(yú),吉。”“‘中’,射中也。孚,借為浮,漂浮在水面。‘中浮豚魚(yú)’,射中漂浮在水面上的豚魚(yú)。”(《周易大傳今注》,第426頁(yè))此時(shí)“中”為動(dòng)詞。以上“中”字都還不具有道德的涵義。而在《尚書(shū)·酒誥》中記載:“丕惟曰爾各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此時(shí),“中”與德聯(lián)系在一起,具有了道德的引申意義。其次是“庸”的涵義,《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的“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意思是周武王把長(zhǎng)女太姬嫁給了胡公滿,此處“庸”解釋為“用”。
“中”與“庸”二字雖早已有之,但“中庸”一詞則首次出現(xiàn)于《論語(yǔ)》之中。在書(shū)中,孔子講“中庸至德”(《論語(yǔ)·雍也》),那“德”從何來(lái)?《論語(yǔ)》中解釋為從“天”而來(lái)。《論語(yǔ)·述而》說(shuō):“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這就說(shuō)明人的道德來(lái)源于天,而“中庸”為德,自然就來(lái)源于“天”。
關(guān)于《論語(yǔ)》中“天”的觀念,筆者認(rèn)為,孔子是繼承并發(fā)展了“三代”以來(lái)“天”的觀念。“三代”的“天”是指“最高的神明”,主宰人類的一切,具有至上性,而孔子繼承了“天”的至上性。“子曰:‘獲罪于天,無(wú)所禱也。’”(《論語(yǔ)·八佾》)只要得罪了天,誰(shuí)都救不了你。這說(shuō)明“天”在孔子思想中仍然具有絕對(duì)的權(quán)威。但此時(shí),“天”還僅僅是“神明”嗎?在《論語(yǔ)·泰伯》中孔子說(shuō):“大哉?qǐng)蛑疄榫玻∥∥『酰ㄌ鞛榇螅▓騽t之。”這句話翻譯過(guò)來(lái)就是堯非常了不起,天是最高最大的,只有堯能夠向天學(xué)習(xí)。只有堯可以學(xué)習(xí)“天”,而堯是具有完美品德的圣人,只有具備了完美品格的圣人才可以向“天”學(xué)習(xí),那“天”不就應(yīng)該具有道德品格嗎?否則圣人就不能學(xué)習(xí)“天”。另外,孔子還說(shuō)“子不語(yǔ)怪力亂神”(《論語(yǔ)·述而》)。孔子將鬼神與怪力放在同一層面上,說(shuō)明孔子并沒(méi)有將鬼神置于崇高的地位,那就不可能將鬼神等同于“天”,視為唯一的至上性存在。而且他還說(shuō):“天生德于予。”(《論語(yǔ)·述而》)“天”給予我德行,并不是“神明”賦予我的。可見(jiàn),孔子繼承了夏商周有關(guān)“天”的至上性特點(diǎn),但“天”具備了道德屬性,不再完全等同于“神明”。“道德”是“天”的一部分,具有了至上性,違背了道德就是違背“天”。而在《論語(yǔ)》諸多德目之中,“中庸”為至德,最高的道德,屬于“天”的一部分,違背“中庸”,就相當(dāng)于違背“天”。
“天”雖然有規(guī)定原則,但實(shí)際上人在做事的時(shí)候并不是全部符合“天”的標(biāo)準(zhǔn),有可能會(huì)符合“天”,也有可能會(huì)違背“天”,違背“中庸”。《論語(yǔ)》中提到“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為政》)。那這些言論為何不正確?因?yàn)檫`背“中庸”。“中庸”就是“恰到好處”,防范“過(guò)猶不及”(《論語(yǔ)·先進(jìn)》)。以老師教授學(xué)生知識(shí)為例,站在老師的角度,所有“教授不成功”的情況無(wú)非兩種:教授的知識(shí)過(guò)于淺顯,學(xué)生不愿意聽(tīng);或者就是教授的知識(shí)過(guò)于深?yuàn)W,學(xué)生聽(tīng)不懂。而只有老師教授得恰到好處,即學(xué)生愿意聽(tīng),也聽(tīng)得懂的情況就是符合“中庸”的。前兩種情況都是違背了“中庸”,第一種情況就是“不及”,而第二種情況就是“太過(guò)”,都不符合“中庸”的原則,是失敗的教育。
“中庸”作為一種道德規(guī)范,指導(dǎo)人的思想和行為,這具體表現(xiàn)在《論語(yǔ)》中的教育思想、工夫論、政治思想三個(gè)方面,同時(shí)也顯現(xiàn)出“中庸”對(duì)于做人做事的重要意義。
二、“中庸”的具體表現(xiàn)
在《論語(yǔ)》的教育思想中,“中庸”主要體現(xiàn)在教的方法和學(xué)的方法這兩個(gè)方面。孔子關(guān)于“教”,主張“因材施教”,針對(duì)不同的學(xué)生有不同的教育方法。它蘊(yùn)含于“中庸”里,是“中庸”的要求。《論語(yǔ)·顏淵》中顏淵、仲弓、司馬牛三個(gè)人都向孔子請(qǐng)教“仁”,但孔子卻分別給出了“克己復(fù)禮為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其言也訒”這三種不同的回答。這幾種不同的答案正是針對(duì)不同學(xué)生的情況所作出的不同回答,恰如其分地解決了學(xué)生的疑惑,是孔子踐行“中庸”的具體表現(xiàn)。孔子能做出恰當(dāng)?shù)幕卮穑且驗(yàn)樗至私膺@三個(gè)學(xué)生的特點(diǎn)。可見(jiàn),要做到合乎中庸,前提就是要了解不同的情況,然后才能做出恰當(dāng)?shù)幕卮穑簿褪且龅健熬唧w問(wèn)題具體分析”。所以,要踐行“中庸”,這一方法認(rèn)識(shí)是必不可少的,“中庸”包括“具體問(wèn)題具體分析”。
在“學(xué)”的方面,“中庸”是認(rèn)識(shí)事物本質(zhì)的一種方法。“吾有知乎哉?無(wú)知也。有鄙夫問(wèn)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論語(yǔ)·子罕》)中的“叩其兩端”的學(xué)習(xí)方法是指針對(duì)不同的事物都要從開(kāi)始和結(jié)束的兩端出發(fā),仔細(xì)了解之后就可以確定事物的本質(zhì)。從“開(kāi)始”和“結(jié)束”出發(fā),最后是在“中”點(diǎn)匯合,那就說(shuō)明“中”等于本質(zhì)。但如果認(rèn)識(shí)偏向于“開(kāi)始”或是“結(jié)束”,就是“過(guò)猶不及”,都無(wú)法正確認(rèn)識(shí)事物。合乎“中”才可了解事物的本質(zhì)。這種學(xué)的方法應(yīng)該是我們?cè)趯W(xué)習(xí)中所采用的普遍方法,是一種平常日用之法,這也就是“庸”的含義。可見(jiàn),《論語(yǔ)》的教育思想中一直貫穿著“中庸”之道。教育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成人,也就是學(xué)會(huì)如何做人,而要做人就必須按照人的標(biāo)準(zhǔn)行事,踐行這一標(biāo)準(zhǔn)的過(guò)程就是工夫論。
《論語(yǔ)》中的工夫論是以“仁”為核心,將人按照踐行“仁”的程度分為小人、君子和圣人三個(gè)層次。在這三種層次里,孔子認(rèn)為圣人的境界太高,眾人能努力做到君子這一境界就已經(jīng)很不錯(cuò)了。“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見(jiàn)之矣;得見(jiàn)君子者,斯可矣。’”(《論語(yǔ)·述而》)而“中庸”就貫穿于成為君子的方法之中。孔子提出“質(zhì)勝文則野,文勝質(zhì)則史,文質(zhì)彬彬,然后君子”(《論語(yǔ)·雍也》)。君子樸實(shí)和文采兩種德行都要具備,就如同于一個(gè)杠桿,樸實(shí)與文采兩種同樣重要的德行各在兩端,要讓杠桿平衡,就必須找到一個(gè)“平衡點(diǎn)”。這個(gè)點(diǎn)不一定一直在最中間,要看具體情況,有時(shí)需要偏向樸實(shí),有時(shí)需要偏向文采,但“平衡點(diǎn)”是一直存在的,這個(gè)“平衡點(diǎn)”就是“中庸”。當(dāng)“平衡點(diǎn)”確定后,就不能再向任意一方傾斜,過(guò)與不及都不行,否則平衡就會(huì)被打破,就沒(méi)有堅(jiān)持“中庸”,自然就不是君子。就如同《論語(yǔ)·季氏》所言:“君子有三戒:少之時(shí),血?dú)馕炊ǎ渲谏患捌鋲岩玻獨(dú)夥絼偅渲诙罚患捌淅弦玻獨(dú)饧人ィ渲诘谩!本釉诓煌瑫r(shí)期所要警戒的問(wèn)題也不一樣,“戒色”對(duì)于少年君子來(lái)說(shuō)就是“平衡點(diǎn)”,“戒斗”“戒得”也分別對(duì)應(yīng)壯年君子和老年君子的“平衡點(diǎn)”。另外,“君子博學(xué)于文,約之于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論語(yǔ)·雍也》)。文要受到禮的約束,如何約束?就是找到文采與禮的要求相符的完美“平衡點(diǎn)”。在這里要強(qiáng)調(diào),任何事物都存在著“平衡點(diǎn)”,但每個(gè)“平衡點(diǎn)”的要求是會(huì)隨著不同的條件發(fā)生不同的變化的。即在不同的情況下,“中庸”作為最恰當(dāng)?shù)奶幚碓瓌t不會(huì)改變,但恰當(dāng)?shù)臉?biāo)準(zhǔn)也會(huì)有所不同。所以君子在做事時(shí)就要堅(jiān)持“中庸”,防范“過(guò)猶不及”。
“中庸”也同樣適用于治理國(guó)家的過(guò)程中。《論語(yǔ)》中所提出的政治思想,涉及了君臣問(wèn)題,“定公問(wèn):‘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duì)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yǔ)·八佾》)。“禮”與國(guó)的關(guān)系,“子曰:‘以禮讓為國(guó)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guó),如禮何’”(《論語(yǔ)·里仁》)。人才對(duì)于國(guó)家的重要性,“子曰:‘先有司,赦小過(guò),舉賢才’”(《論語(yǔ)·子路》)。以“德”治國(guó)的重要性,“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論語(yǔ)·為政》)。這些政治理念中的每一個(gè)都針對(duì)國(guó)家管理中的一個(gè)問(wèn)題,想要解決治國(guó)理政中諸多復(fù)雜的問(wèn)題,就必須依靠“中庸”而行,要在每一個(gè)方面達(dá)到恰當(dāng)合理。如在“君臣”關(guān)系方面,孔子認(rèn)為君臣雙方對(duì)對(duì)方都要有應(yīng)盡的義務(wù),君禮臣,臣盡忠。單純的僅要求一方,就會(huì)出現(xiàn)“太過(guò)”與“不及”兩個(gè)問(wèn)題。若君不禮臣,蔑視臣,縱然有忠臣盡心盡力,向君進(jìn)言,蔑視臣的君又怎么會(huì)重視臣的建議?而臣不盡忠職守,又如何肯為君分憂,為國(guó)出力?而君禮臣忠,正是使君臣雙方都處于一個(gè)恰當(dāng)?shù)奈恢茫粫?huì)出現(xiàn)過(guò)與不及的情況,正是“中庸”的具體表現(xiàn)。
三、“中庸”的最終目標(biāo)
“中庸”來(lái)源于具有道德屬性的天,作為“至德”,規(guī)定了每個(gè)人的行為,從而指引人前行在正確的道路上,而根據(jù)《禮記·中庸》所講,這條路的終點(diǎn)就是“和”。“喜怒哀樂(lè)之未發(fā),是謂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是謂和。”(《禮記·中庸》)感情未發(fā)的狀態(tài)是為“中”,感情顯現(xiàn)出來(lái)后還必須堅(jiān)持“中節(jié)”,就是人與他人相互交流時(shí),根據(jù)具體內(nèi)容而雙方都做出正確的反應(yīng),就是堅(jiān)持了“中庸”。而相互之間都可以做出正確的反應(yīng),就可以使人與人之間相互協(xié)助,從而達(dá)到社會(huì)和諧,國(guó)家穩(wěn)定的狀態(tài),這就是“和”。“在中國(guó)早期的文化形態(tài)中一樣,‘和’不僅僅代表著古代的一種樂(lè)器,而且也相應(yīng)地體現(xiàn)著演奏該樂(lè)器時(shí)所產(chǎn)生協(xié)調(diào)、和暢的音韻,以至令人愉悅的整體氛圍。”(吳霏:《中國(guó)古代和諧思想考略》,內(nèi)蒙古師范大學(xué)博士學(xué)位論文,2014年)而國(guó)家要處于和諧的狀態(tài)正如演奏音樂(lè)一樣,音樂(lè)要有不同的音節(jié)相互組合才達(dá)到和的狀態(tài),國(guó)家和諧就要有不同的人發(fā)揮出不一樣的作用,相互配合,共同促進(jìn)社會(huì)進(jìn)步,國(guó)家繁榮。如果忽視人的差異性,想要把所有人都變成一樣的,那根本就不是“和”的狀態(tài),而是“同”。正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yǔ)·子路》)所言,求“和”是君子的做法,求“同”則是小人的行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禮記·中庸》)。
想要達(dá)到“和”的狀態(tài),則必定要有“中庸之道”做支撐。“和”要求人與人之間相互協(xié)助,要做到這點(diǎn),孔子提倡“愛(ài)人”,“愛(ài)人”才可以相互協(xié)助。而“中庸”之道就貫穿其中,“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jǐn)而信,泛愛(ài)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xué)文’”(《論語(yǔ)·學(xué)而》)。從自己的父母兄弟開(kāi)始愛(ài),逐漸把愛(ài)擴(kuò)充到其他人身上。不愛(ài)父母則“不及”,過(guò)于愛(ài)他人則“太過(guò)”,要把握好“愛(ài)”的分寸。在此基礎(chǔ)上,人與人才可以相互合作,做到了這一點(diǎn),那社會(huì)自然和諧,國(guó)家自然太平,也就達(dá)到了“和”的狀態(tài)。另外,“和”不僅是指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達(dá)到美滿的狀態(tài),還包括了自然界中的其他萬(wàn)物,“致中和,天地位焉,萬(wàn)物育焉”(《禮記·中庸》)。達(dá)到“中和”,即可天地定位,萬(wàn)物生長(zhǎng)。
《論語(yǔ)》的“中庸”既是一種道德,也是處理問(wèn)題的方法。所以我們?cè)谧鋈俗鍪庐?dāng)中都可以依靠它,幫助我們樹(shù)立正確的價(jià)值觀,為國(guó)家富強(qiáng),民族復(fù)興貢獻(xiàn)自己的力量。也因?yàn)椤爸杏埂本哂幸陨线@些特性,才會(huì)被孔子稱為“至德”,稱為“中庸之道”,成為天下人學(xué)習(xí)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