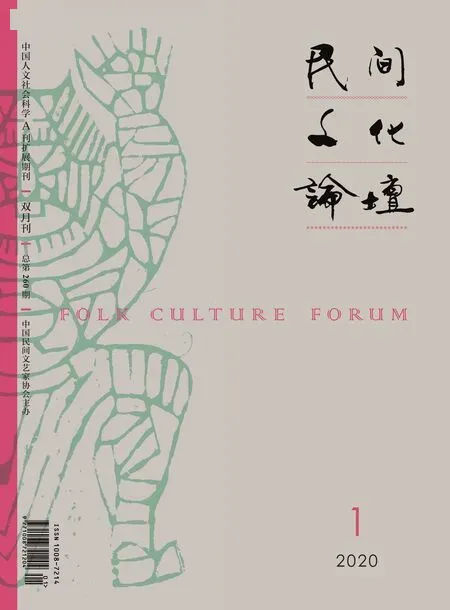胡愈之的民間文學思想研究
—— 基于《論民間文學》的討論
林繼富 魏麗紅
胡愈之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翻譯家、出版家,具有多方面卓著成就的革命學者。胡愈之與中國民間文學結下不解之緣,并在中國民間文學理論建設上具有重要貢獻,其中他的《論民間文學》最具代表性。
既往對胡愈之的研究,很少有學者注意到他在民間文學上的貢獻;在民間文學研究方面,很少有人詳細討論胡愈之《論民間文學》具有的理論價值和學科意義。當前學界對胡愈之民間文學思想觀念的關注還稍有欠缺,本文試圖從胡愈之為何從事民間文學研究、胡愈之如何理解“民間文學”等問題出發展開討論,以此檢討20世紀20年代初期我國民俗學、民間文藝學理論建設的基本情態。
一、胡愈之為何關注民間文學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拉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自此中國就處在內憂外患的激烈動蕩、變化中,救亡啟蒙成為當時最急切的呼聲,眾多有志之士在民族危機中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比如,林則徐、魏源等人開始“睜眼看世界”,洋務運動對西方技術的引入,戊戌變法對西方行政制度的發見,辛亥革命對西方政治制度的嘗試。然而這一切都無法挽救中國衰亡的頹勢,有識之士開始從文化根源上尋求答案。他們日益認識到社會改革需從思維改革入手,思維改革需從文化改革入手。
以陳獨秀、胡適為首的知識分子,在民族危亡、民族文化危機中發起新文化運動,他們高舉“科學”和“民主”的大旗,自覺地反對傳統文化中諸多觀念和禮制,力求把個人從傳統力量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文學革命”以此為契機展開,他們迫切需要文學發揮啟迪民智、改造國民性的作用。而一向被文人所輕視的民間文學也借此進入知識分子眼中,成為他們改良社會的理想寄托與實踐工具,誠如洪長泰所說:
他們急切地尋求新出路,于是在人民大眾的下層文化、特別是其中的民間文學那里,發現了希望。年輕的中國知識分子發展了有關民眾的浪漫主義觀點,指出這種名不見經傳卻藏量豐厚的民間文化,只要利用得當,便可以成為傳導新思想、解決中國利弊的工具。他們認為,恰如其分地評價民間文學,是重新估價中國文化整體面貌的關鍵。以往的失誤卻在于僅僅把正統文學當做中國文化的精華。① [美]洪長泰著:《到民間去——1918—1937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運動》,董曉萍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第2頁。
民間文化是否能夠發揮如洪長泰所說的“傳導新思想、解決中國利弊的工具”的作用呢?事實上,“五四”時期國人對民間文學關注和研究大大增加,并且產出許多優秀成果。也恰是因為這樣特殊的歷史背景,使得“五四”時期民間文學研究與當時社會政治情勢,與新文化運動、文學革命緊緊捆綁在一起。一方面知識分子精英群體逐步重視來自民間的聲音,不自覺地投入到民間文學研究中,客觀上推動了民間文學學科發展、理論建設;另一方面,民間文學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因素、新文學建設的干擾,以至于當時知識分子提倡、談論的“民間”,并不是純正的民間,而是他們通過一套學術話語建構起來的理想化的、帶有烏托邦色彩的民間。當時的知識分子并不是為了推動民間文學學科發展和理論建設而參與到民間文學的討論之中,而是為了推動文學革命、啟迪民智、解放思想等目的。在這種背景之下,民間文學更多是作為一種政治話語的輔助力量,作為新文學產生、發展的助推器,有的時候本身就構成為新文化的基本內容。
著名的社會活動家、翻譯家、出版家,具有多方面卓著成就的革命學者胡愈之,就是在這樣的時局環境中參與到對民間文學的研究中來。1921年1月,胡愈之在《婦女雜志》第7卷第1號上發表《論民間文學》,這是中國現代民間文學學術史上較早全面、系統論述“民間文學”及其特征的文章。因此,“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文化背景和救亡圖存的社會生活成為理解胡愈之民間文學思想的歷史前提。
當時因其出色表現、出眾才華,胡愈之受聘于商務印書館,擔任旗下《東方雜志》《婦女雜志》等報紙、期刊的編輯,是重要的骨干成員。在“五四”運動爆發前夜,胡愈之在商務結識了很多此后共同追求革命和民主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戰友,比如:沈雁冰、鄭振鐸、葉圣陶、章錫琛等。同時期內,他受到了新文化思潮的影響。胡愈之曾說:“早在‘五四’前,新文化運動已經興起,《新青年》舉起科學與民主兩面大旗,提倡白話文,向封建禮教和封建文化進行沖擊,這對我確實起到了啟蒙與思想解放的作用。”②胡愈之:《我的回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頁。正是這種啟蒙與思想解放的積累,到“五四”時期,“我和沈雁冰是提倡白話文最力的兩個人”③同上。。1920年,商務印書館順應歷史潮流,革新編譯所的工作,不再使用文言文而改用白話文。據沈雁冰后來的回憶,也恰是從1920年左右起,胡愈之對于文學十分有興趣。他開始用世界語翻譯外國的優秀文學作品,還特別注意翻譯介紹了一些世界其他國家弱小民族的文學作品。1920年鄭振鐸、沈雁冰等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時,胡愈之成為該會在上海的積極發起人和參與者之一。他除了向《小說月報》《文學旬刊》等積極投稿外,后來還協助鄭振鐸編輯《文學旬刊》。在這期間,他翻譯、發表了幾篇在當時很有影響力的關于文學理論的文章,如《近代文學概論》《文學批評——其意義及方法》《近代文學上的寫實主義》等。
據此,胡愈之在進行民間文學研究前,其商務印書館的編輯身份,對文學革命的關注,對有共同思想主張和民間情結的同仁、好友的結識以及對西洋文化的了解,使其積累了新知、開闊了眼界等,為走上民間文學研究道路以及從新的視角理解、認識民間文學準備了充足的條件。而與同時代許多研究者一樣,胡愈之并非出于要建設民間文學的目的而投身其中;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對“民間文學”的定義、研究價值、分類等所做的探索,為日后民間文學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二、從“民間文學”到“國民文學”
胡愈之雖未能專門從事民間文學研究,但是,他大力提倡民間文學資料的搜集、研究。除《論民間文學》一文外,還發表了《研究民間傳說歌謠的必要》《童話與神異故事》等;這些文章對當時民間歌謠、故事等的搜集、整理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他在寬廣的學術視野下開展民間文學理論研究,于我國民間文學學科建設的開創時期具有重要價值。尤其是《論民間文學》一文,胡愈之廣泛吸納當時歐美民俗學(民間文學)理論觀點,結合國內的具體社會情勢、相關研究成果,創造性地提出了一些關于中國民間文學、民俗學的理解,呼吁建立我國的“民間文學研究會”“民情學會”。①胡愈之也將“folklore”譯作“民情學”,即今日之“民俗學”。需要注意的是,受特殊時代背景的影響,他在民間文學上所做的一切努力并非專為民間文學所做,也并沒有認為民間文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而有其特定的目標與追求。這不僅影響著他的創作和研究,也為我們正確理解胡愈之的“民間文學”含義提供了重要的解釋途徑。
胡愈之時任《婦女雜志》編輯,為響應歌謠研究會的號召,特在雜志上開辟了“民間文學”和“風俗調查”兩個專欄,以征集各地流行的民間歌謠、民間故事為民間文學研究做準備。他的《論民間文學》有兩個目的:“現在要建立我國國民文學,研究我國國民性,自然應該把各地的民間文學,大規模的采集下來,用科學的方法整理一番才好呢”②愈之:《論民間文學》,《婦女雜志》第7卷第1號,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年一月(1921年1月)發行,第35頁。;“這一篇不過是想說明研究民間文學的必要,至于如何采集、如何研究,現在不及講得詳細。最后所期盼的,是大家應有研究民間文學的趣味,把采集民間文學的事情,用著全力干去!”③同上,第36頁。即《論民間文學》的第一個目的——收集整理民間文學是為了建立我國的國民文學,研究我國的國民性;第二個目的源于響應北大歌謠研究會的號召,說明研究民間文學的必要,呼吁大家努力采集民間文學作品,為民間文學研究做準備。
胡愈之“建立我國的國民文學,研究我國的國民性”的主張與文學研究會有很大關系,或者說正是基于相同的思想觀點才促成了文學研究會的誕生。1921年1月4日,文學研究會于北京中央公園來今雨軒正式成立,由鄭振鐸、周作人、沈雁冰等12人共同發起,胡愈之是其在上海的得力干將。文學研究會以“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為宗旨,開展了一系列文學活動;以《小說月報》《文學旬刊》等報刊為主要陣地,發表了大量有影響力的文章。
胡愈之這一時期的文學主張、思想觀念與文學研究會息息相關,他們都主張建立國民文學,新文學要表現國民性;并且與鄭振鐸、沈雁冰等不僅在文學主張、文學實踐上志同道合,還是十分親近的朋友。他們駁斥無病呻吟的舊文學,批評以文學為消遣游戲的鴛鴦蝴蝶派的“禮拜六”文學;他們反對沉溺于才子佳人、王侯將相的虛無舊詞,而揭起現實主義的文學革命旗幟;他們主張新文學創作者需與時代相應答,敏感于國家社會的苦痛;他們呼吁創作一種“血與淚”的文學,刺激麻木的國人起來反抗。
1921年1月10日,沈雁冰主編的《小說月報》第12卷第1號正式出版,同期發表了《<小說月報>改革宣言》,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深信一國之文學為一國國民性之反映,亦惟能表現國民性之文藝能有真價值,能在世界的文藝中占一席之地。”同期還發表了沈雁冰的《文學與人的關系及中國古來對于文學者身份的誤認》,他在文中明確指出,中國的文學者最為先決的重大任務就是創造我國的國民文學。①參見劉勇、李怡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1895—1949)》(第四卷 1920—1923),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4年,第68—75頁。
1921年2月10日,沈雁冰以“郎損”之名,在《小說月報》第12卷第2號中發表了名為《新文學研究者的責任與努力》,他說:
創作須有個性,這是很要緊的條件,不用再說的了;但是要使創作卻是民族的文學,則于個性之外更須有國民性。所謂國民性并非指一國的風土民情,乃是指這一國國民共有的美的特性。……這樣的國民性的文學才是有價值的文學。我相信一個民族既有了幾千年的歷史,他的民族性里一定藏著善美的特點;把他發揚光大起來,是該民族不容辭的神圣的職任。中華這么一個民族,其國民性豈遂無一些美點?從前的文學家因為把文學的目的弄錯了,所以不會發揮這些美點,反把劣點發揮了。這些“國粹文學”內所表見的中華國民性,我們不能承認是真的中華國民性;國民性的文學如今正在創造著!② 郎損(沈雁冰筆名):《新文學研究者的責任與努力》,《小說月報》,第12卷第2號,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年二月發行(1921年2月 ),第5頁。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沈雁冰認為新文學研究者當時緊要的責任之一在于創作民族的文學,創作能表現國民性的文學;而國民性指的是潛藏在我們民族、國民中所共有的美的特性。就在同一期,胡愈之發表了《新文學與創作》,他說:“文學是國民性的反映,所以一國的文學,都有一國的特點,像我們那樣偉大的民族,更應該有一種獨特的文學。因此我們盼望現在除一部分人專事翻譯外,應該有另一部分,努力創作,給我國文學立一個根腳才好呵。”③愈之:《新文學與創作》,《小說月報》,第12卷第2號,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年二月發行(1921年2月 ),第8頁。胡愈之認為新文學的創作與國民性息息相關,新文學應當表現的是我國的、民族的特性,只有這樣的創作才能為我國的文學立一個“根腳”。可以說,他與沈雁冰的觀點一脈相承,尤其在對“國民性”的認識及“國民性”與新文學之關系上。
他們看到國民身上的不足之處,呼吁建立我國的國民文學來重建國民性;同時,他們也看到國民身上潛藏的閃光之處,當前文學的緊迫任務就是將隱伏在罪惡之下的我們民族的真善美重新表現出來。沈雁冰“確信人性的砂礫里有精金,更確信前途的黑暗背后就是光明”①記者(沈雁冰):《引言》,《小說月報》,第12卷第10號(被損害民族的文學專號),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年十月發行(1921年10月),第2—3頁。,胡愈之也持同樣辯證的觀點。1922年《東方雜志》第19卷第1號上發表了他翻譯的羅素所作的《中國國民性的幾個特點》,該文記述了1921年羅素到中國游歷時觀察到的中國國民性中的優點和不足。羅素到中國的時間只有匆匆幾月,但他以敏銳的眼光仔細審視我國的國民性,認為中國人是最善笑的民族,天生有種鎮靜安閑的態度;愛調和、順從公意;有極強的忍耐力,往往能以頑固的民俗、強大的消極抵抗力,在文明上征服武力的征服者,是文明的集合體;但是中國人也有幾大缺點——耽于享樂,貪婪懦怯,缺乏同情心。胡愈之翻譯此文,并公開發表在雜志上,顯然他對羅素的觀點大體上是贊同的,并且他在“譯者附識”中也說,“中國國民性是最足以引起我們的興味的一個問題。看他這篇文字,感覺是何等的銳敏,觀察又是何等的精密!雖然羅素氏因為見了歐洲現局的紛擾,生出一種強烈的反感,所以對我民族不免有許多過分揄揚的話,使我們難堪,但是他對于東西文化的批判,卻也有幾處是很確當的呵。至于末了的幾段,凡是中國人似乎都應該細細的一讀。”②[英]羅素著:《中國國民性的幾個特點》,愈之譯,《東方雜志》,第19卷第1號,商務印書館民國十一年一月十日發行(1922年),第33頁。胡愈之翻譯此文是想引起當時讀者的注意,“不負羅素氏一番忠心的勸告和誠摯的熱望”③同上。;他既承認國民身上有一定的劣根性,但是,也看到那些美的特性。
也正是在這種對“國民性”認識的辨證觀點下,胡愈之倡導的是能表現民族精神(國民的美的特性)、喚起國民性的新文學。為實現這一目標,他大量譯介優秀的外國文學作品、文學理論進入我國,希望國人能從世界文學中學習、積累經驗。1921年4月10日,他在《東方雜志》第18卷第7號上發表《近代德國文學概觀》一文,開篇第一部分就介紹了德國“國民文學的創立”,特別回顧了德國文學如何在建立國民文學中,從落后于歐洲其他國家而到后來居上的過程:
在18世紀初年,德國國民文學,還是一片荒地。除模仿法國文學外,沒有所謂獨特的文學。那時德國國語還未統一,智識階級日常所用的語文,不是法蘭西語,便是拉丁語,文學的幼稚,更可以想見了。到了1740年,有名的菲列德烈大王(Freidrich der Grosse)登位,改革政教,使德意志成為歐洲大國之一。于是國語漸漸統一了,國民性也漸漸顯露了;同時又產生了幾個偉大天才,才把國民文學的基礎樹立起來了。④ 愈之:《近代德國文學概觀》,《東方雜志》,第18卷第7號,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年四月十日發行(1921年),第54頁。
從中可以看到胡愈之對國民文學的一些關鍵元素的關注——民族的獨特性、國語的使用、國民性的顯露等等;德國文學憑借著創建“國民文學”的東風從落后于歐洲諸國到后來居上的經驗,也恰是當時欲建立我國新文學所亟需的。
除了對英、法、德等發達國家的國民文學給予關注外,胡愈之還特別介紹了一些弱小民族的文學來鼓勵、倡導建立我國的國民文學。比如在《亞美尼亞文學》中他提到,“文學好像是一面鏡子,民族精神在這里邊反映出來。一個民族,要是沒有民族文學,那么比沒有國土,更要不幸;因為沒有文學,不但別人看不出他們的民族性,便是他們自己也看不出他們的性格來了。大概偉大的民族,都有偉大的民族文學。”①化魯(胡愈之筆名):《亞美尼亞文學》,《東方雜志》,第18卷第5號,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年三月十日發行(1921年),第74頁。像當時亞美尼亞、愛爾蘭、波蘭、猶太這樣的人口較少、力量較弱的民族,在國情上與中國有高度的相似;這些民族的文學中所表現出來的民族精神、追求民族獨立的呼聲的經驗對我國新文學的建設更有參考價值,胡愈之是站在世界文學的格局下謀求中國新文學的發展。
同時,他十分關心我國文壇新文學創作情況,盼望新文學創作者能創作出有民族精神的國民文學。然而,當時新文學的發展、創作情況不容樂觀。一方面,以《禮拜六》為陣地的鴛鴦蝴蝶派文學大行其道,只做些“清閑娛樂滿足肉欲的東西”②胡愈之語,參見蠢才(胡愈之筆名):《文學事業的墮落》,《時事新報·文學旬刊》,民國十年六月十日第4號(1921年),第3頁。。另一方面,絕大多數新進作家的思想和作風,“大都是板滯的,模擬的,全沒有獨創的膽量。就我個人的感想,近來報紙上的新文學作品,好像是從一個模型里做出來的,題材和結構,幾乎是千篇一律。”③蠢才(胡愈之筆名):《獨創的精神》,《時事新報·文學旬刊》,民國十年六月十日第4號(1921年),第3頁。“他們的詩和小說,在文章的形式上做功夫的很多,至于思想一方面,除卻寫出些不關痛癢的社會事情,寫出些浮淺膚泛的戀愛關系,寫出些從書本上照抄下來的人生觀,此外再沒有什么了。這樣的作品是容易使一般人引起誤會,使一般人以為新文學是只有肉而無靈,只有形式而無實質的。”④化魯:《形勢與實質——對于近時文藝界的一個感想》,《時事新報·文學旬刊》,民國十一年十月十日雙十增刊第52期(1922年),第4頁。
基于現實的需求,循著自己的文學主張,胡愈之在聆聽、閱讀民間流傳的神話、傳說、歌謠中,發現了民間文學于形式與內容上所蘊含的能夠反哺新文學的養分。在《論民間文學》中,他特別提到民間文學的研究價值:
先從藝術的本質看來,……這種故事歌曲,雖然形式是很簡陋的,思想是很單純的,但是一樣能夠表現自然,抒寫感情。而且民間文學更具有極大的普遍性。……再從心理上看來,民間文學是表現民族思想感情的東西,而且又是表現“人的”思想“人的”情感的最好的東西。因為個人的文學作品,往往加入技巧的制作,和文字形式的拘束,所以不能把人的思想感情很確切很真率的表現出來。只有民間文學乃是人們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而且流露出的是民族共通的思想感情,不是個人的思想情感。所以研究民族生活民族心理的,研究人類學社會學或比較宗教學的都不可以不拿民間文學做研究的資料。⑤ 愈之:《論民間文學》,《婦女雜志》,第7卷第1號,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年一月發行(1921年1月),第33頁。
首先,從內容上來看,民間文學所表現的是“人的”思想、“人的”情感,是具有極大普遍性的民族心理、民族精神、民族思想感情的呈現。所謂“人的”思想、“人的”情感繼承自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學”,他們反對非人的文學,倡導以人道主義為本,書寫、記錄人間的諸問題;既向上表現正面的理想生活,也向下呈現人的日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胡愈之發現民間文學是“表現‘人的’思想‘人的’情感的最好的東西”,老農的故事、嬰兒的乳歌、山歌傳說,所講述傳承的都是老百姓自己的生活,并且民間文學流行于民間,為廣大的人民群眾傳誦;民間文學最終描述的是民族生活,流露的是民族共有的思想感情,承載的是民族精神、民族心理,表現的是國民的美的特性。這與鴛鴦蝴蝶派純為消閑而作的文學,與只表現淺薄思想、堆砌“歐而不化”字句就算得革新的部分新文學是截然不同的,也是胡愈之于新文學事業上迫切呼喚的。
其次,從形式上來說,民間文學不受技巧風格的拘束,一切的情感、精神都是自然流露,真率而確切地記錄著百姓自己的生活與感情。它的外在結構雖然簡單甚至是簡陋,但并不影響人們自然真率地吐露自己的心聲。
胡愈之認為,文藝的生命不在于詞章文句的形式而在于思想感情,文學的要素在于內心流露的東西而不是表面的軀體;舊文學之所以破產全在于他們思想的破產,而不是由于艱深不通的文句、“死文字”的無法存立。①參見化魯:《形勢與實質——對于近時文藝界的一個感想》,《時事新報·文學旬刊》,民國十一年十月十日雙十增刊第52期(1922年),第4頁。民間文學在形式上的自然、韻律上的和諧,在內容上對民族思想情感、國民善美特性的呈現,都是他在新文學上提倡的。所以他呼喚從民間文學中汲取營養,希望大規模地收集各地的民間文學,以達成“建立我國的國民文學,研究我國的國民性”的目的。
由此可見,胡愈之提倡民間文學資料的搜集整理乃是為新文學革命而服務。胡愈之于1921年6月30日在《文學旬刊》第6號上發表《研究民間傳說歌謠的必要》,進一步闡釋了這一主張:
民間的神話,傳說,歌謠,俗曲,在中國埋著極大的寶藏,卻從來沒有人發掘過。……我對于現在的創作所不滿意的,便是太不真切,太缺乏民族的特殊性,要是大家對于民間的歌謠故事,有相當的注意,也許所得的創作成績,更要好些。這是我對于努力于新文學創作者所上的一個條陳。② 蠢才:《研究民間傳說歌謠的必要》,《文學旬刊》第6號,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年六月三十日發行(1921年),第19條。
據此,胡愈之寫作《論民間文學》的重要目的在于呼喚從民間文學中吸取其中所包含的民族的情感、民族的思想,并將民間文學運用到新文學創作中,以建立我國的國民文學。從這個角度看,胡愈之對民間文學研究并非在于民間文學本身,而是致力于“國民性”重建和現代文學新發展。胡愈之把民間文學放在“五四”時期中國社會發展、文化建設的背景之下,將其視為革新國民精神生活和新文學創作的手段,意味著我國現代民間文學學科的建立與現代文學的發展緊密相連,或者說,當時民間文學研究是為新文化運動、文學革命服務的。這也正是胡愈之的民間文學理論導向和實踐目的。
但是,我們又必須看到,作為較早全面、系統介紹“民間文學”的學人,胡愈之明確了民間文學的含義,肯定了民間文學的價值,他的論述在客觀上推動了民間文學理論的建立與發展。同時,他大力倡導采集民間文學作品的舉措,在早期民間文學資料搜集、整理上做出了重大貢獻。并且他對“民間文學”“民情學”等關鍵概念及其關系等的觀照,顯示出其對民間文學核心問題敏銳的洞察力;而他對這些問題的闡釋直接影響了20世紀30年代一批學者對“民間文學”的理解并付諸實踐行動。
三、從“民間文學”到 “民情學”
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最先提到“民間文學”的學者是梅光迪。1916年3月19日,梅光迪在給胡適的信中第一次使用了“民間文學”一詞。據胡適在《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一文中說:
1916年3月間,我曾寫信給梅覲莊,略說我的新見解,指出宋元的白話文的重要價值。覲莊究竟是研究過西洋文學的人,他回信居然很贊成我的意見。他說:“來書論宋元文學,甚起聾聵。文學革命自當從‘民間文學’(Folklore, Popular poetry, Spoken language )入手,此無待言。惟非經一番大戰爭不可,驟言俚俗文學,必為舊派文家所訕笑攻擊。但我輩正歡迎其訕笑攻擊耳。”這封信真叫我高興,梅覲莊也成了“我輩”了!① 胡適:《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原載《東方雜志》第31卷第1期,1934年1月1日。此據劉錫誠:《20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74頁。
在梅光迪看來,“民間文學”的內涵與“Folklore,Popular poetry,Spoken language”還有“俚俗文學”相當。他只是引入了“民間文學”一詞,并以幾個英文詞匯做了簡單注釋,而沒有留下詳細的闡釋和解讀,使得“民間文學”的概念在最初呈現一種非常模糊的狀態。就筆者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在梅光迪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幾乎沒有人再提“民間文學”一詞,直到胡愈之1921年發表《論民間文學》來系統解釋、介紹“民間文學”。因為梅光迪只是在給胡適的私人信件中提到,影響范圍比較有限,胡愈之直接從梅光迪處繼承此說法的機率較小;而從《論民間文學》以及胡愈之編輯身份、譯介工作、個人興趣等方面綜合來看,他應該是在工作、翻譯過程中接觸到西方學界對“民間文學”“民情學”相對成熟的研究成果,又趁著響應北大歌謠研究會收集歌謠、故事的號召,寫作了《論民間文學》。所以重新回顧胡愈之對“民間文學”“民情學”的理解是有必要的,一方面,我們可以從中管窺20世紀20年代初期西方民間文學、民俗學相關理論在我國的譯介、接受情況;另一方面,我們得以看到作為學科的民間文學、民俗學在我國發軔的思想史的軌轍。
首先,胡愈之將“folklore”既譯為“民情學”,也譯作“民間文學”;但在具體釋義時有不同的指代。他在《論民間文學》中明確指出:
到了近世,歐美學者知道民間文學有重要的價值,便起首用科學方法研究民間文學。后來研究的人漸多,這種事業,差不多已成了一種專門科學,在英文便叫“Folklore”——這個字不容易譯成中文,現在只好譯作“民情學”,但這是很牽強的。民情學中所研究的事項,分為三種:第一是民間的信仰和風俗(像婚喪俗例和一切的迷信禁忌等);第二是民間文學;第三是民間藝術。所以民間文學是民情學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② 愈之:《論民間文學》,《婦女雜志》第7卷第1號,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年一月發行(1921年1月 ),第33—34頁。
在這里,“民情學”指的是用科學方法研究民間信仰和風俗、民間文學、民間藝術的專門學科;民間文學是民情學研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這時,“folklore”指的是一門學科。“民間文學”“是指流行于民族間的文學,像那些神話、故事、傳說、山歌、船歌、兒歌等等都是。”①愈之:《論民間文學》,《婦女雜志》第7卷第1號,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年一月發行(1921年1月 ),第32頁。這時,“folklore”指的是民間文學研究對象。從這一點來說,胡愈之對“folklore”的理解十分到位,我們今天對“folklore”的闡釋基本也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而來。至于譯作“民情學”,胡愈之自己也說“很牽強”,對于這一點我們不必過于苛責。
其次,《論民間文學》中胡愈之對“民間文學”的理解主要側重兩個視角:
一是從文學方面論述,如上文所言,胡愈之循著自己的文學主張,發見民間文學在形式上的自然質樸,在內容上對民族共同的思想感情、國民善美的特性的表現,所以提倡收集民間文學資料為建設國民文學服務;另外,他對“民間文學”定義的闡釋中有很大一部分考慮還是作家文學與民間文學的區別問題。
二是受國外民情學、人類學的影響,胡愈之從民情學角度看民間文學。他把民間文學理解為民情學研究中的重要部分,在文中提到許多西方從事民情學、民間文學研究的先驅:葛林謨氏兄弟(格林兄弟)合著《兒童及家庭故事集》《德意志神話》;佛賴瑞(弗雷澤)的《金枝集》;哈德蘭(E.S.Hartland)的Legend of Perseus(珀爾修斯傳說);安徒生在采集童話時對文體的處理等等。
也正是從民情學與民間文學的關系出發,在胡愈之主導下,《婦女雜志》特設“風俗調查”欄目,因為他認識到風俗習慣和民間文學之間的緊密關系,他認為理解民間文學不能與風土人情脫離。同一期的《婦女雜志》還特別刊登“編輯余錄”一條:
民間文學的采集,近來雖逐漸發達,但每限于歌謠一方面。據我們所曉得,野老村嫗所講的神話故事一類,可以供文學上、心理學上、人類學上、文化史上的參考的,實在很多;現在卻沒有人從事搜求,也是一件憾事。本志特設“民間文學”一欄,廣搜此類投稿,希望海內同志共加贊助。本號中愈之君所作《論民間文學》一文,于世界各國民間文學采集的源流和方法,敘述極詳,卻是有價值的文字。風俗習慣和民間文學很有關系,《論民間文學》文內已經說得很詳。“風俗調查”一欄,也是為此而設。如蒙投稿,無論有系統的敘述,或片段的記事,都極歡迎。② “編輯余錄”,《婦女雜志》第7卷第1號,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年一月發行(1921年1月),第126頁。
胡愈之及《婦女雜志》的編輯們意識到從民間文學擴展民情學的重要性和必然趨勢。盡管胡愈之寫作《論民間文學》的一大目的是呼應歌謠研究會搜集歌謠的號召,但是,他更進一步看到當時民間文學的采集工作多限于歌謠方面,所以呼應全面地搜集,包括故事、傳說、神話、童話、諺語、俗謎等。同時,他們注意到民間的風俗習慣對理解民間文學的重要作用,所以特設“風俗調查”一欄。自1921年1月在專欄1號發表《論民間文學》開始,《婦女雜志》發表了包括歌謠、故事、傳說、諺語等在內的許多優秀民間文學作品。胡愈之的這種主張大大豐富了當時民間文學資料的多樣性、全面性,也說明他對民間文學內涵與外延有較為清晰的認識,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時人多從文學的角度來理解民間文學,轉而將眼光投射到民間文學自身具有的特質,關注到其與風土人情、民眾生活的關系。
胡愈之認為研究民間文學應該分兩個階段,“最先把各地的民間故事、民間傳說、民間歌謠采集下來,編成民間故事集歌謠集等;隨后把這種資料,用歸納的分類的方法,編成總和的著作。”③愈之:《論民間文學》,《婦女雜志》第7卷第1號,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年一月發行(1921年1月),第35頁。而當時想要研究我國的民間文學還缺乏現成的研究資料,所以應該先從采集入手。出于號召大家采集民間文學作品的目的,胡愈之在《論民間文學》中特別談到了采集民間文學的注意事項:
(1)下手時候應該先研究語學(philology)和各地的方言;因為不懂得語學和方言,對于民間文學的真趣,往往不容易領會。
(2)用文字表現民間的作品,很不容易,因為文字是固定的、板滯的,語言卻是流動的;最好是用簡單的辭句,把作品老老實實的表現出來,切不可加入主觀的辭句和藝術的制作,像丹麥安徒生(Christian Anderson)那種文體最為合式。
(3)采集的時候,應該留心辨別,到底所采的故事或歌謠,是不是真正的民間作品;因為有許多故事或民歌,也許是好事的文人造作出來的,而且造作得未久,還沒有變成民族的文學,所以不應該采集進去。
(4)民間作品的價值,在于永久與普遍;流行年代最久和流行的地方最廣的,才是純粹的民間文學;采集的時候應該注意。① 愈之:《論民間文學》,《婦女雜志》第7卷第1號,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年一月發行(1921年1月 ),第35頁。
除此之外,在《婦女雜志》的同一期“民間文學”專欄后,特附“歡迎投稿”的補白:
本欄特別歡迎投稿,投稿諸君務請注意下列各條:
(1)凡各地流行之通俗故事、民間傳說、神話、童話、寓言、諺語、小曲、兒歌、俗謎,一律歡迎。
(2)故事歌謠,最好用簡單語句,直接表現,切勿加入辭藻,致失本真。其系自行造作而非民間流行者概不收錄。
(3)俗字俗語不可改為官話,如有過于偏僻之俗字俗語,須加以解釋。俗字讀音,最好用注音字母注出,或用西文字母拼出亦可。② 補白“歡迎投稿”,《婦女雜志》第7卷第1號,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年一月發行(1921年1月 ),第111頁。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胡愈之認為采集民間文學時需注意:首先,采集者要有一定的語言學素養,對民間文學作品中方言的使用要予以特別關注,可加以注音和解釋,這樣才能保持民間文學的真趣也便于理解;其次,采集需堅守“真實”原則,既不可主觀造作或進行藝術加工,也要注意辨別流傳長久、普遍的民眾創作才是純粹的民間文學,萬不可將文人創作混為一談;同時,收集時不必拘泥于某一類,凡民間歌謠、故事、傳說、俗語等一律歡迎……這些采集原則反面顯示出胡愈之對民間文學所具有的特質準確地把握。在他的倡導下,不僅采集了大量的民間文學作品,而且提高了民間文學作品的科學性和真實性,這些為中國現代民間文學的建立奠定了資料基礎和理論基石。
盡管我們不能將《婦女雜志》在征集方面的成就完全歸功于胡愈之,但是,不可否認胡愈之在促進民間文學作品收集、研究上起到了關鍵的作用。1921年《婦女雜志》第7卷第12號專門回顧了這一年民間文學專欄的成果:
“在這一年當中,我們收到從各處寄來的歌謠諺語,大約有二三千種,傳說故事也有二百余篇,我們當初并不想得到這許多。對于幾位熟心于民間文學投稿先生們,我們真不知該如何感謝呢!”因為篇幅原因,寄來的歌謠發表的不到十分之一,編輯將它們都保存起來,“希望將來刊行《故事集》《歌謠集》《諺語集》等,以建立中國的Folklore的基礎。從明年起,我們更想把《婦女雜志》里的‘民間文學’欄擴充,盡量吸收各處的來稿。”① “民間文學編輯者啟事”,《婦女雜志》第7卷第12號,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年十二月發行(1921年12月 ),第95頁。
1921年的《婦女雜志》為中國民間文學積累了大量的資料,也喚醒了國人對于這一部分文學的重視;但遺憾的是自《婦女雜志》1921年第7卷第12號之后,“民間文學”“風俗調查”專欄被改版,該雜志上也再沒有刊登過從全國各地收集來的民間文學作品;只有一些零星的對外國童話作品的譯介。對此,編輯給出的解釋是:
近來“民間文學”,來稿頗多,但所收稿件,往往和登過得大同小異,選擇十分為難。然以我國幅員的廣大,歷史的長久,流傳民間的故事傳說歌謠,想決不致僅此區區。我們很希望有更優美的材料,可以滿足我們愿望,助成這采集的事業。
“風俗調查”來稿,也都大同小異,使讀者不能十分發生興趣;以后打算只選擇特殊的登載。記述普遍的風俗的,恕不再登。② “編輯余錄”,《婦女雜志》第8卷第2號,商務印書館民國十一年二月發行(1922年2月),第120頁。
從《婦女雜志》淡化民間文學,并且較少刊載民間文學的說明來看:當時熱心于民間文學資料收集事業的人員從數量上還算可觀,但民間文學作品的采集,不管是從種類還是地域上來說都不夠寬泛和深入;風土人情的調查范圍和調查內容也較為局限,缺乏對民眾生活的地方特色的記錄。因此,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無論“民間文學”還是“風俗調查”,“所收稿件,往往和登過得大同小異,選擇十分為難”不是沒有道理,這里也可以看出胡愈之對于民間文學的理解已經發展到民情學了,或者說,民間文學的意義離不開與之相關的民情民風。
隨著文學研究會、創造社關于“為人生的文學”“為藝術的文學”論戰不休,胡愈之漸漸失去了對文學、民間文學的興趣。加上《論民間文學》發表之后并未引起學界重視,對此,烏丙安在談“Folk-lore”作為學科專名在中國運用時做了分析:“一是這篇文章中介紹的‘Folk-lore’和作者譯出的學科中文名稱‘民情學’,并沒有在學人中引起反響。二是作者用了‘民俗’這個術語,但未與‘Folk-lore’對應,而用了‘民情’。三是作者提出的‘Folk-lore’的三種研究對象,也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因為,1923年5月成立風俗調查會的籌備會議上討論‘風俗調查表’時,并沒有任何參考這篇論文中新意見的痕跡。”③烏丙安:《民俗學原理》,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5頁。
胡愈之對“民間文學”的論述,筆者以為很大程度上被周作人提倡的“平民文學”“人的文學”、胡適主張的“白話文學”遮蔽了,這些更符合、更能直接呼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張。即使這樣,我們依然不可否認胡愈之倡導的“民間文學”,以及當時許多學人重視民間文學、投身民間文學資料搜集,對社會革新、新文學建立所起的重要作用。1922年,甘豫源發表《民間文學在教育上的價值》①甘豫源:《民間文學在教育上的價值》,載《江蘇省立第二師范學校校刊》,1922年第12號。;1923年,胡寄塵發表《中國民間文學之一斑》②胡寄塵:《中國民間文學之一斑》,載《小說世界》,1923年第2卷第4期。;《微音》雜志在1924—1925年間斷斷續續設置“民間文學”專欄,刊登了許多民間的歌謠、謎語;1924年,趙景深的《童話評論》出版,其中特收錄了胡愈之《論民間文學》等。從這個角度來看,胡愈之《論民間文學》在當時學界和文學界的影響仍然十分重要。更為重要的是,胡愈之意識到“民間文學”存在的局限性,就在“民間文學”的理解上提出了“民情學”,這是對“民間文學”內涵和外延的豐富,是將“民間文學”納入民眾生活之學的“民情學”,這是我國民俗學發展史上較早意識到“民間文學”與“民俗學”關系的重要思想來源。
四、“民間文學”如何走向“民族全體”
在胡愈之看來,“民間文學”與英文的“Folklore”、德文的“Volkskunde”大略相同,是指流行于民族間的文學,像那些神話、故事、傳說、山歌、船歌、兒歌等都是。民間文學作品有兩個特質:第一,創作的人乃是民族全體,不是個人;第二,民間文學是口述的文學(oral literature),不是書本的文學(book literature)。③愈之:《論民間文學》,《婦女雜志》第7卷第1號,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年一月發行(1921年1月 ),第32頁。
筆者認為胡愈之定義中“民族全體”外延包括一切階級、民族、群體,從而導致具體指向不明。尤其是從創作主體角度來看,雖說它指明創作者不是個體,但仍舊沒有清晰的對象和范圍邊界。于是,后來學人對“民間文學”的定義為了避免“民間”理解的困難,往往采用否定式的、比較式的定義法,比如“民間文學”是“非作家文學”“與文人文學相比”等。那么,胡愈之所說的“民族全體”其意為何呢?
普通的文學著作,都是從個人創作出來的,每一種著作,都有一個作家。民間文學可是不然,創作的絕不是甲,也不是乙,乃是民族的全體。……有許多故事、歌謠,最初發生的時候,也許是先有一個創意的人,但形式和字句卻必經過許多的自然修正,才能流行民間;因為任憑你是個了不得的天才,個人的作品,斷不能使無知識的社會永久傳誦的。個人的作品,傳到婦女兒童的口里,不免逐漸蛻變,到了最后,便會把作品中的作者個性完全消失,所表現的只是民族共同的思想和感情了。所以個人創意的作品,待變成了民間文學,中間必經過了無數人的修改;換句話,仍舊是全民族的作品,不是個人的作品了。④ 同上。
從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胡愈之所談的“民族全體”包含了多方面的內容:
一是對民間文學創作主體的理解,究竟何為“民”。考察胡愈之同一時期的思想觀念,可以發現在1920—1924年間,胡愈之有很深的民眾意識。他認識到民眾身上潛藏著巨大的力量,希望通過民眾運動來走出時局的困頓。比如,他在《地方自治與鄉村運動》中說:
所以現在要解決時局,必先促起真正的民眾階級,使他們都有政治的自覺,而鄉村運動更是根本的要圖。真正的人民代表應該是從田間來的。不是從腐敗的都市中來的。我們應該使占我國人口百分之九十有零的無知農民,都明白自己所站立的地位,都了解自身所應有的權利義務,使他們能自動的團結起來,干涉地方政治,推翻“紳士”階級,真正的地方自治,這才有實現的希望哩。① 化魯:《地方自治與鄉村運動》,《東方雜志》第19卷第6號,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發行(1922年),第1頁。
胡愈之也像同時代的其他知識分子一樣,深刻體會到農民在人口數量上的巨大優勢;他號召智識階級、青年學生要真正貼近大眾,貼近無智識階級,開啟民智、振奮民力。同時代許多學人喊出“到民間去”的口號,在他們那里,“民”更多的指向農村、農民;胡愈之在《論民間文學》中用“民族全體”則包括全國各地從城市到農村的所有人,所涵蓋的范圍更為廣泛。
二是對民間文學傳承過程、口頭性的把握。他在定義中特別強調“民間文學是口述的文學(oral literature),不是書本的文學(book literature)”;民間文學的活力在于傳承中的再創造,一些板滯的形式、字句不斷地經過自然的修正,融入時代、地域的特色,才能在民間永久傳誦。在民間文學流傳過程“民族全體”參與其中。
三是對民間文學所表現的民族性的發見。民間文學表現的是民族全體共有的思想和感情,是民族的特性,是民族中具有的美的特質。以此為根本,讓胡愈之認識到要建立國民文學、重建國民性必須從民間文學入手。他在1921年發表的《研究民間傳說歌謠的必要》進一步談到:
法國批評家泰奴(Taine)以人種,環境,時代為構成藝術的三個要素,就此可以想見民族和文學的關系了。文學家的思想和情感,常是民族的思想民族的情感之結晶。不能窺見民族精神的,不能代表民族思想的,便不能算作偉大的文學家。所以企圖真實的藝術創作的,必須攝取民族的心靈,探測民眾的深底,使全民族的性格和作者的個性,融合而為一。那么在一方面應該和真實民眾多相接觸(如投身農民社會等),在一方面更應該對于民間的信仰習俗歌謠故事等等,都有相當的研究,要是不然,要窺測民族的思想情感,是很難的了。② 蠢才:《研究民間傳說歌謠的必要》,《文學旬刊》第6號,商務印書館發行民國十年六月三十日(1921年),第19條。
研究民間傳說歌謠的必要恰恰在于民間文學作品承載全民的思想情感,所以,說“民族全體”最終要落腳到民族全體共有的思想和感情上去,落腳到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民族心靈上去,并且意識到民間文學之于民族共同體形成的作用;而不僅是空泛地指向一群寂寂無名沒有面孔的“中國底老兒女”,民間文學是民族全體思想、感情的最好載體。同時,與作家文學、文人文學相比,民間文學在自然直率地表露人們思想感情上更勝一籌,而且流露的是民族共通的思想感情。
除此以外,胡愈之對民間文學表現的“民族性”的理解,離不開世界文學的格局。一方面,胡愈之從外介紹了許多優秀的世界各民族文學進入我國,尤其特別介紹了像亞美尼亞、波蘭那樣的與我們有相似國情的弱小民族的文學,以此鼓勵建設有民族精神的國民文學。另一方面,民間文學中所具有的我們民族善美的特性,表現的民族共同的思想感情,正是我國文學得以屹立世界文學之林的關鍵所在。
胡愈之對“民間文學”精準、精確的認識,不僅對于“五四”時期國民文學的建設、新文學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而且對于中國民俗學、民間文藝學學術思想開掘、學科建立具有推動作用。并且,他對“民間文學”的認識影響非常深遠,以致成為后來學人定義“民間文學”的基本范式。
1926年,章雄翔《嶺東民間文學總論》將“民間文學”定義為“流行于民眾中間的真摯的自然的美妙的普遍的一種表現人生描述宇宙的藝術——文學。”特別提到民間文學與普通文學差別:“(甲)民間文學是口述的文學(oral literature),普通文學是書寫的文學(book literature);(乙)普通文學的作者系個人,民間文學的作者卻系民眾。”①章雄翔:《嶺東民間文學總論》,《留京潮州學會年刊》第2期,留京潮州學會民國十五年三月出版(1926年3月),第1—4頁,有刪減。可以看到章氏的定義與論述明顯繼承胡愈之。1927年,徐蔚南撰著《民間文學》中的“民間文學”定義:“民間文學是民族全體所合作的,屬于無產階級的、從民間來的、口述的、經萬人的修正而為最大多數人民所傳誦愛護的文學。”②徐蔚南:《民間文學》,上海:世界書局,中華民國十六年(1927年)六月初版,第6頁。將之與胡愈之的“民間文學”定義相比照,可以發現兩個定義間的緊密關系,只不過徐蔚南的“民間文學”定義限定得更為具體、細致。
20世紀30年代,民間文學理論建設重要貢獻者,諸如楊蔭深、陳光堯、王顯恩、鐘敬文等人的“民間文學”定義基本沿著胡愈之思路展開。楊蔭深在《中國民間文學概說》中就將“民間文學”表述為:“這里的文學,是口述的,耳聽的,是一般民眾——不論其為智識階級或無智識階級,他們都有演述口傳的可能,這便是真正的民間文學。”③楊蔭深:《中國民間文學概說》,華通書局,1930年,第1—2頁。他特別討論了民間文學與文人文學的區別,認為民間文學是“口述的”“群眾的”“平民的”和“自然的”④同上,第4—14頁。;陳光垚在《中國民眾文藝論》中寫道:“民眾文藝本是一種由全體民眾所合作,經眾人口頭的修改,而屬于平民階級的,深入而淺出的,整個的,口述的自然文藝”⑤陳光垚:《中國民眾文藝論》,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1—2頁。;鐘敬文在《民間文藝學底建設》一文中對民間文學特性進行了概括——“……民間文藝底制作,仍然可以說是集團的”“其次,民間文藝,是純粹地以流動的語言為媒介的文藝,就是所謂‘口傳的文藝’”等等⑥鐘敬文:《民間文藝學的建設》,《藝風》第4卷第1期,民國二十五年一月一日出版(1936年1月1日),第25—33頁。,基本是對胡愈之定義的繼承與發展。
除了對“民間文學”關鍵性定義之外,胡愈之對民間文學價值的探討以及對西方民間文學分類法的引入等方面,對民俗學和民間文藝學學科理論體系建設也發揮著重大作用。胡愈之明確指出民間文學具有藝術、心理、教育價值等,這也是后輩學者研究的著重關注點。他對西方民間文學分類法的引入,不僅對當時收集民間文學資料有益,對后來作為學科的民間文學的理論體系建設也極為重要。雖然他只是直接套用N. W. Thomas的分類法,沒有結合我國民間文學的具體情況做出一些嘗試,但是筆者認為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能把西方民間文學的分類方法引入中國就是了不起的貢獻。胡愈之也清楚地意識到:“以上的分類自然不能說十分完全,但是民間文學的普通種類,大多包括在內了。其中歌謠和小曲一類最為復雜,形式和格調種類極多。我們現在沒有完善的分類法,那么便依據了這種分類采集,也未始不可以。”①愈之:《論民間文學》,《婦女雜志》第7卷第1號,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年一月發行(1921年1月 ),第35頁。胡愈之認識到這種分類法有不足之處,只是因為提不出更好的分類法,便暫時按照這種分類方法進行采集。有的學者批評胡愈之引入的民間文學分類法把講唱、戲曲等棄之不顧,把“綽號”“地名歌”等明顯不符合我國民間文學實際情況的分類也照搬過來等,不免有些苛刻。但是,并不是說胡愈之對“民間文學”的論述沒有任何問題,筆者更愿意強調的是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學術,在胡愈之所處的時代背景下,他對“民間文學”的討論以及對于民間文學相關的民俗學的認識,不僅在當時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而且直接影響到中國民俗學和民間文藝學的理論建設和學科發展,這是應該肯定的。
結 語
胡愈之在時代思潮影響下重視并且闡述“民間文學”思想,得益于救亡啟蒙的迫切需求。他最根本的目的不是為了建設民間文學,而是在新文學建設視域下討論民間文學;更進一步說,他希望借民間文學的力量建設“國民文學”,喚醒并重建“國民性”。
胡愈之投身民間文學研究動因、目的,為理解胡愈之民間文學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解釋路徑。《論民間文學》中,胡愈之與同輩學者一樣,多從文學的角度來理解“民間文學”,常在與文人創作的比對下討論民間文學的形式與內容。胡愈之在對西方民間文學、民情學理論學習、譯介中,雖然并沒有強烈的民情學學科意識,但自覺不自覺地有了民情學學科視角。他對“folklore”的闡釋,認為民間文學意義、功能離不開“民情學”,并且對民間文學與民情學關系的理解都是敏銳而準確的。
基于對“民族全體”的理解,進一步展示了胡愈之對“民間文學”本質的精準把握。他突破了時人將“民”“民間”主要集中在“農民”“農村”的局限,強調民間文學作品在動態流傳過程中的集體參與性;強調民間文學所表現的是民族全體共有的思想和感情,是民族美的特性(國民性),更為重要的,胡愈之認為民間文學是民族共同體建立的重要基礎。
盡管胡愈之無意于建設一門學科,但是,他以實際行動搜集和研究民間文學,號召國人重視民間文學,客觀上推動了學科意義上民間文學理論的發展。他大力提倡搜集、整理民間文學,促進了近代民間文學資料留存的豐富性與多樣性;他對民間文學概念及其特征的論述,對民間文學與民眾生活關系的討論,為中國民俗學、民間文藝學理論體系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