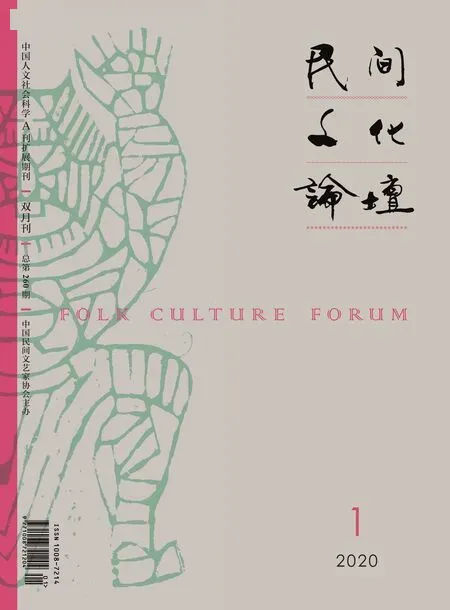由“游”以“藝”:社火舞臺展演的實踐邏輯與傳承風險
賈利濤 張 悅
社火是重要的民俗事象,在民間社會享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具有深遠的影響力。各地社火爭奇斗艷,形成了流傳范圍廣、構成種類多、參與人數眾、技藝表演精湛的社火文化。民間社火及很多社火子類被列入國家級或省市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社火在節慶、廟會、祭祀、賽社等場合搬演,尤以元宵節最為集中,很多地區組織社火花會的展演。城鎮鄉間,社火隊伍且行且歌、且進且舞,觀者夾道簇擁,塞途如堵,堪稱社火盛況。
一、作為“游藝”的社火
“游藝”一詞,溯于孔子“游于藝”言,后多有游于六藝或游學諸藝的意思。在現代漢語語境中,“游藝”頗近“游戲”一詞,幾乎成為同義詞。楊蔭深《中國游藝研究》開篇即言“游藝就是游戲的藝術”①楊蔭深:《中國游藝研究》,昆明:世界書局,1946年,第1頁。。游常取游戲、游玩義,藝常取藝術、技藝義,“游藝”可作游戲的藝術(技藝)解,此為該詞匯的常見義項。鄭重華、劉德增的《中國古代游藝》認為“游藝與游戲同義,是一種娛樂活動”②鄭重華、劉德增:《中國古代游藝》,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頁。。李建民的《中國古代游藝史》重點論述“樂舞百戲”③李建民:《中國古代游藝史 樂舞百戲與社會生活之研究》,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多數冠名“游藝民俗”的通俗讀物多取此義,包含雜技、弈棋、博戲及兒童游戲諸類。《大辭海》“游藝民俗”條的解釋相對較為寬泛:“即‘娛樂性民俗’。民間傳統的文化娛樂活動。包括口頭表演、動作表演、綜合的藝術手段表演的活動以及游戲、競技、民間藝術等,可分為民間口頭文學活動、民間歌舞樂活動、民間游戲活動、民間競技活動、民間雜藝活動等。”①夏征農、陳至立主編:《大辭海·民族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年,第502頁。
民俗學語境中的“游藝”包含游戲,又并非完全等同于游戲。鐘敬文《民俗學概論》中稱之為“民間游戲娛樂”,同時“國內近年來出版的民俗學著作,有的稱‘游藝民俗’,有的稱‘文藝游戲民俗’,也有的稱‘游戲競技民俗’”②鐘敬文主編:《民俗學概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379頁。。以烏丙安《中國民俗學》對“游藝民俗”論述最詳,“比較恰當的、大體上能概括民間文娛體育活動的詞語,以‘游藝’為好”“游藝民俗的概念大體確定為:凡是民間傳統的文化娛樂活動,不論是口頭語言表演的還是動作表演的、或用綜合的藝術手段表演的活動,都是游藝民俗”③烏丙安:《中國民俗學》,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343、348頁。。當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分類中,有“傳統體育、游藝與雜技”大類,游藝(recreation)實際上依然側重游戲的部分。
民間社火是節慶、廟會上演的民間花會演藝活動的總稱,應可歸入“游藝民俗”的大類中。鐘敬文《民俗學概論》中把社火歸入“民間游戲娛樂”中,各類民俗志(如中國民俗大系分省卷)基本都把社火歸入“游藝”一類,這應當較為妥帖。然而,由于社火包羅甚多,各地社火種類少則十余種,多則上百種。實踐中,既有整體的歸類,又有細分后的歸類。國家級非遺中,“民間社火”都歸入“民俗”類,而非“游藝”類。社火的構成品種因其貼近的門類劃分,如抬閣(芯子、鐵枝、飄色)歸入民俗類,秧歌、竹馬、旱船、高蹺歸入傳統舞蹈類,飛叉歸入傳統體育、游藝與雜技類,鑼鼓歸入傳統音樂類等等。
雖然面臨實踐中社火歸類的多維考量,但作為整體的社火應當歸入“游藝民俗”來審視。首先,就“游藝”而言,除了游戲之外,還包括更加豐富的內涵。“游”與“藝”的本義,都并不直接指向游戲。游者,旌旗之流也,具有行進、游走、流動之意,“游戲”亦從此生發。藝者,種也,引申為才能、技能,技藝、藝術得義于此。因此,“游藝”包含游戲意項的同時,還有側重于行進中展演技藝、流動中表演藝術的內涵。社火的各類構成既不違背游藝的詞匯本義,也不違背現代漢語語境,同時也較為貼合民俗事實。
蔡欣欣認為:“游藝、社火與會所指稱的對象基本近似,亦即‘俳優歌舞雜奏’等散樂百戲;或如漳州當地中由四方百姓鐻資參與組織的‘優戲隊’;只是游藝表演的時機場合,可能較后二者更為寬廣,亦即除了依附在歲時節慶與廟會神誕外,也可在官方節慶、民俗節慶與歷史節慶等活動中獻藝:甚至民間或學界將游藝更從屬于社火與會之下,專指在‘廣場街道游走行路’的表演團隊。”④蔡欣欣:《妝扮游藝中的“臺閣”景觀》,麻國鈞、劉禎主編《賽社與樂戶論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6年,第163—164頁。烏丙安概括了游藝民俗的四個基本點,其中一個即是“非劇場化、非大舞臺化的表演活動”⑤烏丙安:《中國民俗學》,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349頁。。顯然,游藝民俗更為側重行進中的、游行式的街頭展演藝術形式,而這恰恰是社火最為突出的特點。
社火的起源發展與賽社、儺儀、迎春、燈節密切相關,而迎神獻藝的賽社、沿門逐疫的儺儀、郊祀表演的迎春、晝夜狂歡的燈節的綜合作用,使社火呈現出多種技藝雜呈、群體性、狂歡式的特點,這些特點都離不開游街演藝的形式特征,因此,社火從發展演變而言,天然具有沿街行進表演的要求和特點。
古籍中的社火場面都是沿街狂歡、觀者如堵之類的描繪。如范成大《上元紀吳中節物俳諧體三十二韻》:
輕薄行歌過,顛狂社舞呈。
(自注:民間鼓樂謂之社火,不可悉記,大抵以滑稽取笑。)
村田蓑笠野,街市管弦清。
里巷分題句,官曹別扁門。
旱船遙似泛,水儡近如生。
(自注:夾道陸行為競渡之樂,謂之劃旱船)
鉗赭裝牢戶,嘲嗤繪樂棚。
堵觀瑤席隘,喝道綺叢爭。① (宋)范成大:《范石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26頁。
《夢粱錄》中說社火舞隊的演出時,人們“攔街嬉耍,竟夕不眠”:姑以舞隊言之,如清音、遏云、掉刀鮑老、胡女、劉袞、喬三教、喬迎酒、喬親事、焦錘架兒、仕女、杵歌、諸國朝、竹馬兒、村田樂、神鬼、十齋郎各社,不下數十。更有喬宅眷、汗龍船、踢燈鮑老、施象社。官巷口、蘇家巷二十四家傀儡,衣裝鮮麗,細旦戴花朵口肩、珠翠冠兒,腰肢纖裊,宛若婦人。……攔街嬉耍,竟夕不眠。……至十六夜收燈,舞隊方散。②(宋)吳自牧:《夢粱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4頁。《西湖老人繁勝錄》《武林舊事》所列社火種類數十種,不僅觀者多,演者亦多,常常一社就有數百人,“福建鮑老一社,有三百余人;川鮑老亦有一百余人”③(宋)題西湖老人:《繁勝錄》,《東京夢華錄(外四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第111頁。。這也是沿街行進演出、且演且進可容納的場景。
明清時期社火熾盛,元宵、迎春、賽神時各色社火扮演,地方志中俯拾皆是,彼時的城鄉社火均是“遍游街巷”的行進式演出。
一家做燈官,好游戲者群往就之,用優人衣冠器具,扮演各色故事,名為“社火”,先謁官長呈伎,領賞后遍游街巷,且歌且舞,男女聚觀,至十六夜燈火歇后,乃罷。——乾隆《延慶州志》
沿街設立松棚,雜綴諸燈,翠縷銀葩絢然溢目。又唱秧歌,謂之社火……隨處演戲,戲秋千,三日為度。——乾隆《赤城縣志》
立春前一日,彩樓、社火,迎春于東郊。……上元前后五日,街市張燈、獅火,社火甚多,謂之“斗勝”。——光緒《保安州志》
元宵,鄉村稍有燈火;城市則鰲山燈海,秧歌、社火、角抵之戲,喧闐街巷,親友過從游觀焉。——光緒《續修崞縣志》
十五夜,張燈結彩,燎炭火,放花炮,演雜劇以游街,謂之“鬧元宵”。——光緒《岢嵐州志》
元宵,燃燈制火,年少做百戲狀,沿街而行,若狂者然,曰“鬧元宵”。——光緒《榆社縣志》① 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 華北卷》,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第17、137、166、563、568、577 頁。
因社火的行進式演出形式與迎神祭祀的出巡、夸官、行像意義相近、相互融合,社火也常被稱為“行會”或“走會”。如在河北贊皇“七月初七日,俗傳劉猛將軍誕辰。是日,人民以五色小幟植土箱上,用長竿兩人肩荷,后有旗鼓百戲,穿街過巷,至神前焚楮帛,祈無蝗蝻,名曰‘行會’”,三河亦如是“又有于是日演雜劇者,名曰‘走會’”②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 華北卷》,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第123、284頁。。
因此,從“游藝”的本義及詞語意涵來講,都內含游行獻藝的意義。作為民俗學概念的“游藝”,不僅包含較為廣義的“游戲”,還包含諸種民間傳統的文化娛樂活動。社火從起源至今,依然保持著沿街行進演藝的顯著特點,因此歸入“游藝民俗”類,不僅是分類上的體認,也是社火基本性質的確證。
二、社火舞臺展演的實踐邏輯
社火具有沿街行進演出的突出特點,無論是歷史上的社火,還是現在活躍在鄉間城鎮的社火,這一點較為顯見。即便當下各地流行的社火匯演,也多是沿街行進式或廣場式的。同時,社火的舞臺展演經常能夠看到。由于社火包含的種類多樣,像歌舞類、說唱類等在沿街行進時有“圈場表演”的特點,實際上具有舞臺演出的條件。而需要過多器械、人數參與眾多、對場地時長有特殊要求的社火在舞臺展演時卻面臨困難。因此,就社火整體而言,沿街行進演出并不完全排斥舞臺展演。社火的舞臺展演有歷史脈絡可循,也有現代社會的訴求。
1.歷史脈絡
社火雜有戲曲、音樂、舞蹈、武術、雜技等多種藝術因素,體現出綜合性的藝術特征。例如秧歌具有戲曲、音樂、舞蹈的綜合特點,抬閣具有戲曲、音樂、舞蹈、雜技的綜合性。傳統戲曲、傳統音樂、傳統舞蹈等民間藝術形式又與社火關系十分密切。現代意義上的戲曲、音樂、舞蹈在發生發展史上也與社火存在交集。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成熟的舞臺藝術形式(戲曲、音樂、舞蹈)曾有過街頭行進演出的階段,這無疑給現在沿街行進演出的社火一些暗示。
與“演有定所”的戲劇相比,社火更傾向于“巡回演出”,王國維認為三教(即打夜胡)、訝鼓、舞隊這類社火形式,在戲劇演進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裝作種種人物,或有故事。其所以異于戲劇者,則演劇有定所,此則巡回演之。然后來戲名曲名中,多用其名目,可知其與戲劇非毫無關系也。”③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1頁。雖然有著沿街行進與舞臺呈現的差異,但社火對戲劇內容、形式多有影響。
社火一般被稱為“行進的藝術”,而戲劇演出場所相對固定。這一行一停的形式差異或許具有某種界樁意義。麻國鈞認為:“所謂‘行’的戲劇,說的是中國古典戲劇是從行進禮儀逐漸演化而來,至少是受到古已有之的‘行進禮儀’的深刻影響,并表現在它成長的全部過程當中。……‘停’的戲劇,是相對于‘行’的戲劇說的,相對于行走的、流動的演出方式說的,進而言之,是指行進的演出隊伍為了滿足觀眾的要求、為了更好地展開一個有著相對長度的故事甚至一個場面而做的短暫停留;是觀演方式的一種變動——由流動的觀演方式變為相對穩定的觀演方式。那些行進的演藝一旦完成了上述意義的‘停頓’,戲劇也就宣告成立了。”①麻國鈞:《“行”與“停”的辯證:中國古典戲劇流變及形態論》,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3年,第1頁。
宋元戲劇的演出場所在城鎮主要集中在“勾欄”之中,相對較為固定了。而在廣大的鄉間,最為常見的演劇場所是神廟。“宋、元以降,最普通的劇場,便是一般神廟了。神廟的建筑,照例于正殿的對面設有一所戲臺。戲臺與正殿之間,必留有一大片廣場,以容納看戲的觀眾,這種形式,在神廟的建筑上,幾乎是千篇一律地。戲劇本起于祀神的儀式……一般人要看戲,便得到神廟或逢有禮祭的其他地方。”②周貽白:《中國劇場史》,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16年,第6頁。恰恰神廟是社火表演最為集中的場合,把適當的藝術形式搬上神廟的戲臺,娛神娛人,社火具有極大的便利性。
在社火發展過程中,并非只有沿街行進演出一種形式,把合適的品種搬上舞臺,至少從宋代就開始了,絕非近時的創舉。
《東京夢華錄》卷八“觀神生日”條載:
天曉,諸司及諸行百姓獻送甚多。其社火呈于露臺之上,所獻之物,動以萬數。自早呈拽百戲,如上竿、躍弄、跳索、相撲、鼓板、小唱、斗雞、說諢話、雜扮、商謎、合笙、喬筋骨、喬相撲、浪子、雜劇、叫果子、學像生、倬刀、裝鬼、砑鼓、牌棒、道術之類,色色有之。至暮呈拽不盡。③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外四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第48頁。
《東京夢華錄》卷六“元宵”條載:
(各類社火獻演)……內設樂棚,差衙前樂人做樂雜戲,并左右軍百戲,在其中駕坐一時呈拽。……(宣德樓)樓下用枋木壘成露臺一所,彩結欄檻,兩邊皆禁衛排立,錦袍,幞頭簪賜花,執骨朵子,面此樂棚。教坊鈞容直、露臺弟子,更互雜劇。近門亦有內等子班直排立。萬姓皆在露臺下觀看,樂人時引萬姓山呼。④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外四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第35頁。
《夢粱錄》“八日祠山圣誕”:
初八日,錢塘門外霍山路有神曰祠山正佑圣烈昭德昌福崇仁真君,慶十一日誕圣之辰。……各以彩旗、鼓吹、妓樂、舞隊等社,奇花異果,珍禽水族,精巧面作,諸色石,車駕迎引,歌叫賣聲,效京師故體,風流錦體,他處所無。臺閣巍峨,神鬼威勇,并呈于露臺之上。自早至暮,觀者紛紛。⑤ (宋)吳自牧:《夢粱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頁。
露臺始自漢代,原為降神之高臺,后成為演出的舞臺、戲臺。至少在宋代,有些雜于社火中的藝術形式,如百戲、雜劇、臺(抬)閣等,都被搬上舞臺來演出了。明清以來,民間社火熾盛,特別是到元宵時,各色社火爭奇斗艷,有些延續著街頭行進演出的形式,有些在舞臺搬演。如民國《萬全縣志》載:“此外,則有社火,晝則游行各處,夜則登臺演劇。每班約百余人,化裝古今男女老少,應有盡有,不倫不類,狀至滑稽,使人噴飯;并雜以多數鑼鼓之聲,沿街舞唱,萬人空巷,到處圍觀。”①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 華北卷》,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第206頁。因此,社火中的很多藝術形式在合適的條件下開始舞臺展演,并且參與了其他藝術形式的演變。社火中的具體藝術形式被改造后成為舞臺藝術形式,如秧歌在很多地方發展成秧歌劇或秧歌戲,原先街頭演出的蓮花落、快板被改造后成為戲曲和快板劇。
2.現代訴求
社火根植于中國傳統農業社會,在社會轉型中面臨的生存問題最為緊要。在種種探索和嘗試之中,“舞臺展演”是最為常見也最受爭議的方式。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各地社火形式的存續都在進行某種程度的“舞臺展演”改造。不唯如此,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保護也存在這樣的傾向。舞臺展演作為社火常見的乃至“共識”的改造方向,有些是根據自身藝術特點自然發展的,更多的是基于社會情況做出的。其暗含的邏輯是由俗轉雅的努力和民俗宣傳的需要。
首先,“沿街行進”和“舞臺展演”兩種形式的差異并非只表現在呈現方式上,實則代表了兩種審美取向。由于社火多由民間自發組織,沒有專業的演員,沒有專業的團隊,常常呈現出濃厚的土的俗的色彩。相較于舞臺藝術而言,化妝、唱腔、服飾、道具都談不上精美。因此,在對社火節目進行改造時,戲曲、舞蹈、音樂等舞臺藝術提供了可對照的標桿。尤其是很多舞臺藝術本就是從民間社火藝術發展而來,舞臺藝術似乎成為社火的發展追求。從街頭搬上舞臺,實際上是反映了街頭之“俗”向舞臺之“雅”的慣有認知。按照此種邏輯,民間社火在面臨存續困境的時候,向舞臺轉變的嘗試多,而向民間轉變的嘗試少。民間社火越來越精致,即是以舞臺藝術為參照和模板的。
其次,在宣傳本土文化、地方文化和傳統文化中,民俗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語境下,對外宣傳成為一項重要的工作。社火常被作為地方文化的代表予以展示。社火特殊的沿街行進的、群眾性的、狂歡式的形式難以在另一地復現,因此只能把展示場地、時間、人數和方式固定在可控的范圍內。往往是截取最精彩的片段或最核心的情節在固定的場合、固定的時間段進行展示,這是舞臺化的改造。這樣的改造更加迎合當代受眾讀圖式的、短視頻式的欣賞習慣。就傳播效果而言,能在短時間內引起足夠的關注度。更為現實的是,很多民俗宣傳的場所就是舞臺,要求展示對象不得不因地制宜地做出改變。
社火作為街頭行進演出的民間藝術形式,進行舞臺展演的實踐邏輯是:在歷史發展中,社火誕生之后,在行進演出的同時,也被搬上舞臺,這是有歷史脈絡的;現代社會發展帶來對社火進行改造的強烈愿望,舞臺藝術成為社火改造的方向和路徑。
三、社火舞臺展演的傳承風險
社火被作為“節目”僅作宣傳和匯演式的舞臺展演,可能是短暫的、權宜的,如果朝著舞臺展演的方向改造,面臨的不僅是表演場地、表演時間、藝術形式的簡單變革,實際上存在著根本性質的轉向。盡管社火并不完全排斥舞臺展演,但單維度的改造路徑很大程度不符合社火發展的規律。尤其是當社火的舞臺展演被視為“保護”和“傳承”的基本舉措時,所面臨的風險更加突出。主要體現在民俗語境、傳承主體、傳承動力的變更等方面。
1.民俗語境的剝離
把社火街頭展演和舞臺展演都視為“展演”(performance)的情況下,它們實踐中的語境(context)差異是十分明顯的。社火作為民俗,能夠搬到固定場所、固定時間段的舞臺上演出,所能保留的民俗信息是值得商榷的。顯然,只有能夠適應舞臺環境的要素才可能呈現,不適合的只能舍棄,那么與社火民俗相關的信仰環境、民間組織社團、行業規則都難以呈現。社火作為“語境中的民俗”,不得不剝離原有的民俗語境,呈現為“類民俗”的樣貌。
理查德·鮑曼認為,民俗與個人、社會、文化等諸種因素相互關聯,從這種關聯中民俗獲得存在和意義。研究民俗需要注意它存在的語境,主要是文化語境(Cultural context)和社會語境(Social context)兩大層面。①Bauman, Richard. The Field Study of Folklore in Context[A].In Richard Dorson. ed. Handbook of American Folklore[M].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p.362-386,另參見孟慧英:《語境中的民俗》,《民間文化論壇》,2004年第6期及楊利慧、安德明:《美國當代民俗學的主要理論和方法》,周星主編:《民俗學的歷史、理論與方法》,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600—601頁。民俗所存在和獲得意義的語境是傳承的根本,脫離民俗語境的“民俗”很難獲得延續性發展。筆者調查過的多種社火類非遺赴外地匯演、搬上電視臺的舞臺等等類似的展演,對于提高知名度和對外宣傳有前所未有的效果,但無法作為傳承的基本策略。
在社火為舞臺展演所做的努力中,脫離民俗語境所帶來的損失同時存在著。街頭行進演出所承載的信仰環境、觀演互動、行業規則都是難以呈現的部分,在現實民俗中至為重要,但在舞臺展演中卻只能剝離。例如在山西清徐徐溝背鐵棍街頭行進演出中,為了協調統一,形成了獨有的“號子”:“為便于行進中指揮,他們還創造了一套專用語言。這種語言徐溝人叫‘號子’。依此,可以在行進中的前進、后退、左彎、右拐、爬坡、過礙以及過橋、穿洞時取得準確的聯系,而且不至與觀眾的吵嚷聲混為一起而誤事。……如果是路面不平、或是有破磚、爛瓦等障礙物時便喊‘左打踼’或‘右打踼’,如果是障礙物多或延伸很長時,便喊:‘一溜打踼’。如果遇上泥濘的道路或結冰的路面時,可喊:‘左打滑’或‘右打滑’以及‘一溜打滑’的號子。過橋時可喊‘左首過橋’或‘右首過橋’和‘過大橋’等號子。”②牛廣明搜集整理:《無言戲劇、空中舞蹈——記徐溝的背棍、鐵棍》,《清徐文史資料(第1輯)》,清徐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6年,第80—81頁。當背鐵棍被搬上舞臺后,既沒有觀眾的吵鬧,也沒有了沿街行進中的遇到各種情況,鐵棍的造型藝術還在,但相關的號子不大需要了。顯然,背鐵棍社火的傳承,這些號子不應在舍棄的行列。
在各種社火中,歌舞類、說唱類其實較為適宜舞臺展演,它們也面臨著民俗語境的問題。秧歌經過發展成為相對成熟的戲劇形式,如秧歌戲、秧歌劇等,很早就搬上了舞臺,并且在很多地方作為地方劇種生存著。“傳統秧歌發展到今天,發生了包括現代舞臺化在內的多種形式轉換,與本土民俗文化形成了一定的疏離。”①張婭妮:《脫“俗”求“藝”:現代舞臺化背景下傳統秧歌的民俗因素分析》,《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主動和被動的剝離在當代社火舞臺展演中都較為常見,其實背后都觸及如何審視社火民俗語境的實質。
2.傳承主體的變遷
社火的組織搬演常常需要整個村落或多個村落的班社來承擔,呈現群體性的特點。因此很難將社火的傳承者固定在某個人或某幾個人身上,更何況社火的舞臺展演實際上進行了某種意義的選拔,把由整體的群眾表演轉換為個別固定人數的表演,對社火傳承有巨大風險。筆者在華北多地調查社火時發現,當地社火在被確定為“非遺項目”之前,社火活動由社首組織,村民自愿參與,確定為“非遺項目”之后,若干社首成為“傳承人”,村民的參與熱情反而受到影響。
社火的傳承主體具有明顯的民間結社色彩。“由于政治、經濟地位的不同,這種活動不可能是政治、經濟活動,而只可能是社區文化活動、民俗活動,這才應該是‘社火’的本意。”②趙世瑜:《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第248頁。社火是作為這一群體(社區)的生活本身延續的,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才有傳承的可能性。“大多數民間傳承都有一定的地方性特點。地域社會或其內部的復數社區,可被理解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或民間傳承得以滋生、扎根和延續的社會土壤、基本條件和傳承母體。③周星:《從“傳承”的角度理解文化遺產》,周星主編:《民俗學的歷史、理論與方法》,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38頁。社火的傳承主體是特定地域民俗生活中按照民間社會組織原則構成的群體。
社火由街頭行進演出到舞臺展演實際上完成了傳承主體的改變,盡管很多舞臺展演的演職人員很大程度上也來自于街頭行進演出的那些人,但脫離民俗語境的前提下,舞臺展演的傳承主要不再過度依賴村社或家族的傳承模式了。
3.傳承動力的變化
社火在傳統社會的傳承動力主要基于民俗生活本身,一方面作為人們日常娛樂文化的一種,能夠為人們提供展示才藝的場合,帶來身心的愉悅,這是自發的因素;另一方面,部分社火也是謀生的一種技藝,可以帶來一定的收入,維持基本的生存。因此,社火的傳承動力主要是民眾生活生存的需要。隨著社會的變遷,此種動力逐漸減弱,甚至難以為繼。在原生的傳承動力不足時,政治的經濟的措施帶來新的動力。很多社火品種的從業者為了生活生存的需要,有專業化、職業化的傾向。這都對社火的傳承有重要作用。
社火的舞臺展演似乎迎合了政治的經濟的措施和專業化、職業化傾向的共同要求,因此成為當下談到傳承保護時的高頻詞。不可否認的是,政治導向和經濟刺激在社火的發展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這并不能為社火傳承提供充足的動力。首先,政治層面的相關政策和措施對社火的宣傳和扶持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各地的實際執行中存在差異,各個社火品種面臨的問題也各不相同,政治層面的話語指令、審美取向、考核體系與民間社火發展規律并非完全符合。在社火向舞臺藝術轉變的過程中,當地政府的意見常常發揮了主導作用,基于短期的宣傳效應還是持續的傳承扶持,可能決定了當地社火的走向。其次,經濟層面的因素對社火的傳承是不可或缺的。社火從街頭到舞臺的變化,實際上體現著從自發到商業性質的探索。商業性質的演出也屬傳承的動力,但比自發的表演需要更嚴格的藝術要求,并且存在相應的藝術市場。不可回避的是,民間社火的舞臺展演雖不乏佼佼者,但大多數民間社火的從業者并沒有富有競爭力的演出技藝,再加之受眾減少、市場萎縮,社火的舞臺展演也很難找到足夠的傳承動力。
結 語
社火具有鮮明的沿街行進演藝的特點,因此可以歸入游藝民俗的分類,在實際民俗生活中,社火均具有“游藝”的內涵。社火除了沿街行進演藝之外,還有舞臺展演的形式,這并非近來才有的。現代對社火舞臺展演的探索嘗試,其實踐邏輯是社火的歷史發展脈絡和現代社會訴求,前者包含了社火在歷史演進中并不完全排斥舞臺呈現,后者包含了舞臺呈現的當代欣賞習慣和宣傳策略。社火的舞臺展演可以作為社火發展的一個考察維度,但卻不是傳承的唯一維度,且不宜不分種類不分地域地搬上舞臺。社火的舞臺展演轉向所面臨的傳承風險主要表現在脫離民俗語境,傳承主體由社區班社轉向社火演員,傳承動力由民俗動力轉為政治經濟促發的動力。社火的舞臺展演是傳承的一種路徑,也是重要的路徑,但需要審視不同社火種類的不同特點、發展的不同階段,充分重視培育社火發展的整體文化環境,才能規避風險,良性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