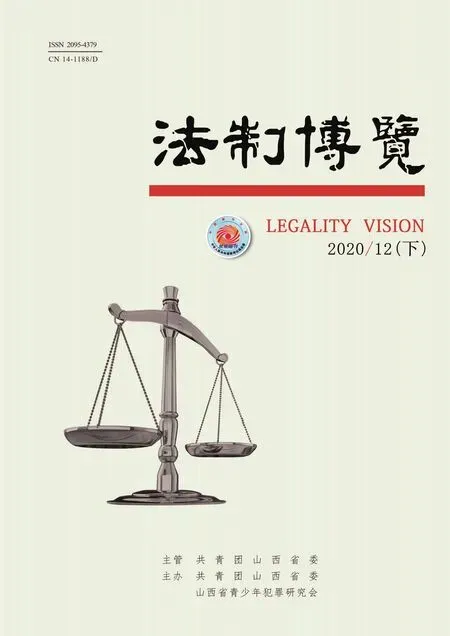非法獲取網絡虛擬財產行為的類型化探討*
張盈穎
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江蘇 蘇州 215000
一、問題的由來
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互聯網在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同時也滋生了許多新型的犯罪。虛擬財產的出現導致了以各種手段非法獲取虛擬財產犯罪的行為,而針對這類行為如何定性,在理論上和司法實踐中都存在較大的爭議。
針對司法實踐中采用各種手段非法獲取虛擬財產的犯罪行為如何定性的問題,從刑法修正案七增設了第285條第2款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以來,較大的爭議點主要體現在虛擬財產是否具有財產屬性,單純將虛擬財產作為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的一種,以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統一進行認定是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等。
事實上,虛擬財產具有不同的類型,非法獲取虛擬財產的手段也多種多樣,針對非法獲取虛擬財產的主體的不同在具體認定上也會存在著一定的不同,并非單純認定虛擬財產屬于財產犯罪的客體就可以一勞永逸的解決問題。關鍵還是以要法條規定為大前提,對不同的行為類型是否符合罪名的構成要件進行具體分析,從而對犯罪行為進行定性。本文嘗試對虛擬財產的法律性質進行分析,根據獲取手段的不同、虛擬財產類型的不同區分為不同的類型,從而在司法實踐中可以針對同樣性質的犯罪行為做出一致定性。
二、非法獲取虛擬財產行為可以成立財產犯罪
針對非法獲取虛擬財產的行為如果只以計算機類犯罪進行規制,首先,就面臨著無法涵蓋具體手段行為的局限性,刑法第285條第2款只規定了侵入或以其他技術手段,那么對于采用合法手段進入系統以及采用欺騙、威脅等手段獲取對方虛擬財產的行為就無法納入該罪的處罰范圍。其次,有學者提出“但網絡游戲中的虛擬裝備被行為人盜用之后,仍然還在網絡游戲運營商控制的網絡游戲場中,甚至可能原樣返還給特定的游戲玩家”。所以,非法獲取虛擬財產的行為只破壞網絡秩序。這種說法顯然不具有合理性,不能因為虛擬財產仍然存在,就忽略行為對玩家所造成的法益侵害。最后,具有財產屬性的虛擬財產,符合財產犯罪的構成要件,當然成立財產犯罪。
(一)虛擬財產具有財產屬性
有學者將虛擬財產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賬號類的虛擬財產;第二類是物品類的虛擬財產;第三類是貨幣類的虛擬財產。虛擬財產指“虛擬”不是指虛無,而是相對依賴于現實空間的財產存在形式,其作為一種電磁數據依賴于網絡空間而存在。但是利用虛擬財產的這種網絡空間依附性以及其可復制性來否認其具有財產屬性的說法并不能成立。首先,虛擬財產不能脫離網絡存在的這種網絡空間依附性只是存在形式的特點,根據我國立法和司法的邏輯來看,我國刑法中財產犯罪的財物可以包含有體物、無體物和財產性利益,其存在形式的這種特點并不足以直接將其排除出財產犯罪保護法益的范圍。而虛擬財產的可復制性則具有相對性,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復制也不能無限復制。針對用戶而言,其對其賬戶內存在的游戲設備等虛擬財產具有支配性。其次,認定其可以作為財產犯罪的客體應從正面論證其具有財產犯罪之“財產”的屬性,而不是通過證明其具有傳統財產所不具有的特征來說明其不是財產犯罪的客體。財產犯罪所要求的財產即具有流通性和交換價值,就虛擬貨幣及虛擬產品而言無論是線上的流通性還是線下的交換價值都滿足了“財產”的要求,具有財產屬性。而就賬號類本身而言,針對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例如配有各種游戲裝備的賬號顯然具有交換價值,而如果只是侵入賬戶獲取信息,則不涉及財產犯罪。
(二)針對不同主體采用不同的犯罪數額計算方式
實踐中存在的非法獲取虛擬財產可以根據行為所侵害的不同的法益主體區分為,針對平臺和針對用戶兩種。
虛擬財產針對不同主體具有不同價值,適用統一犯罪數額的計算方法不符合罪刑均衡的原則。有學者基于這個理由否認財產犯罪的成立,但是因犯罪數額難以認定就否認犯罪成立的看法難以成立。同時,犯罪數額也是財產犯罪認定過程中的重要問題。“財產犯罪的犯罪數額一定等同于被害人的損失數額,如果缺乏這種同一性,就無法解釋財產犯罪。”所以,認定財產犯罪的犯罪數額要從被害人遭受的財產損失入手,由于“法益的價值是與法益的主體密切關聯的。”尤其是虛擬財產是由平臺設置出的電磁數據,就平臺而言其具有復制的特權,所以針對平臺和用戶必然要采取不同的犯罪數額計算方式。
就用戶而言,對于其賬戶內的貨幣類虛擬財產如果平臺具有售賣價格,就應該按照其購買的金額認定其財產損失;對于只能通過打怪、升級等完成任務的方式獲得的游戲裝備或者貨幣類虛擬財產,則可以通過玩家之間的流通價格來認定犯罪數額。
就平臺而言,如果按照市場價格認定犯罪數額,則犯罪數額就與行為人遭受的財產損失不具有同一性。如果根據其成本認定其沒有損失,就會導致非法獲取用戶賬戶內的虛擬財產可以成立財產犯罪而獲取平臺內的虛擬財產則不成立的尷尬局面。有學者提出按照其市場價格計算,然后根據數額來判斷其情節的嚴重程度來對具體罪名進行認定也不失為一種解決辦法。
三、非法獲取虛擬財產行為的類型化
互聯網背景下,行為人多采用侵入或其他技術型手段進入系統非法獲取虛擬財產的行為方式,但同時也存在著其他行為方式,針對不同的行為如何定性存在著較大的爭議。本文根據行為方式以及針對的不同類型的虛擬財產將實踐中存在的非法獲取虛擬財產行為分為三類:
第一,正如上文所述,單純針對侵入系統獲取賬號信息,不涉及物品及貨幣類虛擬財產的行為,由于并沒有侵害到財產法益,難以認定其行為成立相關的財產犯罪,而只能認定為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
第二,當行為人并沒有采取侵入或者其他技術型手段獲取虛擬財產,不符合成立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的法定手段要件,而是通過其職權合法進入系統,或者通過采取欺騙威脅等手段使得被害人將賬戶內的虛擬財產轉移給行為人,由于這類虛擬財產具有財產屬性,所以只要根據具體行為,判斷符合相關財產犯罪的構成要件,則可以成立對應的財產犯罪。
第三,在其行為符合非法侵入或采取其他技術性手段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罪的法定手段要件,同時非法獲取的是具有財產性和數據性雙重屬性的虛擬財產,則應該同時成立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和盜竊罪。那么這種競合是想象競合還是法條競合呢?“想象競合與法條競合的根本區分,不在于行為是否必然觸犯數個法條,而在于想象競合是事實意義上的競合,而法條競合則是法律意義上的競合。”就盜竊罪和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而言,難以認定其存在邏輯上的重合和交叉關系,而只是基于虛擬財產的雙重屬性,基于非法獲取虛擬財產的這種特定的行為事實產生了一種競合,因此,認定為想象競合更合適。
四、結語
盡管我國刑法中的財物可以包含廣義的有體物、無體物,財產性利益基本得到了學界的認可。但盜竊罪又有其特殊性,盜竊罪的成立要求違背對方意志轉移占有,如果認為這種占有轉移只能是物理上的占有的轉移,那么侵入系統非法獲取虛擬財產的行為仍然不符合盜竊罪的構成要件。但是如果將占有過度觀念化又會導致盜竊罪失去定型性,淪為財產犯罪的兜底條款。如何對盜竊罪的構成要件進行修正,使其可以包含財產性利益,或者面向互聯網背景增設新罪名來解決傳統罪名難以涵攝的新型犯罪行為,是不得不面對的新時代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