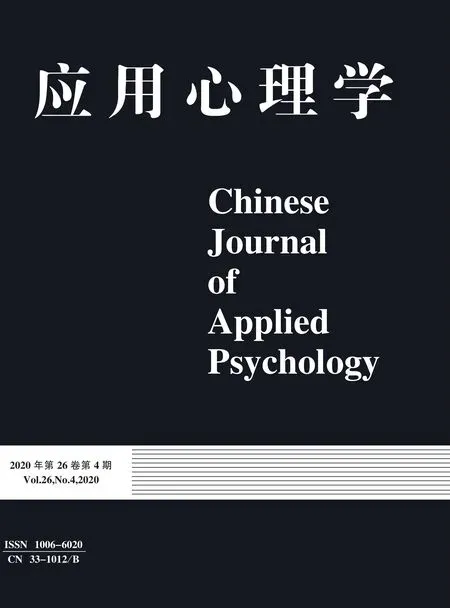難易概念的情緒隱喻及其雙向映射
(云南師范大學教育學部,云南師范大學民族教育信息化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云南 昆明 650500)
1 引 言
概念既是認識的起點、高級認知能力的基礎,也是思維活動的產物。個體是如何表征和加工概念信息的,一直以來都是認知研究領域的熱點問題(王斌,李智睿,伍麗梅,張積家,2019)。難易概念指能夠表達事物困難或容易的抽象詞匯概念(如艱難、簡單),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經常用它來評價事物,任務難度也常被作為自變量引入認知研究。
語義表征具身理論(Embodied Theory of Semantic Representation)認為,在概念表征過程中,情緒經驗和感知經驗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個體常借助感知運動信息來表征具體概念,抽象概念的表征則主要來自情緒經驗信息和語義信息,難易概念承載著情緒經驗信息,這些信息又促進難易概念的語義加工(姚昭,朱湘茹,王振宏,2016;Vigliocco,Meteyard,Andrews,& Kousta,2009)。Lakoff和Johnson(1980)提出的概念隱喻理論(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認為,抽象概念是在具體概念的基礎上形成的,抽象概念具有隱喻性。具體來講,個體可以將無法用身體感受到的抽象概念映射到一個與身體感知運動系統相關聯的概念領域,以實現對抽象概念的表征與體驗式理解(賈寧,馮新明,魯忠義,2019;李子健,張積家,喬艷陽,2018;趙巖,伍麟,2019)。隨著認知心理學、語言學等領域對概念表征的不斷探索,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認為概念的隱喻映射具有雙向性(鄭皓元,葉浩生,蘇得權,2017;Slepian & Ambady,2014)。
情緒作為一種對人類生存至關重要的心理與生理現象,體現了個體對事物的態度、體驗以及相應的行為反應,存在著積極與消極之分(孟昭蘭,1994;Watson,Clark,& Tellegen,1988)。在一般認知任務中,即使是內隱情緒也會影響個體對任務難易程度的感知。Genolla(2012)提出的IAPE(Implicit Affect Primes Effort)理論假設,在消極情緒下,個體會感覺任務難度增加,導致其主觀任務需求(個體主觀評價任務完成過程中所需努力的量)上升,以至于在任務執行過程中,個體也將調動更多的認知資源(即努力動員);相反,在積極情緒下,個體會認為任務相對簡單,損耗的認知資源也會更少。在該理論中情緒與難易信息間的對應關系仍停留在經驗推理層面,目前尚未有實驗研究對此進行直接探討,但一些相關理論與研究為情緒蘊含著難易信息提供了參考。
情緒信息理論(Affect-As-Information Theory)指出,情緒的產生不僅會帶來情緒體驗,還包含著一定信息線索,這便是情感與認知聯系的關鍵所在。具體來說,積極情緒是安全、舒適環境的信號,寓意著容易、有價值;而消極情緒是需應對難題的信號,寓意著困難、無價值(Clore & Huntsinger,2007;Huntsinger,2012)。有研究者認為,正是這些難易、有無價值等信息,才使得不同情緒下的個體采用不同加工策略,進而對認知加工過程產生促進或阻礙作用(方平,馬焱,王雷,朱文龍,2018;劉雷,索濤,2018)。Lasauskaite,Gendolla和Silvestrini(2014)發現,相比于快樂情緒啟動,在悲傷情緒啟動下,個體的主觀任務需求會更高,Esposito,Gendolla和Martial(2014)認為主觀任務需求是依據任務難易程度評估得來的,任務越困難,個體感受到的任務需求也將越高。
如果上述積極情緒與容易、消極情緒與困難間的聯系真實存在,那么根據語義表征具身理論以及隱喻映射的雙向性反推,容易概念承載的情緒信息應是積極的,困難概念承載的情緒信息應是消極的。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采用序列啟動范式(a sequential priming paradigm)進行兩個實驗,以著重探討兩個方面的內容:(1)情緒與難易信息的對應關系。實驗1使用情緒面孔圖片作為啟動刺激,難易詞作為靶刺激,要求被試進行難易歸類,以驗證積極情緒與容易信息、消極情緒與困難信息的對應關系,進而為IAPE理論、情緒信息理論提供直接依據。(2)難易概念與情緒的對應關系。在實驗1的基礎上,實驗2使用難易詞作為啟動刺激,情緒面孔圖片作為靶刺激,要求被試進行情緒歸類,以探討容易概念與積極情緒、困難概念與消極情緒是否存在對應關系,進而驗證難易概念與情緒間隱喻映射的雙向性。本研究認為積極、消極情緒分別蘊含著容易、困難信息,容易、困難概念分別承載著積極、消極情緒,即難易概念的情緒隱喻映射具雙向性。在序列啟動范式中,個體對靶刺激的反應會受到啟動刺激的影響,而這種影響恰好反映了個體認知結構中靶刺激與啟動刺激的聯結情況,當靶刺激與啟動刺激效價一致時,被試的反應顯著快于效價不一致條件,即出現序列啟動效應(高志華,魯忠義,2019;張玥,辛自強,2016;Wentura & Degner,2010)。因此,本研究假設在兩個實驗中,相比于不一致條件(積極情緒-困難、消極情緒-容易;容易-消極情緒、困難-積極情緒),個體在一致條件下(積極情緒-容易、消極情緒-困難;容易-積極情緒、困難-消極情緒)的反應速度顯著更快。
2 實驗1:情緒面孔對難易詞的序列啟動效應
2.1 被試
從某高校選取30名大學生,視力或矯正視力正常,均為右利手且從未參加過類似實驗,其中男生12名,女生18名,年齡為20.50±2.62歲。
2.2 實驗材料
從中國情緒圖片庫(白露,馬慧,黃宇霞,羅躍嘉,2005)中選擇12張情緒圖片,積極、消極和中性情緒圖片各4張(男女各半)。邀請25名大學生對圖片的喚醒度和效價進行7點評分。積極(6.61±0.50)、消極(1.40±0.45)、中性(3.99±0.22)情緒圖片的效價差異顯著(F(2,48)=885.63,p<0.001,ηp2=0.97)且兩兩間差異均顯著(p<0.001),為進一步驗證結果的有效性,進行貝葉斯分析(吳凡,顧全,施壯華,高在峰,沈模衛,2018),結果仍顯著(BF10>100);積極(6.55±0.39)、消極(6.34±0.66)、中性(6.23±1.58)情緒圖片的喚醒度差異不顯著(F(2,48)=0.83,p=0.44,BF10=0.22)。
選擇能表達困難、容易概念的詞語各11個,邀請30名大學生對詞語的難易程度進行7點評分,最終篩選出困難詞、容易詞各6個。困難詞(6.46±0.34)與容易詞(1.39±0.26)的難易程度差異顯著(t(29)=52.953,p<0.001,d=16.72,BF10>100)。
2.3 實驗設計
采用3(情緒類型:積極/中性/消極)×2(難易類型:容易/困難)的被試內設計,因變量為難易詞判斷的正確率和反應時。
2.4 實驗程序
在安靜的實驗室中,使用聯想ThinkPad 14英寸液晶顯示器(1024×768,60HZ)通過E-prime 2.0呈現實驗材料,被試的眼睛與屏幕間水平距離為50~70cm。
實驗流程:黑色背景上呈現白色注視點“+”500ms,然后呈現情緒圖片27ms,隨后呈現隨機點圖掩蔽刺激133ms,最后呈現難易詞(最大呈現時間為2000ms),被試需判斷詞語是容易詞還是困難詞,并按相應鍵(一半被試的按鍵規則是出現容易詞按“A”鍵,出現困難詞按“L”鍵;另一半被試的按鍵規則相反),按鍵后詞語消失并呈現“您已按鍵”,呈現時間為(2000ms-被試反應時)。試次間間隔時間隨機,范圍為500ms到1500ms。所有刺激均呈現在電腦屏幕中央。
整個實驗共兩個組塊,每個組塊有144個試次,兩個組塊之間至少休息2分鐘。理解實驗流程后,被試需練習16個試次,至少正確完成14個試次才能進入正式實驗。
2.5 結果
啟動刺激和靶刺激效價一致時被試的反應時顯著小于不一致條件即為序列啟動效應,因此先區分出一致(積極-容易、消極-困難)、不一致(積極-困難、消極-容易)以及中性條件(中性-容易、中性-困難),從而產生一致性變量。
僅考慮反應正確且反應時在正負三個標準差以內的數據,對反應時進行單因素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發現,一致性的主效應顯著(F(2,58)=13.70,p<0.001,ηp2=0.32,BF10=1310.99),反應時從一致條件(617.69±11.23ms)到中性條件(627.69±10.43ms)再到不一致條件(636.37±9.88ms)不斷增大,事后檢驗顯示一致與不一致(p<0.001)、一致與中性(p=0.006)、中性與不一致(p=0.011)條件下的反應時差異均顯著。對反應時進行3(情緒類型)×2(難易類型)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發現,情緒類型的主效應(F(2,58)=1.44,p=0.25,BF10=0.09)、難易類型的主效應(F(1,29)=1.81,p=0.19,BF10=1.43)均不顯著,交互作用顯著(F(2,58)=12.23,p<0.001,ηp2=0.297,BF10=60.18),事后檢驗結果如圖1,相比于消極情緒啟動(634.14±9.36ms),積極情緒啟動下(610.49±10.45ms),被試對容易詞的反應顯著更快(p<0.001);相比于積極情緒啟動(638.61±11.64ms),消極情緒啟動下(624.88±13.23ms),被試對困難詞的反應顯著更快(p=0.01)。

圖1 不同情緒啟動下難易詞判斷的反應時(M±SD)
不同情緒啟動下難易詞判斷的正確率為M=96.46%(SD=0.04)。對正確率進行單因素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發現一致性的主效應不顯著(F(2,58)=3.09,p=0.053,BF10=1.09)。對正確率進行3(情緒類型)×2(難易類型)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發現情緒類型的主效應(F(2,58)=0.51,p=0.61,BF10=0.07)、難易類型的主效應(F(1,29)=2.93,p=0.098,BF10=0.17)以及交互作用(F(2,58)=2.22,p=0.12,BF10=1.83)均不顯著。
3 實驗2:難易詞對情緒面孔的序列啟動效應
3.1 被試
從某高校選取30名大學生,視力或矯正視力正常,均為右利手且從未參加過類似實驗。去掉正確率低于50%的被試(2名),得到28名被試,男生12名,女生16名,年齡為20.50±2.12歲。
3.2 實驗材料
材料選擇同實驗1。
選擇能表達困難、容易以及中性概念的詞語各11個,30名大學生對其難易程度進行7點評分,篩選出困難詞、容易詞、中性詞各4個。困難詞(6.57±0.34)、容易詞(1.20±0.24)、中性詞(3.97±0.13)的難易程度差異顯著(F(2,58)=2970.18,p<0.001,ηp2=0.99,BF10>100),且兩兩間差異均顯著(p<0.001)。
選擇積極、消極情緒圖片各6張,25名大學生對其喚醒度和效價進行7點評分。積極(6.50±0.45)、消極(1.53±0.55)情緒圖片的效價差異顯著(t(24)=29.18,p<0.001,d=9.88,BF10>100);積極(6.31±0.43)、消極(6.19±0.67)情緒圖片的喚醒度差異不顯著(t(24)=0.80,p=0.43,BF10=0.28)。
3.3 實驗設計
采用3(難易類型:容易/中性/困難)×2(情緒類型:積極/消極)的被試內設計,因變量為情緒類型判斷的正確率和反應時。
3.4 實驗程序
同實驗1但有所改變:啟動刺激即難易詞呈現53ms;掩蔽刺激為“XXX”;靶刺激即情緒面孔最大呈現時間為1500ms;被試需判斷靶刺激是積極還是消極情緒并按相應鍵。
3.5 結果
首先區分出一致性變量,包括一致(容易-積極、困難-消極)、不一致(困難-積極、容易-消極)以及中性條件(中性-積極、中性-消極)。
僅考慮反應正確且反應時在正負三個標準差以內的數據,對反應時進行單因素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發現,一致性的主效應顯著(F(2,54)=10.39,p<0.001,ηp2=0.28,BF10=153.64),被試的反應時從一致條件(636.29±15.23ms)到中性條件(641.89±14.74ms)再到不一致條件(651.84±15.39ms)連續增大,不一致與一致(p=0.001)、中性(p=0.001)條件下的反應時均出現顯著差異,一致與中性條件下的反應時無顯著差異(p=0.13)。對反應時進行3(難易類型)×2(情緒類型)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發現,難易類型的主效應不顯著(F(2,54)=0.49,p=0.62,BF10=0.07),情緒類型的主效應顯著(F(1,27)=13.95,p=0.001,ηp2=0.341,BF10>100),表現為對積極情緒的反應(628.55±14.18ms)顯著快于消極情緒(658.13±16.73ms),交互作用顯著(F(2,54)=10.53,p<0.001,ηp2=0.28,BF10=3.62),事后檢驗結果如圖2,相比于困難詞啟動(638.81±14.73ms),容易詞啟動下(621.27±14.19ms),被試對積極情緒的反應顯著更快(p=0.003);相比于容易詞啟動(664.88±17.28ms),困難詞啟動下(651.31±17.34ms),被試對消極情緒的反應顯著更快(p=0.016)。
不同難易詞啟動下情緒類型判斷的正確率為M=96.38%(SD=0.03)。對正確率進行一致性的單因素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發現一致性的主效應不顯著(F(2,54)=1.05,p=0.36,BF10=0.24)。對正確率進行3(難易類型)×2(情緒類型)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發現難易類型的主效應(F(2,54)=0.081,p=0.92,BF10=0.06)、情緒類型的主效應(F(1,27)=3.40,p=0.076,BF10=0.52)以及交互作用(F(2,54)=1.15,p=0.32,BF10=0.22)均不顯著。

圖2 不同難易詞啟動下情緒圖片判斷的反應時(M±SD)
4 總討論
本研究實驗1以情緒面孔圖片作為啟動刺激,難易詞作為靶刺激,要求被試進行難易歸類,結果顯示,從不一致條件到中性條件再到一致條件被試的反應時顯著遞減;相比于消極情緒啟動,被試在積極情緒啟動下對容易詞的反應顯著更快、對困難詞的反應顯著更慢。表明在個體認知結構中情緒與難易信息存在著對應關系:積極情緒蘊含著容易信息,消極情緒蘊含著困難信息。在實驗2中,啟動刺激為難易詞,靶刺激為情緒面孔圖片,兩個實驗所使用的情緒圖片、難易詞均有所不同,但結果仍發現,被試在一致條件下的反應時顯著短于不一致條件,中性條件下的反應時大小居其中間位置,達到整體線性;相比于困難詞啟動,被試在容易詞啟動下對積極情緒的反應顯著更快、對消極情緒的反應顯著更慢。表明在個體認知結構中難易概念與情緒存在著對應關系:容易承載著積極情緒,困難承載著消極情緒。本研究兩實驗的結果為難易概念與情緒間隱喻映射的雙向性提供了直接證據。
4.1 情緒蘊含著難易信息
前人研究已驗證IAPE理論模型中難易信息會影響主觀任務需求、主觀任務需求會影響努力動員以及情緒對努力動員有著深刻的影響(Chatelain & Gendolla,2015;Genolla,2015;Silvestrini & Gendolla,2013)。在此基礎上,本研究實驗1表明,在個體認知結構中,積極情緒蘊含著容易信息、消極情緒蘊含著困難信息,這為IAPE理論總體邏輯的完善驗證提供了支撐。
IAPE理論總體邏輯得以完善論證有助于解釋情緒啟動對個體認知加工的影響。徐慧芳,張欽和郭春彥(2015)指出,負性情緒強度越高,個體注意資源的分配就越多,王寶璽等人(2018)還借助這一觀點來解釋為什么負性情緒圖片的再認成績顯著高于中性圖片;馮墨女和劉曉明(2019)也發現積極情緒下認知抑制功能下降。在大量生活經驗的積累下,個體認識到在某些情緒下應對挑戰會更容易或更困難,容易、困難成為了不同情緒心理表征的重要特征。消極情緒往往預示著阻礙與困難,以至于在任務執行過程中個體會調用更多的認知資源,付出更多的努力,比如采用精細加工模式來解決問題,從而提高認知任務表現;積極情緒則相反,它意味著沒有威脅、任務是容易的,從而降低了個體主觀任務需求以及努力動員,比如采用簡單啟發式加工模式,導致認知表現下降(梁家銘,陳樹林,2015;徐富明等,2015;Richter,Gendolla,& Wright,2016)。
4.2 難易概念承載著情緒
本研究實驗2表明,在個體認知結構中,容易承載著積極情緒,困難承載著消極情緒,這與語義表征具身理論所強調的“概念能承載情緒信息”一致。
文字是情緒信息的重要載體,語言網絡和情緒網絡之間存在著復雜的聯系(曹陽,王琳,2018)。就一個簡單的詞匯概念而言(例如玫瑰),它不僅蘊含著語義信息(一種植物,有香味的),還承載著豐富的情緒意義(正性的、積極的),難易概念亦是如此。在難易概念的習得過程中,生活實踐經驗能夠促進和加強個體對難易概念的理解(如“難于上青天”、“不費吹灰之力”),而這些生活實踐常伴隨著情緒體驗。例如,當個體遭遇一些無法及時解決的、困難的事件時,常會因任務過重、自我能力不足等原因而伴隨著消極情緒;而當處理那些有能力解決的、容易的事件時則相反。久而久之,個體便將困難與消極情緒、容易與積極情緒關聯起來。
此外,實驗2顯示被試對積極情緒的反應顯著快于消極情緒,出現了積極情緒識別優勢。以往研究也發現,在情緒面孔識別中,被試對高興面孔的識別更快(Nummenmaa & Calvo,2015),于明陽、李富洪和曹碧華(2018)也曾指出,愉快面孔識別優勢具有廣泛性和穩定性,個體識別高興面孔的反應時均短于其他情緒面孔。
5 不足與展望
本研究結果不僅支持情緒信息理論和語義表征具身理論觀點,證實了IAPE理論總體邏輯的準確性,還驗證了難易概念與情緒的雙向映射關系,為概念隱喻理論的延伸即隱喻的雙向性觀點提供了支撐。但值得注意的是,也有研究發現,在高要求的體能耐力運動中,積極情緒啟動促進了任務完成(Anthony,James,& Samuele,2014),這可能是由于任務難度和情緒會共同影響主觀任務難度,進而影響個體主觀任務需求和努力程度。因此,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探討在不同任務難度下,情緒對個體認知任務表現的影響。其次,本研究的情緒材料僅涉及快樂、悲傷與平靜情緒,鑒于憤怒與積極期望、高應對能力有關,恐懼與低控制、低應對能力有關(Framorando & Gendolla,2018;Lerner & Keltner,2001),個體是否會以同樣的形式把恐懼和困難、憤怒和容易聯系起來?因此,接下來的研究還可以綜合探討更多不同情緒與難易概念間的隱喻關系。
6 結 論
本研究采用序列啟動范式進行兩個實驗,得出難易概念的情緒隱喻具有雙向性:
(1)積極情緒蘊含著容易信息,消極情緒蘊含著困難信息。
(2)容易概念承載著積極情緒,困難概念承載著消極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