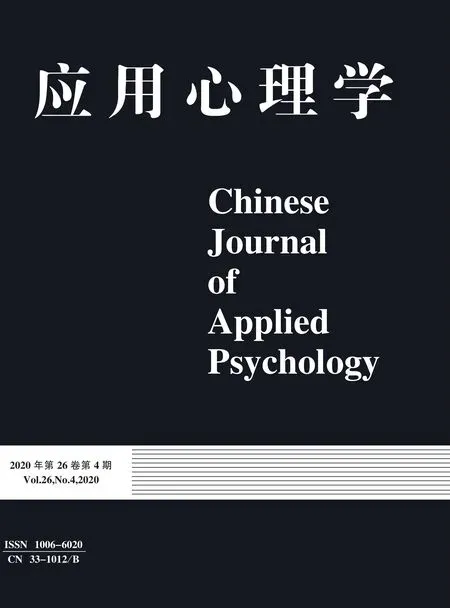“隨緣”對網絡公益平臺捐贈金額的影響
(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市場營銷學系,杭州 310058)
1 引 言
慈善捐贈對整個社會的發展有著無法取代的重要作用。如何募集到更多善款?前人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識別出了眾多影響因素:情境因素(Ferraro,Shiv,& Bettman,2005)、特定的捐贈媒介(捐錢 vs.捐時間)(Liu & Aaker,2008)等。這都屬于“以小撥大”:對選擇架構進行微小的調整和設計,使決策者的行為發生預期的改變,增加個人福祉,甚至推動社會的巨大變革(何貴兵,李紓,&梁竹苑,2018)。
以往研究大多考察線下的捐贈情境(Andreoni,Rao,& Trachtman,2017;Dana,Cain,& Dawes,2006;Simpson,White,& Laran,2018)。但是,隨著互聯網技術和移動支付技術的普及,網絡公益平臺逐漸興起,為公益事業的發展增添了力量,同時也向學術界拋出了更多問題。網絡平臺可以實現很多線下募捐無法實現的功能。例如,眾多網絡公益平臺在捐款頁面推出了一項新的設置:金額隨緣(見附錄1)。人們可以通過按下“隨緣”鍵,得到一個隨機的捐贈金額,例如16元、66元等;這一金額并非固定,如果人們覺得不合適,可以再次按下“隨緣”,再次得到一個金額。
它能提升人們的捐贈金額嗎?本研究將重點考察隨緣對于人們的捐贈金額的影響。隨緣捐贈的設置降低了個體在捐贈行為中的主動性,這可能反而會降低人們的捐贈(Choshenhillel & Yaniv,2011;Handgraaf et al.,2008)。除此之外,隨緣設置可能對于不同個體的影響也不同。本研究對隨緣這種新興募捐模式進行了研究,結果對網絡公益平臺的設計具有非常重要的應用意義,是對親社會行為理論的豐富和延展。
1.1 隨緣與捐贈
傳統的捐贈平臺中,人們在了解捐贈的相關信息后,自行決定捐贈金額。這是一種“pay-as-you-want”的定價機制,通過提升消費者對交易的公平感知(Kim et al.,2009),它能使產品獲得更大的市場占有率(Schmidt et al.,2015),使消費者產生自我認同(Gneezy et.al.,2012)。
與傳統捐贈設計不同,隨緣捐贈的定價由系統隨機給出:人們按下“隨緣”鍵,網絡平臺隨機地提供一個捐贈金額。人們的主要決定權在于是否接受這一金額,如果不滿意,人們可以再次按下“隨緣”,再次隨機得到一個捐贈金額。根據傳統的控制感研究(Gurin,Gurin,& Morrison,1978),人們對事物的控制取決于兩個維度:一是個人主導性(personal mastery),即認為自己控制外界的能力強度;二是感知限制(perceived constraints),即感受到的阻礙他們實現目標的因素。在隨緣捐贈的情境下,盡管人們可以選擇反復按下“隨緣”鍵,但是由于系統生成金額的隨機性,個體的行為和行為的結果已經不存在直接聯系。也就是說,個體無法對捐贈金額進行主觀的控制,在隨緣捐贈的情境中感知到的個人主導性會更低。另外,隨緣捐贈直接限制了個體自行輸入捐贈金額的能力。個體不再像傳統的捐贈平臺那樣自主地決定并捐出一筆金額,而是只能通過按下一個按鍵,得到一個系統生成的金額。也就是說,個體在隨緣捐贈情境中有更多的感知限制。綜合來看,比起自行決定金額的傳統捐贈,捐贈人在隨緣捐贈中感受到的控制應該更低。
作為一種普遍存在的心理需求,控制感的降低會引起人們的不適;人們會進行一系列的行為以進行調節(Su,Jiang,Chen,& Dewall,2017)。特別地,當這一感知被剝奪,當務之急便是重建它。在這種動機的驅使下,人們會以自我為導向,更多地關注自我,尋求自我的價值(Mikulincer et al.,2005)。人們如果過于關注自我,對他人的注意力就會降低;當人們不再關注他人,人們的親社會行為便會減少(Campbell et al.,2004)。一系列研究表明,控制感在親社會行為中發揮了重要作用(Handgraaf et al.,2008)。例如,當人們不能感知到控制感時,人們在合作任務中給他人分配的金額便大幅度下降(Choshenhillel & Yaniv,2011)。聯系隨緣捐贈的設置,它降低了人們的控制感;當人們處于控制匱乏中,其注意力會被更多地導向自我。當人們不再關注那些需要幫助的捐助對象,不再感受到捐助對象所經歷的痛苦,人們的捐贈意愿也就有所下降,降低捐贈金額。即:
假設1:隨緣設置會降低人們的捐贈金額。
假設2:隨緣設置降低個體感受到的控制感,從而降低捐贈金額。
1.2 控制欲的調節作用
隨緣效應的強度取決于個體的控制欲(desire for control)水平。控制欲指人們對外界環境施加控制的欲望與動機,它驅動著人們的行為(Donnerstein & Wilson,1976)。但是,不同個體對控制的欲望存在著強弱差異,這一差異將帶來個體的不同表現(Parker,Jimmieson,& Amiot,2009)。Ashford和Black在1996年發現:新入職的員工會積極地進行“組織社會化”,變成組織的一員,獲得對組織施加控制的能力,從而滿足其控制需求;但是,當這些新員工的控制欲較低時,新環境造成的控制感匱乏也不再促進他們的組織社會化行為了。因此,個體在控制欲上的強弱差異將調節特定變量對個體產生的影響,控制欲較低的個體表現出來的控制尋求行為也會更弱。在捐贈情境中,“隨緣”的引入會降低個體的感知控制。對于高水平控制欲的個體,隨緣設置剝奪了他們在親社會行為中的控制,他們會降低捐贈金額;但是,對于控制欲較低的個體,他們控制外部環境的動機更低,即使缺乏對捐贈金額的主觀控制,他們也不會由此改變自己的關注導向,其捐贈金額也不會受到顯著的負面影響。即:
假設3:個體的控制欲可以調節隨緣對于捐贈的負面影響:對于控制欲高的個體來說,隨緣設置降低捐贈金額,但是對于控制欲較低的人,隨緣設置不影響捐贈金額。
2 實驗1
實驗1的目的在于驗證“隨緣”設置對個人捐贈的影響及其中介機制(假設1與假設2)。
2.1 實驗設計
本次實驗通過Qualtrics在線進行,來自國內某高校的121名學生參與了本次實驗。實驗為單因素(隨緣捐贈vs.控制組)組間設計。在捐贈決策前,被試被告知他們給出的捐贈金額將從實際報酬中扣除,因此,實驗反映了個體在真實捐贈情境下的真實捐贈行為,在實驗結束后,研究者根據被試給出的捐贈金額進行了實際的捐贈。
2.2 實驗流程
被試被隨機分配到隨緣捐贈組和控制組。閱讀完相同的捐贈材料后,被試進入捐贈決策。頁面顯示:參與此次問卷你將得到10元報酬,你愿意拿出多少進行捐贈?被試了解到:這是真實的捐贈,問卷的實際報酬將根據自己的回答進行折算,研究者會將他們選擇捐贈的金額轉交給慈善基金會。在控制組,被試需要在1元、2元至10元共10個金額選項中進行決策;此外,被試也可以選擇不捐贈,直接翻頁跳過。在這種情況下,被試捐出的金額將被記為0元。
而在“隨緣”組,被試看到的界面跟“水滴籌”網絡公益平臺的隨緣設置完全一樣。被試可以選擇“隨緣”或者選擇不捐贈。被試讀到,如果自己選擇“隨緣”,捐贈金額將從1—10元隨機生成。跟控制組一樣,被試也可以選擇不捐贈直接翻頁跳過。選擇不捐贈直接翻頁的被試捐出的金額將被記為0。如果被試按下“隨緣”,他們將進入“隨緣”模式。在下一頁里,被試會看得到一個1—10之間的隨機數字,表示系統隨機為被試生成的捐贈金額。這一設置由Qualtrics的Randomizer功能實現,數字在1—10之間隨機生成。在這個時候,被試可以選擇接受,捐出系統生成的X1元,或者再次點擊“隨緣”生成另外一個金額。如果被試選擇了接受,他將結束捐贈,捐出由系統生成的X1元金額,進入問卷的后續環節;而如果被試選擇了再一次點擊隨緣,在下一頁他將再次獲得數字X2(X2同樣由1—10之間隨機生成,與X1不存在聯系),面對這一捐贈金額,他們同樣可以自主地決定是否接受。這一循環將一直進行,直到被試決定接受系統生成的金額Xn,進行捐贈。被試在隨緣組最后接受的金額便是他們會捐出的金額。
捐贈環節結束后,被試進入中介變量“控制感知”的測量。結合實驗具體情境,題項由控制感知量表(sense of control,Lachman & Weaver,1998)改編而成,為“幫助小得鵬是我自己作出的決定”,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最后,匯報了自己的年齡和性別后,被試獲得了扣除捐贈金額的實驗報酬,未捐贈的被試領取了全額實驗報酬(10元),實驗1結束。
2.3 實驗結果
我們按照Oppenheimer,Meyvis,& Davidenko(2009)設置了一道對被試是否認真作答的檢測題目。共有12名被試沒有按要求答題,剔除后得到有效樣本109人(女性71人),M年齡=22.69,SD=4.03,其中隨緣組54人,控制組55人。
主效應: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顯示:與控制組被試相比,隨緣組被試的捐贈金額更低(M隨緣=3.22,SD=2.99vs.M控制=5.38,SD=3.96,F(1,107)=10.27,p=0.002,d=0.62,Bayes Factor10=17.8)。假設1得到支持:隨緣設置對捐贈產生了負面影響,造成了人們更低的捐贈金額。與控制組的5.38元相比,引入隨緣設置導致捐贈金額下降了40%。
中介效應: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顯示:與控制組被試相比,隨緣組被試的感知控制更低(M隨緣=5.54,SD=1.19vs.M控制=5.98,SD=1.03,F(1,107)=4.36,p=0.039,d=0.40,Bayes Factor10=1.40)。進一步采用Bootstrap方法來檢驗感知控制的中介作用(Preacher & Hayes,2004)。以捐贈金額作為因變量,是否“隨緣”作為自變量,感知控制作為中介變量,進行以樣本量為2000的Bootstrap中介檢驗(Hayes,2012;Preacher & Hayes,2004)。在95%的置信區間下,感知控制的中介檢驗結果匯總不包含0(LLCI=-0.99,ULCI=-0.06),效應量大小為-0.40,感知控制起到了中介作用,假設2得到了支持,見圖1。

圖1 隨緣、感知控制與捐贈金額的中介效應模型
實驗1證明了隨緣在捐贈金額上重要的主效應:相比控制組,隨緣組的被試給出了更低的捐贈金額:相比控制組的55名被試自行決定捐出的296元,隨緣組的54名被試一共只捐出了174元。隨緣設置對捐贈金額的削弱達到了41.22%。同時揭示了隨緣對捐贈影響的內在機制:隨緣降低了人們在親社會行為中感知到的控制,繼而降低了人們的捐贈金額。
3 實驗2
實驗2有兩個目的:一是更換公益項目的相關材料,考察在不同捐贈情境中“隨緣”設置對捐贈金額的影響;二是考察個體差異(假設3):對于控制欲水平不同的個體來說,隨緣的效應也有所不同。
3.1 實驗設計
實驗通過Qualtrics在線開展,來自國內某高校的105名學生參與了本次實驗。實驗為單因素(隨緣捐贈vs.控制組)組間設計。被試被告知,他們的捐贈金額將從實驗報酬中扣除,因此本實驗考察的是真實捐贈行為。研究者在實驗結束后將被試給出的捐贈金額捐給了相應的公益組織。
3.2 實驗流程
被試被隨機分配到隨緣捐贈組和控制組。同實驗1相似,在閱讀完捐贈材料后,被試被隨機分配到隨緣組和控制組完成同實驗1相同的捐贈金額決策。整個捐贈流程和實驗1完全相同。
之后被試填寫了控制欲(Desire for control)的測量。本實驗采用了Burger和Cooper(1979)的控制欲量表(DC scale)中的9個代表性條目,如“我更喜歡那些自己能夠控制時間和內容的工作”,該量表在實驗中表現出較高的內部一致性信度(α=0.72)。
最后,被試作答了同實驗1相同的認真檢查題項,匯報了自己的年齡和性別。實驗結束之后,被試獲得了扣除捐贈金額的實驗報酬,未捐贈的被試領取了全額實驗報酬(10元),實驗2結束。
3.3 實驗結果
按照與實驗1相同的標準,在刪除了6名沒有認真填寫的被試之后,得到有效樣本99人(女性66人),M年齡=22.81,SD=10.29,其中隨緣組52人,控制組47人。
主效應:以捐贈金額為因變量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跟實驗1一致:與控制組被試相比,隨緣組被試的捐贈金額更低(M隨緣=4.75,SD=2.91vs.M控制=6.15,SD=3.39,F(1,97)=4.87,p=0.03,d=0.45,Bayes Factor10=1.79)。假設1得到進一步支持:隨緣設置顯著降低了人們的捐贈金額,降低程度達到23%。
控制欲對捐贈金額的調節效應:參照(Spiller,Fitzsimons,Lynch,et al.,2013)檢驗控制欲和自變量對捐贈金額的交互影響。結果顯示,自變量和控制欲對捐贈金額的交互影響顯著,F(1,95)=6.261,p=0.014,η2=0.062,見圖2。當人們的控制欲較低(均值-1個標準差),隨緣對捐贈不存在顯著影響,β=0.24,t(98)=0.27;p=0.79;而當人們控制欲高(均值+1個標準差),隨緣顯著降低了人們的捐贈金額,β=-2.98,t(98)=-3.37;p=0.0011。假設3得到支持。

圖2 隨緣與控制欲共同影響人們的捐贈金額
實驗2再次證明了隨緣的消極效應(假設1):與控制組47名被試自行決定捐出的289元相比,隨緣組的52名被試僅僅捐出了247元,下降了14.53%;同時檢驗了隨緣對于捐贈的負面影響的邊界條件(假設3):對控制欲較高的人,隨緣降低了人們的捐贈金額;但是當人們的控制欲水平較低時,隨緣對捐贈不存在顯著影響。
4 討 論
本研究關注了網絡公益平臺的新現象:隨緣生成捐贈金額。通過兩個實驗考察了人們的真實捐贈行為,結果揭示:相比于控制組的自行決定捐贈金額,網絡公益平臺中的隨緣設置會導致人們捐出更少的金額,原因是它削弱了人們在捐贈中感知到的控制感。實驗1的隨緣設置減少了41.22%的捐贈,實驗2的隨緣設置減少了14.53%的捐贈。這個結果跟前人的發現一致:當人們被剝奪控制感時,會變得更加自我導向,減少對他人的關注(Campbell et al.,2004;Mikulincer et al.,2005),減少人們的捐贈行為(Choshenhillel & Yaniv,2011)。另外,本研究還發現了隨緣設置對捐贈的影響將受到個體差異的影響:對于控制欲較高的人,隨緣降低了他們的捐贈金額;但是對于控制欲較低的人,隨緣對他們的捐贈金額沒有影響。
本文首先揭示了“隨緣”在網絡捐贈中對個體捐贈金額的重要影響,填補了學術界的空白。這一類新興捐贈設置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它們對人們在捐贈過程中的認知、行為會產生怎樣的影響?為了提升個體的捐贈意愿,促進公益事業的發展,未來研究應進一步關注此類募捐方式。再者,本研究為隨緣對捐贈金額的影響識別了一個調節變量:控制欲。募勸方式產生的效果往往不是絕對的,它受到個體的權力距離信念(Han,Lalwani,& Duhachek,2017)、自我構念(Simpson,White,& Laran,2018)的影響。本研究同樣揭示了個人差異如何在親社會行為中發揮影響,對于控制欲較高的人,隨緣降低了他們的捐贈金額;但是對于控制欲較低的人,隨緣對他們的捐贈金額沒有影響。這一發現深化了對隨緣設置的理解;同樣也對親社會決策中個人差異的作用進行了強調,為未來相關研究提供了思路。第三,本研究識別了影響人們捐贈行為的新要素。現有的研究多從情緒(懷舊感,Zhou et al.,2012)、捐贈情境(Ferraro,Shiv,& Bettman,2005)入手。本研究著眼于現實生活中的新興勸募方式,從感知控制的角度證明了這一微小的改變如何影響人們的親社會行為,豐富了“以小撥大”的相關文獻(何貴兵,李紓,&梁竹苑,2018),有著重要意義。
本研究的實踐意義同樣豐富。隨緣會嚴重降低控制欲很高的消費者的捐助金額。一方面,平臺應該精準定位于控制欲較低的個體。另一方面,網絡捐贈平臺需要注意調控人們感受到的控制感,因為控制欲不僅是一種長期的個人差異,同時也會受到情境的影響。例如,在捐贈頁面中加入邊界和框架的設計,這可以提升人們的控制感(Cutright,2012)。通過確保人們的控制感,人們的控制欲便得以調控。另外,網絡的不流暢等情境要素也會造成人們的控制欲提升(Vanbergen & Laran,2016),進而強化隨緣的消極效應。
本研究為未來研究開拓了道路。在方法上,首先,為了控制其他干擾變量,本文的實驗數據全部源于高校學生。雖然大學生等年輕群體為網絡公益平臺的主要用戶,但為了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確保研究結論的普遍性,未來研究的樣本選擇可以更為多樣化。第二,為了對網絡公益平臺上的隨緣設置進行完全模擬,本研究中的隨緣捐贈均采用了“無限次觸發”設計,即隨緣組的被試可以無限次數地觸發隨緣鍵,最終得到一個捐贈金額;存在一種可能是當按鍵次數無限大時,被試可能反而從中感受到了控制感的增強,從而提高自己的捐贈金額。因此,隨緣設置的效應值得未來更多深入、細致的研究。在理論上,本研究中采用的捐贈訴求為金錢。不同的捐贈媒介下,隨緣是否會產生不同的效應?例如,前人發現當捐贈的是圖書、文具等產品時,人們會對捐贈人給出更高的道德好評(Gershon & Cryder,2018);物品的捐贈情境下,隨緣是否會促進人們的捐贈?再者,通過啟動時間的概念,人們的道德行為有所提升(Gino & Mogilner,2014),時間的隨緣捐贈是否能夠提升人們的參與意愿?未來的研究均可以對上述假設進行探索。其次,本研究著眼于捐贈設置在募集公益資金上的有效性,但是,這一類捐贈設置對捐贈人會產生怎樣的影響?人們常常會對捐贈行為進行躲避(Andreoni,Rao,& Trachtman,2017),在捐贈后產生消極情緒(Dana,Cain,& Dawes,2006)。隨緣設置是否可以緩解這一消極作用?最后,為了明晰隨緣設置對捐贈金額的影響,在本研究的實驗設計中,對于“隨緣”組的被試,“隨緣”捐贈是他們決定捐贈金額的唯一方式。但是,在實際的網絡公益平臺中,還有眾多與“隨緣”同時存在的設置,例如,人們可以選擇是否匿名捐贈;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時,人們的捐贈金額會發生怎樣的變化?考慮到個體決策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未來研究可以結合這一設置對更多有意義的變量、個人差異進行探索。綜上,網絡公益平臺的蓬勃發展向學術界拋出了更多的疑問,對這些問題的探索與解答將幫助有需要的人更快地募集到更多的資金與支持。
5 結 論
相比傳統的捐贈設置,網絡公益平臺中采用的“隨緣”設置會降低人們的捐贈金額。因為隨緣設置削弱了人們在捐贈中的感知到的控制感。另外,隨緣對于捐贈的負面影響只存在于控制欲水平比較高的消費者身上。而對于低控制欲的個體而言,“隨緣”對個體捐贈金額不存在顯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