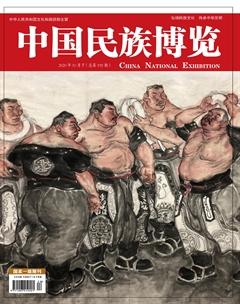《安東尼努斯敕令》對羅馬帝國埃及行省稅收制度的影響



【摘要】公元3世紀初,卡拉卡拉皇帝頒布了《安東尼努斯敕令》,將羅馬公民權授予帝國境內所有的自由民。從理論上講,帝國民眾政治身份、法律地位的變化會對埃及行省的稅收制度產生不可忽視的沖擊。然而,眾多考古資料證明,埃及行省的稅收制度并未受到太大的影響,土地稅與人頭稅這兩項主要稅種的征收制度基本沒有受到《安東尼努斯敕令》的直接沖擊,其他稅種也基本保持穩定。這種現象折射出了《安東尼努斯敕令》的頒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羅馬公民權的內涵。
【關鍵詞】安東尼努斯敕令;羅馬公民權;土地稅;人頭稅
【中圖分類號】k411 【文獻標識碼】A
一、緒論
公元212年,卡拉卡拉(Caracalla)皇帝頒布的《安東尼努斯敕令》(Constitutio Antonniniana,下文或簡稱“敕令”)把羅馬公民權賜予羅馬帝國境內的所有自由民。《安東尼努斯敕令》深遠地改變了羅馬帝國埃及行省的希臘人、埃及本地居民的政治身份與法律地位。奧古斯都皇帝開創的稅收制度大體可以分為直接稅與間接稅:直接稅分為土地稅(tributum soli)與人頭稅(tributum captis);間接稅有關稅、解放奴隸稅、遺產稅、營業稅、各種雜稅等。[1]納稅人的政治身份與稅收制度有著較強的關聯度,決定了其是否在某稅種的征收范圍之內是否享有優惠稅率。
從理論上講,羅馬帝國埃及行省所轄民眾大規模的政治身份、法律地位變化(獲得羅馬公民權)會對埃及行省的稅收制度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本文的主要觀點恰恰與之相反:由于羅馬帝國埃及行省具體情況的特殊性,《安東尼努斯敕令》帶來的納稅人身份變化并未對埃及行省的稅收制度產生較大的沖擊。敕令頒布后,埃及行省的稅制基本保持穩定,沒有因此而出現明顯的變化,稅收額度并沒有因敕令的頒布而明顯增加。
國內外目前尚未出現關于《安東尼努斯敕令》對羅馬帝國埃及行省稅收制度影響的專題研究,不過,一些國內學者們在相關研究中涉及了《安東尼努斯敕令》對羅馬帝國整體稅收制度的影響。厲以寧在《羅馬—拜占庭經濟史》一書中簡要提及了敕令對遺產稅的影響,認為擴大公民權的授予范圍增加了帝國遺產稅的收入,但并未對占據古代稅收絕對主導地位的稅種——土地稅與人頭稅(占稅收總額的90%以上)可能受到的影響發表觀點。[2]劉小青的《“安東尼努斯敕令”新論》作出了敕令并不能使皇帝有效增加物質收益的推測,雖然該推論與本文的觀點有一定的共通之處,但由于其文章主題的限制,其分析過程較為簡略,缺乏對帝國稅制的整體深入梳理與切實的史料支撐。[3]
國外學界在該主題周邊領域的研究成果較為豐碩,如關于《敕令》的公民權授予范圍的討論;埃及行省的基本稅收制度、社會結構、行政管理體制與改革。在埃及出土、經國外學者整理后發表的莎草紙文獻中,羅馬時期,埃及行省的稅收單據、財產申報書等相關史料非常豐富,其原文可以通過數據庫進行精確檢索。這些一手史料與國外學者的學術成果為本篇論文的研究提供了輔助。
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首先分析安東尼努斯敕令在羅馬埃及行省的實際公民權授予范圍,同時簡要描述埃及的社會經濟概況;然后在此基礎上結合學術成果與相關史料,通過前后史料對比,逐一分析各稅種所受的影響,對本文的中心論點進行論證;最后進行總結。
二、公民權授予范圍
本文的第一個任務是要研究清楚《安東尼努斯敕令》在埃及行省的實際公民權授予范圍。羅馬埃及行省的社會結構主要分為四個等級:第一等級是亞歷山大里亞市民與羅馬公民,二者地位與待遇相同,亞歷山大里亞市民擁有一定的自治權。第二等級是希臘城市(Greek cities)市民,其地位類似于亞歷山大里亞市民;第三等級是城市居民(Metropolites):亞歷山大里亞以外的埃及行省被劃分為40個地區(nome),每個地區擁有一個中心首府城市,中心城市管理周邊的鄉下區域,其市民屬于“城市居民”等級。與鄉下的埃及原住民相比,城市居民享有一定的特權,但地位不及羅馬公民、亞歷山大里亞市民和希臘城市市民,該等級的民眾直到2世紀末3世紀初才獲得自治權;第四等級是鄉村居民,他們大多數是埃及原住民,居住在城市以外的鄉村地區,基本沒有任何政治權利與經濟特權。不同的階級對應不同的稅種與稅收優惠(下文會詳細提及)。[4]因此,研究埃及行省的公民權授予范圍實質上就是研究哪些階級在安東尼努斯敕令頒布后獲得了羅馬公民權,哪些階級被排除在公民權授予范圍以外。
埃及Apollonopolites Heptakomias地區發現的P.Giss. 40號莎草紙文獻是研究該問題的重要史料,該文獻是一份法律文書,記載了卡拉卡拉皇帝頒布的3條敕令與1封書信選段。第一條敕令即為安東尼努斯敕令的原文。其原文由Paul M. Meyer教授于1910年整理發表。[5]F.M.Heichelheim在1941年的《埃及考古學雜志》(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上發表了P.Giss.40號文獻的英文譯本。關于公民權的授予范圍,敕令中是這樣描述的:“我宣布將羅馬公民權授予給羅馬世界除了被征服者以外的所有民眾。”(I grant,therefore,to all free persons throughout the roman world the citizenship of the Romans,no other legal status remaining except that of the dediticians.)[6]由此可見,《安東尼努斯敕令》在埃及行省的公民權授予范圍是“除了被征服者(dediticius)以外的所有人”。因此,搞清楚埃及行省“被征服者”的具體身份與定義是解決埃及行省公民權授予范圍這一問題的關鍵。根據蓋烏斯(Gaius)與李維等羅馬歷史學家、法學家的定義,“被征服者”沒有任何的政治權利,他們的命運完全任由羅馬人擺布。A.H.M.Jones認為,在被羅馬征服之初的短暫時間內,行省居民的身份是“被征服者”,當羅馬當局依照行省法(Lex Provinciae)授予他們自治權后,由于獲得了一定的政治權利,就不再是“被征服者”了。簡言之,享有自治權的行省居民不是“被征服者”[7]。3世紀初,塞普提米烏斯-塞維魯皇帝(Septimius Severus)改革了埃及的行政管理體制,在各城市建立了城鎮議會(boulai),授予地方城市以充分的自治權。但與此同時,廣大居住在鄉下的埃及原住民(the Egyptians)既沒有希臘化,也沒有羅馬化,他們并不屬于任何城市社群,沒有參與地方政務的權利,仍然直接向帝國官方承擔義務。由此可以做出推論:在《安東尼努斯敕令》頒布時的212年,埃及行省的城市居民獲得了自治權,因此已不再是“被征服者”,居住在鄉村的大量埃及原住民由于沒有獲得自治權,所以仍然保留了“被征服者”的身份。《安東尼努斯敕令》的公民權授予范圍只擴大到了城市居民一級,不附屬于城市社群,未獲得自治權的埃及原住民并沒有依法取得羅馬公民權。
帝國官方為何在“行省羅馬化”的大潮流中堅持將埃及原住民排除在城鎮議會、地方自治權之外,保持其“被征服者”的法律地位政治身份?為何限制埃及行省的公民權授予范圍,拒絕將公民權授予絕大多數埃及原住民?對于該問題有三種解釋,第一種觀點認為,埃及原住民難以管控,羅馬化程度有限,因此只能采取壓制性統治政策,不能授予其自治權,僅與埃及行省上層的希臘精英群體合作即可。古羅馬著名歷史學家塔西陀記載的奧古斯都皇帝的想法,可以用來解釋第一種觀點:奧古斯都認為,埃及是一個“難以進入、生產糧食、被教派紛爭與宗教狂熱所擾亂的省份,對法律與官員的權威一無所知”。第二種解釋主要從帝國統治者的經濟考量方面入手,主要觀點為:埃及是羅馬皇帝的私人領地,經濟地位極為重要,是帝國的兩大糧倉(阿非利加與埃及)之一,手工業發達,每年的東方貿易為帝國官方帶來巨額海關稅收(四分之一稅),埃及出產的糧食直接運往羅馬城,供應羅馬城的居民。埃及行省的社會是否穩定、皇帝對埃及行省的控制是否牢固直接關系到帝國的財政收入多寡與皇帝個人權威的穩固與否。奧古斯都將埃及列為皇帝的私人領地,明令禁止元老階級進入埃及,派出出身騎士階級的官僚掌管埃及的行政事務,限制地方城市的自治權利,通過種種手段將埃及行省的政治經濟大權與人口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奧古斯都后歷代皇帝均沿襲了他的壓制性政策。第三種觀點是從政治層面,即中央與地方的博弈為出發點來進行論述的,在某種程度上與第二種觀點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前文提到過,由于埃及行省在經濟上的重要性,羅馬皇帝們均延續了奧古斯都加強管制的埃及治理政策,就連在埃及行省建立城鎮議會,授予地方城市自治權的塞維魯皇帝也不例外,如果將鄉村地區的大量埃及原住民納入地方自治體的范圍之內,就會改變他們的法律地位,這些不再是“被征服者”的原住民便會向地方自治城市承擔一定的義務,享有一定的權利,羅馬當局對這些重要農業人口的控制力就會減弱,長遠來講會擴大埃及行省的地方權力,不利于皇帝們對埃及行省的全方位管控。
三、土地稅所受的影響
土地稅(tributum soli)是埃及行省的主要稅種。奧古斯都創立的埃及行省土地稅收制度將埃及行省的土地分為公有土地(ge demosia/ager publicus)和私有土地(ge idiotike/ager privatus),其余方面基本沿用了托勒密時期的稅制。[8]兩種類型的土地負擔不同的稅率。奧古斯都改革之后的私有土地主要有三種來源:一、托勒密時期的軍人安置土地(catoecic),該類土地在奧古斯都改革后可以隨意買賣;二、私人購買的國有土地(羅馬公民、希臘城市居民metropolites享有優先購買權,埃及本地鄉下人無權持有私有土地);三、托勒密時期的少部分神廟地產,其耕種者為本地佃農。[9]根據Rowlandson與Monson等學者的研究,羅馬統治時期的大部分埃及土地屬私人所有。與公有土地相比,私有土地享有較為低廉、穩定的稅率——1阿爾塔巴(artaba,干量單位,1阿爾塔巴約等于27.13L)稅[10],雖然每年的稅率根據尼羅河的泛濫程度會有所差別,但基本穩定在一定的范圍之內,即每阿羅拉(aroura,面積單位,1阿羅拉約等于2756.5m2)的土地需要繳納的實物稅在1~2阿爾塔巴之間,波動較小,約等于全部收成的10%~20%。[11]南埃及出土的一份公元45年的土地調查書記載,當地78%的土地為征收1阿爾塔巴稅的私有土地,在這78%的土地中,56%的稅率為1阿爾塔巴/阿羅拉,21%的稅率為四分之三阿爾塔巴/阿羅拉。[12]私有土地的稅收存在著一些土地持有人的政治身份帶來的例外,主要有二:第一個特例是亞歷山大里亞公民與羅馬公民在除亞歷山大里亞城市所轄區域以外的其他地區持有的部分私有地產享有一定的稅收優惠,城市市民(metropolites)所持有的部分私有地產也有一定的稅收優惠,但優惠程度不及羅馬公民。在Thmuis(Mendesios)地區出土的P.Ryl.2 216號文獻記載了當地一份二世紀晚期的土地稅收普查清單,其中記錄到對亞歷山大里亞公民(Alexandrians)收取2德拉克馬的優惠稅率,對城市居民(Metropolites)收取3德拉克馬的優惠稅率。亞歷山大里亞公民權與羅馬公民權享有相同的特權,[13]因此可以作出羅馬公民同樣享有土地稅收優惠的推論。第二個特例是亞歷山大里亞周邊的城市直轄領地完全由其市民持有,免于向羅馬當局繳納土地稅。公有土地(ge demosia,/ager publicus)主要分為國有土地、皇家土地(ge basilike)與部分神廟地產(hiera ge),由世俗當局/神廟祭祀租給被稱為demosioi georgoi的當地佃農(即埃及本地人)耕種,大多數的神廟土地被當作普通的公有土地進行管理,少數神廟土地的地位等同于私有土地。[14]與私有土地低廉且穩定的稅率相比,公有土地的稅收負擔沉重且多變,其具體稅收額視每年的年景而定,類似于西西里的什一田的制度,由每年一次的財產審查(census)核算稅額。公有土地的具體稅率介于2阿爾塔巴/阿羅拉至5阿爾塔巴/阿羅拉之間,上限與下限差距大,約等于全部土地收成的20%~50%。[15]關于土地稅的支付形式,由于通貨膨脹嚴重,塞維魯王朝后(212年前后)實物支付占絕對主導。[16](g p99 100)總的來說,羅馬埃及行省的土地稅收制度的基礎是土地的所有制類型(公有還是私有),公有土地稅率遠高于私有土地,同時,私有土地持有者的政治身份會帶來一些額外的稅收優惠。
以上為筆者對埃及行省土地稅收制度的梳理,下面結合史料證據研究《安東尼努斯敕令》對埃及土地稅收制度的實質性影響。
Arsinoites地區出土的P.Cair.Isid.11號莎草紙文獻是一份稅收單據,收錄了公元308—309年當地兩個村莊(Karanis與Horiodiktia)的稅收狀況,[17]Roger S.Bagnall將其中的數據初步整理發表。[18]根據筆者的進一步翻譯、整理與計算,Karanis的公有土地面積為717.83阿羅拉,公有土地收取的總稅額為1448阿爾塔巴的小麥,合2.02阿爾塔巴/阿羅拉(小麥);Karanis的私有土地面積為480.63阿羅拉,私有土地收取的總稅額為1189阿爾塔巴大麥(即644阿爾塔巴小麥),合1.34阿爾塔巴/阿羅拉(小麥)。Horiodiktia的公有土地面積為1288.83阿羅拉,公有土地的稅收總額為3079阿爾塔巴,合2.39阿爾塔巴/阿羅拉(小麥);Horiodiktia的私有土地面積為1731.69阿羅拉,私有土地的稅收總額為2526阿爾塔巴大麥(即1368阿爾塔巴小麥),合0.79阿爾塔巴/阿羅拉(小麥)。這份稅收收據記錄的公私土地稅率差距基本與奧古斯都稅制相吻合,直接證明了 “公有土地遠高于私有土地” 這一根據土地所有制類型進行差別化征收的稅率一直延續到了《安東尼努斯敕令》頒布后幾十年的四世紀。




(二)入境稅
埃及行省的另一大主要財政收入來源是東方貿易的商品入境稅(稅率為25%,故又稱四分之一稅)。[30]埃及行省的紅海—印度國際貿易非常繁榮,每年從印度次大陸安全返回埃及紅海沿岸各港口的商船不少于100艘,可能超過200艘。據斯特拉波記載,每年從埃及紅海沿岸的米奧斯-赫耳墨斯港一地駛向印度的商船就多達120艘。每年紅海貿易進口商品在亞歷山大里亞的售價可能超過10億塞斯特斯。繁榮的紅海貿易為羅馬當局帶來了巨額的財政收入。據鄧肯·瓊斯估計,奧古斯都時代埃及每年從紅海貿易中可獲得至少7740萬塞斯特斯,約占埃及年財政總收入的30%。《安東尼努斯敕令》的頒布完全沒有影響到該項稅收。[31]
(三)其他
其他諸如1%消費稅、關稅、釋奴稅、營業稅、商品稅、拍賣稅、王冠金等稅的征收與納稅人的法律地位、政治身份沒有關系,不受安東尼努斯敕令頒布的直接影響。
六、結語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安東尼努斯敕令的公民權授予帶來的政治身份、法律地位的變化并沒有理所當然地明顯影響埃及行省的稅收制度。敕令頒布后,原有的稅收制度基本保持穩定;羅馬公民先前所享有的稅收優惠(如上文分析中提到的羅馬公民免繳人頭稅、土地稅的優惠稅率等特權)反而消失了。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這要聯系當時的時代背景進行分析。《安東尼努斯敕令》頒布不久后,帝國就進入了戰火紛飛、政局動蕩的“三世紀危機”,經濟蕭條,軍費暴漲,財政危機日益嚴重。在此背景下,未受戰火侵襲的埃及行省對帝國財政收入的重要性便越發凸顯。從理論上、法律上來講,擴大埃及行省的羅馬公民權授予范圍會使得納稅人減少,擴展稅收優惠、稅收特權,進而會影響到埃及行省的稅收總額,進一步加劇帝國的財政危機。總之,收足稅額是統治者的剛需,擴大公民權的授予范圍便會與之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統治者會做出什么樣的選擇是不言而喻的。
同時,羅馬公民稅收減免特權的消失與學術界的一個通行觀點不謀而合,從經濟稅收領域佐證了該觀點:《安東尼努斯敕令》廣泛授予羅馬公民權的做法使得羅馬公民權失去了以往的意義,“羅馬公民”的身份不再是特權階級的象征,不再附有相應的政治經濟特權,不再是社會階層劃分的標志。羅馬公民失去了投票權、上訴權等政治權利,同時也失去了稅收減免這一經濟特權。正如羅斯托夫采夫在其著作中所說的:“《安東尼努斯敕令》把羅馬公民資格賜給了每一個人,賜給了形形色色的人,反而使羅馬公民權失去了重要性。于是“羅馬公民”便僅僅只是一個稱號了,它成了整個羅馬帝國任何一個居民的同義語。”[32]
參考文獻:
[1]王三義.古羅馬“賦稅名目”考略[J].史學月刊,2002(6):87-92.
[2]厲以寧.厲以寧經濟史文集第2卷羅馬-拜占庭經濟史上[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3]劉小青.“安東尼努斯敕令”新論[J].世界歷史,2013,(6):91-107,159
[4]Bowman A K,Rathbone D.Cities and administration in Roman Egypt[J].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1992(82):107-127.
[5]Griechische Papyri im Museum des Oberhessischen Geschichtsvereins zu Giessen[M].BG Teubner,1912.
[6]Heichelheim F M.The text of the Constitutio Antoniniana and the three other decrees of the emperor Caracalla contained in Papyrus Gissensis 40[J].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1941,26(1):10-22.
[7]Jones A H M.Another Interpretation of theConstitutio Antoniniana[J].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1936(26):223-235.
[8]Rathbone D. Egypt,Augustus and roman taxation[J].Cahiers du Centre Gustave Glotz,1993(4):81-112.
[9]Monson A.Rule and revenue in Egypt and Rome:political stability and fiscal institutions[J].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Historische Sozialforschung,2007:252-274.
[10]Wallace S L.Taxation in Roman Egypt[J].1938.
[11]Rathbone D. Egypt,Augustus and roman taxation[J].Cahiers du Centre Gustave Glotz,1993(4):81-112.
[12]Bell,Harold Idris,and Walter Ewing Crum. Greek Papyri in the British Museum.Vol.3.[M].British museum,1907.
[13]John de Monins,Martin Victor,Hunt Arthur S.P.Ryl.II.216[DB/ OL].http://papyri.info/ddbdp/p.ryl;2;216,2020(6):18
[14]Connor A J.Temples as Economic Agents in Early Roman Egypt:The Case of Tebtunis and Soknopaiou Nesos[D].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2015.
[15]Rathbone D. Egypt,Augustus and roman taxation[J].Cahiers du Centre Gustave Glotz,1993(4):81-112.
[16]MacMullen R.Some tax statistics from Roman Egypt[J]. Aegyptus,1962,42(1/2):98-102.
[17]Boak,Arthur E.R/Youtie,Herbert Chayyim,P.Cair.Isid.11[DB/ OL].http://papyri.info/ddbdp/p.cair.isid,11,2020(6):23.
[18]Bagnall R S.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taxation in later Roman Egypt[J].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1974-),1985(115):289-308.
[19]Vitelli,Girolamo,P.Flor.1 50[DB/OL].http://papyri.info/ ddbdp/p.flor;1;50,2020.6.28
[20]Bowman A K. Papyri and Roman Imperial History,1960-75[J].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1976(66):153-173.
[21]Evans J A S.The poll-tax in Egypt[J].Aegyptus, 1957,37(2):259-265.
[22]Bell H I.The constitutio Antoniniana and the Egyptian polltax[J].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1947(37):17-23.
[23]Sansoni,Matilde,PSI.3 164[DB/OL].http://papyri.info/ddbdp/ psi;3;164,2020.7.1
[24]Preisigke,Friedrich,SB.I 5677[DB/OL].http://papyri.info/ ddbdp/sb;1;5677,2020.7.8
[25]Zereteli G.,Jernstedt,Peter V,P.Ross. Georg.5 20[DB/OL]. http://papyri.info/ddbdp/p.ross.georg;5;20 2020.7.3.
[26]Krebs,Friedrich,BGU 2 667[DB/OL].http://papyri.info/ddbdp/ bgu;2;667 2020.7.8.
[27]Jouguet P.La vie municipale dans lEgypte romaine[M]. Fontemoing et cie.,1911.
[28]Frank R I. Ammianus on Roman taxation[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1972,93(1):69-86.
[29]Sherwin-White A N.The roman citizenship[M].Clarendon Press,1987.
[30]Fitzpatrick M P.Provincializing Rome:the Indian Ocean trade network and Roman imperialism[J].Journal of World History,2011:27-54.
[31]陳思偉.埃及與印度次大陸的海上貿易及其在羅馬帝國經濟中的地位[J].歷史研究,2018(1):113-133
[32]羅斯托夫采夫.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 下[M].商務印書館,1985.
作者簡介:常源遠(2000-),男,漢族,河南濮陽人,本科,研究方向:世界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