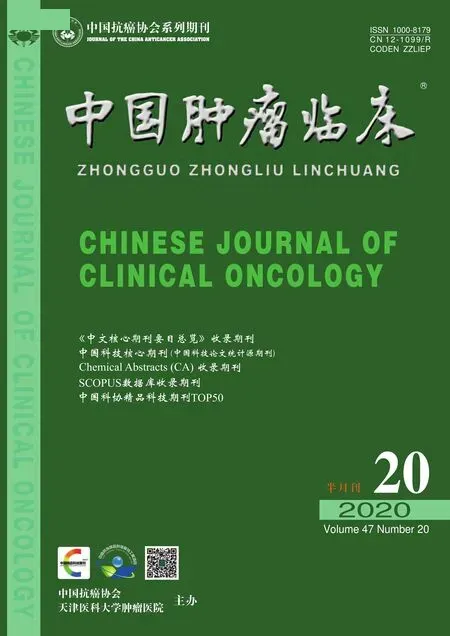腫瘤模型研究進展及應用
陳瑩瑩 吳玉亮 綜述 程忠平 審校
隨著國內腫瘤發病率和死亡率逐年攀升,腫瘤成為2010年以來的主要死因,是我國一個重大的公共衛生問題[1]。由于目前的腫瘤研究模型尚未模擬體內腫瘤,臨床前的治療研究與臨床研究結局往往存在較大差距。構建理想的腫瘤研究模型為目前腫瘤研究領域的重點之一。目前,腫瘤模型包括自發瘤模型、動物誘癌模型、人源性腫瘤細胞系(patientderived tumor cell lines,PDC)、人源性腫瘤異種移植物(patient-derived tumor xenograft,PDX)、多細胞腫瘤球體模型和腫瘤類器官模型。PDC 在無限傳代的過程中,基因組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改變,且基于平面培養體系建立起來的腫瘤平面模型缺乏原始腫瘤的結構、異質性及腫瘤基質間的相互作用,從而限制了細胞系作為臨床前模型的潛力[2]。PDX 的缺陷為培養時間長、成瘤率低、早期發生克隆選擇[3]而改變了原始腫瘤的異質性,尚不能作為腫瘤研究的理想模型。隨著3D培養技術逐漸成熟,建立了腫瘤3D培養模型,包括腫瘤懸浮球模型和腫瘤類器官模型。這兩種模型不僅模擬了原始腫瘤的生長環境,而且很好地模擬了細胞-細胞和細胞-基質間的相互作用。但腫瘤懸浮球因其穿透性差、成像困難、藥物篩選時的差異性大,從而限制了其在腫瘤研究方面的應用[4]。類器官作為最新的腫瘤研究模型,具有培養簡單、成瘤率高、適合高通量藥物篩選和遺傳操作等優點,并且在最大程度上維持了原始腫瘤的結構和異質性,在腫瘤研究領域已大規模應用[5]。隨著類器官在藥物篩選領域的應用,臨床上針對患者的個體化藥物成為現實,進一步推動了精準醫療的發展[2]。
1 動物誘癌模型
在動物身上誘發出與人癌相類似的惡性腫瘤,稱為癌模型,其目的在于獲得與臨床相對應的基礎資料。動物誘癌模型是利用致癌物在動物模型體內誘發癌變的模型,如大腸癌、膀胱癌、口腔癌、肺癌、食管癌、胰腺癌、肝細胞癌和乳腺癌等[6]。王玉民等[7]使用wistar 大鼠研究了238钚誘發骨肉瘤及其劑量-效應相關模式,建立了穩定的骨肉瘤實驗動物模型,并從骨肉瘤組織中,分離出骨肉瘤細胞系,建立了穩定的瘤細胞模型,組成了完善的骨肉瘤模型系統,提示在工業作業中向空氣排放的有毒物質,可以導致骨肉瘤,威脅著人類的健康。動物癌模型的建立為環境和食物誘導癌癥的防治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并且也為癌癥的一級預防提供了方向[6]。
2 腫瘤細胞系模型
腫瘤細胞系是利用患者的腫瘤組織,在平面培養體系下建立起來的一種平面永生化細胞模型,具有易于構建、培養周期短、存活率高,能夠進行高通量藥物篩選的優點[5]。在20世紀70年代,有研究建立了第一個人類永生細胞系即HeLa宮頸癌細胞系。隨著細胞遺傳學、2D培養體系等技術的不斷完善,細胞系作為應用最為方便、高效的腫瘤模型被廣泛應用[8]。
隨著研究的深入,細胞系模型的缺點也逐漸顯露出來。在2D 培養條件下,由于缺乏腫瘤組織的免疫微環境和血管網絡系統,細胞系模型并不能維持原始腫瘤細胞的遺傳表型和遺傳異質性,而且不能重現原始腫瘤組織的形態及功能[8]。隨著腫瘤研究的深入展開,細胞系模型已逐漸不能滿足研究人員的需求,與原始腫瘤更為相似的腫瘤模型成為了腫瘤研究的必備選項。
3 腫瘤異種移植物模型
PDX 是指將患者來源的腫瘤組織直接移植(原位或異位)到免疫缺陷的動物體內而得到的異種移植物。由于直接取腫瘤組織進行移植,腫瘤細胞及其細胞基質可以很大程度的保留下來,所以PDX 可以較大程度上維持原始腫瘤的異質性以及腫瘤與其周圍基質間的相互作用,目前已用于臨床前藥物評估和生物標志物的鑒定[9]。
早在1775年,人類便嘗試著將腫瘤組織移植到動物體內。之后,Toolan[10]研究證明了人類的腫瘤細胞能夠在輻射過的小鼠和大鼠體內生長。此外,當X射線輻射過的宿主用免疫系統抑制因子可的松治療時,腫瘤組織的增殖能力顯著增加。隨后,Phillips等[11]使用抗淋巴細胞的血清治療宿主小鼠,尤其當與胸腺切除聯合使用時,PDX 的存活比例會大大增加,這表明抑制免疫反應可以提高移植效率。
此后,免疫缺陷的小鼠模型也逐漸建立,使得腫瘤組織的移植效率大大增加。嚴重聯合免疫缺陷(severe combined immunodificiency,SCID)小鼠、非肥胖糖尿病/重癥聯合免疫缺陷(non-obese diabetes/severe combined immunodificiency,NOD-SCID)小鼠等免疫缺陷小鼠模型被廣泛用于腫瘤研究,使得PDX臨床前模型的研究得到了飛速發展[12]。各種惡性腫瘤的PDX臨床前模型也相繼建立,包括結直腸癌、胰腺癌、乳腺癌、肺癌、皮膚癌、頭頸部腫瘤、前列腺癌和卵巢癌[13]。然而由于移植時并不能將整個腫瘤組織移植到小鼠體內,免疫缺陷小鼠所培養的腫瘤移植物可能無法捕獲原始腫瘤組織的全部遺傳特性[14],與原始腫瘤仍具有一定的遺傳差異性。
Morgan等[5]與對原發性非小細胞肺癌的PDX進行突變數的檢測發現,僅有43%的突變被檢測到,并且在PDX早期傳代中發現4個原始腫瘤中不存在的突變,提示克隆選擇和突變可能發生在腫瘤組織植入小鼠的早期過程中。因此,PDX尚未完全模擬體內腫瘤。除此之外,PDX移植成功率仍然非常有限,在不同癌癥中差異很大[15]。且PDX的周期往往較長,遺傳操作困難,造模成本往往非常高。研究者們期待成功率更高、周期更短、性價比更高、與體內原始腫瘤更為相似的腫瘤模型(表1)。
4 腫瘤3D培養模型
近年來,研究者們建立了一種3D培養系統,將細胞引入一個多孔生物相容性支架中[16],使細胞能夠脫離平面而懸浮培養,以3D 的方式進行生長。體外3D 培養體系包括頂部矩陣、矩陣嵌入、矩陣封裝、自旋器燒瓶、微型圖板、超低吸附板、懸掛滴、磁懸浮和磁性3D打印等[4]。3D培養模型可分為全動物和器官外植體培養(包括胚胎)、細胞球體、微載體培養和組織工程研究模型,目前用于廣泛的細胞生物學研究,包括腫瘤生物學、細胞黏附、細胞遷移和上皮形態的發生[17]。腫瘤3D 培養模型的建立,使腫瘤的治療方法變得更為具體和個性化[18]。與2D 培養系統相比,3D 培養系統模擬了原始腫瘤的生長環境,使得腫瘤細胞可以由一種細胞或多種細胞形成腫瘤球體模型,從而更好地模擬了細胞-細胞和細胞-基質間的相互作用[19]。目前,常見的腫瘤3D 模型包括多細胞腫瘤球體(multicellular tumor spheroids,MCTS)模型和腫瘤類器官(patient derived tumor organoids,PDO)模型。
4.1 多細胞腫瘤球體模型
多細胞腫瘤球體模型(multicellular tumor spheroids,MCTS)是將患者來源的組織和細胞進行物理和酶促解離,形成單細胞懸浮液,然后將獲得的單細胞懸浮液在在具有無血清培養基的低附著板中培養,形成多細胞腫瘤球體模型。該低附著板是由于覆蓋一層薄層惰性底物(瓊脂、瓊脂糖或聚甲基丙烯酸羥乙酯(hydroxyethyl methacrylate,HEMA),使得細胞與培養皿之間的黏附性降低,促進了細胞與細胞之間的聚集和緊密生長,從而形成能夠懸浮生長的多細胞腫瘤球體[20]。
MCTS被廣泛用于腫瘤細胞的代謝[21]、侵襲和轉移[22]及腫瘤相關信號通路[23]、抗癌藥物的篩選[24]等研究。雖然腫瘤球體模型作為3D培養模型的先驅曾被廣泛應用,但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一方面,球體尺寸和均勻性一致性差,光散射差異以及抗體穿透性差,其成像困難,且用于藥物篩選/敏感實驗時差異性較大,限制了應用;另一方面,由松散排列的細胞形成的球體處理難度高,極易碎裂[4],操作難度高,不適合用于大規模實驗。更重要的是,腫瘤球體模型雖然空間上很大程度模擬了原始腫瘤的三維結構,但仍缺乏腫瘤微環境與免疫系統的相互作用,限制了腫瘤球體模型在腫瘤研究中的應用。因此,類器官模型研究應運而生。
4.2 腫瘤類器官模型
類器官是指成體干細胞或胚胎干細胞在體外3D培養體系下,自組裝形成能夠反映原始組織(成體干細胞來源)或定向分化組織(胚胎干細胞來源)特性的具有3D結構的組織類似物[25]。在特殊的培養條件下,腫瘤類器官模型能在一定程度上模擬腫瘤微環境,為腫瘤的體外研究提供了與體內環境更為相似的研究平臺(圖1)。

表1 常見的腫瘤模型之間的比較

圖1 卵巢癌類器官的培養過程
早在2009年,有研究通過在Lgr5+干細胞的Matrigel中加入R-spondin-1、表皮生長因子(epithelial growth factor,EGF)和Noggin,成功建立了mini-gut類器官培養體系[26]。在此培養體系基礎上建立了成體干細胞來源的、能夠自我更新、增殖并分化形成后代所必需的信號轉導因子的小腸類器官。類器官在正常組織上的成功嘗試與應用,使得類器官培養技術在腫瘤研究領域也快速發展,如結腸、胰腺、前列腺、乳腺、胃、肺、食管、膀胱、卵巢、腎臟、肝臟等腫瘤組織[13]。這些腫瘤類器官均具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征,能夠部分或完全重現原始腫瘤的異質性[27],非常適合用于腫瘤研究。
Kopper 等[28]團隊利用不同患者的卵巢癌組織分別培養了卵巢癌類器官,測序結果表明不同來源的卵巢癌類器官之間存在異質性。隨后該研究使用卵巢癌化療方案中常用的鉑/紫杉醇類和非鉑類藥物測試化療藥物對患者來源的卵巢癌類器官體的敏感性,結果表明不同患者來源的卵巢癌類器官的藥物反應是存在明顯差異的,這與臨床治療中的個體差異相契合[28]。這提示類器官非常適用于精準醫療,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解決由于個體差異而出現的不同患者對同一治療方案的顯著差異化問題,改善患者的預后[2]。源自患者的腫瘤類器官可用于高通量藥物篩選和藥物敏感試驗,為個體化治療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為精準醫療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依據。
類器官在腫瘤機制研究也中有著較大的價值。腫瘤的發展是一個高度動態的過程,其突變通常因腫瘤細胞快速DNA復制而累積,包括染色體不穩定、微衛星不穩定以及表觀遺傳修飾的變化[2]。由于腫瘤的病因復雜、在發展的過程中受到多種因素的調控,所以應從多角度出發,對其發生機制進行研究,尤其是分子層面,如腫瘤的基因調控與信號轉導。采用CRISPR-cas9介導的基因工程地在健康的人來源的結腸組織類器官上成功逐步重現了腺瘤-癌的發生發展過程[29-30],在腫瘤類器官上看到了巨大的研究價值。目前,研究證實結直腸癌的發生和WNT、TGFβ、TP53、PI3K/MAPK通路的突變有關[29]。后續的研究證實,這一系列的致癌突變能有效促進結直腸癌的生長、轉移和定植[31]。
5 結語
目前,常用的腫瘤研究模型是PDC 和PDX,但因PDC 缺乏原始腫瘤的異質性,PDX 培養周期長、成瘤率低,應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3D 培養模型的建立為腫瘤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體外3D 培養技術的產物更能模擬原始腫瘤的生長環境和形態,然而MCTS 因穿透性差、成像困難,而限制了其發展。腫瘤類器官作為一個新興腫瘤研究模型,為腫瘤研究提供了新的平臺。因其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腫瘤異質性,并能長期傳代和冷凍保存,而被廣泛用于腫瘤機制、精準醫療等領域的研究。但類器官仍存在局限性,且尚不能完全模擬腫瘤細胞與基質間的相互作用,也缺乏脈管系統,與體內腫瘤環境還有一定差距。隨著精準醫療的逐步發展,相信腫瘤類器官能進一步發展,更大程度上模擬體內腫瘤,成為腫瘤個體化治療的有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