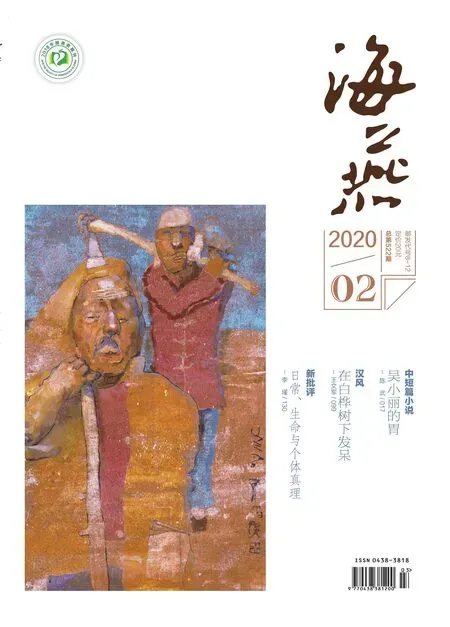詩的戰神和語言的穿墻術
—— 讀趙瓊的軍旅詩歌
文
我對軍旅詩歌一直知之甚少,直到細讀趙瓊的詩歌,我才對這一題材有了具體的認識。趙瓊多用革命浪漫主義的筆法來表達對守衛和平者的禮贊,尤為可貴的是,他的詩歌沒有美化戰場,沒有粉飾死亡,沒有矮化敵人——他筆下的軍旅生活,真實、殘酷。
而最為重要的是,盡管趙瓊一生戎馬倥傯,翱翔于祖國的藍天,但他并不宣揚戰爭:暴力不是目的,反暴力才是初衷。
托爾斯泰將狄更斯的“勿以暴力抗惡”思想和雨果的“道德自我完善”內涵融進宗教當中,并徹底否定暴力革命的合理性。或許是受到諸多人道主義思潮的影響,趙瓊用詩歌對 “人”的生命價值與意義,對人道主義做出了有益探索。
詩的戰神:不是花紅,便是血紅
“在他的面前,所有的出路/都是出征。/在他的身后,不是/花紅/便是血紅。”(《戰神》)
這是一首凝練的短制,也是一首英雄的贊歌。它選擇了最經典的英雄模式,即“英雄之旅”的結構,用英雄(戰神)的出發——冒險——回歸的永恒脈絡,實現了令人震撼的心靈謳歌。這與《荷馬史詩》中奧德修斯的偉大履跡并無二致,卻一語中的,更顯悲壯。詩歌中的戰神和古希臘英雄奧德修斯是一樣出發的,作為戰士特別是英雄(戰神),出征是他們唯一的選擇和神圣的出路。“冒險”即是戰爭,在這首詩歌里被省略,但讀者可以根據“花紅”“血紅”,感知冒險(戰爭)的殘酷——它不比奧德修斯的十年漂泊、九死一生溫和。古希臘英雄在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幫助下返回故鄉,而戰神只有在戰場上用生命的代價,才能實現英雄的回歸。
英雄之旅的第一階段,就是從“日常的世界”里出來。“故鄉”在他冒險的過程中常伴左右,即成為一個內心的羅盤,引導英雄回家,并在旅途中指引方向。但是,戰爭是最殘酷的冒險。上述戰神生死未卜,不成功便成仁,視死如歸——英雄之旅,在戰爭中更多地表現為“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悲壯:那天,隊伍就要從/村里開走/跪罷了爹娘和老屋/他沒回頭,也沒張口/一把戰刀,被他拎著/每走一步/都要在身后/一下一下地揮舞//二爺說,三爺那是在/自斷后路(《出征》)。
所有出征的英雄們,都像“三爺”一樣,頓悟了自己的命運,即解放暴政下的世界,并且毫不遲疑地接受自己的悲劇命運。他們明白,英雄必須拒絕“后路”的寬門,義無反顧地走進“前路”的窄門。三爺們放棄了他們在物質世界所擁有的,為了家園、土地和親人,他們完全奉獻了個人。
不過,英雄之所以成為英雄,戰神之所以成為戰神,在于“人”身上的神性被客觀現實激發,那是命運的安排,我們別無選擇。“其實,英雄/在沒有成為英雄之前 /一直生存在無聞之中/與你我一樣,隱于平日/一聲不吭”(《英雄》)
“誰都可以忽略/一個死者的來路/但一定得記住/一些英雄的/去處……”(《根本》)。英雄誕生于凡人,但最終,三爺們為了正義的理念情愿犧牲自己,成為趙瓊詩歌中的“戰神”。他們給同胞傳遞了訊息——獨立自主、勇氣和自決權。最終,這些英雄故事變作神奇的藥水和詩意的化身,成為啟發人對抗暴政并擺脫恐懼、自由且開放地生活的象征:“只有不忘鋼槍/英雄就不會啜泣//只有崇敬捍衛/江山才不會沉淪”(《條件關系》)。
語言的穿墻術:阻止一場戰爭的一群鳥
前文說過,趙瓊的詩歌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去思考戰爭中人的價值與作用,從而激發出自身對歷史進度的理解。他尊重客觀事實,拒絕簡單的臉譜化,沒有落入意識形態強行介入的窠臼,從而練就了語言的穿墻術。
趙瓊為了塑造英雄,為了表現真實,詩歌中不乏慘烈的戰爭場景,在展現戰爭的殘酷性上很有沖擊力:“面對一枚,飛來的炮彈/他一躍而起/他將自己的肢體,分給了/身后/那幾個活著的兄弟”(《戰友》);“那些被炸飛的野花/以及野草/在空中,時不時地就能看到/一些人的影子/從身邊/沖上了九霄……”(《又一場惡戰》);“在腦袋掉下的那一瞬/仍還往前的一些沖鋒”(《亂世間》)。
正因如此,和平才是文學永遠的訴求,“反戰爭、反暴力”才是趙瓊的寫作初衷。在《阻止一場戰爭的一群鳥》中,趙瓊敘述了這樣的事件:由于森林里的一群鳥受到驚擾而飛出,軍事行動被暴露,從而避免了一場戰爭。“埋伏者/被一群又一群鳥/一一揭露/不得不,把一枝又一枝鋼槍/扛出了森林”。
這群鳥,我們可以理解為希望的和平鴿,它們用神啟的方式,阻止了一場暴力的戰爭。
《在于都河畔,聽人講王香蘭殺雞》是一首情感渲染和人物塑造均真實自然的詩歌。王香蘭前后兩次殺雞的心理變化,生動地刻畫了一個普通勞動婦女的革命犧牲精神。“于都河面漣漪粼粼/多像是一碗雞湯上面,飄浮著的/一層又一層的油花”,這是詩人對“人”的精神的深情贊美。王香蘭的第二次殺雞是有人道主義內涵的,而詩人把于都河比作雞湯,是詩意在人道主義面前的又一次升華。詩人天性的悲憫是人道主義的一部分。
人道主義特別強調關心人的生命和基本生存狀況,關注人的幸福,強調人類之間的互助、關愛,重視人類的價值。“戰斗,在夜的最深處/出現了停頓/因為,夢被打碎/活著的人/誰也無法入睡”(《一場惡戰》)。戰爭打碎了人類向往和平的美夢,所有的“惡戰”,帶給人類的都是“噩夢”。戰斗出現停頓,使我們所期待的和平在夢境里得到了延續的可能。這才是詩人內心的真實袒露。
趙瓊也寫了很多類似戰場上的景物素描一樣的作品,這些作品用現實語境還原寫實的想象,使鮮血淋漓的客觀現實浮現出短暫而迷人的浪漫主義色彩:
“生長在營盤里的/一切苦樂/都會在月亮歇過的山坡上/坐胎,成果”(《一座營盤里的春天》);“即使在冬天,倒下去/戰地上的那些草/只要春風一吹,它們就會/在一剎那間,紛紛站立”(《戰地寫生》);“當寧靜收留了槍聲和硝煙/與落日一起,歸于黑暗/在信仰之河的兩岸/英雄們,枕著同一座江山/相對,無眠”(《戰事》)。
通過這些靜水流深的文字,通過語言的穿墻術,深受觸動的我們才從中意識到,一個人在戰爭中所要超越的不僅是生死,更是狹隘的世俗眼光;要贏得的不僅是戰爭,更是對心靈危機的拯救。
趙瓊寫過一首《穿墻術》:“在春天,沿一堵墻/走在墻外/總有一些花香,穿墻而來。//墓園的墻與墓壁一樣,有一些/虛妄/總有一些漏網的花瓣,無視生死/總想攜著我的影子/在月光下,一起飛翔……”
這首詩歌恰巧回答了我們對趙瓊詩歌的所有疑問:它是對死亡的歌頌,還是對新生的渴望?它是陷于現實的泥濘,還是翱翔于虛構的天空?像是花香可以穿墻而過,詩意的光芒也可以跋山涉水,穿越生死疲勞,讓靈魂有了飛翔的可能。
詩的戰神從來沒有遠去。語言的穿墻術,也是詩人通過與自己曠日持久的戰斗逐漸練成。
趙瓊說,“就像一把/經過了千錘百煉的好刀/磨礪之末/始見刀鋒……”(《說給誰聽》)。此句用來形容他對語言的追求也是相當貼切的。
我將趙瓊的詩歌視作一種切入現實境遇(比如戰爭)所導致的一場朝向歷史的迂回。這種境遇無疑包含了我們的集體記憶,具有真實感和人性意味。盡管戰神和戰爭被安放在特定的歷史場景之中,與真正的內心真實保持著一墻之隔,但是詩人的穿墻術,已經可以使之自由地穿梭在歷史、現實和未來之間。
于是,語言穿過現實的墻壁,成為花香;語言穿過睡倒的墻壁,成為礦藏;語言穿過虛構的墻壁,成為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