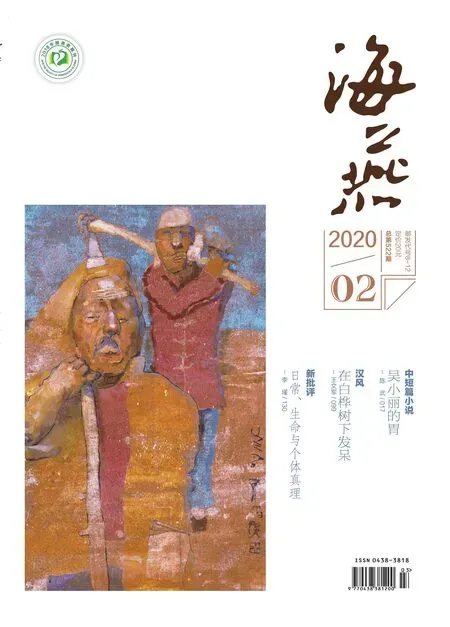日常、生命與個體真理
—— 談談施浩詩歌創作之“道”
文 ?
對于文壇而言,施浩是一個難以言說的存在。我曾試圖尋找一個合適的名目概括這個突然離場又突然現身的吟詠者到底負有何種使命,但一時之間難于定論。固然可以將施浩命名為“新歸來詩人”,但他的詩意一直如熊熊之火卅年不息;若然將其視為“非典型詩人”,他的詩歌卻表現為典型的“個體真理”。不管如何界定,施浩都是一個真正的詩人,一個優秀的歌者。總體而言,他的文本在保持對自我質問、對社會詰問的同時,提供了一個觀察詩歌藝術具體而微的窗口:如何書寫,才能獲得有價值的、永恒的和稱之為“詩”的東西。
由是,可能會引發海德格爾之問:“在唯一一位詩人的作品那里,我們竟能讀出詩的普遍本質嗎?”
一
《周易·系辭上》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百姓日用而不知。”“道”的偉大和其不可捉摸就在于其日常性,無處不在,無時不有,人們卻茫然不知。這種不知不是“愚”,而是融而化之的結果。有意思的是,詩歌之“道”卻被孔子抓住了。據《論語·陽貨第十七》記載:“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這里,切不可將詩歌當作目的性、工具性的東西。孔子認為,通過學詩,其精義可以內化為我們看待這個未知世界的一種觀念乃至價值體系。這個意義上,詩即人。通常我們將詩歌這種“純潔無邪的事業”看作語言的最高成就,但在突出語言的同時忽視了一個根本的問題,詩歌是人的自我吟唱,當詩歌被書寫出來,作者實際上是在進行自己的精神性構建:我和萬物乃至他人的區別,是底建于抒情性詞語基礎之上的。這個意義上,林語堂將詩歌看作是宗教的替代物,他說:“蓋宗教的意義為人類性靈的發抒,為宇宙的微妙與美的感覺,為對于人類與生物的仁愛與悲憫。宗教無非是一種靈感,或活躍的情愫。中國人在他們的宗教里頭未曾尋獲此靈感或活躍的情愫,宗教對于他們不過為裝飾點綴物,用以遮蓋人生之里面者,大體上與疾病死亡發生密切關系而已。可是中國人卻在詩里頭尋獲了這靈感與活躍的情愫。”換作海德格爾的話說,則是“人類此在在其根基上就是‘詩意的’”。
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理解施浩的離場和返場了。施浩在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詩歌創作,經由《人民文學》等刊物,他成功地將自己塑造成一個著名的后朦朧詩人,但當詩歌創作成績斐然之際,突然抽身離去,經過三十年的沉寂,又突然出現在詩壇之中,不僅寫詩,而且編詩,用一個中國最大開本和最豪華“裝飾”的《深圳詩歌》,引發詩嘯。個中轉變,若細讀其文本只有一種解釋,即無論他在場與否,詩歌都是無法剝離的命運,都是潛存在日常生活中用而不覺的“道”。也就是說,在千人一面的公共生活中和一個不需要詩歌的時代里,盡管詩歌和其他藝術一樣,處于非神圣化祛魅和世俗救贖的沖突而“一天天地減少自己的尊重”,①但施浩這個社會變革中最敏感的體驗者,因其詩人身份而“既是現代生活的熱心支持者又是現代生活的敵人”,仍以內心之筆描摹著這個眩暈而怪誕的世界。在《在圣母院的一張版畫上》一詩中,他這樣寫道:
頌歌在雨水中翻滾
生命、生命、生命
煉鋼的聲音
伐木的聲音
鮮血的聲音
收藏在青銅下的那只船上
銅呵銅呵銅呵
原來是一張廢紙上的圖紋
“在波德萊爾這里,現代生活內部有一種田園詩和反田園詩之間不可調和的張力。”而在施浩這里,詩歌不是一種修飾物,也不是一種即興消遣或一時的靈感,而是和生命緊緊連結在一起,通過非機械性的有機整合形成了肯定性反詰——我們所珍愛的生命是不是“廢紙上的圖紋”?這就進一步說明了詩歌的日常性,不是指它是一種須臾不可離的生活用品,或者說是我們念念有詞的頌歌或感嘆調,而是一種不可剝離的尊嚴,一種不可掩飾的氣質。由于“詩面對的始終是一個難以‘祛魅’的世界”,經由詩歌書寫,在詩人看來可以為現實世界提供一種解決方案。由此可知,施浩離場一定有生活不能承受之重。在西方幾百年和中國一百多年的現代敘事中,民族國家、世界市場、技術生產、大眾文化和消費社會粉墨登場,以“惡之花”的形態,詮釋著啟蒙現代性、審美現代性以及一種獨特的“社會生活和組織模式”的多元維度。我個人猜想,當商業力量日益顯著,欲望蓬勃發展,施浩無疑要在詩歌之外探索肉身的立足之地。一旦他突然意識到,人必須用詩歌的性情和慈悲來與世界對話,他就會將詩歌找回來—— 回歸詩歌的過程,也是回歸自然、回歸自我的過程。
沒有一種藝術樣式比詩歌能讓人感覺離自己更近。
二
這里,不妨讀兩節施浩的詩歌。一節選自《星辰》:
列車行進夜幕
夜幕是一條很深的隧道
隧道里也有星星
星星不是摹造的
是永生的
星星離你很近
可以交談
可以伸手去握
她贈你一雙明亮的眼睛
讓你穿越無奈的憂愁
走出這片靜靜的土城
一節選自《清明節》:
我穿過這一年的冬天
本來
冰雪覆蓋了我整個老家的大地
那些低矮的土屋
一小塊塊禾園和茅舍
在我事隔二十年老屋的歸路上
依然如故
只是屋頂少了一縷縷親近的炊煙
那些炊煙也都跟隨她的孩子們
離鄉背井
去了城市和工業生活
理解這兩節詩的關鍵不在于標題和其運用的意象,也就是說,“星星”和“禾園和茅舍”雖然迥然有別,但施浩經由物中返觀自己,“讓你穿越無奈的憂愁/走出這片靜靜的土城”和“那些炊煙也都跟隨她的孩子們/離鄉背井/去了城市和工業生活”統一在對現代性、文明的追問、凝視上。海德格爾說:“詩是一種創建,這種創建通過詞語并在詞語中實現。” 詩歌正是通過語言創造世界:它創造生命與文化的世界,也創造“物”的世界。但是,這個“物”的世界一定是觀念的、價值的而非實實在在的物質的。因為,沒有一種“物”可以跨越三十年時間,一直閃爍在施浩的腦海中揮之不去,除了精神,還有自得之堅守。
分析文本的內涵非是重點。這里,我想說明的是,這兩節詩歌一節創作于1988年,一節創作于2018年。兩節詩歌的震撼之處在于經過漫長的三十年,施浩居然表現出了穩定、統一且面對共同的主題持續追問的風格。必須指出,風格的穩定、統一是一個詩人寫作乃至精神成熟最重要的標志。三十年時間,將施浩由一個少年變為一個中年,但詩歌這束火焰卻在他的心里劇烈燃燒著,沒有絲毫改變。按照有關學者的說法,“現代”就是在當下的生活中尋求永恒的詩意。顯然,時間在施浩這里是有形的,也是無形的;時間在施浩這里是槳,也是岸。某種意義上,時間承擔著批判和救贖,而我們這些塵世的過客,若干年后將會以異體人的形式出現。話說回來,這種主宰和強制是誰賦予的呢?顯然不是社會、國家或者高高在上的人。由是,詩歌是施浩尋找答案的唯一方式,盡管答案是非實體的、具象的,且體現在過程之中。里爾克曾說:“只有一個唯一的方法。請你走向內心。探索那叫你寫的緣由,考察它的根是不是盤在你心的深處;你要坦白承認,萬一你寫不出來,是不是必得因此而死去。這是最重要的,在你夜深最寂靜的時刻問問自己,我必須寫嗎?你就根據這個需要去建造你的生活吧;你的生活直到它最尋常最細瑣的時刻,都必須是這個創造沖動的標志和證明。”
必須指出,詩人不可能忘記自己的生存。詩人借助語言展示自己的生存,構筑自己的靈魂,但生活體驗和語言意志并不是詩人和詩歌的統治者,唯一可以宰制詩人的就是時間。因為時間既是物質的又是精神的,既是超我的又是小我的,既是實踐的又是體驗的,詩人必須借助時間建造個人的生活,而時間的秘境非走向自己的內心不能獲得—— 詩歌是一種自為和自慰,沒有什么可以替代它的神性。這個邏輯上,時間就是“元詩”。詩歌是時間和人之間的媒介、橋梁:詩歌不是寫出來的,而是時間在人體內的自然流淌。一雙睜開又閉上的眼睛,一定比世界上所有“制造”而出的詩歌更動人心魄。
這么看來,施浩的創作就不是爆炸式的、沖擊式的,其紳士般的藝術表達氣質本質上傾向于一種內燃內爆乃并借此實現自我肯定和提升。由此,施浩實現了藝術創作和生活日常的無縫對接,實現了精神玄想和當下之境有機融合。亦即,單就詩歌這門文學體裁而言,施浩不是在創作,而是在生活,在踐履。他就是宇宙,而宇宙里只有他自己,內燃內爆式創作體現出了生命書寫和文本自足的完美統一。必須指出,這種忽略技術、技藝、技巧的詩歌是無法創作、拒絕模仿的,除非其他創作者也能達到這樣的境域。
三
施浩詩歌的“無技巧”或“自然流露”之特性并非低難度寫作,相反,這種“行于所當行,止于不可不止”的把控能力,是洞徹生命本真、返歸自然之后的率性而為——只有真正的詩人,才會將升華了的情感和日常生活緊密融合。如是,就涉及到詩歌到底是什么的問題,我們可以籠而統之地將詩歌界定為人,抑或將詩歌視為精神的密語、自我之間的私語,但不可否認,作為“最高文學成就”的詩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即日常生活。自《詩經》《離騷》到唐詩宋詞,詩人即便在詩之外,也一直處于生活之中,其反復吟詠的絕非字詞所表現的那樣超脫,而是艱難地包含在不可抑制的“to be or not”的設問、答疑之中。施浩在《音樂之旅》中說:
眼中看不到的方向
是完人的圣土
是長夜
它們在詩行深處
向我張望
我的修長的生命
點燃玻璃上的火
火的輝煌的背景
我想起
黑的貓
在坐夜
嬰童輕啼的呼喚
一堆喋血
從窗口
長出我四只爪的樹根
抓住中心地帶的饑荒
那無邊的晚唱
生命如果可以稱之為“東西”,那么,這個東西太神奇了,每個人如此相同又別具一格,如此悲傷卻又興高采烈地活著。施浩和普通人一樣有自己的七情六欲,但他活在自己提純過的世界里。熟悉的朋友都知道,這個外表忠厚、言語木訥的男人其實一直處處刁難自己:通過越野活動向外擴張生命的可能性限度,通過詩歌活動向內挖掘生命的不可能縱深。他身體力行地踐行著這樣一個樸素的真理:活在自己之中,溢出自我之外。也就是說,他要活得透徹、灑脫、明白。一般人會認為越野和寫作是兩種相反的東西,前者沖動、暴烈,后者安靜、舒展,事實上兩者都是不羈的、自由的、一種出于原始本能卻又有節制的放縱。由是,當詞語或物象反復出現在他的腦中、筆下——這些不是情感的碎片,如果是,也是生命的一種物質體現——通過不斷拼接,施浩將自己持續放大,進而將自己塑造成一個可以自我安慰、自我保護但又不斷展開胸襟的有情人。
在談到生命這個懸而未決的“玄學”問題時,一個西方詩人的觀點頗具參考意義。他說:“繆斯保持安詳;……精靈呢?精靈在哪里?從空空的拱門進來一縷神智之風,堅持在死者們的頭上吹,尋找新的景色和未知的音調:一縷帶著嬰兒唾液、折斷的青草和水母面紗味道的風,它在宣示對新創造的事物不斷的命名。”
多么好的“不斷的命名”,詩歌豈不就是一種自我命名?當然,作為一個借助語言提純獲得生命真實之境的詩人,施浩不會如此邏輯性地思考自己的未來或生活的當下困擾,他只有情感,只有直抒胸襟、有觸而發的血性語言。如下這些語句都是從他的脈管中流淌出來的——因為流淌,拒絕浮華、浮夸和一切矯飾之詞的阻礙:
我無休止的叩問我自己。
每當在人群里
我總找不到自己
每當在深夜里
我的世界
總是如此地孤寂
什么都聽不見
什么都看不到
什么都遠去
我不愿接近你
上帝的殿壇
——《無題》
施浩即是通過自我對話(包括與物的通話)確認或證實自己在這個世界的存在的。也就是說,施浩詩歌中的自己既不是過往的自己,也不是縹緲的自己,更不是夢境里虛幻、虛浮的自己,而是那個用靈魂不斷敲擊骨骼的、原始的、祛除了精神污染的自己。
四
我們最大的誤解在于想當然地認為詩歌是一種語言、文字。需要記住約翰·洛克的忠告,他鮮明地指出:“文字本身沒有意義的。”他進一步表示:“機智和想象比枯燥的真理和實在的知識更動人。因此,人們不愿承認,比喻和隱喻也是一種語言的缺陷和濫用。” 詩歌唯一可以對應的就是情感,情感即詩歌,反之亦然。故而才會說“詩者志之所至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施浩的作品絕不是對生活的簡單的語言性提煉,毫無疑問,他和所有詩人一樣都是抒情主義者,都是現代和古典結合的風神。但施浩異于眾人之處在于,他拒絕用玄而又玄的字詞、意象和修飾(拗意的邏輯更被排除在視野之外),而是通過直白本心,進而直指本質。我們不妨讀一下《稻草人的故事》:
秋分時刻
我們都很小
我們在稻場上玩戲
比我們更小的妹妹
赤腳站在稻場中間
我們仿照她的模樣
扎成稻草人,然后
在五厘田之外
用芒草制成箭,射中她的胃
妹妹遠遠倒下
秋分時刻
妹妹嫁給一座小山岡
山后面是山
妹妹便抱著一棵榕樹
站在荒涼的山岡上
貓頭鷹也常常在家門口叫她名字
小妹小妹小妹
小妹!
你走以后
我的小屋落滿灰塵
到了秋節
我又想起大地豐收后黃昏景色
農家的燈盞依依亮起
我們作為孩童
抱著冬天的大雪和春天的雨水
在母親了糧食的家中
我們扎的那個稻草姑娘
一個人站在田野上
想明年的農事
一夜沒有睡去
這首詩歌簡單、直接,僅僅通過山岡、榕樹等“孤獨”的語詞便讓那種痛徹心扉的情感結實地落在地上、落在人們心坎,進而獲得了揪取人心的巨大動能——“妹妹”是你的,是我的,是我們心底最柔軟而讓人流淚的隱秘之一部分。但是,簡單不意味著蒼白,痛徹不意味著泛濫,又節制又放縱恰恰是施浩的詩歌“技能”。這里,不用“技藝”一詞乃防止我們對施浩的自然之性的詩歌創作出現誤讀。詩歌永遠是神諭的、天籟的,若非站在語言的制高點上,寫作的意義何在?可以說,詩歌即便取自于最泥腥的素料,也是卓絕探索的獲得、激流涌動的產物,將口語乃至口水作為詩歌,無論怎樣矯飾都是一種“臨淵自墮”。
當然,施浩的情感表達不是“世俗經驗的簡單總結”“啊呀嗯哼”的偽抒情,不是在嘩眾取寵的年代里自我褻瀆式的賣弄情操,而是借助于種種語詞,制造出一種“漂移”和“蜂擁”,詩歌之所以是一種人的藝術,就在于人的經驗和自然、宇宙構成了玄妙的默契。通讀施浩的作品,可以看出,他的感情是真摯的、細膩的,甚至會產生一種椎心之痛,這種“直擊”的力量首先來自于他的表達沒有過多雕琢,如《平安夜,獻給海》
只有午夜之后
玻璃才會迷亂
影子才會迭折
只有午夜之后
我才不會重來
我把過去遣送回白晝里
我把自己歸還給醒夢之后
水和火焰重疊
風和塵土合流
情和怨迷離
雨停之后
留下一行空格
玻璃、影子、水、塵土、雨……,這些平凡的東西經由情感的組合而有了詩學的意義。施浩不談自己的孤獨——孤獨是多么常見而又奢侈的精神體驗啊,而是談“物”,通過“物”,施浩的精神得到了落實,“物”本是非人的,通過吟詠性的描摹,“物”不僅人格化了,且具有對世界和自我審視的能動性。
現在,我很想下一個這樣的結論:施浩是一個優秀的詩人,一個將日常吟為詩之人,他用三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證明,詩歌是抵御世俗、避免自墮的最偉大的精神力量。無所事事和醉心詩歌都是一種人生,但詩歌創作者會在焦慮、孤獨、挫折感與幻滅中鼓起勇氣,而不是忍受與逃避,如果沒有詩歌作為日常,而僅僅依靠香煙、啤酒甚或爵士樂喂養自己,生活將是多么單調而乏味。
這么說來,詩歌多么值得信賴,而詩歌又是多么可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