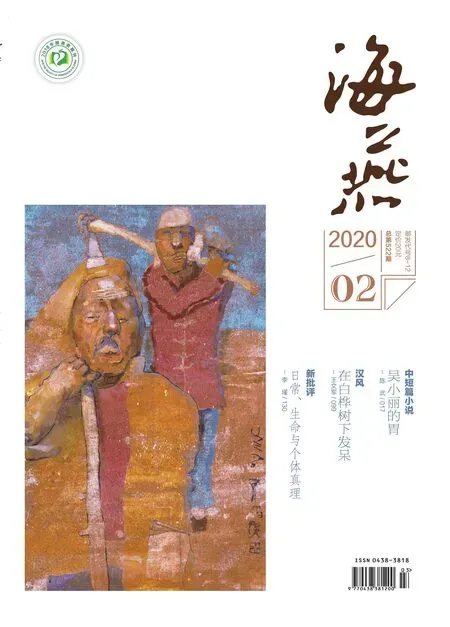無所依托的生活
文
母親沉默地進進出出,我悲哀地望著母親,仿佛望到了遙遠的我自己。我總是無法相信我們是母女,仿佛她就是一個軀殼,一個我曾經(jīng)借助降生的工具。漫長的時光磨損著她,她自己也任意驅(qū)使著她自己。她從來沒有領略過生活的快樂,她只是為活著而活著,麻木、卑微而順從。
一
兩年前,母親做了闌尾切除,是個小手術(shù),但彼時的母親已經(jīng)七十六歲了,肌體的生長能力遲緩脆弱,我們都很擔心。母親卻坦然,仿佛不知道什么是危險。
我趕到醫(yī)院時,母親已經(jīng)回到病房,蜷縮在床上,聲音虛弱,有氣無力的。醫(yī)生叮囑術(shù)后要多運動,我看著時間,每隔半小時就讓她起來,扶著她在地上轉(zhuǎn)圈。第一次轉(zhuǎn)半圈就氣喘吁吁了,弟弟不忍,說讓她歇歇,我心里疼出了一個洞,還有瞬間的慚愧,就好像我和她有仇,借此機會為難她。還是她自己堅持,說再走走吧。她矮小瘦弱,身體歪斜著,腿腳也彎曲了,靠在我身上輕得像一縷風,我怕我一松手她就沒有了。從晚上六點到十一點,從走一圈到走六圈,她就像個聽話的孩子,讓她起來她就起來,不發(fā)脾氣也不說哪兒疼,努力做出慢慢好起來的樣子。半夜過后,我不折騰她了,讓她躺著睡覺。那個時候,麻醉藥藥力過了,刀口應該很疼,我告訴她如果疼就喊出來。我躺在邊上看著她,準備好聽她咝咝啦啦地哼嘰,甚至準備好了握向她的手。可她一點聲息都沒有,只是偶爾慢慢翻動著身子,證明她是極度不舒服的。七天的時間,我一個人照顧她幾乎沒費什么力氣。似乎那刀口沒長在她身上,我們母女是在那間屋子度假的。
帶母親回家的那天,下起了那個冬天的第一場雪。積蓄了一年的雪來得兇狠猛烈,大片大片的雪花前仆后繼氣勢洶洶。母親迷蒙著雙眼,縮緊了身體,蹣跚著走路。我咒罵這無情的雪,抱怨這惡劣的天氣,母親卻一直平靜著,笑笑說,沒什么,慢慢走不會有事的。
我攙扶著母親,就像攙扶著她的整個人生。那白茫茫的雪刺目又驚心,我們母女兩人孤單又渺小,我摸著母親沒有體溫的身體,仿佛摸到了她沒有溫度的靈魂,我被這一想象嚇著了。我們是母女,卻是有著不同生活軌跡的兩個女人, 我脾氣暴躁易怒,對什么都沒有耐心,可她啊,她平靜幽深,像一片浩大的湖水,人生所有的兇險苦難到她這里都消失了融解了。她不嗔不怒,當然也不喜不悲。她啊,是我想模仿的榜樣,也是我想遠遠避開的命運。
二
老家的墻上有一張母親年輕時的照片。她穿綠底的大格子襯衣,偏分一側(cè)的短發(fā)用一根頭繩扎起來,臉上涂著腮紅,很土氣的樣子。她目光迷茫地看著前方,膽怯木然還有一絲無所適從的緊張。還記得多年前有一次,父親難得高興,向我們講述他和母親相親的過程。他說他去見她的時候,她在很香地吃著一根油條,對他不理不睬,更不羞澀不避讓。我仿佛看到我年輕的母親麻木淡漠的情態(tài)。她不關心眼前的男人,也不關心未來的生活,她的眼里只有那根可以吃到嘴里的油條。她不知道世界的繁復和浩大,也不關心未來的世界是什么樣子,她仿佛只是一只任憑命運擺布的木偶,從來沒有準備要和命運抗爭什么的,就那么隨著自己的命運飄飄蕩蕩,跌倒了再爬起,爬起了再跌倒。可是,我分明想起小時候的那個夜晚,母親躺在炕上給我們唱的那首歌:櫻桃好吃樹難栽,小妹妹有話口難開……她在命運的激蕩里,偶爾睜開雙眼打量這個艱難的世界,內(nèi)心掠過一絲隱密的幻想和憂傷。
從我記事時起,見過母親太多的哭泣,都是由父親造成的。那個暴怒的男人,每天都要對母親橫挑鼻子豎挑眼,把家里弄得雞飛狗跳永無寧日。母親從來不反駁,隱忍克制,悶聲不響地聽憑父親發(fā)泄,然后躲起來偷偷抹眼淚。我曾經(jīng)嘲笑母親,怎么就那么老實,被父親欺負了整整一生。母親不辯白,只是毫無來由地說,如果沒有你們幾個,我早就不和他過了。彼時的母親頭發(fā)已經(jīng)灰白,皮膚接近土地的顏色,臉上密布著重重褶皺。我在她的身上尋找我的影子,除了身高,沒有找到一點相像的地方。可她就是我的母親。這些年,雖然我總有一種想把這個世界掀翻的沖動,甚至多次都想從高處跳下去不活了,但我還是得努力活著,活得忍氣吞聲,活得沉默無言。我身上流淌的是她的血液,我繼承的是她性格中的因子,我活著活著就活出了幾分她的樣子。
那一年冬天,帶朋友去家鄉(xiāng)看雪,我在醉酒之后放聲痛哭。父親急躁狂亂,催逼母親問我為什么。母親說這妮子心事重,她不會說的。整個夜晚,她把自己坐成了一個雕塑,只是偶爾低低嘆息一聲。我的內(nèi)心里曾經(jīng)有那么多的渴望啊,可是我還是慢慢地自己把自己束縛住了。我努力掙脫母親的懷抱,但我還是沒能掙脫與母親相似的命運。
三
記憶中的母親強健而忙碌,似乎從來不生病,也從來不歇息。家里養(yǎng)著幾頭豬、若干只雞鴨鵝,有大片的自留地,從春天到秋天她腳步咚咚地走過田間地野,背負回一切可以供養(yǎng)我們成長的事物。冬天她要給我們做衣服、做鞋子、做被子。她自己彈棉花,紡羊毛,她頭上飄落著一層白絮的樣子在我的心里就像個跌落凡塵的仙女。那個時候,我忙著長大,忙著如何逃離那個小山村,從來沒有留意過母親自身的生活,仿佛她就是為我們而存在的。她總是不聲不響,沉默地生活在她自身的那個沉重的世界里,從來不表達一絲痛苦,或許她的痛苦是沒有聲音可以表達的。
母親沒進過學校,但她識字。記得小時候,她會在偶爾的閑暇時間里,翻看我們的小人書,也會盯著看墻上的報紙。但恒常的歲月里,母親就是一個角色,圍繞我們幾個疾速成長的孩子,侍候那個時時暴怒的丈夫。或許母親有過些微的幻想,有過朦朧的憂傷,但苦難的生活已經(jīng)把我的母親湮滅在掙扎里。經(jīng)年麻木的表象下是蝕骨寒心的鈍痛,她不得不放棄哪怕是一點點的幻想,在眼前的日子里茍且生活。
那一年秋天,母親在家鄉(xiāng)的站臺上送我去讀大學,她第一次略帶儀式感地對我舉起手臂,望著面色平靜無悲無喜的母親,我突然覺得她舉起的手臂是那么沉重,似乎她舉起的是我們母女兩人的希望。此后,我離開生育我的鄉(xiāng)村,在不同城市間穿行,我已經(jīng)長成了一個城市人應該有的樣子,但我的精神依然是母親式的孱弱,我似乎一直在自我欺騙,把懦弱當成寬容,把忍讓當成從容。我才知道,生活是如此強大,我和母親的希望,不舍晝夜,慢慢逝去。
四
當我描述母親的時候,母親就成了過去。過去的母親似乎就是苦難本身。
母親的血液里一定缺少鋼鐵的成分,她從來不發(fā)火,沒和任何人紅過臉,誰說什么她只是聽著,她不和任何人任何事抗爭。但她卻是堅韌的,仿佛不知道應該體恤自己,什么事都自己忍著,一切苦難都自己背著,她常常會把自己弄得遍體鱗傷結(jié)痂帶血。
母親三歲時,我的姥姥去世了,姥爺很快續(xù)弦再娶。他娶回的那個女人每到吃飯就把母親扔到外面餓著。一個三歲的孩子,搖搖晃晃地,還感受不到人間的殘酷,她只是被無邊的餓意折磨著,可能都沒有力氣哭泣了。我二姨回娘家時,看到我的母親已經(jīng)奄奄一息了。二姨沒有別的法子,只好把我母親送給了一戶沒有孩子的人家。那個年代的孩子,似乎就是父母隨意丟在地上的一顆草,我的姥爺對母親一直不聞不問,直到臨終前,隔了重重的光陰,他才想起曾經(jīng)有過的那個女兒,并囑咐我的兩個舅舅,如果可能找一找母親,如果她過得不好,要想法幫助一下她。母親在那戶人家也沒過上幾天好日子,那家的女人不久之后懷孕有了自己的孩子,她開始將母親當作累贅日日打罵。
母親的身體是我最不忍直視的,她的肚子上、腰上、腿上密布著大大小小的傷疤,有毒瘡的疤痕、有惡狗咬過的痕跡,那些疤痕剌目又驚心。或許那是死神留下的,它和她糾纏得久了,失去了耐心,只在她身體留下一個終極的記號。
母親不可抵制地衰老了。她的眼神已經(jīng)混濁了,她洗過的碗筷、擦洗過的地面我都要重新偷偷重復一遍。仿佛地心的重量對她也有特別的吸引力,她的雙乳低垂下來,像兩個布袋子吊在身上。她的皮膚斑斑點點,仿佛已經(jīng)不能自由呼吸。給她洗澡時,我撫摸著她肌膚的紋路,如同撫摸漫長的時光,我看到風霜雨雪年復一年在母親的身體上雕琢侵蝕。此后經(jīng)年,我要看著母親的身體一點點殘缺和零落。歲月給每個人都準備了一個長長的儀式,我們都得學會從容告別。
五
父親去世后,母親一下子萎靡了,那個一直壓榨她的老頭似乎是一臺專門強制她生產(chǎn)力氣的機器,老頭走了,她的力氣也跟著沒了。我聯(lián)合哥哥和弟弟,剝奪了母親的發(fā)言權(quán),決定母親此后的生活由我負責,然后幾乎是強行地把母親接到了我家。
我給母親準備了單獨的房間,安裝了單獨的電視,配備了一應俱全的生活必須品。想象著母親之前要自己劈柴擔水,自己對付一日三餐,我想當然地以為,我給予母親的是她之前從來沒有享受過的美好生活。
但弟弟送她到我家時,我聽到她對弟弟抱怨說她沒有家了,那聲音里隱含著一絲幽怨和凄苦。母親說話的音量不高,但我卻瞬間臉紅心跳起來,仿佛我就是個不孝的女兒,被母親看穿了看透了。或者我把她接到我家就是存心要折磨她,要讓她在我的臉色下討生活。
哥哥事先囑咐我,說母親是忙碌慣了的,得讓她在我家也動起來。我把家里要做的事情濾了一遍,找出幾件她能夠做的事,讓她做的事情她都牢記著。每天早上,我從床上剛爬起來,她就去給我疊被子,我剛要出門,她就操起了拖布,我在廚房做飯,她跟在我身后,不停地問,去土豆皮不?扒蒜不?或者就打開柜門,找米里的飛蛾。母親做事的時候,顯得小心翼翼和用盡全力。
母親在家的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她自己的屋子里,看電視或者躺在床上發(fā)呆。偶爾,我逗她說笑,她努力做出笑的樣子,但笑得潦草和漫不經(jīng)心,看不出神彩和光亮,仿佛一個沒有家的人已經(jīng)沒有了歡笑的理由。每天晚上,母親關上房門,調(diào)小電視音量,悄無聲息在她的屋子里盡量不發(fā)出聲響,寂靜無聲的恍惚里,我一點也感覺不到母親的存在。偶爾,我給她買件新衣服,她高興地接過來,在身上迅速比劃一下,但突然地,她臉上的笑容還沒綻放就消失了,眼神也隨之暗淡下來,仿佛是拿了不該拿的東西,有些手足無措地念叨,說她老了,不需要那么多衣服了,說我不應該為她浪費錢。
母親接受了她要長久生活在我家里的事實。她先是小心翼翼地在廣場上轉(zhuǎn)圈,然后認識了若干老太太。她們一起溜彎,一起玩撲克,一起逛街。她和她們打電話聊天,和她們相約去某個地方閑逛,但她從來不領任何一個老太太到我們家。她有時會在超市或者集市上買回來便宜的蔬菜,然后拿著給我們看,一臉的自豪和邀功的表情。偶爾,她澆花時水溢出來,或者把什么東西碰碎了,她就會像個做錯事的孩子,不停念叨,人老了啥用也沒有了。
春天的時候,我?guī)赣H回到家鄉(xiāng)。車一進入村子,母親突然直起身,指著遠處橋頭上的豆腐攤兒,說要在那兒停一下,她要買塊豆腐,然后又半是自言自語地說著還應該做些什么吃的。回到老屋,我進去打掃衛(wèi)生。一個冬天過后,老屋更加沉默,也似乎更加蒼老,她努力地支撐著身子,散發(fā)出微弱的溫情,某一刻的恍惚里,我似乎看到,她敞開懷抱,卻拒絕我入懷,她在癡心等待的只有母親。而母親,母親這時候已經(jīng)沒了人影,一會兒功夫,她又回來了,和她同時回來的還有鄰居朱阿姨、江嬸子、劉大娘,母親布滿褶皺的臉在陽光下微微上揚,配著清脆的笑聲,仿若在無聲地宣告,她是這個院子的主人。
母親在我們家的日子,除了吃飯,仿佛再沒有任何需求。每次哥哥或弟弟打電話,她都對他們說一切都好,一切都好。但我知道,一切都好的母親事實上是寂寞和凄苦的,她小心翼翼,誠惶誠恐。即使我是她的女兒,她曾甘心情愿地拉扯著我長大,卻不能毫無顧忌地聽憑我的照顧。她的心是懸著的。她從此過上了無所依托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