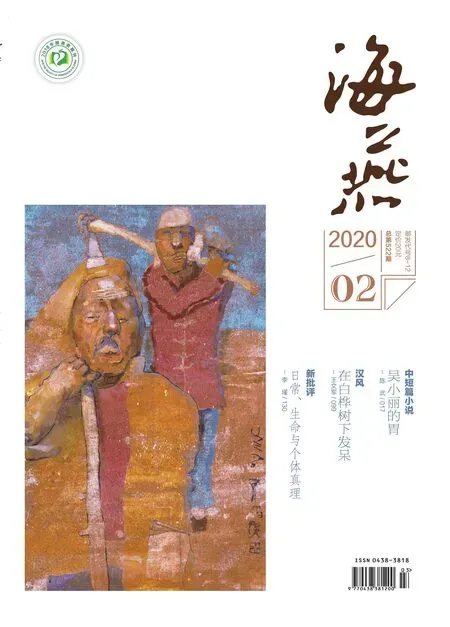秋 生
文
1
秋生結婚的那天是臘月二十八,大雪紛飛。日子是他叔早就掐算好的。人們說秋生叔一輩子的心數都是為秋生設計的。那天秋生叔早早就把借大隊的兩輛牛車放在大街上,前面的牛車用席子扎了一個拱形棚,做新娘的轎子,后面的拉著打鼓敲鑼的人們。后面還有一隊人抬兩個斗方的食盒。大黃牛提前一天就牽到家里,早晨還往牛槽的草料里倒了一碗稀粥,秋生叔拍著大黃牛肥碩的腰身說:“大黃牛啊,好好把我侄媳婦給娶回來,你就是功德無量啊,晚上還給你一碗粥。”
“叔,真氣派,哪天俺娶媳婦你也給俺鼓搗這個。”傻平安把大紅綢子掛在車棚上,蹦下來笑嘻嘻湊到秋生叔面前。秋生叔拍了拍傻平安的肩膀,“行,包在叔身上。”
一切妥當,敲鼓打鑼驟然響起,都把天震亮了。
走在車前面的是秋生叔請的村里紅事主持大根,大根一臉喜氣,頂著一頭稀疏的白霜,腋下夾著一塊紅氈,大喊一聲:“打起鼓來敲起鑼,咱們秋生娶親啦!”牛氣哄哄地帶領一隊人向十里外趙家莊前進。傻平安跟在秋生后面,叫秋生叔一拐杖打回來,“傻小子,回來,跟我在家等著接新媳婦。”傻平安只好眼巴巴看著秋生跟在大根叔后面走了。
秋生這天穿著一雙借來的黑色平紋布棉鞋,和一件借來的中山服上衣,黑色褲子雖說洗得有些泛白,可也算干凈。臨行前,他掀起褂子前襟,掖了掖露出灰絨套的棉襖。臉上收不住嘿嘿嘿地笑,回頭看了他叔一眼后,腰板又挺了挺。
“秋生,你看看你今天都樂傻了。”
“嘿嘿嘿,叔,沒傻。”
趕牛車和抬食盒的人們哄笑起來。
“秋生,你個兔崽子,聽說你媳婦可是很俊。”
“這夜里的事要不要我們教教你。”
寒風下,本來就凍得一臉通紅的疙瘩,這會兒都紫了。他彎下腰抓起一把帶雪的泥土朝他們扔過去。趕牛車的栓子,年紀小,溜脫,一下絆腳,讓秋生摔一個仰天倒。大家又是一陣哄笑。
“晚上,就那么躺炕上,讓你媳婦伺候你。”
“以后不用憋著了,指不定滿臉疙瘩也好了。”
秋生紫著臉爬起來,指著他們,“等著,等著……”始終那后半句沒說出來。秋生脫下中山服,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撲打了一個遍才穿上。又掖了掖棉襖里漏出的絨套,跑開跟上大根叔。大根叔在他后背捶了一拳,“挺直腰板,把手從襖袖里抽出來,你叔可囑咐我好幾遍,今天要精神點。”秋生一邊嗯著一邊伸出手,給大根撲了撲背上的雪花片子。
打發迎親隊伍走后,雪花飄得密起來,有小風斜斜刮過,秋生叔緊了緊扎在棉襖外的草繩,領著傻平安一瘸一拐的,把每個門上貼的對聯挨個摁了一遍,然后回到牛棚,坐在用木頭板子搭建的床上,愣了半天又笑了半天,“哥,秋生今兒娶媳婦了,你跟嫂子在那邊給保佑著,俺是用了一點手段,可咱秋生人不孬,不會害了人家姑娘的。”
傻平安就坐在他家柵欄門前的石頭上托著腮等著。直到看上去像個雪人,才聽了秋生叔的叫喚,站起身蹦跶回屋。一蹦跶雪花就成片地落。
正如秋生叔所料,下著大雪,又因為害羞,秋生媳婦根本沒仔細瞅她的新郎官,只見騰不起衣服的瘦削和凍得瑟瑟的背影。可秋生躲一邊卻是看了個仔仔細細,在心里大呼,我的叔啊!值了值了都值了。
2
秋生媳婦進門之后才看清楚秋生。秋生滿臉痘窩子,像孩子們摔的泥瓦,一個坑一個坑的。他一年四季喜歡把手抄在襖袖筒里,就算夏天穿件帶窟窿眼的汗布衫,兩個胳膊也搭一塊,放在胸前,低著頭聳著肩,向前拱。對,就是拱,人家都是走路,他拱路,一拱一搖。他自家叔每每看到就攥緊拐杖戳地罵,直起腰來走路,跟個蛆一樣。秋生自八歲就跟著他叔生活。他叔是個瘸子,一輩子也沒找上個媳婦。秋生落地后他爹就許諾他叔,等生了第二個孩子不管男女都給你,讓他給你養老送終。可是秋生娘在生第二個孩子的時候難產死了,孩子也沒保住。那時候秋生三歲,三個男人組了一個家。秋生爹自媳婦死后一直打不起精神,日子得過且過。他叔雖說瘸了一條腿,可在村里為人仗義,辦事公正,有威望,后來被選上生產隊長。好日子沒過五年,秋生爹得了肺癆沒折騰半年也走了。從此,這個家就剩下秋生和他叔了。
媳婦是他叔夜里拖著瘸腿,到鄰村最有名的媒婆陳小巧家里,一趟一趟送糧食才得來的。因為這事,秋生婚后第二年東窗事發,生產隊長就被人給擼了。
看著秋生這樣子,媳婦羞怯的臉上瞬間就打上一層霜,扎扎實實愣著不知道何去何從。瘦弱的身子捂著被子在炕上坐著抽搭了一宿,愣是沒讓秋生張燈,更沒讓秋生碰。秋生除了給媳婦端碗熱水遞過去,什么也沒做什么也沒說。那些聽門子的只聽到秋生媳婦時斷時續嚶嚶的哭聲。
因為馬上就要過年,魯北鎮有省卻三日回門禮的規矩,所以秋生媳婦就在這三間昏暗的破土屋里,哭了三天,雪也下了三天,屋頂上和院子里厚厚的白雪,捂得秋生大氣不敢喘。
過了年回門,也沒讓新姑爺進門。秋生把準備好的白面饅頭和一包點心,裝在布袋里背著,跟在媳婦后面送到她娘家村頭,遞給她,“我知道,我長得寒磣,我在這等你。”他媳婦低著頭愣了一下,目光穿過秋生,望著他們踩過深深淺淺的腳印,輕輕嘆了口氣,接過布袋子就走了。后來,秋生媳婦說你不用跟著了,秋生就不再跟著去。整個春天秋生媳婦每次回娘家來,都到村頭燒窯的洞里哭半天再回家。
驚蟄后一天早晨醒來,秋生睜開眼就發現天格外亮,門外的大地突然復蘇了,他端著一碗棒子面粥,哧溜哧溜喝著說:“榆樹開始泛青啦。”回頭再看媳婦的臉色也轉暖了許多。“秋生,改日你到你大根叔家移栽過來棵石榴樹吧。”秋生叔一邊說一邊喝完最后一口粥。秋生呼呼大口把粥喝了個底朝天,看了一眼媳婦,從她手里奪過碗,“我來洗,你不是那啥嘛。”秋生媳婦慌忙看了他叔一眼,低下頭,“已經走了三四天了。”奪回碗放進洗菜盆里。秋生叔干咳了兩聲站起身,“我到你大根叔家看看去。”他左腿剛拐出院子的柵欄門,向胡同前后望了兩眼,噗嗤一聲笑了。
“你這兩天拾掇拾掇牛棚,壘個炕,讓咱叔住北屋。”
秋生看了一眼媳婦,不顧媳婦濕漉漉的手,攔腰抱起來,用腳踢上門喊著,“金蘭我的金蘭”就上了炕。
等到小滿,秋生媳婦跟半個村里的人都熟絡了,經常有嬸子、大娘、嫂子找她,她們坐在胡同口背墻處納鞋底。那時候夏天剛來春天還沒走,秋生媳婦肚子已經微微隆起,可模樣還是清瘦,讓太陽兒一曬臉頰像是施了桃花粉一樣。每每見人她都是微微笑開的臉,一笑,眼仁深陷,像一枚放在清澈湖底的青石,小嘴一張開,就算吐一句,“秋生去東坡里了。”也像一縷棉絮。那張臉那落進心里的聲音,不知道讓村里多少閨女媳婦嫉妒得眼里冒出火光,讓多少大老爺們兒摩拳擦掌,他們一想到秋生那熊態跟這女人在床上,恨不得端著菜刀砍了他,來個英雄救美。后來人們又說,金蘭就是秋生的再生父母,沒有她哪來以后的秋生。
娶媳婦后的五六年,秋生沒閑著,相繼兩個女兒落地,隨后竟生了個雙胞胎兒子,那些圍著秋生媳婦打轉的男人們,終于也消停了不少,都說,這女人不簡單,守得住婦道,也守得住這個家。要說秋生這輩子干了點啥,還真不好說,可能就是生了四個孩子,尤其是人家生了雙胞胎兒子,這在村里是獨一份,這是秋生抄著襖袖子在街上晃悠的資本。
“秋生,你看看你一年到頭這個熊態。”
“你不熊態,你一下生兩個兒試試。”
3
秋生叔死在冬月前,到底還是石頭要了他的命。
那年春天家里已經六口人,牛棚漏了頂子不能再住人。秋生媳婦張羅著,把三間土屋兩頭用向日葵棵扎起來糊上報紙當墻,這樣就有了單獨的兩間房子,東為上住著秋生叔,西頭壘了一個大土炕住著秋生跟媳婦和四個孩子。到了晚上,秋生只要起夜,回去就找不到躺下的地兒了,孩子們在炕上睡覺打滾,秋生還得挨個抱起來給重新順好了。隔出來的中間一間,壘了兩個小灶膛,都通到兩個炕洞里,一個灶膛是專門做飯用,另一個冬天燒點木柴熱炕頭。剩余的空間就剩放一張飯桌和幾個板凳,算是全家人公共活動的地方。
秋生叔踅摸著,他還得給孩子們蓋兩間西屋,閨女大了得單獨住。那一年夏天田里打了一袋子小麥,秋天打了兩袋子玉米,他讓秋生各留出半袋子來,其余的叫秋生背到集市上賣了,買回兩頭山羊。秋生叔每天瘸著腿去放羊,一邊放羊一邊還得打草為冬天儲備著。牛棚修繕成了羊棚。他天天沒事就圍著這兩頭羊轉,他的想法不僅僅是蓋兩間西屋,還要給那三間北屋換換屋頂,村里很多人家已經把原來的土屋頂換成紅瓦了,看上去又漂亮又實用,半尺厚的土堆在房梁上太沉,時間長了梁和檁條都會扛不住。秋生叔覺得到死也得給孩子們完成。
霜降那天,有些陰郁,秋生端著一只空碗從傻平安家里回來,碰到他叔趕著羊出柵欄門。
“平安還發燒嗎?”
“好多了,昨燒了一夜,我剛給喂了一碗粥。”
“給我,我去,今兒天不好。”秋生把碗遞給他叔,去奪他叔手里的鞭子。他叔閃開了,也沒接碗。“你今天就多跑著看看平安吧,我去就行,中午不回來了,帶著干糧呢。”“也行,你別走遠了,在村西頭放放就行。”秋生看著他叔斜挎著空包袱,一瘸一拐牽著羊走出胡同口,一轉彎就不見了。
平安跟秋生一般大,是這條胡同頭住著的同喜跟一個撿來的傻女人生的孩子,生下孩子傻女人就走了,村里人跟同喜到處撒信,找了幾個月沒找到就死心了。他一個人把孩子拉扯大,可這孩子遺傳了他娘,從三四歲開始光長個子不長腦子,從小喜歡跟著秋生玩。秋生結婚的前一年,同喜給傻平安逮魚吃,淹死在村后面的灣里。從此,秋生叔說,讓他跟咱過吧,只要咱有口飯吃總不能讓傻小子餓死。
那晚找到秋生叔的時候已經是夜里十一點,小雨還沒停。他抱著一只羊躺在草地上,羊也奄奄一息,他也奄奄一息。另一只羊趴在他身邊。原來,為了讓羊吃得飽,他帶著兩只羊去了村子十里外的白茅嶺,那里沒有耕田,只有大片大片的茅草,羊兒吃得又飽又美。傍晚秋生叔打算回家,甚至哼起小調,可不知道誰下的兔子扣,刺穿了他的羊腿,他的羊咩一聲就躺到了,血流不止。秋生叔著急,到處找堅硬的石頭想把鐵扣砸開,他爬上一個高坡,找見了一塊板凳那么大的石頭,還有一塊拳頭大小的。他沒想到還是跟當年一樣,下坡的時候,那塊大石頭又砸到了他的右腿上,他甚至又聽到一聲骨頭斷裂的聲音,他強烈地意識到,這下他要完了,這次真要完了。他還是掙扎著爬到那只羊身邊,用包袱給羊腿包起來,使勁攥著,血還是透過來了。他無力地倒在泥水里,這場雨真冷啊!我的羊會不會凍死?他沒意識到他的右腿已經被血水泡了。
秋生叔在熱炕頭上躺了兩天。村里的赤腳醫生說:“失血過多,再加上營養不良,已經救不了了。”秋生想把他叔搬到牛車上拉到鎮醫院去看看,他叔不肯,抓破了糊墻的報紙,抓住向日葵棵不放手。秋生叔指著炕,又指了指兩個孫子。秋生就把他的兩個兒子抱炕上。兩個孩子圍在老人身邊,一會抓抓爺爺的胡子,一會動動爺爺的胳膊,秋生媳婦訓斥孩子們,秋生叔擺擺手不讓。
晚上,秋生把傻平安喊過來一起吃飯。
“秋生哥,俺叔啥時候好?”
秋生看了看他沒說話。飯后傻平安坐到秋生叔跟前大聲喊“叔,叔,你腿疼嗎?”
秋生媳婦端著一碗雞蛋粥,打算給他叔喂幾口。兩個閨女喝了一碗玉米面粥,眼巴巴瞅著。家里養了三只雞,只有一只母雞下蛋,青黃不接。平時秋生媳婦給他叔吃,秋生就會挨罵,他叔說,孩子長身體,我老了吃啥都沒用。秋生把兩個兒子抱下炕,秋生叔閉著眼,一巴掌拍在炕上,秋生又把倆個孩子抱上去。自己也爬上炕抱起他叔,讓他靠在自己懷里。
“叔,來,喝幾口粥。”秋生媳婦拿著小勺舀了一口,湊近他叔的嘴跟前。秋生叔睜開眼看了看,搖搖頭,看了看坐在他面前的兩個孩子,傻平安跟秋生的兩個孩子一樣乖乖地坐在那里,又指了指那兩個站在炕跟前的閨女,手臂就耷拉下來,再也沒抬起來。
后來,秋生賣了那只死羊也賣了另外一只。可西屋也沒蓋,屋頂也沒修繕。賣了的錢買了木材,修繕了傻平安的那兩間快要塌了的土屋,給傻平安用泥土圍了一個院墻。
4
秋生的兩個女兒小學畢業就相繼回家,跟著秋生媳婦到田里干活。秋生抽著旱煙,蹲在地頭上看著她娘仨忙活,傻平安也蹲在地頭上,瞅著秋生。
“秋生哥,你有白頭發了,”然后抬頭轉了一個圈,“我還沒有白頭發。”
“我老了,你還小著呢。”秋生抽完半袋煙,在地上磕了磕,“志剛跟志強快放學了,你去學校等他倆回家吧。”傻平安噗噠噗噠轉身離開了。秋生看著傻平安沿著太陽落山的方向走遠,心里想,時間是個啥玩意,連傻平安都蹦跶不起來了。
秋生的兩個兒子志強和志剛學習成績并不好,初中畢業,老大去了外地打工,老二在家也不下地干活,倒騰收音機磁帶賣。兩個女兒因為長得俊俏,說媒的踏破了秋生家的門檻,秋生誰也不答應,直到陳小巧搬著一雙老腿盤坐在他家炕上時,秋生才答應大女兒的婚事。
“就算你不說這戶人家有多好,我也答應,就憑你給俺說來了金蘭。”秋生抽著陳小巧拿來的帶著過濾嘴的香煙,一邊咂摸嘴一邊樂呵呵看了一眼坐在馬扎上納鞋底的金蘭。一年四季只要不到田里干活,金蘭的針線活就不停,一大家子穿的衣服穿的鞋,還有傻平安的,都是她一個人做出來。
“這……這家條件可是真好。”陳小巧眼里閃過一絲歉意瞄了金蘭一眼,眼里又放出金燦燦的勁頭來,搖著她那滿頭白發說:“人家說了,趕集的時候早就瞧上你家大姑娘了,不要陪嫁嫁妝就要人。”
“那俺也得給俺大姑娘做兩床被褥,這孩子從小跟著我們受苦了。”秋生媳婦話還沒落音,淚就要掉下來,已經展不開眼了。秋生坐在那里挪了挪腚,最終還是站起來去院子里抬頭看著天。
秋生的兩個姑娘嫁妝都是給了兩床被褥和三百塊錢,錢用來買新衣服置辦點新家的物什。這都是志剛打工寄回來的,再加上志強倒騰出來的給金蘭買衣服的錢,金蘭一分也不舍得花,一直攢著。
兩個姐姐結婚后,志剛從外地突然回來了,說回來在家里找活干,再也不走了。回來的第一年,志剛跟志強把老院子整飭了一番,屋頂子換成了紅瓦,蓋了兩間西屋,兩間東屋,把柵欄門也換成磚壘的大門,用碎磚給那棵石榴樹砌了個池子,一個小院子頓時清亮了許多。三間北屋,重新規整,換了磚壘的隔斷,收拾好,哥倆就去鎮上打工了,掙錢來都拿回家給他娘。每個月都有那么一夜,秋生媳婦會點點孩子們給的錢,秋生就會端一碗熱水,在一邊看著。
“金蘭,多虧了有你。”
“別說些沒用的,你知道就行。”
秋生媳婦兩鬢的白發絨絨落在臉上,秋生忍不住給她別在耳朵后。
5
進了臘月,秋生還是抄著襖袖筒在大街上晃,傻平安還是跟著,不同的是,兩人不是一前一后了,而是并肩走,兩人還會嘚啵嘚啵說個不停。
志剛志強兄弟倆二十歲那年,加上兩個姐夫,一共四人用了一年半時間,蓋了五間房子,房子窗臺以下是磚,窗臺以上是拓泥坯壘起來的。五間房子兄弟兩個一人兩間半。盡管那時候村里人蓋房子都全部用磚了,但兄弟倆心里有譜,先蓋房子結婚用,畢竟那三間土屋再也不能當他們的婚房。村里人說這心數,都是秋生他叔傳下來的。
志剛很快就跟村里租賃白事物什,別號大奸臣的獨生女花葉談了對象。花葉其實早就看上志剛了。志剛長得一米八的個子,秀而挺拔,就像秋生不是他爹一樣。其實兄弟兩個都隨了他們的娘舅。大奸臣從一開始就不同意這門親事,不光看不上秋生家,還看不上秋生,說他一輩子過得讓人瞧不起,啥也沒給孩子們掙下,還有臉整天樂呵呵地在街上晃悠。可花葉是鐵了心的,她說她嫁的是志剛又不是秋生。結婚前花葉瞞著她爹把他爹給他攢著的六千塊嫁妝錢給了志剛,當彩禮拜見了難纏的岳父大人。盡管后來還是被發現了,可那時,花葉已經有孕在身,不得不結婚了。
老二志強,在集上倒賣磁帶收音機,認識了臨街商戶老張家獨生女,一來二去,終于也是非他不嫁。兩兄弟一年隔半月,分別在兩間半土屋里抱得美人歸。兩個孩子結婚,秋生算是一分錢也沒花,孩子們掙得都給了孩子們,這就是他能做的。
其實秋生就算有了兩個孫子也是半毛錢沒拿出來。人家跟他說話故意嗔他,“秋生,你給你兩個大胖孫子多少見面錢啊?”他嘿嘿嘿一笑,“給啥錢啊,又不是我讓他生的。”人們就會罵他,“操,你還算人嘛!”他還是笑呵呵的,抄著袖子,低著頭走。
孫子們會跑的那年,秋生生了一場病,全村人等著看笑話,看看讓他的孩子們怎么給扔了。誰也沒想到,四個孩子湊錢,把他的病治好了。兩個親家沒有一個來看他的,都裝作不知道。在村里碰到都是折回頭避開。后來志剛他丈人得了胃癌,秋生為了讓志剛跟她媳婦安心上班,一年半的時間都是秋生和他媳婦照顧著。秋生半句揶揄的話也沒說過,志剛丈人臨閉眼攥著秋生的手掉了最后一滴淚。
其實那時候秋生的病已經復發,打發親家公走后,他也住了院,醫生已經不建議化療,盡管孩子們不說,通過一年半伺候親家公,他也知道了自己得的是啥病。為了不讓孩子們擔心,秋生裝作啥也不知道。出院接回來的那天,志剛說:“你跟俺娘住我家吧,給你們收拾了一間,我們照顧著也方便”。秋生在志剛剛蓋的大院子里轉了一圈,“真好!院子都是水泥的,不過還是把我送回去,我覺得還是那三間老屋好,住起來舒坦。”那時候那三間老屋已經是危房,兄弟倆商量著給老倆口新蓋三間,可是秋生跟他媳婦都不同意。
“孩子們給蓋房子你為啥不同意?”,金蘭躺在被窩里望著黑乎乎的屋頂問秋生。
“你為啥也不同意?”秋生爬起身咳嗽了幾聲,“咱倆都一個意思。”
秋生媳婦翻了個身閉上眼,“拉燈睡覺吧。”
秋生給媳婦掖了掖被角,坐起身滅了燈,靠在墻上捂著嘴,咳嗽還是沒停下來。
6
秋生走在一個有太陽的秋日午后,金蘭就坐在他身邊,孩子們都圍在那站著,傻平安擠在人群里哭喪著滿臉灰蒙蒙的褶皺。
秋生已經皮包骨頭,氣若游絲,蠟黃的臉上可還是掛著笑意,他用盡全力睜著眼,他看了看圍在他身邊的人,“拉開燈。”志剛趕緊跑過去把燈拉開了,又張了張嘴還要說什么,志強湊跟前仔細聽。秋生媳婦說:“他叫你哥倆照顧著平安呢。”秋生眨了眨眼。孩子們都忍住,沒有一個哭出聲。
秋生把手搭在他媳婦手上,他媳婦反過來握住。
“你會長命百歲,你是咱家的福根。”一屋子人都抬眼互看了一眼,誰也沒想到,到死秋生語出驚人。
金蘭青筋暴出的手指動了動,嘴唇抖了抖。
“拉開燈,我看不見你。”
“好,我拉開燈,放心走吧。”
金蘭看著他閉上眼,給他撫平了臉上的皺紋,她覺得那些麻窩子已經跟她的手心一樣,柔軟、光滑,舒展開來。
等孩子們喊一聲爹哭出來,傻平安噗通跪下扒扯秋生的胳膊,“秋生哥,秋生哥,你得帶著我,帶著我。”
“叔你別哭,俺爹不安心。”兩個女婿把傻平安拉出屋外。
出殯的那天,陽光明晃晃撒了一院子,窗前的石榴熟得像秋生呲牙笑著。孝子孝孫跪了一地。人們一邊幫忙挑火給秋生燒紙錢一邊還打趣,秋生這貨,竟有這么好的命,這輩子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