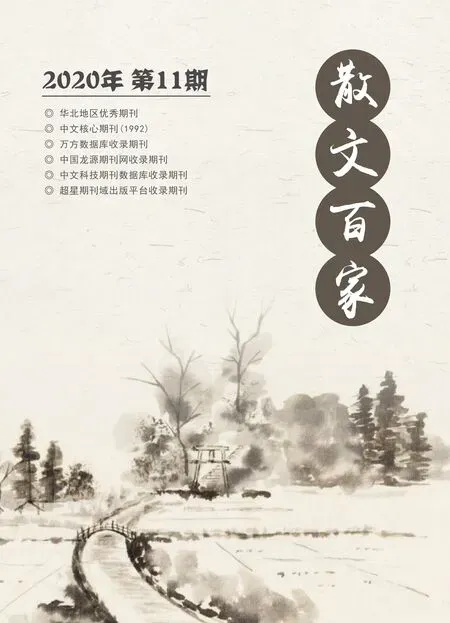論《詩經.衛風.氓》中的婚俗婚制
冼楚賢
華南師范大學
《氓》是《詩經》婚戀詩、棄婦詩的代表,講述了一個衛地女子的愛情悲劇:氓婚前費盡心思追求女子,婚后卻始亂終棄。女子飽受欺凌,只能暗自悲傷。最后,看透現實的女子毅然與氓斷絕夫妻情誼。
一、《氓》的完整性與典型性
在情節上,作品具有完整性,時間跨度長。從“總角之宴,言笑晏晏”的少年到“匪來貿絲,來即我謀”的戀愛;從“以爾車來,以我賄遷”的新婚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的決裂。其間經歷了戀愛、結婚、婚變三個階段,是《詩經》情節最完整的婚戀詩。在選材上,作品具有典型性。主人公是衛地的普通女子,也是周代女子的縮影,悲劇的結尾使詩歌具有沖擊力。完整的情節、典型的選材為《氓》作為探討婚禮習俗制度的文本提供可能。
二、六禮皆備的婚禮習俗
《禮記.昏義》提到“昏禮者,將合二性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皆主人筵幾于廟,而迎拜于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于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在周代,婚禮就已承載著維系家族延續的重要功能,因此需禮制加以規范,《禮記》的婚禮流程包括“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而《儀禮.士昏禮》新增了“親迎”,構成古代婚禮“六禮”。
“六禮為為妻之征。故六禮不備,貞女守義不住,以嫌于為妾也。”[1]在古代社會,“六禮”是婚姻必不可少的流程,也是見證婚姻禮成的證據。《詩經》婚戀詩處處有“六禮”的影子,而《氓》更是將“六禮”集中體現。
1.納采與問名。納采是男方派媒人送禮物到女方家,以示求婚并征求女方意見;問名則一問女家的姓氏,二問女方生辰八字以便占卜。這兩項流程都離不開媒人。
《氓》開頭提到男子“抱布貿絲”來與女子商議婚事,女子雖有意嫁他,卻委婉道“匪我愆期,子無良媒”。這體現了周代婚禮媒人的重要性。沒有媒人,“納采”、“問名”二禮不成。禮不成,則名不正、言不順。雖然沒有媒人,但女子被迫無奈還是決定答應“秋以為期”。“子無良媒”已為愛情悲劇埋下伏筆。
2.納吉與納征。問名后,男方將女方信息帶到宗廟占卜,得到吉兆后,就派媒人告知女方。而納征則是男方向女方送訂婚禮物,又稱聘禮。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就是納吉的體現,卜是占卜活動,通過加熱鉆洞后的龜甲,觀察龜甲裂紋而判斷吉兇;筮是占卦活動,通過組合香草竹片,根據其根數卦象預測吉兇。通過占卜占卦,得結果為吉兆。
納征在《氓》中并無明顯體現。筆者認為“納征”的省略是有意為之,可能也是為悲劇結局埋下伏筆。有觀點認為氓是平民,家中貧窮,難以納征。但《周禮.媒氏》有言:“凡嫁子取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下聘禮可多可少,少也不過五兩,因此,不存在氓付不起聘禮的情況。
3.請期與親迎。請期是定婚期吉日,期間要三請于女子家族,因此有“請”,但女方家族則要謙和推辭,男女雙方“禮尚往來”,從某種程度上是對彼此家族的尊重。而親迎,則是新婿前往女方家迎娶新娘的儀式。
《氓》未詳細描寫“請期”場景,但卻提到“秋以為期”。短短四字,蘊藏婚期吉日擇取的奧秘。“秋”字說明周代已有秋天嫁娶的習俗。結合《詩經》其他篇目,不難發現,周除了夏天不行結婚禮,春秋冬季皆可作婚期。在《召南.鵲巢》、《周南.桃夭》、《邶風.燕燕》、《豳風.七月》、《豳風.東山》中,婚禮環境描寫皆春日之景。呂思勉認為古以九月至正月為婚期;仲春而優不克昏,則其乏于財可知;乏于財,故許其殺禮。[3]
婚期當日要行親迎之禮。“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寫了氓駕車迎娶女子的情景。“六禮之中,親迎最重。”[4]《詩經》出現親迎場景的詩歌超15篇,“六禮”中親迎出現的頻率也是最高的。
三、早期形成的婚禮制度
1.同姓不婚制。早在西周,就出現“同族不婚”。《郊特牲》曰:“娶于異性,所以附遠而厚別也。”《左氏》載鄭叔詹之言曰:“男女同姓,此生不蕃”。[4]上述都證實了“同姓不婚”的婚制。
“問名”也是為避免同姓結婚。“送子涉淇,至于頓丘”表明女子與氓有相距較遠的地理距離。因此兩人為同姓宗族的可能性極小。而《詩經》的其他作品,如《燕燕》、《碩人》寫新娘跨諸侯國出嫁,更能體現周人的異族婚制。另外,《詩經》從未提及同姓通婚。因此,“同姓不婚”成為先秦婚制的特征之一。
2.出妻與離婚。《儀禮》記載休妻的“七出”,但《詩經》成書早于《儀禮》,休妻還沒有嚴格規定。但那時已形成男權社會,婦女沒有獨立經濟地位。[5]男女主人公一開始地位就不平等。婚前,在婚期約定上,氓處于主動方,女子只能說“秋以為期”;而婚時,氓則把嫁妝占有,女子喪失自己的財產;婚后,面對女子日夜辛苦操勞,氓卻“二三其德”,粗暴相待。男女主人公不同的婚姻態度表現了男女社會地位的懸殊。
周代婚禮習俗制度在《氓》中得到相對全面的呈現,結合婚禮文化常識,讀者能夠更好理解情節,“六禮”也為女子愛情悲劇結局提供了合理解釋。另外,在反映女性婚戀的同時,作品還展現了女性自我覺悟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