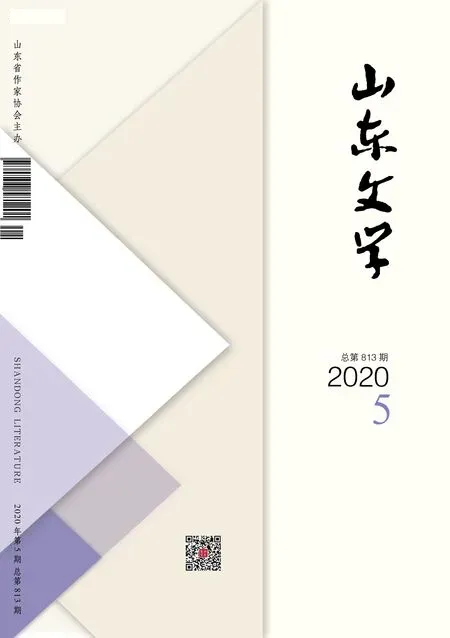為什么不是東河西營?
2020-11-19 04:18:06王二冬
山東文學
2020年5期
王二冬
我們不曾離開故鄉,我們不曾回到故鄉,甚至我們沒有擁有過故鄉。
兩年前的這個時節,我寫過一篇題為《為什么是東河西營?》的創作談,彼時的我在濟南,以為自己會久居泉城;再往前推兩個兩年,我在聊城,以為自己大學畢業后會流連于東昌湖畔;此時的我在北京,不知道自己會待多久……
自2010年離開東河西營,十年間,我自問自答又自我否定,生活給予的不安就在一次次的返鄉、逃離、回望中消解著。我肯定自己在這個村莊真實的生活過,那些老屋、河流、魚塘、果園、麥田……我可以清楚地描繪出它們存在時的位置和場景,但沒有一張影像可以證明;我肯定自己在這個村莊遇到過一些人,打一輩子光棍的羊倌王、愛抽哈德門的二逛蕩、生下一個瘋丫頭的外村媳婦……他們都死于非命,仿佛沒有人再提起,他們就從來沒有活過。
我試圖叫他們活在我的文學世界中,至少有一行曾記錄其曲折的一生。我是自私的,因為我只有用寫作的疼痛去消解前路無望的疼痛。我在尋找,是不是所有的村莊都發生著東河西營一樣的故事?
2010年8月至2014年6月,我用一本《沒有回家的馬車》、一輛二手自行車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魯西平原尋找東河西營。讀海子、寫詩歌、談戀愛、辦報刊、去遠方……大學四年我用僅夠及格的力氣追隨自己的心。我數次騎行至聊城的東阿、陽谷,平陰的洪范池、泰安的東平湖、舊縣鄉,也曾徒步在邯鄲的長壽村、七步溝、京娘湖……那個名為書院村的地方,曾一度成為我心中的東河西營,時至今日回想起來,那些夏夜的螢火蟲仍可以照亮我心中沉睡的憂傷。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