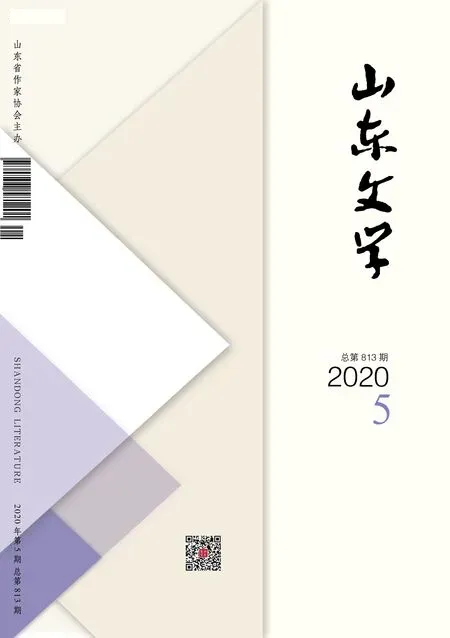四重奏的四個變奏:家庭、感覺、魔幻現實與城鄉
2020-11-19 04:18:06孫恒存
山東文學
2020年5期
孫恒存
一、引言
文學和音樂都是一種線性的時間藝術,二者具有學科交融創新的可能性。而文學音樂學則是這種可能性的一種嘗試。如何在文學音樂學視域看待文學批評與文學作品之間的關系?我們可以通過一個公式來回答這個問題:A+A1+A2+A3+A4。其中,“A1+A2+A3+A4”在音樂理論里面是指四次變奏,但在文學理論視域則代表四篇文學作品或一篇文學作品的四個部分;A在音樂理論里面是主題旋律,而在文學理論范圍則代表著文學批評,文學批評的任務則是揭示審美文本所內含以及如何內含社會現實的,而社會現實既是文學創作的來源又是文學創作的目的;因此,A和A的四次變奏組成一首變奏曲,而文學批評與文學作品則塑造了一支包裹人性和良心的傳聲筒,提供了文學的發言權和話語權,故而二者在更高層面上構成了時代強音的文學變奏。
在文學音樂學理論下,一個非常巧合的事情是2019年度“山東文學獎”的獲獎小說《驚懼》《小千》《最后一根稻草》《狀元村》如同音樂的四個變奏一樣恰如其分地組成了一首變奏曲,而這個變奏曲又是一首四重奏。更進一步說,家庭、感覺、魔幻現實與城鄉則是這首四重奏的四種樂器,四篇小說分別以某個樂器為主并以剩下的其它樂器為輔形成了不同的變奏。因而,它們不是一個主題旋律重復四次,而是同一個主題旋律在不同樂器的音色變換中所進行的四次變奏。這里,我們就是在用這篇文學批評來揭示這個主題旋律,或者說文學批評的本質就是找出這個主題旋律,并跟文學作品一道組成一首完整的主題變奏曲。……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中國新聞周刊(2024年18期)2024-06-07 22:40:49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2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0
紅豆(2022年3期)2022-06-28 07:03:42
文苑(2020年11期)2021-01-04 01:53:20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9期)2019-10-17 02:25:50
現代計算機(2016年12期)2016-02-28 18:35:29
發明與創新(2015年25期)2015-02-27 10:39:23
中國衛生(2014年12期)2014-11-12 13:12:38
西南學林(2014年0期)2014-11-12 13: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