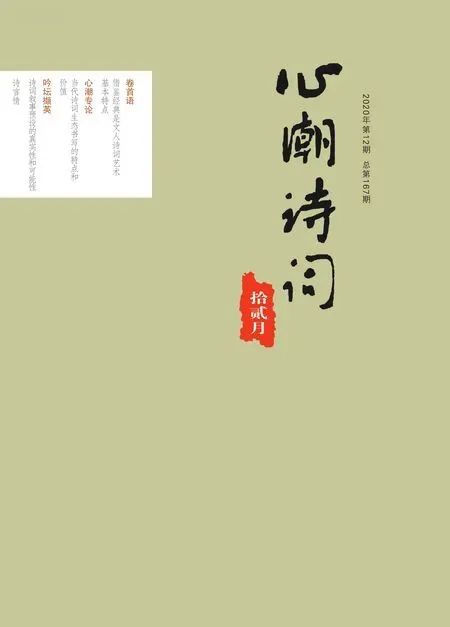詩言情
胡 彭
(作者系《中華詩詞》編輯)
很古老很古老的時候就有先賢說過“詩言志”三個字,后來就有人專門探索這個“志”是什么,于是有了《毛詩》“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的表述。《說文》更細致地解釋:“從心之聲。志者,心之所之也。”《禮·少儀》則舉例:“問卜筮,曰:義歟,志歟。義則可問,志則否。”后又加注:“義,正事也;志,私意也。”
可見古人之“志”,與現代的“志”略有不同,現代的“志”更近乎古人的“義”,古人的“志”更近乎現代的“情”,情志也。
詩言志,用現代語言翻譯一下,就是:“詩,寫的是情。”
情有多種,一言難以蔽之。但善詩的人常說“喜怒哀樂皆可入詩”,此中“喜怒哀樂”四字不是僅指四種情,而是千萬種世間情的縮略。作詩就是表情,言情,道情。一首好詩,必然動人心弦,引人共鳴,令人擊節感嘆。反之,無情之作,不管堆砌多少美麗辭藻,響應多么高尚主題,都不算好詩。所以我在寫作詩詞的時候,最重的就是這個“情”字。力求在每一首作品中,把相關之情寫足寫透。
萬物有情,可及草木,可泣鬼神。就是說天上天下萬事萬物,都有動人之處,都可以被發現并凝練出詩意的精華。至于怎樣去發現去凝練,我有三個方面的感想。
第一在善,看待萬事萬物,須有善良之眼,悲憫之心。詩人行走于天地間,睹天地萬物于目,采天地萬物于心,難免有不喜,有排斥。此時便須善良悲憫,讓自己的心放柔軟,方可容天納地。這樣說有些復雜,但實際上卻不難做到。推己及人即可。畢竟天下事物都有共性,人與自然之間也有一種通感,因為感物生情而生發出或喜悅、或悲哀、或恐懼、或憤怒、或思戀、或憧憬的各種情感,天下皆然。詩人能寫出這種真情感,自有知音遍天下。比如屈原的《橘頌》:“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曹操的《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李白的《渡荊門送別》:“渡遠荊門外,來從楚國游。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月下飛天鏡,云生結海樓。仍憐故鄉水,萬里送行舟。”孟郊的《游子吟》:“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無不是對己對人的悲憫之心所化。自古至今,不勝枚舉。
今年春天,武漢新冠肺炎疫情暴發,突如其來的疫情引發全國人民的愛國之情抗爭之志。抗疫,成了揪人心催詩筆的第一主題。我雖不在疫情中心,但卻無時無刻不把武漢看作第一關懷目標,感同身受:
定風波·和羅輝公原韻致武漢
看似無關最有關,金銀潭亦玉淵潭。天下誰人不惜命,疫病,奈何惡瘧虐當前。 淚臉早隨相思染,江漢,感同五內受笞鞭。痛苦抗爭都在眼,艱險,夢中擁你在身邊。
只有善良悲憫,才能體會他人之喜怒哀樂,才能有包容。善待他人,能得到有愛的作品;善待自己,能得到優美的情詞。
第二在真,以真為體,包括真實之真,純真本真之真。也包括以意念方式存在的真,乃至夢的真。以真為體,除去指詩的感情是真實的,還特別指詩的細節構成是真實可信的。
詩,有形象有意念有寄托。每一首詩詞都有想說的中心思想,有想描寫的景象,想說明的意念,也想引起讀者的欣賞和共鳴。場景可以寫實,也可以虛構出來,但虛構的場景要可信,要栩栩如生,活靈活現。夢中的情景都是活靈活現的,所以莊子“栩栩然蝴蝶也”。李白《夢游天姥吟留別》:“霓為衣兮風為馬,云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這是夢幻中的真實場景,毫無違和感。王昌齡《送柴侍御》:“流水通波接武岡,送君不覺有離傷。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兩鄉。”這是現實中的場景。王昌齡的瀟灑一揮,今年各地運送到武漢防疫物資的包裝上,都還寫著“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兩鄉”。詩的生命隨著它真實的情感、真實的描寫活過了1600年,還會繼續活下去。
王昌齡的《從軍行》:“青海長云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王之渙的《涼州詞》:“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真實的場景,真實的心境,真實的誓言,真實的怨念。王昌齡用優美的詩筆告訴我們,詩的真實該怎么寫。
正因為基于場景真實細節真實的理念,我每作一首詩,總想寫得讓人相信讓人共鳴。比如今年新冠病毒肆虐的上半年,是這樣過來的:
避疫三十三天初次下樓買菜
下樓頓覺一輕松,大好心情謝小蔥!
三十三天嚼枯蠟,街頭辜負柳梢風。
武漢疫情三歸零
年來避疫若昏鴉,一旦清瘟百事嘉。
昨日春風賜三美:綠茶雷筍豆梨花。
4月8日零點武漢解封
茫茫漢水禁孤舟,七十余天煉楚囚。
今日遙瞻放黃鶴,心隨片羽到磯頭。
這是真實的場景。
中秋玉兔小吟
無家卻也遠紅塵,有藥聊能慰主人。
每見女仙攜小寵,星河踽踽自相親。
這是虛擬的場景。
有了真作為體,就如同人有了骨骼血肉的身體,靈魂可以依附,衣服可以穿搭,粉黛可以妝飾。如果場景變成了不合理,情感變成了假惺惺,或許能寫成詩,但不能讓人信服,更不能讓人共鳴。
第三在美,詩的美,是文藻之美,是音韻之美,是意蘊之美。以美為衣,調動一切手段把詩寫得有韻味有詩味,是詩人的追求。
這個美是廣義的美,美學審美中的美,不單指“漂亮”。老子《道德經》有云:“美之為美,斯惡矣。”意即美與丑是對比著存在的。自然界本沒有美丑之分,但是由于人心情的不同,眼前所見景致相同但情味截然不同,也就是說美和丑并不是一種自然現象或者自然屬性,而是人類移情的一種表現,人們會將自己的感情融入客觀存在的對象中,而得到不同的審美體驗。用審美的手段處理詩的材料,遠近、高低、濃淡、繁簡,應用得準確充分,必定是好詩。
杜牧《寄揚州韓綽判官》:“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隱隱”“迢迢”、草木尚綠的江南深秋、有橋有水的月明之夜,簫聲在耳而玉人何處?有聲有色的文字,充分表達了詩人對友人的懷念之情。也許詩人只是一時動念,但這一輪月,照我中華近1500年,這一縷簫聲,在無數中國人心中縈繞至今。李清照的《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云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 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典雅流麗的文字,深沉柔美的相思。700年了,這一種相思,一直還在情人之間無計可消除。這就是詩詞語言動人心弦的美。而魯迅先生的《自嘲》:“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則用冷冽的色調犀利的筆鋒、用“破帽”“漏船”這等“不美”的詞語,記錄了動亂時代的文化人的憤怒和無奈。
我不知道是否寫出了自己想寫的美。熱烈的,清泠的,喜悅的,憂傷的……文字中自有色香味形聲,就如自然界的繽紛繁復的材料。所謂剪裁,對于裁縫師來說,是尺寸,是版樣,是配色;對于詩人來說,是格律,是聲韻,是節奏掌控。
且試著料理一下:
初見羅平油菜花海
身在羅平錦繡叢,深金淺碧畫圖中。
翩然一似莊生蝶,誤入瑤臺第幾宮。
過小雞登入十萬大山一嘆(新韻)
尋常夢不到滇東,入目最奇峰若叢。
山水撩人名亦好、大雞登與小雞登。
注:小雞登、大雞登均為當地彝族音譯地名。
也曾直抒胸臆:
三姝媚·聽敦煌人扮漢將軍執戟誦“不破樓蘭終不還”
樓蘭沉久矣!剩漫漫黃沙,渺無邊際。縠縐新平,又被風旋起,踏波隨履。疏勒荒煙,縈漢壘、其名還是。示警烽臺,拒敵關樓,可憐都毀。 古道西風凄厲。掩壯士刀弓,帝王符璽。佛窟多情,畫節旄高簇,漢家天使。青海長云,遙望處、詩心如熾。一卷滄桑,最懷邊塞,最傷變徵。
也曾因某些丑陋現象憤怒過:
【雙調·對玉環帶過清江引】網絡暴力
爪印霜痕,都在網上留。微友玩家,無非網上囚。須提防造謠生事兒的頭,翻云覆雨的手。你是英雄?管教你英雄秒變狗。你是紅人?管教你紅人秒變丑。 他設個局假假真真引領悠悠萬眾口,你撇不清是是非非想躲怎能夠?沒羞臊成“裸奔”,沒來由被“人肉”,說白了你是被指名道姓群毆群揍百度谷歌無縫搜。
我的詩詞曲都比較追求淡色調。少用典故,不作驚人蹊蹺語,只求節拍明亮通透易懂即可。而且我的詩詞曲多是言情小作,“婉轉詩成封小箋,多情耽美杏花天”(七絕《有所思》)是我自認的風格。“此身合共頑冰老,此地長留春夢好。動人顏色不須多,占斷風流何恨少”(《玉樓春·詠臘梅》)是我自許的堅持。也許,有了這種堅持,可以讓詩心有寄,讓生命升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