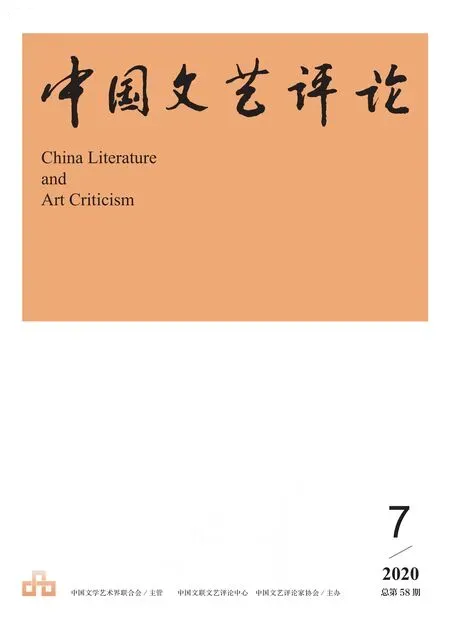中華曲藝如何再創時代新經典
鮑震培
由于歷史上崇雅貶俗的社會文化心理,曲藝長期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的“玩意兒”,曲藝人很少考慮經典的問題,曲藝理論界也較少以此命題進行專門研究。當中央文史研究館提出要編寫《中華曲藝經典百篇》的時候,我們才發現,在曲藝幾千年的發展歷史長河中,蘊藏著浩如煙海的經典,遠遠不是百篇所能概括的。總結中華曲藝經典,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大工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從文獻價值來看,從古代變文到明清曲藝,再到民國時期和當代的優秀曲藝作品,其中收集到的文字材料、圖像資料都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從現實需要來看,無論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普及,還是作為曲藝教育教學的參考,甚至是對提高曲藝界的文化自信都有重大意義。曲藝經典應當成為曲藝創作的標準和范式。在編寫《中華曲藝經典百篇》的過程中,專家們發現,經典往往是經過長時間的藝術實踐后才能達到藝術至境,“一遍拆洗一遍新”這句有名的藝諺正是揭示了曲藝經典化的過程,重排曲藝經典在活態傳承中有著現實意義。本文希望通過對曲藝經典的特征、曲藝經典的形成機制及經典化問題等方面的探討推進研究的深入。
一、曲藝經典是薪火相傳的藝術精品
“經典”一詞古已有之,漢代許慎《說文解字》中解釋:“經,織也”,“經”是紡織時縱向的紋路,南朝梁時期劉勰所著《文心雕龍》的《宗經第三》中這樣解釋“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1][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譯注》,王運熙、周鋒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頁。即所謂“經”是亙古不變的根本道理,不可改變的偉大教導。經學指儒家之學,如《詩》《書》《禮》《易》《春秋》五經之屬,佛教、道教也以教義書籍為某某“經”。“典”的本意為常道、法則。《爾雅·釋詁》中說:典,常也。“經”“典”合并在一起,在《辭海》和《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解釋大致相同,即“最重要的有指導作用的權威著作”和“古代儒家的經籍,也泛指宗教的經書”。在英語中canon(經典)出自希伯來語,表示“規范”“規則”,也指古希臘羅馬文獻,意思是被視為典范的或傳統的東西。
經典是客觀存在的,是歷時性的。論述什么是曲藝經典,可以參照文學研究界比較通行的對文學經典的界定。有的學者提出典范性、權威性、思想性、文學性四條標準;有的學者指出經典作品具有超越時空的永恒性,無限的復讀性等;也有的學者認為經典應該從原創性、陌生化角度去衡量。與以上“本質主義”下的經典觀不同,“建構主義”下的經典觀認為經典與時代性、歷史性、民族性等因素密切相關,沒有普遍適用的價值標準,一部作品能夠成為經典,除了源于文本自身所蘊含的豐富的文化信息與情感外,也與它在歷史發展中被不斷挖掘、提煉的新內容有關。所以對經典的界定是具有一定主觀性和當代性的,經典延續的語境更為重要。
2003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庫切在《何為經典——一個經典演講》中說:藝術經典有不少是經歷了野蠻攻擊而得以劫后余生的幸存者,“幸存是因為數代人不愿放開緊握住它的手、忍眼看它就此流逝,以至于無論付出何種代價都愿一直將它保留著——這即真正意義上之經典”。“如果不是經典之作,那么在一個音樂家的生命終止之后,專業人士將不會一代接一代地付出精力和勞動去保存其作品。”[1][南非]J.M.庫切:《何謂經典——一個經典演講》,吳可譯,《外國文藝》2007年第2期,第126頁。庫切演講中的這段話指出了經典對于人的重要性,真正的藝術經典會有“一代接一代”的薪火傳遞,除了經典本身具有的客觀性外,還有后代人為傳承經典主動付出精力和勞動的主觀性,故而永久性或長期流傳成為了經典最顯著的特征。比如評話和評書《三國演義》、相聲《扒馬褂》、京韻大鼓《劍閣聞鈴》、單弦《杜十娘》、蘇州彈詞《珍珠塔》等都因為是藝術中的經典,一代又一代的曲藝人將其薪火傳遞、久演不衰。
筆者認為,曲藝經典是具備原創性、思想性、藝術性,流傳相對永久的作品。精品不等同于經典,精品是指藝術質量高的作品。凡經典都是精品,但精品不一定能夠成為經典。
二、曲藝經典藝術特征豐富且鮮明
1.原創性
曲藝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溯源于先秦時代,形成于漢唐時期,經過歷史的淘洗,留下來的古代曲藝文學有很多已屬經典。無論在大眾情感的抒發方面,民間智慧的總結方面,漢語口語的運用方面,民族的歌唱、演奏方面,古代曲藝文學都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比如唐代變文、宋代話本、鼓子詞、金元諸宮調、宋元平話、明代詞話、清代的彈詞和子弟書等曲藝文獻文本,其原創性程度都很高。再如唐代“弄參軍”的《三教論衡》可以視為我國相聲最早的濫觴,敦煌寫本《目連變文》成為后世所有目連戲的母體,《王昭君變文》是最早說唱昭君故事的曲藝,在南音、梅花大鼓等許多曲種中都保留了此曲目。宋代說經話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之于小說《西游記》,元代說書人的記錄《三國志平話》之于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金代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之于王實甫《西廂記》,明代《明成化說唱詞話叢刊》中包公系列詞話之于小說《三俠五義》,無不體現了曲藝的首創之功。雖然我們現在看不到當時的音像資料,但僅僅根據這些曲藝文本文獻便可以斷定它的經典性,可以說,曲藝是創造了古代的文學、藝術經典的藝術形式。
在搜集、整理或評估古代曲藝文獻時,原創性應是界定經典的第一標準,其蘊含的經典意味或是曲藝文學體裁的雛形,或是曲藝音樂范式的草定,或是某種故事題材、人物形象的選擇,或是價值觀和思想情感的呈現,或是綜合以上所有達到的真善美的境界。有的原創作品可能在藝術上相對粗糙、單調,如鼓子詞《元微之崔鶯鶯商調蝶戀花》,但它是最早的曲牌連綴體曲藝,在音樂體制上作為諸宮調前身,有不可磨滅的經典意義。有的原創作品起點頗高,如宋元話本《快嘴李翠蓮記》《西廂記諸宮調》,清代子弟書《憶真妃》,彈詞《再生緣》,木魚書《花箋記》《二荷花史》等,都是曲藝文學史上“兀立的高峰”,對后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快嘴李翠蓮記》塑造了一個反抗封建包辦婚姻的具有喜劇性格的女性形象,李翠蓮的潑辣、明快在后世的傳統曲藝中可以找到不少影子。還有的原創作品,經歷了發展演變的“經典化”過程,如明代詞話《鶯哥行孝義傳》,講述的是民間廣為流傳的一只會作詩的鸚鵡孝母的故事,經過了明清兩代南方地區曲藝曲種“宣卷”《鸚哥寶卷》和河西地區曲藝曲種“念卷”《鸚哥寶卷》的發展,塑造了鸚哥不屈從于強權和皇權的反抗性格,在西北甘肅青海地方曲藝曲種“賢孝”中形成了《白鸚哥吊孝》這一經典曲目,至今傳唱不衰。
相聲是扎根民間、源于生活、深受群眾歡迎的曲藝表演藝術形式。傳統相聲主要指清末至1949年期間演出的作品,總數在200段以上。傳統相聲具有高度發達的原創性,即使有的創編思路或來自歷代笑話,或來自民間神話、故事、傳說等,其中的創作成分仍占很大比例。相聲鼻祖朱紹文憑著他“滿腹文章窮不怕”的文化功底,創作出白沙撒字(舊時演出習俗)的《字相》,后來教徒弟合說對口相聲,其創作的《三近視》《千字文》《大保鏢》等對口相聲,至今還在舞臺上表演。即使是單口相聲也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講故事,而以幽默風趣的喜劇性貫穿始終,在嬉笑怒罵中針砭時弊。單口相聲大師張壽臣和劉寶瑞都有很多原創作品傳世,如張壽臣的《化蠟扦兒》《賊說話》《洋藥方》等,劉寶瑞的《珍珠翡翠白玉湯》《假行家》《連升三級》等,堪稱傳統相聲的經典。大部分的傳統相聲并未署名,民間文藝的集體性特點決定了這些經典作品是藝人群體長期實踐和傳承的結果,是嘆為觀止的中國民間智慧的結晶。除此之外,相聲還具有鮮明的時代感,不光傳統相聲記錄、描摹了過去的社會百態、人生百相,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新相聲作品——從20世紀50年代的《夜行記》《買猴兒》,到改革開放以來的《如此照相》《虎口遐想》《五官爭功》《巧立名目》等精品佳作——也很好地反映了當下的時代變化和民情人心。
2.地域性
曲藝經典的地域性特征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摹地方之景、敘地方之事。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扎根民間的曲藝,作為民眾喜聞樂見的文藝形式,鮮明的地方特色與生俱來。講述地方傳說、演繹地方風情的作品在很多曲種中占有重要位置。比如福建泉州、福州、廣東潮州一帶喜唱南音,其最經典的作品是《陳三五娘》,講述泉州人陳三在潮州與五娘邂逅的愛情故事,與地方戲潮劇《荔鏡記》形成互文。溫州鼓詞《陳十四》(《南游傳》)講的是流傳于浙南與閩北的民間神祇陳靖姑的事跡。彈詞中的《珍珠塔》源于蘇州吳江同里鎮,《三笑》說的是蘇州明代吳中四才子的故事,《白蛇傳》敘述了流行于杭州西湖的白蛇、青蛇和許仙、法海的恩怨糾葛,《楊乃武與小白菜》講述了清末發生在杭州余杭縣的真實冤案。揚州清曲中的《水漫金山》描繪了白蛇與法海在鎮江金山寺長江畔發生的一場“水斗”。湖南漁鼓中的《乾隆訪江南》講唱清代乾隆皇帝微服私訪下江南,扶危濟困的喜劇故事。福州評話中的《蝦米俤》講的是鄉下漁民在福州賣蝦米喜結良緣的故事。揚州評話《皮五辣子》描繪了一幅幅揚州市井眾生的風俗畫。數來寶《同仁堂》唱頌北京城里的各種買賣鋪面。南京白局《采蘆蒿》《金陵遍地景》唱的是江南名城南京的優美景色。山東快書《武松打虎》《武松打店》唱的是《水滸傳》中山東好漢武松的故事。二人臺《走西口》《五哥放羊》則以塞外風光作為敘事背景。還有東北二人轉、河南曲藝、京津冀曲藝、四川曲藝,及各地方曲藝中都有大量結合本地風土人情的代表作品,這是曲藝服務于地方文化這一特點所決定的。
二是說地方之言,唱地方之調。曲藝是方言的藝術,但這種方言并不拘泥于某個地方的語音。曲藝方言是經過提煉加工的、藝術化的方言,是在保持地方語言特色的同時,最大限度拓展觀眾群的方言。如京韻大鼓從河北木板大鼓衍變而來,一開始用河北方言演唱,被天津觀眾戲稱為“怯大鼓”,而后有人用天津方言演唱,出現了短暫的“衛調大鼓”的階段,繼而劉寶全等人對此進行改良,用北京語音演唱,因而獲得了京津冀廣泛的觀眾群,遂定名為京韻大鼓,形成劉派、白派、駱派、少白派等,各派擁有不同的經典曲目。如劉派的《長坂坡》《戰長沙》《大西廂》,少白派的《紅梅閣》,駱派的《劍閣聞鈴》《俞伯牙摔琴》,白派的《黛玉焚稿》等“紅樓段兒”。其中白派傳人閻秋霞用河間語音語調演唱,有別具一格的韻味,形成了特有的經典曲目。一些使用方言的評書、快板、相聲等也以獨特的語言親和力贏得聽眾,如山東快書、四川評書、大同數來寶、海派相聲等,方言特色十分鮮明。由此推斷,在方言漸行漸遠的現代社會中,曲藝經典的傳承因具備了保護地方方言這一非遺功能將備受重視。此外,曲藝音樂唱腔是以語言為基礎的,依字行腔、依情走腔、一曲多用。所謂“字正腔圓”,字正是咬字要正,不管是方言還是普通話,音調都要到位。和京劇、昆曲、地方戲相比,曲藝演唱的上口音少,方音不僅用于對話,也用于敘述,所以方言特點更加濃郁。如果減少方言味道,曲藝音樂也就失去了獨特的韻味,致使一些經典曲目在傳承中出現“走味兒”“沒味兒”的現象。
三是展地方之習性,觀地方之民俗。曲藝經典體現了與當地人性格相協調的審美情趣和審美特征,比如蘇州彈詞的細膩、糯軟,陜北說書的粗獷、火熾,南音的古雅、悠遠,粵曲的深情、婉轉……拿評書評話來說,北方多袍帶書,南方多世情書,北京人好說“三國”“西漢”,天津人好說“聊齋”“三俠五義”,東北人好說“隋唐”“岳飛傳”,四川人好說市井滑稽等。總之,曲藝的傳統經典也好,新經典也好,其鮮明的地方特色是不可小覷的特征。另外,曲藝的民俗性在少數民族地區體現為民族性,嶺仲藝人說唱的《格薩爾王傳》是藏族史詩,瑪納斯齊說唱的《瑪納斯》是新疆柯爾克孜族史詩,陶力或烏力格爾藝人說唱的《江格爾》是蒙古族史詩,這三大史詩堪稱史詩典范,在世界上都有很高的地位。朝鮮族盤索里的《春香傳》和《沈清傳》亦是流傳了六百多年的經典。少數民族曲藝使用少數民族語言進行表演和傳承,從中華曲藝整體發展來看,還需加強漢譯工作,才能更好地實現少數民族曲藝經典的傳播和研究。
3.互文性
曲藝的前身是“百戲”,從它誕生之日起,就是具有包容性的藝術形式,如同海綿吸水般汲取各兄弟姊妹藝術的養料,所以有特別明顯的互文跡象。在單純曲藝文本中的互文是指曲藝與小說、戲曲的互文現象,突出表現在曲藝對小說和戲曲的改編、加工、轉化,其中有的改編是創造性的。按照高頻率互文的出現,曲藝與小說、戲曲互文可用六部名著作為板塊來概括,它們是:《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西游記》《西廂記》和《聊齋志異》。另外,宋元以來的所有說部,按照講史(袍帶書)、公案(短打書)、煙粉(世情書)、神魔、靈怪、傳奇等題材劃分的古代小說,幾乎被一網打盡地改編成曲藝的書(曲)目,或唱或說,或長或短,地域不限,形式各異。一部《賣油郎獨占花魁》,可以是評書,也可以是東北二人轉,還可以是南京白局、鐵片大鼓、蘭州鼓子等。
曲藝互文性經典首推《三國》。《三國》無疑是最有曲藝緣的一部書,它的母體本來自曲藝——依據對宋代“說三分”技藝的考究,宋元時已有說書人的簡約記錄本,即《三國志平話》。自明代羅貫中寫出《三國演義》之后,北方評書、南方評話都喜“說《三國》”,多數的大鼓書、四川揚琴、四川竹琴等都有《三國》段,曲目繁多,其中不少是經典曲目,如《古城會》《長坂坡》《草船借箭》,等等。再說《水滸傳》,屬于英雄傳奇類。評書和評話都有《水滸傳》書目,揚州評話藝術家王少堂擅說《武松》《宋江》。山東快書原被稱為“說武老二的”,就是因為它以說武松故事為主,有《武松打虎》《魯達除霸》等經典。單弦中有曲目《武十回》,各地鼓曲中也有《武松打虎》《楊志賣刀》《野豬林》《林沖夜奔》等許多經典曲目。曹雪芹的《紅樓夢》作為中國古典小說的巔峰之作,其在民間的流傳和接受,曲藝發揮了很大作用。早在清代的子弟書中就有大量《紅樓夢》題材的作品。在木板大鼓、京韻大鼓、梅花大鼓、河南墜子、奉調大鼓、蘇州彈詞等諸多曲種對《紅樓夢》的演繹中,《黛玉葬花》《黛玉焚稿》《寶玉哭黛玉》《寶玉娶親》《祭晴雯》《寶釵撲蝶》等曲目成為膾炙人口的曲藝經典。《西游記》的曲藝改編之作雖不是很多,但過去評書評話中皆有大書說《西游記》全本,樂亭大鼓、西河大鼓等有曲目《大鬧天宮》,徐州琴書等有曲目《豬八戒拱地》,二人轉有曲目《高老莊》,快板書有曲目《孫悟空三打白骨精》,這些曲目都來源于小說中最精彩的情節,改編后成為了與小說互文的曲藝經典。《西廂記》源于唐傳奇,經過說唱諸宮調《董西廂》后發展為王實甫元雜劇名作《西廂記》,這一古典愛情喜劇經典表現在長篇曲藝作品中有蘇州彈詞《西廂記》,名家楊振雄能說50回之多,被譽為“楊西廂”。短篇曲藝名段則有京韻大鼓《大西廂》,二人轉《西廂觀花》《西廂觀畫》,樂亭大鼓《拷紅》,梅花大鼓《十字西廂》等,把張生和崔鶯鶯的愛情故事作為古代自由戀愛的范本,不斷用各種藝術手段演繹出來。《聊齋志異》是清代蒲松齡獨創的文言小說集,自清末宗室德月川將《聊齋》改編為評書后,出現了董云坡、張致蘭等名家,基本上采用照本宣講的說法。陳派評書創始人陳士和取諸家之長,借鑒前輩說書家的藝術經驗,對《聊齋》數十篇內容進行再創作,成為近代《聊齋》說書藝術的集大成者。他一改傳統說法,用通俗語言說講世俗之事,重人情事理,善于使扣子,使人百聽不厭。陳士和一生說《聊齋》51段,名段有《畫皮》《嶗山道士》《夢狼》《席方平》《辛十四娘》《張鴻漸》等。另外單弦也有不少名家擅長演唱《聊齋》改編的曲目,如《水莽草》《胭脂》《巧娘》等。
除此之外,評書評話中的《東周列國志》《西漢演義》《東漢演義》《隋唐演義》《岳飛傳》《大明英烈傳》《封神演義》《包公案》《濟公傳》等,均與小說、戲曲形成互文。盡管在文學史中有些作品不在經典之列,但并不妨礙改編為曲藝之后成為了經典之作代代相傳。除了長篇的“大書”以外,短篇書(曲)目如《姜子牙賣面》《韓信算卦》《羅成算卦》《楊八姐游春》《樊金定罵城》《雙鎖山》《草橋斷后》等,都是久演不衰的優秀傳統書(曲)目。
研究曲藝互文性的意義正在于曲藝擅于借鑒各兄弟姊妹藝術或其他門類藝術,借勢而上,實現優質創新路徑。由此可知,曲藝在演繹經典的同時也創造了經典。
4.藝術性
自清朝到民國,曲藝藝術發展達到鼎盛,突出表現為曲種大繁榮,并且每個曲種都產生了代表性的藝術精品,即我們現在所說的傳統書(曲)目,這些作品呈現出文本文學性強、敘事與抒情結合、藝術手段豐富多彩的藝術性。與戲劇藝術相比,曲藝以演員敘述性表演說唱故事,同時具有非常鮮明的抒情特色,達到了以訴諸于聽覺藝術為主的藝術高峰。曲藝理論家薛寶琨總結曲藝的兩大藝術特征是“敘述性”和“抒情性”。[1]胡孟祥主編:《薛寶琨說唱藝術論集》,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9年,第19-35頁。
曲藝中,好的唱詞講求雅俗共賞的文學性,運用了“合轍押韻”“貫口”“垛字句”“對仗”“聯喻”“雙關”等諸多修辭手段。如西河大鼓《玲瓏塔》,上海說唱《金陵塔》,河南墜子等曲種的《王婆罵雞》,青海賢孝《老鼠告狀》,河南墜子《借髢髢》,紹興蓮花落《借大衫》,湖北小曲《蘇文表借衣》等,無不巧言之,善辯之,對口語語言藝術的運用達到淋漓盡致、詼諧風趣的藝術境界。曲藝是敘事藝術,無奇不傳,傳事之奇,傳人之奇,傳人之常情,演悲歡離合,抒七情六欲。拿評書來說,運用了“開臉兒”“賦贊”“擺砌末”“明筆”“暗筆”“伏筆”“驚人筆”“倒插筆”“書中扣”“蔓上扣”“連環扣”等豐富技巧,醒木一拍壓四座,藝不驚人死不休。
對比戲曲,曲藝作品更擅于片段式敘事,往往截取生活片段,濃墨重彩地表現人物思想感情,在尖銳的戲劇沖突中刻畫人物心理活動,如同影視劇里的感情戲、內心戲。如東北大鼓《憶真妃》及京韻大鼓《劍閣聞鈴》,唱出了唐明皇既悔且哀,以及對楊貴妃的無限思念之情。河南墜子《楊家將·砸御匾》中,佘太君怒斥謝金吾不該砸御匾,痛說楊門一家“征戰英烈史”,一方面表現她保家衛國的赤膽忠心,另一方面表現她痛失親人的悲憤之情,感情真摯、感人至深。類似的還有《鞭打蘆花》《昭君出塞》《藍橋會》等,優秀曲目不勝枚舉。還有岔曲《風雨歸舟》、京韻大鼓《丑末寅初》、天津時調《放風箏》、四川清音《小放風箏》、南音《客途秋恨》、粵曲《再折長亭柳》等,都是傳唱至今,令聽眾為之癡迷的傳統曲藝經典。
綜上所述,通過對曲藝經典的四個主要特征“原創性、地域性、互文性、藝術性”的研究,可見其內在藝術機制富有獨特的規律性,也構成這門藝術向前發展的動力系統。曲藝的經典化欲照此機制運行,就要注重原創,講求內容為王,堅持地方特色和民族審美情調,汲取多種文藝形式營養,守正創新,凸顯曲藝的藝術特征。
三、新時代下曲藝的經典化與再生產
梳理、探討曲藝經典,可以為當下曲藝精品創作提供參照系,這也是曲藝非遺“活態”傳承所必須開展的工作,要實現曲藝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需要解決曲藝經典化過程中的以下幾個問題。
1.價值重現為經典化拓寬路徑
一方面,對經典的研究是對既有優良文化傳統的認定,對優秀文化因子的闡釋,這關乎文化自信的建立和文化傳統的傳承;另一方面,藝術作品從潛在的經典發展為既定的經典,其不斷的經典化是推動文學藝術隨時代發展而創新的重要動因。經典是與時俱進的,每一個時代都會面臨經典的重新界定、重新發現與弘揚,而重新發現與弘揚則意味著在價值觀層面的時代傳承。例如明代文學家徐渭的詩、書、畫及雜劇創作,荷蘭畫家梵高的畫作等都是經歷了當時的默默無聞,在后世被人發現其蘊含的偉大深刻的思想價值而成為經典的。尤其是對于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新創作品來說,必須經過一個經典化的過程才能留下來、傳下去。在這一過程中,對作品價值的重新發現十分重要,比如這些年對家風家訓、中華孝文化、年節文化、反腐倡廉等風氣的推廣、弘揚,使一些曲藝名段重新被召喚、被復排,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歡迎,使曲藝經典煥發出新的光采。京東大鼓《白雪紅心》原是文藝作品中較早創作的歌頌焦裕祿愛民為民這一公仆精神的作品,近年來從曲藝家董湘昆的原創百段作品中脫穎而出,成為當下傳唱率最高和最受歡迎的曲目之一;西河大鼓《魯班學藝》中呈現的魯班專注、專研、創新、創造的能工巧匠精神,在時下弘揚“大國工匠”精神的背景下被賦予了新意;鞭撻現實生活中不孝行為的鐵片大鼓《良心》,在弘揚中華“孝道”精神、扶正家風家訓的行動中廣為流傳,等等。原創佳作越具有傳唱性,證明其越能經受時間的考驗,經典化的程度也就越高。曲藝是一種具有鮮明時代烙印的藝術形式,雖然與其他一些藝術相比,并不那么高深和富于前瞻性,有些作品會因時過境遷被淘汰,但它堅持以平易、樸實的風格講述中國故事、展現中國精神,其價值力量日積月累,隨著時間的推移將不斷涌現經典。
2.題材創新為經典化賦能
作為當代曲藝家,原創精品意識必不可少,由此才能創作出賦有經典因子的精品力作。凡原創精品以內容為王,故題材創新可為曲藝經典化賦能。當代曲藝創作題材的自由度很高,可以有文化民俗題材、現實生活題材、革命歷史題材等。其中反映20世紀以來中國社會劇變的革命化敘事內容,集中體現了中國人民在實現民族獨立自由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的偉大斗爭,是中國人民在20世紀的集體記憶結晶,這種特定題材在學術界往往用“紅色經典”涵括。2011年《曲藝》雜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時推出90篇曲藝經典名錄[1]《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 新中國曲藝經典作品90篇名錄》,《曲藝》2011年第7期,第18-20頁。,其中大部分是在新中國成立后產生的最能夠代表和反映廣大人民思想感情和生活愿景的優秀作品,它們深深植根于新的曲藝土壤中,被中國人民偉大的革命斗爭實踐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生活洪流所激活。如陜北說書《劉巧團圓》《翻身記》,評書《肖飛買藥》《許云峰赴宴》,快板書《劫刑車》,京韻大鼓《黃繼光》《羅盛教》《韓英見娘》,單弦《地下蒼松》,湖北小曲《江姐進山》等,無不洋溢著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而以現實生活為題材的相聲《夜行記》《買猴兒》《昨天》《五官爭功》《虎口遐想》,四川清音《布谷鳥兒咕咕叫》,河南墜子《摘棉花》,彈詞開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快板《天安門前看升旗》,天津時調《軍民魚水情》等,有的反映社會主義建設的進程和成就,有的歌頌融合的新型軍民關系,有的以喜劇的方式和昨天告別、和不良傾向作斗爭。這些經典的書(曲)目既是社會主義偉大時代前進的記憶,也是當代人民努力奮斗生活的寫照。由此可見,涵蓋革命斗爭歷史和社會主義實踐這一內容的“紅色經典”,是高度反映廣大人民思想感情和生活愿景的優秀作品,具有旗幟鮮明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強烈的教育引導功能。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邁向新征程的今天,傳承、傳播、研究這些曲藝“紅色經典”,并沿著這一創新之路繼續創作原創精品,對促進和實現“中國夢”有著積極的作用。任何對主流文化語境抽離和顛覆的創作,對英雄形象消解和消費的創作,都是曲藝藝術發展中的逆流,終不能阻擋曲藝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展示中國精神、中國力量的前進步伐。
3.堅持人民性為經典化導航
當下,文藝的創作導向事關精品的產生,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1]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4年10月15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頁。,這一方針繼承了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總結出的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是在文藝活動中一貫堅守的創作原則。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指出:“社會主義文藝是人民的文藝,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進行無愧于時代的文藝創造。”[2]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35頁。要做到以人民為中心,首先要深入了解和反映人民的生活,現實生活永遠是文學藝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尤其是曲藝這樣的通俗文藝,更與大眾生活無縫對接,但反映生活并非是原生態的呈現,而是要高于生活,實現藝術真實。而要做到藝術真實,就要從生活中提煉出鮮明的價值取向和思想感情,這些觀念和情感只有跟人民群眾的所思、所想合拍,才能引起觀眾思想和情感的共鳴,贏得他們的喜愛。正如姜昆所說“你離人民有多近,人民對你有多親”[3]來源于2019年5月6日在青島舉辦的全國曲藝聯盟首期專業素養提升班上,中國曲藝家協會主席、相聲表演藝術家姜昆所作的《你離人民有多近,人民對你有多親》專題輔導講座。。有的人認為曲藝藝術形式簡單、創作門檻低,把“接地氣”的人民性僅僅理解為“娛俗”,這種理解是片面的。好的作品光有“接地氣”的真實是遠遠不夠的,要成為經典,還必須擁有“善”和“美”的高度,這是由藝術家的時代感和立場決定的。我國文藝理論家黃藥眠曾說:“文學中的人民性是歷史的范疇,因此它所包涵的具體內容,也隨著社會形勢發展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有在人類童年期的古代敘事詩中的人民性,有古代奴隸制度時期作品中的人民性,有資產階級興起時期作品中的人民性,有革命民主主義的人民性。”[1]黃藥眠:《論文學中的人民性》,《文史哲》1953年第6期,第34頁。雖然都是反映生活的真實,但時代不同、立場不同、站位不同,所達到的對社會的認知理念和所呈現的價值觀就有很大的區別。如果單純追求娛樂噱頭,思想意識滯后,混淆善惡是非,作品的美學品位就會大打折扣。因此對作品具有的人民性的要求是“講品位、講格調、講責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2]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35頁。。只有做到符合“真、善、美”的人民性,才能產生無愧于偉大時代和人民的新經典。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歌謠文理,與世推移”[3][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譯注·時序》,王運熙、周鋒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11頁。。我們研究經典不是固守著老祖宗留下的遺產孤芳自賞,而是要實現傳統藝術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優質作品的經典化離不開時代傳承,即審視和思考當代社會思潮的特點,不斷深化中國故事的內涵,為敢于擔當、不辱使命者謳歌,鼓舞人民奮發有為實現中國夢。“曲藝的經典化是一個傳承與創新的對立統一、相輔相成的過程。曲藝之所以到今天仍散發著藝術的幽香,就是因為她在傳承過程中不斷創新發展,并向經典化的愿景邁進。”[4]周思明:《經典化:曲藝向上向善的美學通衢》,《曲藝》2019年第11期,第42頁。“雛鳳清于老鳳聲”,老樹新枝更著花。曲藝不僅僅是非遺藝術,更是鮮活的當代藝術。在新時代的長征路上,讓曲藝聲音唱響中國故事,讓曲藝經典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大顯神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