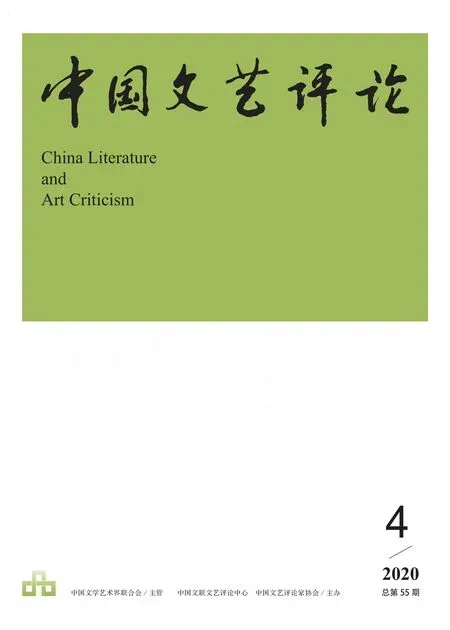電影改編:借用還是生發?
蘇妮娜
電影,既古老又正值青春。它是人類最重視的講故事能力的當代續航,也源于“20世紀的大部分歲月里,電影一度是工業、后工業社會最大的娛樂”。[1]戴錦華:《電影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前言”,第5頁。迄今為止,電影票房的收入及每年電影銀幕的數量仍然持續增長,證明上述論斷中的20世紀的盛況已經延續到了21世紀。與這種盛況相悖的是劇本荒。劇本荒的狀況曠日持久,需求持續增長與供給始終不足,使這一矛盾愈演愈烈。在這種情勢下,編劇的創作能力,或稱“內容輸出”能力就一再受到關注。就現狀來說,編劇有兩種來源,一種是原創,另一種是改編。要解決劇本荒的問題,原創力需大幅度提升,但原創力絕非創作者與研究者加以呼吁或開出“藥方”就能在短期內得到提升。現實是“講故事這門手藝日漸失傳”[2][美]羅伯特?麥基:《故事:材質?結構?風格和銀幕劇作的原理》,周鐵東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頁。,既然這一狀況無法根治,那么只能暫圖緩解,改編就是用其他敘事作品的“遠水”解原創力不足的“近渴”之道。
一、如何看待改編?
當下,人們在評價原創與改編這兩種形式時,常常會出現一種相互比照、各取其徑的情況。似乎所拍劇本居于原創位置的是用一種評價尺度,來源于改編的便置于另一種尺度中。從創作的應有之義來看,原創能體現出創作者的創作精神,然而目前具備寫作劇本這一原創能力的導演只是一小部分人。綜觀當下電影界,集編劇與導演能力于一身的電影人,例如賈樟柯、徐浩峰、刁亦男、畢贛等都屬于少數,而且這些有著“電影作者”跡象的導演,也比較集中于小眾的文藝片領域。
在更加廣闊的類型片領域,改編——無論是脫胎于文學作品還是其他藝術文本——為電影創作提供藍本,已經成為一種通行方式和主流。那么不妨設問,難道改編中就不需要原創嗎?改編自然要在“改”上下功夫,但它仍然側重于“編”,“編”始終是它的主體。改編是編劇的一種形式,較早適用于電影、電視、戲劇,如今還包括游戲等以敘事為主,又必須經過導、表、演加以呈現的藝術形式。改編從來源角度可分為兩類:一種是電影、電視、戲劇、游戲等向文學“借”故事,另一種是電影、電視、戲劇、游戲中好的故事資源彼此互用、共用(也被稱為翻拍)。其中,前一種改編在國內外的電影行業中占較大比例,例如奧斯卡的最佳改編獎中,每一屆的入圍名單90%以上都出自文學作品。[1]嚴前海、黃文英:《奧斯卡與文學:權力裝置的媒介關系》,《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7年第4期,第92頁。國內的情況與之類似,有人例舉:截至2014年12月23日,“在國內票房前60名的中國電影中,從文學改編而來的有22部,與文學保持了緊密關系”[2]陳林俠:《當下中國電影的改編問題與文化競爭力——兼及電影與文學的關系》,《中州學刊》2015年第6期,第157頁。。但第二種改編也十分常見,并引起熱議,我們時常會看到關于經典作品翻拍的N個版本得失優劣的對比。可見,在翻拍行為中,觀看者觀看的重點已經從“看故事”演變成了“怎么改”“怎么拍”“怎么演”,既涉及大眾文化接受心理中的審美變遷,也將編、導、表、演等二度創作中的創作重點、創作能力問題推到了全體觀眾矚目的前臺。“翻拍中我們在看什么”——這似乎構成了又一種景觀,在此暫不涉及。
改編是實踐中出現的創作行為,牽涉到復雜而廣闊的領域。它一端連接著原創作品意義空間的再次生發,另一端連接著觀眾欣賞和接受的期待視野,以及這種期待視野與創作理念不斷的生長、變化、遷移。作為一個實踐維度的問題,必須放置到實踐中去考察,經受現實的檢驗。改編與原創都是創作,其難度和立場本該不分軒輊。
如果說原創是從無到有的一種“發明”,那么改編則意味著“衍生”和“使用”,由再次創作的形式、來源決定。向文學借故事的這種改編,看上去是文字體例和表達屬性的轉換,似乎只要故事內容而已,即“核”沒變,改變的只是“外殼”、形式。然而藝術內容的講述、藝術語言的轉譯、藝術形式的切換,遠非新瓶裝舊酒這樣簡單。歸根到底,藝術的形式本身就是藝術的內容,并不存在那種完全剝離內容類似容器一般獨立出來的藝術形式。這就要求我們充分理解改編的復雜含義與操作難度——事實上,它已經超越了原創的復雜與難度。
將文學作為來源創作劇本,可以視為文學作品向同樣是以文字呈現的戲劇作品的轉換,始終沒有脫離文字這個“殼”,是一度創作范疇中的轉換。[1]本文中,一度創作指創作用于電影拍攝的劇本、文字腳本的過程,二度創作指把一度的文字呈現通過導演、表演、拍攝、排練等呈現為戲劇、電影、電視作品的過程。轉換的是內在模式,從閱讀中的“傳達—接受”模式向觀看中的“傳達—接受”模式切換。這方面的例子眾多,如常有人指出,嚴歌苓的小說就十分適宜改編。另一種“互用、共用故事資源”的改編則意味著同一部作品從一度創作到二度創作的轉換,或者不同藝術領域中的二度創作到二度創作的切換,這就更為復雜。一度創作與二度創作雖然是存在于同一個作品創生過程的不同階段,但內在的轉換在于藝術語言的迻譯。不同的藝術語言無法通用,即便是同一個故事核的衍生品。“因此,視覺的戲劇是絲毫不能襲用各種舞臺手法的,不論什么樣的舞臺手法都不行。但是,在這個被各種傳統所僵化、所慣壞而另一方面卻還很健全和能夠幻想的歐洲,電影依然被愚蠢地當作戲劇的奴隸。”[2][意]里喬托?卡努杜:《電影不是戲劇》,施金譯,楊遠嬰主編:《電影理論讀本》,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年,第19頁。這種認為電影是戲劇的奴隸的觀點無疑冒犯了電影的尊嚴。
從一度創作到二度創作的改編發生在從“編”轉“導”的階段。電影是一種集體創作的藝術,是一個不同時段、不同領域、不同人的既相互疊加又相互取消,既互相詮釋又互相悖謬,既互相帶動又互相牽制的集體作業的成果。無論在演員中心論還是導演中心論的實踐體系中,電影的創作比任何一種藝術創作都更為復雜。或許,只有當人類自身走到一個后現代、后工業的階段,進入一個足夠復雜的感知系統,才能創新并深度擁抱這種藝術樣式。藝術語言的迻譯是改編中的規定動作,但不同藝術形式的通約又需要逾越很多天然障礙,這是一種高難度動作,應結合實踐去理解改編的復雜性。
以文字為載體的改編在面對原著時,首先要解決的是故事本身是否需要大的改寫。這里考量的既有改編中新的創作意圖是否產生,相應的創作功力能否完成這一意圖,同時也必須考慮改編所置身的新的文化語境對作品解讀的影響,接受主體的接受能力和審美趣味,這些在改編中都需一一斟酌。創作意圖和創作功力主要是創作者自行解決的問題,而文化語境和接受主體就牽涉到了文化心理問題,涉及復雜的社會環境對于創作與接受的投射。
一般來說,“原著黨”是以原著為圭臬來看待、衡量改編的,常見于對經典文本與流行文本的改編,二者都以原著擁有的眾多讀者來保證改編之后的關注度——所謂大“IP”最大的優勢就是自帶流量——然而這是一把“雙刃劍”。因為越是這樣的作品留給改編的空間就越小,所承受的苛求也越多,那些由讀者轉型而來的觀眾,也許不是理想的觀眾,甚至不是理性的觀眾,在他們的視域中完成一個新故事或是一個新瓶裝舊酒的故事顯然需要冒險。如中國作家劉慈欣的《三體》的改編,日本作家東野圭吾的《白夜行》《嫌疑人X的獻身》的改編,美國作家雷蒙德?卡佛的小說被改編成電影《鳥人》,英國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說被改編成電影《東方快車謀殺案》,等等。在“原著黨”監督之下的改編顯然不可——或者說不敢——有太大的變化,這主要表現在故事結構、人物關系、人物設定、故事情節等方面的穩定性上。經典名著改編的情況則更為典型,如古典文學名著《紅樓夢》《西游記》《水滸傳》《三國演義》的改編,當代文學名著《白鹿原》《紅高粱》的改編,以及日益經典化的金庸作品的改編,等等。經典作品本身自帶保守性和封閉性,外來的改編因素只能被納入經典原有的“閱讀—接受”系統,創新性很難從經典性中“逃離”“逸出”。
過于強調原著的經典和權威,意味著對原著文學敘事的服從,因此這類電影作品的構成還是文學語言編碼,不是視覺語言編碼。其實,在不亦步亦趨之處,才更加能考查出改編過程中創作者對于原著的理解深度和運用電影語言的敘事功力。熱衷于觀看經典改編的電影觀眾,其注意力和興奮點往往不靠情節調動,他們看的多是改編、表演和演員。名著改編的難度系數隨著改編次數的增多而不斷加大,但驚人的市場號召力與票房回報率仍然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創作者,使得這類改編至今仍層出不窮。例如,20世紀90年代起周星馳創作的“大話”系列電影,21世紀的“西游”系列創作,既是對作為文本的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記》的改編,也是對原有的影視、戲劇、動漫作品的翻拍,二者同一。在“西游”“射雕”這類系列的翻拍中,觀眾所享受到的,既不是單純的重溫原著,也未完全脫離對母本的記憶,無法完全摒除“前置”的信息與情感,實則是兼有兩者的“互文”式接受。唯有熟知這種頗具后現代特征的接受方式和審美取向,才能在致敬、重溫經典與戲仿、翻新原作之間找到一個完美的“焊接點”。
經典的改編正意味著文化權力的博弈與讓渡。經典具有的權威性為改編帶來了“求安全”的顧慮,但經典本身是“經典化”過程的產物,任何作品在成為經典之前,都自帶開創性、先鋒性,因此也為開放式的改編預留了空間。經典怎么改,為什么要改,日益成為實踐者和研究者的焦點。
與這種處處受制于原著不同的是對故事核進行再加工的改編。電影工業中劇本的現代運作模式,時常是編劇提供一個故事核,之后才是投拍者為其注入資金,同時完善劇本,甚至啟動較大規模的集體性重寫,這種改編日益催生出大銀幕上備受矚目的作品——因為有成熟的市場眼光、強大的創作團隊和極具原創意識的編導人才為初創者買單。電影導演李安2019年新作《雙子殺手》的劇本據說是在好萊塢流傳多年未獲投拍的一個故事。還有一種做法是從當代流行的文本中選擇一個目標,然后剝洋蔥般層層剝掉故事的外殼,只余一個故事核,接著重新開始大規模的刪補、增減,以致移植,這類例子不勝枚舉。中國當代影史上很多作品如《霸王別姬》《讓子彈飛》均屬此類型。好萊塢影史上值得銘記的許多作品也出自這種類型的改編,《肖申克的救贖》《沉默的羔羊》在列其中。曾流傳過這樣的“金句”:一流作品、二流改編,以及與之相對的:二流作品、一流改編,此語道出了改編作品常常與原作的藝術品質難以持平的一種窘境。這其實也提示了一種改編思路:去尋找為改編預留了創作空間的文學作品。
二、什么作品更適合改編?
導演和投資方如何挑選要改編的作品?答案似乎只能從以往現成的經驗中總結而來。相對說來,形式簡潔,情節跌宕起伏,節奏鮮明,人物性格變化大,行動較多,篇幅為中短篇的作品,比起那些沉浸于藝術腔調,人物絮絮叨叨,過于強調內心表述而吝嗇于外部行動的長篇文學作品,前者更容易被導演團隊及影視公司看中。可以從內容的明晰,風格的鮮明和操作的便利這些角度概括改編對象選擇的標準,即具備較好的視覺化特征。
除上述標準中所概括的外部特征外,還應從故事核中去尋找“什么作品適合改編”的答案。中國香港作家李碧華的小說《霸王別姬》《青蛇》《胭脂扣》受導演陳凱歌、徐克、關錦鵬的青睞,改編拍攝而成的電影廣受觀眾的喜愛和追捧。這些純文學作品中具有通俗元素和情感親和力的那一類易于被電影創作者看中,扎實的劇本基礎自帶了通往創作者心靈的情感通道,它們先是打動了創作者,然后經拍攝、制作打動了觀眾。其獲得的成功并非僅僅因為原作的篇幅、風格、人物、情節,更是因為這些作品中各種元素交織所召喚出的社會集體意識下的一種情感認同、一種心理結構的印證。
這些作品為同時代的創作者和觀眾提供了故事母本和情感通道。談及改編,必須承認,故事核中的核心物質不是文學性,最出色的故事不一定會出自最優質的文學。法國的瑪格麗特?杜拉斯是在電影史上做過很多嘗試的大作家,比較成功的有由她改編,阿侖?雷乃執導的電影《廣島之戀》,該片在國際上獲得多項電影獎項。盡管如此,電影仍缺少了文字中獨特的節奏與調性,缺少了直接、酣暢、性感的藝術魅力。正如米蘭?昆德拉所說的:(真正的)小說是無法改編成電影的。“長篇小說是作家綜合能力的競逐地,中短篇小說則是文學實驗精神的演練場。”[1]李靜:《2008年文學一瞥》,《必須冒犯觀眾》,北京:新星出版社,2014年,第174頁。僅僅從借故事的角度上去看待改編,無疑犧牲了當代文學佳作中文學性的核心要素:獨特的敘事能力和文學的實驗精神。這正是改編后的作品成為了文學版的降級的緣故。
那么提升原著精神品質的改編有沒有?答案是有的。當代較為年輕的電影導演中,程耳、張楊、徐浩峰、萬瑪才旦等都有較高的文學造詣。近年來的新銳導演曾國祥則更有說服力,他以對青春題材深沉細致的描繪而撼動人心,走出了一條比較成熟的改編之路。從《七月與安生》到《少年的你》,觀眾欣喜地看到,不借助玄幻仙魔,不搞大制作,不消費歷史,不強說情懷,僅僅靠踏實地講故事和打磨人物,就能獲得將原著精神品質大大提升的改編。
《七月與安生》改編自作家慶山(曾用筆名安妮寶貝,本名勵婕)的同名小說。慶山是飽受爭議的第一代網絡作家,她前期的小說有著當時網絡文學的一些弊病,如人物情感浮夸,行動極端。導演曾國祥在改編時著力把情感和腔調降維處理,把故事和人物托實,用對生活細枝末節的準確觀察和演員對情感的細膩把握,實現了作品內外人物與觀眾的共情,較好地克服了原著的弊病。曾國祥擁有一個強大的編劇團隊,這個團隊把小說中原有的單一的文青腔調去除,萃取純真,使作品內容更集中且豐富。
可見,改編文學作品,不是簡單地把文學語言翻譯成電影語言。就像某些同樣是暢銷作品的改編中,人物動不動口吐“金句”,只是因為該“金句”是原著的亮點,便原封不動地粘貼過來——這類通過復制便想獲得成功的思維,顯然過于簡單,沒有把握好在不同敘事類型中切換的原則。好的作品不是靠各類好的元素做加法,不是將文字往影像中嫁接、勾兌、復制,而是超越于具體類型之上,把握不同敘事類型中精神品質的共通性,然后重新摸索、開創、運用獨屬于電影的敘事語言。
三、如何更好地改編?
不管原作有多么深刻的思想內核,文學作品被改編后,都應進入電影語言的具體形式中,改編要為價值和觀念尋找合理的“肉身”,也只有深入到具體形式的特性中才能實現深切表達,甚至是拓展意義和豐富理念,這個實踐過程和思考過程同一。婁燁說過:“你是一個電影導演,你就從電影角度來表達你對哲學、社會學、人類學的建議,而不是說你就要成為歷史學家、哲學家、人類學家,要按電影藝術家的邏輯來工作,這是一個通行規則。”[1]婁燁、陳偉文:《全世界的導演都在解決時間問題》,格非、賈樟柯等:《一個人的電影》,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183頁。從一度創作到二度創作的改編,核心問題是原先屬于文學固有的東西,電影劇本該怎么表現?閱讀者可以輕易地感知小說的語言特色和蘊含其中的獨特風味、情感訊息,但轉換為電影語言后,又該如何傳達同樣的至少是相近的質素、腔調和味道呢?這涉及從主觀感受到客觀顯現的難題。基于文學特定的敘事功能、抒情功能、修辭功能,在轉譯過程中,以上內容是減少了還是增值了,這些探討為評價一個作品的改編是否成功提供了相對客觀的標準和參數。不能只依靠從文學語言到電影語言的轉譯,要在某種程度上放棄文學性拐棍,實踐一次全新的、完整的影像創作,才是有勇氣、有新意的改編。這其實已經是原創,而不是移植或是復制。
語言的敘事與影像的敘事雖同為敘事,但使用的是不同的介質。當影像化的敘事試圖還原文學敘事時,就會遇到各種屏障。在語言的敘事中需要處理的視角、人稱、語序、語氣等等,在轉換為影像敘事時,必須結合電影拍攝的物質條件和技術手段。敘事功能是電影的本體功能,也是文學的本體功能,能否從這一本體到達另一本體,是考驗改編者的一個核心問題。
影史上有很多對當時創作帶來沖擊的技術革新,是應電影敘事本身要求而產生的。例如常常被談論的固定機位、低機位的采用;一直被視為藝術片常用的、作為風格美學標志的長鏡頭的發明。低機位和固定機位模擬的正是固定不動、與人身體坐臥相適應的視角和目光,這一狹小而受限的視角多用于第一人稱敘事,即主觀敘事。相應的,廣角鏡頭和推拉搖移不停運動的鏡頭,顯然是對宏觀的、全方位的、行進中的視角的模擬,更適合表現全景。長鏡頭最適合模擬、再現一個行走中的人物的視角,即“移步換景”。“移步換景”是中國文人畫獨具的一種觀看之道,將它沿用到電影創作中,顯然更適合中國古典名著、歷史著作的改編。2019年播出的現象級網劇《長安十二時辰》據稱用的就是電影拍攝手法,在作品的開頭采用了類似“移步換景”的長鏡頭,以一個外來者進入長安的視角復現昔日繁華。除此之外,很多經典文學作品的開頭,如“林黛玉進賈府”的經典段落,都很適合用長鏡頭加跟拍模式來展現。這些鏡頭語言的創造與征用,正是出于對文學敘事特征的跨類型還原這一目的。技術服從于觀念而創生,又反過來帶動了觀念的表達與生成,這正是電影語言作為藝術實踐的獨特價值。
改編的形式特征之一表現為跨類型語言的調動和使用,但電影語言的界定并不十分清晰。“在電影的創作實踐與電影理論表述中,電影語言無疑是一個相當重要又相當模糊的概念。”[1]戴錦華:《電影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頁。電影理論家克里斯蒂安?麥茨的論斷是,并非電影是一種語言,它才講述了如此精彩的故事,而是因為它講述了精彩的故事,所以才成為了一種語言。此論斷可以旁證電影語言具有極強的實踐屬性,什么是電影語言——這一問題的答案不是規定的,而是追認的。一位電影導演必須先找到他所需要的電影語匯,而且應是“一部一格”、不可重復的創造,這是對電影藝術本質的考查。
電影語言是一種藝術語言,它不僅僅是一種技術性操作,或者說,唯有當電影語言從攝影技術中獨立出來,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創作才得以成立。“電影藝術建筑在一個穩定的四邊形的四個端點之上,它們分別是時間、空間、視覺、聽覺;電影藝術便是在相對的時空結構中以視聽語言建立起來的敘事連續體。”[1]戴錦華:《電影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頁。電影中復合手段的綜合運用,遠遠便捷于在文學之中。電影語言的獨特美學在于它特有的“修辭”,可以運用視聽語言使不同層次的體驗得到立體的展示,觀者可以通過這一“復調”式的構成去體會電影的復雜意蘊。而在文學的范疇中,達到“象外之象”“韻外之致”層次的文字則十分稀少,畢竟作用于通感的文學修辭技巧是有難度的。在導演姜文的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與《邪不壓正》中,鏡頭跟隨少年飛奔,帶領觀眾俯瞰美麗的北京城,同時,歡快又不乏諧謔的多聲部、復合變奏的音樂一并響起。電影的視覺語言飽滿充盈,伴奏音樂節奏輕快,隱隱透露出少年對于自由的熱望,也顯露出北京城精致優雅表象下的混亂與隱憂。
與語言的轉換相比,更深層次的改編是價值觀念與敘事理念的切換。價值觀念與敘事理念切換的背后是文化意涵和心理訴求的變遷。很多評論者沿著不同時期電影改編重點的遷移,去審視作品折射出的不同時段社會文化心理的表征。這也是一段時間以來改編作為越來越熱的文化研究命題的原因。文化研究、文化批評的重點溢出了創作層面,不是創作者需要考慮的事,但不妨害通過評論與研究得出的結論有助于創作,有助于思考改編的價值和路徑。
有一種改編中的弊病不常為人所提及,就是跨文化移植改編中情境的丟失和接受的錯位。[2]參見蘇妮娜:《情節的忽略造成接受的錯位——談〈嫌疑人X的獻身〉改編的缺失》,《遼寧日報》2017年4月6日,第8版。例如,推理小說家東野圭吾是近年來在中國擁有讀者最多的日本作家之一。2017年,導演蘇有朋將他的代表作《嫌疑人X的獻身》做了中國版的翻拍。之前日本和韓國都已經拍過同名電影,相比之下,中國這一版的改編乏善可陳。其中有一個疏漏便是此類翻拍中的典型錯誤,即在故事的跨國移植中,把原著里看似不那么重要的輔助元素與信息直接刪除,造成人物活動的外部環境——包括時間感、年代感、地域感——與中國本土觀眾的接受發生錯位,導致觀眾理解人物心理的路徑懸空。試揣測,改編者可能覺得沒有必要或沒有可能把原著中的地點與時間——繁華市區中一片令人瞠目的破敗之處,日本遭遇經濟蕭條后荒涼、絕望的社會氛圍——放置到當代的中國城市,也就是說很難將故事生長的社會的環境土壤一并移植過來,于是索性放棄了這個任務。同時也沒能努力去找類似的環境土壤來填補空白,就此造成觀眾理解人物行為時頗為吃力。更為嚴重的是,這一情節內容的丟失在表層上似乎能模糊過去,卻造成觀眾對情節深層接受的不適,原著中與那些輔助故事元素同在的深刻的社會影像,也在翻拍中縮略、減掉,這必然削弱了原著作為社會分析文本的批判力量與精神品質。類似的例子還有2015年上映的改編自1957年美國影片《十二怒漢》的電影《十二公民》,盡管這一模仿秀作為類型化影片的嘗試給中國觀眾帶來了新鮮感,但作為倫理與法理并重的一部影片,很難說包含了對應中國現實的真切體驗與情感關聯。翻拍作品看似省力、安全,但若想打造成精品,反而需要花費更多的心力。
可見,無論哪種方式的改編,都需站在獨有的文化立場上去思考,站在人類共通情感與理念基礎上去實踐。無論怎樣追求陌生化,追求當代性,追求與當今語境的映照和對不同受眾的迎合,都不能遺忘原先的作品是建立在語言存身的歷史/社會/心理這一結構之中。妥善處理和對接觀眾的接受與審美,重塑觀念并重述故事,才能做出有意義、有價值的改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