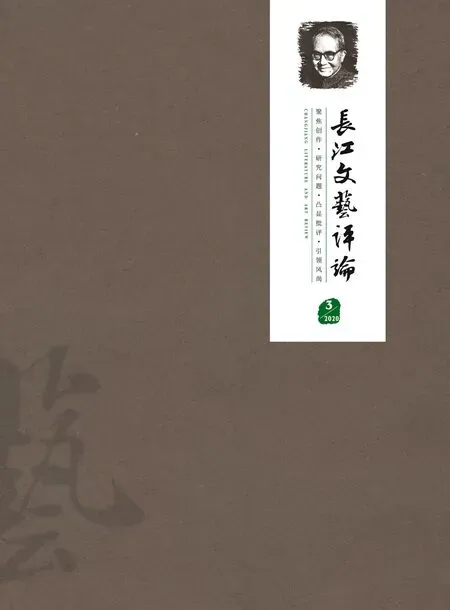薄言情悟 悠悠天鈞
——淺論謝倫《黃昏里的山岡》的文學風格
◆張治國
謝倫的散文集《黃昏里的山岡》因其豐贍的精神性內涵和悠遠的審美韻味而先后榮膺“冰心散文獎”(2010—2011年度)、“湖北文學獎”(2012年)、“屈原文藝獎”(2013年)。這不僅顯示了謝倫散文創作的深厚功力,也奠定了他“是一位能代表湖北散文創作水準的‘實力派’作家”[1]的地位。
謝倫散文,猶如“幽人空山,過雨采萍。薄言情悟,悠悠天鈞”,甘以雯對謝倫散文的思想深度和積極的社會意義予以充分肯定,她評價《黃昏里的山岡》“篇篇有‘我’,有‘我’的情感,‘我’的心靈,‘我’的生命,‘我’眼中的大千世界。情感的濃度,人性的深度,達到了一定的高度”。認為在最容易迷失人性本我、忽視自己感情、扭曲自我心靈的激烈競爭和動蕩的當代社會,“靜心閱讀謝倫的散文,對于保持本我,凈化感情,撫慰心靈,會得到積極的啟示”。中南民族大學羅漫教授贊賞謝倫散文的詩美風格和凡中顯偉的創作技巧。認為謝倫作品“像一幅幅淡淡的農村田園畫,看似淡墨無痕,一種如孟浩然田園詩‘淡得看不見詩了’的風格”。盡管他講述的都是些親身經歷的農村生活瑣事,“卻取得了以小博大,尺幅千里的效果”[2]。
優秀的散文是抒發心靈的文字,這些文字往往彰顯出高尚的思想品質、非凡的文化品位和獨特的詩人氣質。作品風格是作家個性和文本特色的標志,是情景交融、物我交會、人事和諧所達到的一種境界,是創作主體的作家與創作客體的作品主客觀的高度統一。理解作家作品的風格可以從作家的創作個性和獨特的言語形式出發,而文本的題材、主題、意象的營造以及藝術構思等等,又是把握作家風格形成的關鍵——這在謝倫散文集《黃昏里的山岡》以及謝倫與其散文集的關系中均得到了較為充分的印證。
一、謝倫的創作個性
任何一個優秀作家的創作個性往往都是通過其創作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學文本或顯或隱地予以呈現,謝倫的創作個性通過其代表作《黃昏里的山岡》得到了較為全面的展現。這其中既有顯在的個性氣質的展露,也有較為隱含的創作心理動機、歷史意識等因素的外化。
謝倫在《黃昏里的山岡》的代序《給一個寫作的理由》一文中說:“我是個孤僻的人,自卑的人,嘴巴笨拙木訥,常常因懊悔說話不得體而陷入苦悶中,甚至氣得只想打自己的嘴巴。”這體現出謝倫細致、敏感的內心世界。人際交往對于謝倫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迷宮,“我不愿意人云亦云,遇事又不會像人家那樣能見縫插針左右逢源,在這個迷宮里,就老好迷路,就老有找不到出口的痛苦。”這種復雜的內心情感體現出謝倫內向憂郁的性格特質,表現出謝倫對寧靜的偏愛,對虛假逢迎人際關系的抗拒。謝倫的性格中還有一種非常重要的特質——真誠:“家鄉給我的是貧窮、是愚昧、是酸楚,是家族大戶們的白眼和羞辱,我不能違心說我熱愛家鄉,甚至有恨。”“我時常地想念家鄉……她幾乎成了我全部的情感寄托。”他坦誠地將自己對于家鄉的真實情感訴諸筆下,對家鄉又愛又恨的復雜情感不加絲毫掩飾,他敢于將自己的內心情感世界展示于讀者,體現出謝倫對于自己的正視;敢于剖析自我,敢于面對自己的內心情感,體現出謝倫對于生活、生命的思考。
從謝倫散文集的字里行間,我們可以清晰地看見一個飽滿立體的作家形象:他內向的性格中富有藝術家的憂郁氣質,擁有對世界、人類、自我的真誠之心;敢于正視自己的內心世界,善于自省,勇于剖析自我,擁有豐富復雜、細致而敏感的內心情感世界;他不懂圓滑、喜好安靜,是一個熱愛生命、熱愛自然、懂得尊重他人的人。
與作家的個性氣質密切關聯,創作動機是驅使作家投入文學創造活動的一種內在動力,是一種常在暗中支配作家搜集材料范圍、決定作家藝術發現方向的潛在的操縱力量。創作動機往往能夠決定文學創作的選材和藝術沉思的走向,在創作動機的背后潛藏著作家復雜的心理因素,創作心理動機對作家文學創作活動的影響不可忽視。獨特的生命體驗和多愁善感的藝術氣質影響了謝倫散文創作的心理活動和規律,在代序《給一個寫作的理由》中,謝倫說自己的寫作是以喊叫的方式去忘卻或者是銘記。謝倫在散文創作中大多采用回憶的方式,積極地從生命記憶中提取有意義的信息,把自己生命體驗中對自己刺激最強、自己最為熟悉的信息提取出來與創作中的意念掛鉤。
影響謝倫創作的心理動機有潛動機和顯動機。謝倫在童年、少年的生命體驗中逐漸積累,且經由遺傳機制留存下的集體潛意識在謝倫進行散文創作的過程中遇到某種機緣而被喚醒。身為依賴于大地的地道農民,在謝倫潛意識的驅動之下就以農民為主要人物形象來進行塑造,把發生于大地、土地、莊稼之上的農村物事作為主要描寫對象來進行散文創作;而謝倫在中年時期的生命體驗帶給了謝倫完全不同的觀念感受,甚至于沖突:城市文明的發展、自然風物的變遷、物質文明的復雜富饒和精神文明的日趨單調、扁平、匱乏等,給謝倫的心理造成了失衡和波動,引發了巨大的情感波瀾,從而給謝倫的散文創作帶來了直接的心理驅動力,這是謝倫散文創作心理顯動機,在此種心理動機的驅動下,謝倫的散文中往往會產生一些意象,比如山岡、黃昏、古柏、鷹、墳場、廟、女子、紅紗巾等。
謝倫不僅具有關注當下的現實情懷,更具備反思過往的歷史意識。歷史意識是人類對自然、人類自己在時間長河中發展變化現象與本質的認識,謝倫對此有著自己獨特的認識,形成了個人獨特的歷史意識。
“山岡是恒久的居所,而村莊只是人在旅途中的一個驛站。”謝倫筆下的山岡不僅僅是一個地點、一處自然風貌,它更是一個典型意象,代表一種精神,是謝倫對生命存在本體的認識。在他看來,人的歸宿是“山岡”,人是在山岡的孕育中得到了生命,而當有限的人生走到時間的盡頭時,生命本體又將回歸山岡,在山岡的庇護下得到延續和留存。山岡是謝倫對生命本體存在方式和存在意義的一種思考,是一種生命的思考,它飽含了謝倫對人類來自于大自然、生長于大自然、歸宿于大自然的深切感受,蘊含了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歷史意識。
謝倫眼中的大自然是真、善、美的所有者。“面對大地,勞作,就是虔敬和皈依。”這是謝倫對人生命存在的價值思考和意義探尋。人生存的價值和意義就在于勞動,身為農民,不僅需要從土地獲得生存所需的物質,而且還要通過勞作回饋于大地,獲得生命的延續。勞作不只是人類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狀態,勞作也是人類生命存在的價值體現。人生是有限的,生命的厚度卻是無限的,生命依賴于大地,生命的厚度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慢慢積累。“時光將生命壓倒在地,時光堆積愈厚、愈沉重,生命貼大地愈緊,一切真實的事物就開始浮現、消逝。”謝倫的人生經歷讓謝倫在回首往事時發出“為什么年輕人總是那么的無知”的喟嘆。在謝倫看來,人生的運動軌跡是遵循著一定的規則來演進的,年少時生生死死的概念注定得不到孩子們的敬畏和重視,有許多遺憾的心緒總是會縈繞在生命記憶中,不分時日地浮現,人往往把握不好此刻,在將來的回憶中總是會銘記過去的錯誤和遺憾,現在的思考表達的是一種愿望,“愿望如何利用現在的情境,以過去的模式構建出未來的圖畫。”[3]謝倫對人類生命的變遷進行了深入思考,其散文創作中對過去的回憶也是對現實狀況的一種反映,是個人對人生現實的思考回答。
大自然的水是萬物之源,因為“水拒絕一切有毒的東西,除非水不再是水”。謝倫的童年記憶中流蕩著一條河流,它不單單是指滾河這條自然景觀意義上的河流,它也是謝倫整個童年的美好回憶,是謝倫對人生、生命的初步思考的啟蒙之河,是生命的時光之河。在童年的記憶中,河水是孩子們歡樂的場所,孩子們在這里玩耍、嬉鬧、快樂;河水也能夠帶給自己一些生活常識,比如在河水中久久浸泡過的肩頭可以用手指刮出一條條的白印,這時的河水是藏不住秘密的河水;河水雖然也有危險,比如馮老五的幺兒子,只有四歲的凹三被河水所淹沒,可是這種生命的隕落卻沒有讓謝倫對河水產生恐懼。在謝倫的眼中河流是能夠賦予生活大美的存在。
謝倫對自然的思考和對人類自身的思考是交織在一起的。在謝倫的歷史意識中,“上善若水”——水在自然中占有重要位置,生命在人類自身發展本質中也占有極大的分量,因而謝倫的歷史意識是生命與水的交融:“生命的歷程就是寫在水上的字,順流而下,想回頭尋覓時卻總是失去痕跡。”生命因水的承載而流動,水因生命的孕育而有意義。
二、《黃昏里的山岡》的內容與形式
文學風格的形成包括客觀因素(外部因素)和主觀因素(內部因素)兩大部分。其中客觀外部因素是指時代、民族、階級、題材、體裁等方面;內部因素則涉及到作家個人的生活實踐、所受的思想及藝術傳統影響、心理功能(感情、氣質)等方面。以上分析了《黃昏里的山岡》風格特點形成的主觀因素:謝倫的創作個性,下面將從客觀因素方面來探究《黃昏里的山岡》風格特點的形成。
《黃昏里的山岡》題材廣闊、內容豐富,反映了謝倫豐富的人生閱歷形成的開闊的文學視野。從農村走出來的謝倫當過農民,做過工人,學過繪畫,出色的寫作能力使他最終成為一名優秀的新聞工作者。農民、工人的經歷讓他切身體驗到了社會底層民眾的疾苦和歡樂;學習繪畫的藝術經歷使他能夠從藝術的角度思考人性、生命、生活的意義,在普通的人事風情中感受到深層的哲學韻味,獲得生命的啟示;謝倫的童年經歷及個人內向的性格又使得他能夠擁有細致的觀察力、堅韌的毅力和深刻的記憶力,這些因素都深深地影響了謝倫散文集《黃昏里的山岡》的創作,因為“生活實踐對于作家的意義不僅表現在為他們的創作提供了素材,而且培養了他們的創作思想、創作見解[4]”。
《黃昏里的山岡》所收錄的散文大多作于2006年至2008年間,是謝倫人生經歷和人生感悟的真實寫照。其題材之一是優美奇異的自然風光:如作者家鄉棗陽的固云水庫、亂石洲、大廟、墳場、古柏、大棗樹、梧桐、山岡、滾河、魚臺島、獅子山、磨盤山等,作者工作及居住地湖北襄陽的桃花島、漢江、檀溪村、虎頭山等,以及保康美麗原始的山谷,武當山的榔梅樹、官道和神道等,華中屋脊神農架的山頭峰巒、藍天白云、峽谷高山、晴日烈雨、山水云霧等,還有湖南鳳凰的沱江、輕舟和桃花島,歐洲的萊茵河。其題材之二是充滿歷史記憶和人生體驗的人文景觀,如棗陽吳店鎮、狗骨頭巷、鎮文化館,襄陽的古城墻、跨江大橋,鳳凰的從文故居,武當山的金殿、太子山的太上老君廟觀,神農架的木魚鎮,歐洲高達宏偉的科隆大教堂、波恩的貝多芬故居等。其題材之三是各色人物的素描:如老古、海拉爾、吹九伯、仇有志、黃四兒等各具個性的鄉親們,有李家嬸嬸、瞎姑等美麗善良又聰慧的女性形象,有景先生、付先生等有文化的知識分子。另外,這本集子還記錄了各種奇聞異事,將人性和生命的存在問題暴露于眾。
《黃昏里的山岡》表達了鄉愁的主題意蘊。謝倫在創作這些散文時已經生活在繁華的城市之中,故鄉的美麗風景和鄉親們質樸真誠的品質都在現實中與作者漸行漸遠。可是在作者的記憶深處,這些美好的“鄉情”與“鄉景”卻并未被城市繁華的物質文明所掩蓋。
與其他書寫鄉愁主題的作家作品迥然不同的是,“謝倫寫出了童年記憶的神秘,是他的鄉愁的一大特色”[5]。在散文中謝倫講述了自己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童年生命體驗,比如童年記憶中那次墳場的迷失,為什么謝倫在一條自己一天能走上四遍、閉著眼都能走回去的路上迷路了,而且生了許久的病?這次山岡上的迷失是極具神秘性的,包含了謝倫對靈魂、死生、生命的思考。又比如在謝倫童年記憶中一幅寓意深遠的圖畫里,一名裊裊婷婷的女子在滾河的冰凌里消失,香消玉殞,以及一條在冰凌花上輕輕一落的紅紗巾,這些在孩子的眼中是那么真實,可是大人們卻說根本不存在這樣一位女子,這一記憶是謝倫生命中永遠難解的謎,是“一個結,一樁懸案”。
從本質上說,謝倫的鄉愁是一種“文化鄉愁”。作者歷經人事的變遷和社會的飛速發展,在對家鄉的懷念之情中融入了自己對文化的深刻思考,包含了作者對淳樸精神文明日漸衰竭的“憂患意識”。在作者記憶中的親情是生命最溫暖的血液,可現實中人們的親情卻變得越來越冷漠,這是作者鄉愁中的憂患意識。
《黃昏里的山岡》所體現的鄉愁是作者對“土養人”的堅定信仰,是作者對大地的尊敬和感激,也是作者對所信奉的“人也要養土”這一信條的實踐,大地(山岡)是人類的永恒歸宿。
善于營造具有豐富內涵的意象,是散文集《黃昏里的山岡》的一大特點。關于意象,龐德指出,一個“意象”是在瞬間里表現智慧和情感的復合體[6]。意象是在作者主觀的“意”和客觀對象的“象”兩者的相互作用之下,通過直覺思維瞬間形成的藝術表象。謝倫在作品中營造了許多意象:山岡、滾河、廟、七棵古柏、鷹、女子(紅紗巾)等,這一系列意象都是較為偏重于主觀的,是謝倫主觀之意的滲透使這些客觀物象發生藝術變形,從而將這些經驗表象升華為藝術表象。
“山岡”在《黃昏里的山岡》中是指作者老家屋后的山岡,是一個有著一座大廟、一片墳場和七棵古柏的山岡。同時,“山岡”又是一種意象,是人類生命恒久的居所。山岡是每一個人的歸宿,山岡中的人們不分貴賤、沒有階級,再高貴的帝王將相也逃脫不了山岡的歸宿,代表著人類生命本體生存的最終價值。“黃昏”是“過去時的一個象征”,既指一天的結束,也代表著人生的最后時光,是人類經歷了一定的生命體驗、積累了一定的生存智慧后對人生、生命進行思考的時段。“謝倫的‘黃昏’,不是一個虛幻的風景,那是生命的舞蹈”,是謝倫對于時間與生命的沉思,黃昏籠罩下的山岡給人以靜謐、深重、沉思的感受。“滾河”不僅是作者家鄉的一條河流,是謝倫童年的歡樂地和記憶源泉,是養育家鄉百姓的母親河。同時,它又是時光之河,是時光流逝的見證,富含悠久的歷史記憶,是人類生命的歷史演變進程,滿載著生命存在的意義。“鷹”出現在城市大廈的辦公窗前,也出現在家鄉山岡的高空之上,“鷹”的飛翔有著一種象征意義,象征著生命的自由,精神的自由,鷹在天空中追逐的姿態也代表著生命存在的一種形式,揭示了生命存在的意義。
另外,作品中的“墳場”“七棵古柏”和“女子”的意象透露出一種神秘、陰森的氛圍,作者童年時在墳場的迷失,七棵古柏的詭誕傳說,記憶中被冰河吞噬的美麗女子,這些謎題是作者對生與死的疑問和思考,對生命存在的追問,是作者對人類死亡、生命消失的思考,體現了作者靈魂說的生命觀。
《黃昏里的山岡》所采用的語言表達方式,使用的修辭技巧,不僅鮮明地體現了作家的語言風格,也與各文本所傳達的主題十分契合。
從總體上看,該散文集主要采用敘述和抒情的表達方式來詮釋主題。集子中有豐富的故事和人物,情節細致生動,人物飽滿鮮明,敘事和抒情兩種表達方式交融結合,在敘事中抒發感情,從情感的表達中展現生動真實的歷史畫面。例如《魚臺蒼蒼》,這篇散文的題目本身就充分體現了敘事和抒情兩種表達方式的完美結合:“魚臺”是一個地名,指家鄉棗陽吳店鎮文化館后河上的魚臺島,這個地名理所當然地蘊含了一個故事,發生在魚臺的故事;而“蒼蒼”借用《詩經·蒹葭》中的“蒹葭蒼蒼”,蘊含著一種惆悵的意蘊,縈繞著傷感。從文本內容的角度看,這篇散文以優美的筆法描繪了滾河、魚臺上蘆葦等自然景觀的美,由樟樹春天的落葉頓生悲愴之感;緊接著記敘了西街劇團日漸衰微的事情,敘述了劇團成員的分道揚鑣,發出了“人的命運里有很多東西是我們自己所不能把握”的無奈喟嘆,這是作者因感受到人事變遷、曲終人散的輪回而對人生的迷茫發出的追問。
比喻、擬人和對比是《黃昏里的山岡》常用的修辭技巧,為作品增添了靈動的文采。例如作者將滾河比喻為一條白色的時光,把清晨滾河上的水霧比喻為一層層紗帳,將夏季的熱風比作滾滾白浪,從洞穴游出的水蛇擬人化為扭動腰肢的舞蹈,把正投入水中玩耍的孩子們的動作比喻為青蛙跳水。謝倫還把狗和狼、狐貍放在一起進行對比,表現出狗的老實、本分。在散文集中,謝倫還經常將深奧的人生哲理和哲學思考以比喻等修辭技巧化為生動通俗的語句。例如將天和地比作時間的磨,“總把一切都磨得粉碎,塵土飛揚,稍不留神就會迷離了你的眼神”,表現出對生命的敬畏、對時光的敬畏。再如,“人間好花,都是開在人心里的”,將人心的真、善、美比作自然界美麗的花朵,這是對高尚人性、美好道德品質的高度贊揚。
散文集《黃昏里的山岡》體現出謝倫靈透、清秀、真誠直白的語言特點。謝倫善以口語為文,高頻率地將方言極其自然地融入作品之中。像《滾河筆記·滾河》中的仇二伯提醒大家坐船時要抓緊時所說的“招呼啊”——“招呼”是湖北省棗陽市的一種方言,就是注意的意思,為引起聽者的注意,起著一種提醒的作用,作者在這里直接應用方言是為了使仇二伯這個形象更加逼真,使仇二伯熱心的性格更加真實;再如《滾河筆記·大棗樹》中將和尚的光頭稱之為“葫蘆瓢”;《鄂西人物·竹孝才》中形容竹孝才的嘴巴“地包天大撇嘴”等等,都生動地體現出謝倫散文極具生活氣息和地域色彩的語言特點。
從篇什的組合來看,該散文集共分為五輯:大地行走、滾河筆記、人來人往、浮世閱讀和水流云在。這五輯的取名頗能體現作家的創作宗旨,且相互之間形成了極為嚴密的邏輯關系。從散文的內容看,其重點不在展示奇景異物,而在于描摹與講述人事。文集中介紹的鄂西人物達十幾位之多:既會過陰又嗓音響亮、音域寬廣的“唱喜兒”,能手瞎姑和她會拉胡琴、打竹板的男人貴五;性格倔強的仇有志;抓野生動物泛濫、因技(釣黃鱔、打獵)而滅的黃四兒和田貴貴;前支書牛是啟,內蒙人老藥劑竹孝才,馮嘆氣馮民生等。散文集第三輯“人來人往”中收錄的全是一篇篇鮮明生動的人物志。這些人物多是有才學的知識分子,在這些人物身上體現出與鄂西人物完全不同的氣質,這些知識分子處于現實而不得志的困境,體現了作者對于知識分子命運的思考。在第四輯“浮世閱讀”中,謝倫以讀畫錄為題進行散文創作,以著名畫作命題,將畫品的描繪與畫家的介紹融合在一起。第一輯“大地行走”和第五輯“水流云在”所收錄的散文篇章都是情景交融的佳作,是敘事和抒情深度融合的體現。
三、結語
“風格是作家在創作實踐中逐步形成的,是作家的創作見解通過獨特的藝術形式的表現,是一個作家在全部作品中反映出來的基本特色。通過風格,我們可以看到作家的創作個性。它是作家成熟的標志。”[7]對此,法國作家布封提出了“風格即人”的著名論斷。他認為風格就是作家本人,風格是屬于作家個人的獨特標識[8]。風格通過文本體現出來,即使文本可以被其他人模仿和復制,但是文本所體現出來的風格卻是獨立于文本而依賴于作家個人的。謝倫的性格特質影響了他的創作心理動機,繪畫的經歷培育了謝倫憂郁細致的藝術氣質,形成其獨特的創作個性,深刻地影響了《黃昏里的山岡》的風格特點。《黃昏里的山岡》所體現出的風格特點是在謝倫創作個性的內驅動力和文本客觀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作家謝倫與作品《黃昏里的山岡》在本質上的水乳交融,是謝倫“薄言情悟,悠悠天鈞”精神特質的藝術外化。
注釋:
[1]高曉輝:《關于時間的沉思——讀謝倫散文集〈黃昏里的山岡〉》,《湖北日報》,2011年3月18日第14版。
[2]王大春,周建春:《寫作讓人豐滿——記冰心散文獎獲得者、市作協副主席謝倫》,《襄陽晚報》,2012年8月28日第7版。
[3]【德】弗洛伊德:《論文學與藝術》,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103頁。
[4][7]吳功正:《文學風格七講》,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頁。
[5]樊星:《日暮鄉關何處是——讀謝倫散文集〈黃昏里的山岡〉》,《湖北日報》,2014年10月12日第6版。
[6]黃晉凱,黃秉真:《象征主義·意象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頁。
[8]張燈:《劉勰的“風格論”與布封的〈論風格〉》,《文學遺產》,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