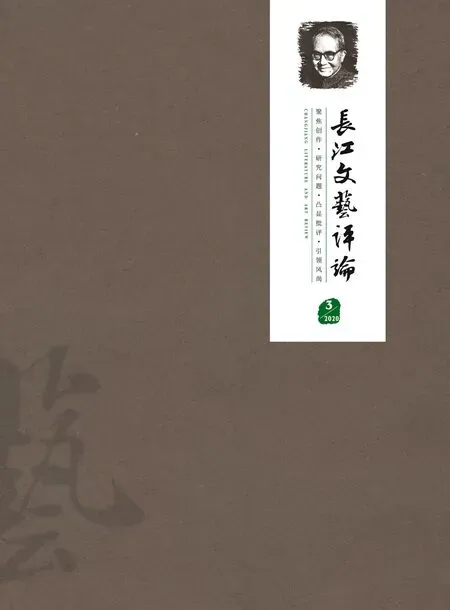“啟蒙式”批評與“志業式”批評
◆梅蘭
近日,編輯部轉來牛學智先生《“主持人化”恐怕難以拯救批評》(以下簡稱牛文)一文,經細讀,產生了不得不發聲的想法。牛文雖然指向當前文學批評期刊的欄目制和主持人現象,實際上是從期刊的欄目制談到了兩種批評的現狀:學院里的專家批評占據了各大文學研究期刊的版面,而原來相當活躍的“作協派”“自由評論”等從人員、文體到發表陣地都受到嚴重擠壓。牛文不僅對這兩種批評的此消彼長提出質疑,而且認為這導致了當下批評的窄化和脫離現實,換句話說,批評的專業化帶來了公共性的減弱甚至消失。
之所以出現兩種批評,這要從中國當代文學的生產機制說起,建國后到20世紀80年代,文學藝術皆屬于社會思想戰線,作家和批評家當然就是新中國思想戰線的戰士,批評者的身份、言論影響力以及文學批評導致的各種始料未及的后果,都非今日所能想象。20世紀90年代以后,文學不再是整個社會關注的熱點,作家很大程度上恢復為一種自由職業,文學批評的規模和影響力也相應改變,批評的學院化、專業化成為近30年來的大趨勢。牛文所列舉的“主持人化”的特點,比如主題化、片面專業化、急切經典化甚至某種程度的門閥化,可以說都是批評的專業化帶來的。這其中最大的不同是身份及批評觀念的差異。“作協派”批評代表的是培育、指導、幫助作家進行創作的官方力量,可以以集體名義開展批評,代表了官方的政策、方針、意圖導向等。同時,作為一種直接介入社會生活的宣傳方式,“作協派”批評具有明確的意識形態立場。比起“學院派”批評,“作協派”更為強調文學與現實的關系,看重作品體現出來的社會價值及意義。“作協派”批評,體現為快速有力的文學社會學批評范式,具有強烈的啟蒙現代性特點,可以稱之為“啟蒙式”批評。在傳統媒體時代,“啟蒙式”批評的價值判斷和各種大討論曾經發揮很大作用。近30年來,一方面社會公共空間受到壓縮,另一方面批評的專業門檻越來越高,這兩方面共同造成了“作協派”等“非學院派”批評的困窘。但是“啟蒙式”批評并不僅限于“作協派”等“非學院派”批評,“學院派”批評中同樣有“啟蒙式”批評身影。以“啟蒙式”批評來命名,所根據的不是從業者的現實身份,而是其所持的批評立場及方法。
相對于“啟蒙式”批評的意識形態特色,一部分“學院派”批評立足于文學的教學與研究,把自己限定為一種學術活動,側重事實判斷,聚焦于文學作品的闡釋和分析,追求對文學作品及現象的學術問題的發現與解答,套用韋伯的說法,可以稱之為“志業式”批評。“非學院派”批評里面也存在“志業式”批評。更為準確的說法是:很多“非學院派”批評受到了“志業式”批評的影響。
牛文認為,當下批評表現出現代性的主體性缺失、規避現實等問題,很大程度是因為欄目“主持人化”體現的“志業式”批評占據了優勢地位。牛文指出的批評危機,比如批評的集體失聯、被終結、被背叛等,應該說也是從“啟蒙式”批評的立場出發的。“啟蒙式”批評的核心是價值評判,它有著悠久的中外批評傳統,傳統的文學批評基本上都側重于道德功能和認識功能。儒家“興觀群怨”的詩教,從人格修養、認識社會、凝聚群族到宣泄怨憤,囊括了文學的大部分現實功效;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詩學,都著眼于詩的認識功能和道德功能,其中后者更為重要。賀拉斯、布瓦洛等后世批評家繼承了批評的寓教于樂的道德目標,直到19世紀、20世紀的阿諾德、利維斯,文學批評仍捍衛著文化傳統的道德標尺。但是文學批評傳統并不能解釋“啟蒙式”批評的現代性立場,甚至這種立場與文化傳統剛好是批判關系,“啟蒙式”批評的現代性起源意味著對傳統批評的重新審視甚至斷裂。17世紀之前,歐洲的文學批評從屬于文法和修辭學。17世紀批評(criticism)這一術語及批評活動才得到承認并傳播起來,“這個過程與一種普遍的批評精神及其傳播有關,這種精神包含了一種逐漸增長的懷疑主義,對權威和陳規的不信任……這一過去被嚴格限制在對古典作家進行詞句批評這種意義之內的術語,后來則逐漸與對作家的解釋、判斷這一總體問題,甚至與知識和認知的理論等同起來。”[1]顯然,新的文學批評凸顯了建立現代性線性時間秩序中的批判精神,正如浪漫主義運動中的雨果對原始時代、古代、近代的三階段區分,每個時代都有它相應的文類及審美原則。如果說17世紀、18世紀的批評活動涵蓋了作家作品的校勘、判斷、闡釋、說明,以及報刊評論,還在哲學、美學、歷史學、心理學等學科外徘徊,那么“啟蒙式”文學批評的出現則要歸功于19世紀的浪漫主義、現實主義文學與歷史、哲學的結合。伴隨著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19世紀的文學批評從一種文學趣味的判斷和表達,成為擔負起民族國家精神建設重任的角色,俄國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等批評家將“啟蒙式”批評推到了巔峰,別林斯基以及他氣勢磅礴的“年鑒式”批評,給20世紀的現當代中國批評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啟蒙式”批評從根本上來說,是伴隨著現代民族國家的興起,以人的主體性為核心,有著極強的現實政治關懷的意識形態批評理論與實踐。在20世紀的中國語境中,“啟蒙式”批評是從對自我消遣式的傳統詩文小說批評,到啟迪民智推動社會變革的功能巨變,是從傳統文人到知識分子的批評家身份的改變,也是文類等級劇烈變化后的現實主義文學及批評的一路披荊斬棘。在“啟蒙式”批評看來,作家、文學和社會是一個互相影響的有機整體,文學批評即是直擊社會現實的公共性批評。“啟蒙式”批評主體往往具有集體主體的特點,通過把自己與批評精神等同,構建起不容置疑的批評倫理,批評因此具有崇高風格。“啟蒙式”批評因為它的價值評判而建立合法性,“啟蒙式”批評的價值評判來自于現代理性個體對文學的生活時間與歷史時間的雙重感知,后者決定了“啟蒙式”批評的高度。但20世紀上半葉兩次世界大戰已宣告現代理性個體與歷史時間的失敗,20世紀的大部分西方批評流派或思潮都建立在非歷史主義或反歷史主義基礎上,比如俄國形式主義、新批評、神話—原型批評、精神分析批評、結構主義批評、后結構主義批評等。“啟蒙式”批評所依賴的歷史哲學和文學類型都來源于19世紀的歐洲,“啟蒙式”批評的信念源自思維與存在、主體與社會生活之間的同一性邏輯,表現為物質決定論(或主體決定論)、文學反映論、本質主義文學觀等,這決定了它難以回應當下非同一性的文學現象和問題,只能頻頻回到19世紀文學和批評中找尋思想動力和典范文本。但是,通過這種回溯活動,“啟蒙式”批評也僅保持著對當代文學及批評的批判姿態,無論是可疑的批評主體、陳舊的文學觀念、高度雷同的批評模式,還是蒼白的道德評價、避實就虛的批判鋒芒,都顯示出其合法性危機。
“志業式”批評去掉了“啟蒙式”批評的意識形態立場,批評成為一種科學研究,而不是作為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或社會學家的分析、預言活動。牛文稱“志業式”批評為價值共同體,但事實上,“志業式”批評并不存在價值共同體,單一的價值觀恰恰被學院的考核制度所忽略,甚至學術生產機制所反對的——學術期刊組織學術問題討論時,尤其鼓勵價值立場相互論辯。牛文還認為,“學院派”批評的主題化、專業化等特點來自學院的科研考核制度,從經濟角度考察“志業式”批評的成因當然有其根據,但并不能解釋“志業式”批評的非功利性特點,比如審美立場、問題意識、跨學科研究方法等。這種評價忽略了“志業式”批評的批評立場的合理性,而且把批評的專業化與公共性立場完全對立起來,也頗為狹隘。
不管是就某些學術問題組織討論,進行文學史史料的整理和發現,開展作家作品批評,還是回顧新時期40周年的文學研究成果,研究當代著名批評家或推出青年批評家,當下的“志業式”批評構成了一個學術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學術規范而不是現實關懷構成其道德底線,知識生產而不是思想批判成為它的主流,比如文學史的發現與重新闡釋。“志業式”批評的研究立場來源于20世紀文學批評的幾個轉變:
第一就是批評由哲學、美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學科的附庸發展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變化。如果說“啟蒙式”批評與政治、哲學、歷史更為契合,政治激情、歷史意識、批判立場和辯證法構成了“啟蒙式”批評的獨斷論模式。那么,“志業式”批評則更類似科學研究,研究對象的觀察描述、批評對象的選擇、問題的提煉論證和解答,這些是“志業式”批評的常規活動。相對于“啟蒙式”批評對普遍真理的追求和捍衛,“志業式”批評對真理的譜系、話語及運作機制更感興趣,它致力于對文學的客觀分析、闡釋。20世紀被稱為“批評的世紀”,這很大程度體現在批評成為了一門獨立的學科。20世紀文學批評引人注目的是其自律性追求,批評甚至可以切斷文學與作者、讀者等外界事物的聯系,把文學批評作為一門科學對待。文學觀、文學文本、文學語言、批評方法、文類、文學史、文學制度等被重新勘測,這些批評活動完全改變了人們對文學的理解方式。
第二,文學批評的審美建制。雖然這一特點現在飽受批評,但批評的審美建制并不是當代文學批評的成就,而是啟蒙主義時代以來隨著宗教信仰的衰落,藝術救贖功能被逐漸放大的結果。另一方面,審美批評一直伴隨著啟蒙現代性的發展,是批判啟蒙現代性的同一性思維的對立面,它排斥普遍性、主體性、中心、確定性、同質性等,努力彰顯文學藝術的非功利性、異質性特點,比如現代主義及后現代主義文學對現代性的批判。文學批評審美建制的問題在于自身的僵化,可以通過重新激活其價值批判維度來解決,審美實踐本身包含意識形態內涵,而且20世紀文學批評的人文主義和形式主義思潮構成了審美自律性與政治功利性的對話與融合。
第三,文學批評的理論化和超學科方法。后現代主義思潮擁抱差異和異質性,幾乎在文學批評的每個環節,都出現了決然不同的概念和路徑。文學批評研究他者、反諷、含混、話語、外位性、身份、夢境、規訓、編碼、仿真、互文、狂歡、身體、欲望、社會性別等等。在一些哲學家看來,文學批評已經取代了哲學,成為一種綜合性的跨越多個學科的理論,卡勒稱其可以解答陽光下一切現象和問題,“為意義提供了新的和有說服力的說明”[2]。文學批評的理論化背后是對同一性邏輯的分解,范疇概念的更新意味著批評思想的重新建構,大量的人文甚至自然科學術語的涌入改變了文學批評與歷史哲學的緊密聯系。批評不再與現代民族國家、社會現實、主體精神休戚相關,背負過重的功利性內涵與功能,而成為各有特色的“片面的真理”的對話場域。可以說20世紀文學批評本身即是非同一性思維的成就。文學批評的理論化不僅僅表明20世紀文學批評對哲學、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語言學等學科的廣泛借鑒,而且也充分證明20世紀是一個泛文學時代,幾乎所有的人文學科都注意到了文學的價值,它們的跨學科研究從各個角度擴展了文學批評的領域。
知識體系的變化決定了批評的學科化和專業化,同時,對同一性思維及其一元論后果的反思也促使了批評的轉向,“志業式”批評是新時期以來西學東漸和學術思想反思的結果。當下中國的“志業式”批評也并不缺乏牛文所憂心的批評公共性,批評公共性的萎縮很多時候并不能僅靠指責“志業式”批評就能解決。“志業式”批評是文學批評脫離政治話語的結果,也是批評從神壇走向職業化的結果,批評者不再承擔政治任務和思想導師的職責,而是回到學術工作本身。但“志業式”批評是不是去政治化、去公共性,要看如何定義政治。倘若政治指的是權力的分配和斗爭,“志業式”批評當然遠離政治。但朗西埃認為,文學的政治指的是感性的分割,是對空間和時間、地位和身份、言語和噪聲、可見物與不可見物等進行的再分配,當文本立足于感性的實踐與分配,它就在歷史、詞語和事物之間建立了自己的政治領域。[3]由此看來,專注于文學研究的“志業式”批評同樣含有政治性和道德性,只不過不是充滿道德優越感的“啟蒙式”批評的政治與道德立場。
注釋:
[1]【美】勒內·韋勒克:《批評的諸種概念》,羅鋼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3-34頁。
[2]轉引自【美】彼得·基維主編:《美學指南》,彭鋒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68頁。
[3]參見【法】雅克·朗西埃:《文學的政治》,張新木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4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