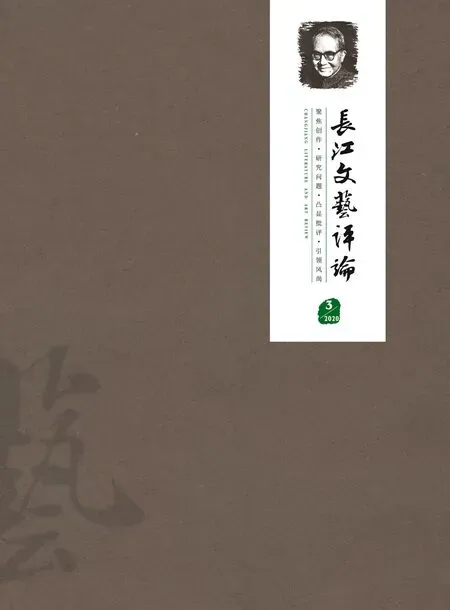關于話語
◆馮黎明
自從福柯的思想和理論在中國學界流傳,“話語”這一概念就漸漸地演變成為了人文學術知識分子們的“常用詞”。特別是在文藝評論和文化研究領域里,諸如“批評話語”“文學話語”“理論話語”“敘事話語”等等,幾乎成了理論“熱詞”,被學術知識分子們廣泛使用。但是從這一術語在學界的使用情況看,“話語”作為具有特定內涵和外延的理論概念,并沒有得到清晰的規定;學界在對該概念的使用中存在著非常明顯的隨意性。就漢語的表達習性而言,我們當然不可以阻止人們以日常語言的方式使用“話語”這一詞匯,但是作為學術概念和思想概念的“話語”卻必須在嚴格的學理規定性下使用,因此我們有必要對“話語”這一概念的源流、內涵、邊界等作出學理維度上的梳理和界定。
一、“話語理論”所涉及的一些關鍵詞匯及其基本內涵
1.關鍵詞:語言(language)、言語(speech/parole)、話語(discourse)、陳述(statement)、話語理論(discourse theory)、話語與權力(discourse and power)、話語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話語范式(discourse paradigm)
2.關于“話語”概念的基本理解
斯圖爾特·霍爾認為,話語可以表述為“一組陳述,這組陳述為談論或表征有關某一歷史時刻的特有話題提供一種語言或者方法。話語涉及的是通過語言對知識的生產。但是,由于所有社會實踐都包含有意義,而意義塑造和影響人類所作所為以及操行,所以一切實踐都有一個話語的方面。”[1]福柯在《知識考古學》中也明確地表示,一切均在話語中。一般說來,我們將福柯思想的內核理解為關于知識—權力的批判,其實福柯關于知識—權力的批判的起始點(或者說切入點)是話語問題,因為福柯將人類的社會實踐的屬性、形態、結構和價值均視為話語活動的產物。在福柯思想的影響之下,現代人文學術對話語問題給予了特殊的關注。尤其是在文化研究中,話語成為了“理論”和“后理論”從事批判工作的端口,由此形成了現代人文學術領域的一個引人注目的論題,即所謂“話語理論”或者“話語批判”。
關于話語理論可以作如下一般性的釋義:(1)話語是一種語言實踐,它以談論、陳述的方式進行;話語對存在的談論或者陳述是意義、知識和真理生成的機制;一切社會實踐都緣起于人類的話語行為,話語生產出知識、知識構筑了權力。(2)話語受制于語言規則,但是它并不能等同于語言,它是具體的語言行為而非普遍性的符號系統或結構模型,同時話語又具有社會實踐的某些特性,因此它也不能等同于speech或者parole,即不等于個別的“說話”;話語是具有同一性和持續性的言語行為。(3)后結構主義的話語理論將話語理解為全部社會實踐的生成機制,因此話語分析被認為是理解社會文化歷史的介入點;文化研究從話語理論中發展出來一套“批判性話語分析”的方法,這一方法將語言論轉向和批判理論結合成為一種新型的人文學科知識形態。
話語概念的直接起源是索緒爾關于“語言”和“言語”的區分。語言是普遍性的符號系統和結構模型,而言語則只是具體個別的“說話”或者“書寫”行為。語言和言語的區分使得人們開始關注既有具體行動的特性又有行為的同一性的“話語”。索緒爾之后的結構語言學以及結構主義敘事學,都曾經或者以text(文本),或者以utterance(段落),或者以sentence(語句)為基本表意單元來表述跟話語概念相類似的意思。“話語”這一概念可以在日常語言意義上泛指所有被說出的句子,但是日常語言意義中的“話語”跟學理意義上的“話語”是有著明顯差異的。在日常語言中,“話語”幾乎可以指稱所有“說出”或“寫出”的句子。而在學理意義上,“話語”既非“語言”亦非“言語”,作為語言行為的“話語”表現為一組或數組具有同一性、持續性特質的陳述或者談論,這些陳述或談論在用詞、句法和邏輯關系等方面顯示出系統性的特點。
趙一凡主編的《西方文論關鍵詞》一書中,由陳永國先生執筆的“話語”條目,從“話語”概念在現代語言學中的演化、巴赫金和福柯等人關于話語的闡述以及西方現代文論中話語概念的使用等角度對話語進行了比較細致的介紹。[2]國內還有不少學者研究福柯的話語理論并由此推進至關于話語的一般性理論界定,西方學界在話語理論研究領域中的代表性學者有哈貝馬斯、E.拉克勞、斯圖爾特·霍爾、圖恩·梵·迪克(Teun A.van Dijk)等人,普通語言學領域中也有“話語分析”理論,但僅僅只是語言分析技術層面上的一種知識形態。
二、語言論轉向與話語
1.話語理論是語言論轉向的后果。語言論轉向將西方思想從近代的知識論哲學推進到現代的語言論哲學;語言論哲學的各種學派——諸如邏輯經驗主義、分析哲學、現象學、闡釋學、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等等——大都認定人與世界的基本關系乃是語言關系。自新康德主義以來的西方人文學術為話語理論的生成提供了豐富的思想和知識資源;由語言論轉向潮流普及開來的語言本體論——語言是一切意義、知識和真理之源——是話語理論形成的觀念前提,因此我們既可以將話語理論當作一種反思哲學,也可以將其當作一種語言本體論。
2.語言論轉向的思想運動可以理解為三個歷史段落——也可以視作語言哲學的三大主題,即:a.語言本體論(以語言為人與世界的本體論關系,認定語言活動是存在之出場,其代表性思想家有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等);b.語言結構論(以語言的符號結構為意義的創生機制,認定能指的差異性組合生成了語義,其代表性思想家有索緒爾、列維-斯特勞斯等);c.語言行為論(以敘述行動為語言的主體內涵,認定話語是意義、知識和真理的生產者,其代表性思想家有伽達默爾、德里達等)。話語理論屬于其中第三個段落/主題,即話語理論是一種特殊的語言行為理論。話語理論從維特根斯坦的日常語言用法的分析中獲取了較多的思想能量,同時也從言語行為理論的語言學那里汲取了一些專業技術性的營養。
3.語言本體論在形而上學層面上認定人與世界的本質關系就是語言關系,語言結構論從形式層面上認定語言的自主性和自洽性的構成,語言行為論則從實踐層面上認定語言“用法”的意義建構機制。因此“話語”作為語用學實踐,它以關于存在的談論或陳述的方式賦予存在以秩序,亦即:話語用“詞”賦予“物”以秩序,使得我們關于存在的原初經驗進入某種普遍可理解的境界。最為重要的在于,話語對存在的陳述將原始的、無意義的存在導入某種意義狀態,比如十進制的數理邏輯的陳述將自然運動導入一種循環時間化的意義世界的存在模式。
4.語言論轉向之最為重要的思想后果是:全部意義、知識和真理都是語言對存在進行追問、理解和言說活動的產物,因此語言行為是人類全部社會實踐的起源。歷經語言論轉向的三個階段/主題,至后結構主義出場,話語被人文學界設定為人類全部社會實踐的啟動機制;后結構主義者將話語當成理解和評價文化文本之意義的窗口。比如對于新歷史主義的歷史編撰學來說,作為“事件性”的歷史事實通過特定話語的敘述而獲得了因果聯系,于是“事件”被編撰成為了“歷史”;進而在比如E·拉克勞、雅克·朗西埃等學者眼中,政治斗爭也只是話語或者審美的后果而已。
三、話語理論:從巴赫金到福柯
1.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文本中發現了一種多元敘述主體“對話”(dialogue)的“復調性”。在巴赫金看來,長篇小說的敘事就是一場“對話”,而且這場“對話”在時空中無限延伸。“存在就意味著對話的交往,對話結束之時也就是一切終結之時”。[3]巴赫金的“對話”概念跟后結構主義的話語概念有著明顯的相通之處,只是巴赫金強調的是話語的“談論”(discuss)行為,而后結構主義的話語概念更強調“陳述”(statement)。
2.德里達的“延異”理論:德里達關于“延異”的論述從話語建構角度終結了邏各斯中心主義。“延異”表明話語行為作為社會實踐的無處不在,也表明任何“陳述”或者“談論”都必然地內在于歷史,話語不是超歷史的封閉系統。“La différance”這個詞既有差異的意思也有延續的意思,德里達用以表達的真正含義是一種在時間中無限延續的差異性,延異決定了任何一種敘述行為都必然地以“互文”形態存在于歷史之中,也決定了作為語言游戲的話語跟社會實踐的普遍聯系。
3.福柯的“知識型”理論:對于福柯來說,特定的話語活動生產出特定形態的知識,特定形態的知識則生產出特定場域的權力。話語作為一種建構性的陳述或者談論的活動,是全部知識、真理和意義的構型機制,“話語之外無他物”。福柯以“話語構型”(discoursive formation)一語來表明自己關于社會實踐中權力運作機制的理解。自福柯的話語權力理論現身于學界始,現代人文學科發生所謂“話語轉向”,對話語的批判性分析成為文化研究和社會研究的重要主題之一。福柯的話語理論為人文學科的知識生產開辟了一條新的路徑,這條路徑的入口是“話語”,它通往關于人類社會實踐中權力關系建構歷史的反思。
4.拉克勞和墨菲關于話語的論述:這兩位學者意圖通過話語形態的分離、對抗等現象解析政治斗爭的本質。在拉克勞和墨菲看來,人類的各種社會實踐中充斥著“浮動的能指”,這是話語活動致力于重新設定能指與所指的關聯的表象,這種設定能指與所指間指涉關系的話語活動指向“領導權”的建構,因此話語活動本身就是“身份政治”的實踐形式。話語的紛爭、對立、聯合等等,其實質是領導權的配置、分解、占有等等,所以關于話語的批判就是關于政治的批判,反之亦然。[4]
5.話語理論的知識學資源:結構語言學、后結構主義、分析哲學、精神分析學、批判理論、言語行為理論等,可以說,進入20世紀以來主要的人文學科知識潮流,幾乎都被話語理論承續了一種或者數種知識資源或者方法論資源。作為人文學術的話語理論跟普通語言學教學技術意義上的話語分析有著迥然相異的知識學面孔;人文學科的話語理論是一項通過話語的分析實施對人類社會歷史文化的批判性詮釋的思想工作,盡管它也需要從普通語言學的話語分析中獲取技術元素。
四、話語·知識·權力
1.福柯的思想和理論是導致話語概念風行于現代人文學術的主要原因。作為后結構主義的代表性思想家,福柯由“話語”入手解釋理性主義文化霸權化歷史的學理路徑是語言論轉向以來人文學科知識領域里最具革命意義的思想成就之一。福柯關于知識與權力的論述、關于譜系學和考古學方法的論述、關于監獄瘋癲診所性觀念等等的進化歷史的論述,其闡釋入口就是“話語”的建構性實踐。在《何為啟蒙》[5]一文中,福柯討論了一個康德式的問題,但是他對啟蒙的解釋卻迥異于康德在《何為啟蒙》中關于啟蒙的解釋。在福柯看來,啟蒙運動的主題是“啟蒙話語”的生產和流行,啟蒙話語表明了一種“現代性的態度”,被現代人文學界認定為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的啟蒙在福柯那里只是一場特定形式的話語的建構活動而已。
2.福柯理論的核心內容是對于知識建構權力的歷史的批判性反思。在關于社會權力建構史的考古中,福柯首先論述了話語構建知識的“生產史”。對于福柯來說,“話語”以一種持續性的、同一性的敘述將“秩序”加之于敘述對象之上,使之獲得一種可普遍理解的且具有規定性的質態和結構,于是形成了由系統化的概念和邏輯關系構成的所謂“知識”。比如,理性主義文化關于“瘋癲”的敘述,最終構成了現代醫學關于瘋癲的病理學知識體系,因此我們可以說知識的本質在于一種話語行動。用福柯的話來說就是,“詞”賦予了“物”以秩序;原本無意義的“物”之所以能夠被人們普遍地理解和評價,都是這“秩序”規訓的結果。新歷史主義學者海登·懷特等人依據福柯關于話語的“生產史”的論述將“歷史”視作“話語”對“事件”的“塑形”。
3.福柯認為,被話語構型產生的知識是權力生成的基本機制。“知識”用系統性的術語、概念、句法以及指涉邏輯使得“物”以“秩序”的形態呈現,知識因此而占據了實施“規訓”行動之主體的地位,具有了對“物”以及對知識接受者們進行規訓以至于展開監控的權力,比如在《規訓與懲罰》中,學科分類形態的知識就是一種“紀律”,即由形態學層面作出的一系列必須遵循的限定。[6]福柯在《作者是什么》[7]一文中認為,“作者”這一署名權力生成于一種特定的話語形態,作者中心論只是主體論哲學的一種想象而已,所謂獨創性的作者,其本身也只是特定的話語形態的產物。比如說,不是魯迅創造了魯迅式話語,而是魯迅式話語創造了魯迅這一作者署名。
4.在1969年出版的《知識考古學》中,福柯在考察人類中心論思想譜系時描述了文藝復興以來西方知識的構型歷史。14至16世紀(文藝復興)的知識以相似性為基本理念,其敘述話語跟存在的關系是一種比喻性的關系;17至18世紀(古典時期)的知識以再現性為基本理念,其敘述話語跟存在的關系是一種同一性的關系;19世紀的知識以人類中心論為基本理念,其敘述話語跟存在的關系是一種主客體性質的關系;現代知識則是一種“能指自由滑動”的話語游戲。跟現代主義的文學藝術一樣,現代知識也是一種能指的自由游戲,即話語脫離“大地”自我指涉的純粹形式化的知識。
五、作為敘述行為的話語
1.話語在其表層形態上是一種敘述行為,它以關于某話題的談論的方式展開。如果說“語言”概念表達的是抽象符號的普遍性結構模型和規則系統,那么“話語”概念表達的則是語言的實踐行動。盡管話語必須遵循普遍性的語言規則,但是話語這種語言實踐行動更主要的屬性在于它的行為性,即它是語言主體使用特定的詞匯和句法談論特定話題的一次或者數次的“行動”。話語的行為性將話語理論跟普通語言學理論區別了開來。話語的行動性質要求我們不僅需要將話語視為一種文本狀態的符號結構體,更應當重視話語的動機(比如敘述行為的倫理訴求、政治目的或者審美欲望等等)、話語的策略(比如詞語的選擇、指涉關系的設置、修辭手段的運用等等)、話語行動主體(比如敘述者的社會身份、歷史處境等等)。文本這一靜態的符號結構體的背后隱含的是更有歷史內涵的“話語行動”,只有將話語行動中的敘述動機、敘述者身份、敘述技術揭示出來,話語的分析才會彰顯其思想的力量。
2.作為敘述行為的話語不同于言語行為理論意義上的“說話”。話語是一種持續性、同一性的語言行為,它有著相對統一的詞匯、句法以及指涉關系,因此話語理論跟奧斯汀、西爾等人的言語行為理論在知識學屬性上有著根本性的差異。相比結構語言學,言語行為理論關注的不是普遍性的語言表達式的結構模型,而是具體的言語行為,即speech而非language。話語理論雖然也以具體的敘述行動為學理對象,但是話語理論需要超越個別性的言語活動而去發現那些持續性地反復出現的敘述行為,因為只有在這樣一些具有同一性功能的敘述行為中,我們才能夠見出話語賦予“物”以“秩序”的知識構型機制。正是因為話語理論致力于通過對敘述行動的辨析找到意義、知識和真理被生產出來的歷史,所以話語理論比任何專業技術意義上的語言學理論更具批判性和歷史內涵。
3.話語理論需要對敘述行為中的那些反復出現的詞匯、句法和邏輯結構予以特殊的關注,因為這些語言實踐會形成敘述的持續性和同一性,進而在此基礎上構成所謂敘述范式。比如我們在體檢報告中讀到的那些有關人的體質的數據、分類、標準、判斷等等,這些范式化的敘述話語,構成了病理學的學科知識體系。由話語的敘述構型而形成的知識系統借助于術語、句法和指涉關系對存在的屬性、價值和結構做出了規定,知識主體由此把秩序化的意義投向無意義的存在之物(物自體)從而將主體自身推進至所謂“澄明”的境界。這“澄明”讓知識主體自以為徹悟了存在之存在性并獲得了主宰存在的權力,于是他們聲稱自己是“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殊不知人類自詡的“主體”卻是被一段一段的話語造就的。話語構制成了文化,而人則是文化的互文性產物。
六、作為知識構型的話語
1.福柯的話語理論是康德以來哲學轉向的必然后果。康德之后,古典時代的宇宙論哲學轉向主體論哲學,這種主體論哲學以人類理性為思辨對象、以先驗人性為思辨啟點、以反思和批判為思辨方法,力圖在與“自然”相對應的“人文”意義上通過“反思”界定人類“自我”的主體性。進入20世紀后,主體論哲學走出認知理性的自我反思的階段,推進至人類作為語言主體的自我反思階段;至后結構主義登臺,語言的“延異”殘忍地消解了啟蒙思想塑造的個人主體性,語言實踐本身成為了能夠以“說出”或者“書寫”方式“造人”的一種最重要的力量。于是,作為語言實踐的話語,也不再被看作“知識”的表述手段或工具,而升華成為“知識”的“生產者”。
2.結構主義將語義的生成機制定位于句法結構,此一定位給予語言本體論以學科化知識的合法性依據。后結構主義以之為意義生成機制的“話語”,則突破了“句法結構”的自洽性邊界,將語言活動納入全部意義世界的實踐之中。后結構主義借助于話語的“延異”性質而使得人文學科理論恢復了歷史性,以話語的意義建構功能為基石重建了人文學科理論跟社會實踐的普遍聯系。作為“法國理論”[8]的代表,福柯的話語理論最為重要的創新價值在于,這一理論以“詞”對“物”的秩序化功能為前提闡述了話語構建知識進而形成權力的歷史內涵。
3.話語對個人性的、偶發性的“意義”進行陳述或談論,這種陳述或談論將在三個維度上進行:其一是術語,它體現為一整套具有相對集中性質的(學科體系的、意識形態指向的、社群或者文化的,等等)詞匯,比如中國古代詩學常用的“言志”“載道”“緣 情”“情景”“意 象”“韻味”等等,這些術語可以將不確定性的感覺經驗固化為具有特定內涵的概念;其二是句法,它體現為具有一定的同質性結構的(語法體制的、修辭格式的、語音或書寫形態的,等等)表達程序,比如中國古代詩學常用的對應性句法、詞性漂移式謂詞函項,等等,這些句法將詞匯整合、序化成為系統性的敘述;其三是指涉關系,它體現為確立能指與所指間(再現的、比喻的或能指自主性的,等等)的關聯方式,比如中國古代詩學中的自然物意象隱喻的表意習性、“不完全形式化”的意指行動,等等,指涉關系的確立意味著話語獲得了闡釋的普遍有效性價值。
4.話語通過具有相對同一性的術語、句法和指涉關系對原初的“意義經驗”進行陳述,這種陳述的反復展現并為特定社會實踐場域(比如某某學科領域等)普遍接受,則其陳述就形成為一種范式,該范式為這一社會實踐場域提供了普遍有效的知識構型。話語行為是特定知識范式得以生成的機制,話語的敘述行為一旦擴展成為范式,則某一知識系統便完成了其構型。我們在各個學科的知識系統建構中都可以通過話語的分析梳理出該學科從原初的意義經驗“形式化”為概念、邏輯系統的“知識”的歷史,比如中國古代詩學理論的知識學構型的歷史,等等。
七、作為權力實踐的話語
1.由話語構型的知識借助于普遍有效性的闡釋功能而形成“知識范式”,這意味著知識對所謂“真理”的占有,因為知識的范式化使得該類型的體制化知識至少在場域內擁有不可置疑的闡釋有效性。托馬斯·庫恩借“鴨兔變形”描述知識范式革命帶來的變化:“在革命以前在科學界中的鴨子在革命以后變成了兔子”。[9]這也就是說,知識范式的改變帶來了知識對象屬性的改變,比如在中國古代畫論中,“形似”是非藝術性的,而在西方近代寫實主義藝術哲學中“形似”則是藝術的典范形態。“形似”是否具有藝術屬性是由“理論話語”來判定的,這判定的權力屬于“理論話語”。話語的這種“構型”機制在范式中發展成為一種“構性”的功能,于是建構了知識范式的話語在這一為存在“構性”的行動中獲得了一種“創世”的權力,亦即:話語為存在立法。
2.話語的知識學構型以相對統一的術語、句法和意指邏輯將特定范疇的知識對象納入秩序化的表意體系之中,這一方面“規訓”了存在的“存在性”,另一方面也“規訓”了知識接受者的認知行為。因此由話語構型而生成的知識范式關于知識的陳述便具有了“真理性”,而“知識”一旦升級為“真理”,那么構造此知識的話語也就宣示了一種“言說真理”的權力。比如特定學科的話語活動建構了特定的學科理論(諸如文學理論、美學理論等等),進而學科理論作為一種知識范式為本場域內的存在制訂了概念、句法、邏輯關系、闡釋邊界等等法規,于是該學科理論就排他性地占據了本領域的“文化領導權”,福柯就是在此意義上談論discipline(學科)的含義的。對于福柯而言,話語這一概念揭示了權力在具體的人類行為中被生產出來的歷史,因此他堅持使用“話語”概念而拒絕那個模糊不定的“意識形態”概念。
3.話語通往權力的道路上有三道門檻。其一是話語對于感覺經驗的初級談論,此談論形成了“意義”,其二是同一性的話語實踐對于意義的構型,此構型形成了“知識”,其三是知識集約成為“范式”,此范式制作出了“真理”,“真理”的出場則意味著權力的建立。知識范式在本場域內配置并擴展權力,于是“話語”便表現為“身份政治”的實踐。在知識構型實踐中創造或者持續性地使用特定話語系統的話語主體,借助于“署名體制”而占有了文化領導權,因此他們也獲得了本場域內的權力設置、權力分配和權力承續的地位。就此而言,我們可以在比如學科知識生產實踐活動中探尋出文化資本(話語創制能力)權力化的基本路徑,再比如通過政治領袖的話語策略探尋其獲取并占有最高權力的路徑。
八、文化研究:批判性話語分析
1.艾倫·盧克(Allan Luke)認為,批判性話語分析是20世紀以來人文學術領域主要思潮聚合的結果,因此這一方法成為了文化研究的核心技術。[10]我們可以將文化研究視為19世紀新康德主義關于“人文科學”知識學屬性反思以來人文學術演變的最新形態。以學科知識的“歷史性聯合”為其特征的文化研究的知識學同一性一直是一個令人迷惑的問題,而批判性話語分析這一闡釋技術的定型及其實踐使得文化研究借助于方法的同一性而獲得了學理意義上的同一性。批判性話語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最為顯著的思想特性在于它把語言分析和批判理論有機地結合了起來。
2.批判性話語分析作為人文學科知識生產的新技術,是語言論轉向以來各種思潮歷史積淀的結果,其句法分析源自于結構語言學、其癥候式分析源自于弗洛伊德主義、其語言用法分析源自于分析哲學、其現代社會批判源自于批判理論,等等。批判性話語分析是當代人文學術領域最具有增長效應的一種闡釋技術,這一技術通過為話語理論注入歷史主義和批判精神而提升了話語理論的思想功能,避免了話語理論滑入純粹學科技術的“鄉愿化”狀況——比如普通語言學教學中的所謂“話語分析”。批判性話語分析繼承了批判理論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理性主義文化的批判性反思的傳統,同時又祛除了經典批判理論的“大敘事”思路;批判性話語分析接納了結構主義的語言結構本體論,同時又將言語行為置于人類社會實踐的無限“延異”之中從而重建了話語的歷史性。
3.批判性話語分析的技術方案首先認定作為語言實踐的陳述行為對意義、知識和真理的構型功能。這就是說,一切文化文本都是話語構型的結果,話語以其“邏各斯”功能賦予原始的感官經驗以可理解性的秩序從而形成了“意義”,“意義”再被話語納入同一性的邏輯化陳述體系從而形成“知識”,“知識”又被話語陳述為“主體”和“范式”,于是產生了權力化的“真理”。其次,批判性話語分析要求人文學術發現那些具有“癥候”特性的話語。文化文本由話語實踐生成,話語持續性地使用同一性的術語、句法和指涉關系,這又彰顯出話語的特殊“癥候”。話語的構型機制就潛藏在這些“癥候”之間,發現話語的癥候意味著找到了話語分析的入口。第三,批判性話語分析要求對話語癥候進行分析式處理,即:從語義、句法關系、修辭策略、意指邏輯等角度辨析話語的結構及其跟社會實踐的關聯,然后由此關聯解析話語中隱含的權力關系、意識形態等歷史性意涵,最后則是對此歷史性的意涵做出屬性、價值的判斷。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在此作簡短闡述,那就是漢語的“話語理論”應該跟西方語言的“話語理論”有所區別。漢語是一種“字本位”的符號系統,其辯義原則被艾偉先生界定為“形—義關系”[11],因此漢語的話語構型跟拼音文字的語言體系相比有其自身的特定屬性。作為一種“不完全形式化”的符號系統,漢語以“字形狀物”訴諸視覺聯想為其表意的基本機制,因此“書寫性”可以說是漢語的一項特長。如果說“句本位”的西方語言長于用句法結構“敘事”的話,那么,漢語這種“字本位”語言則長于用“字形”構造“意象”,這一語言學差異不僅形成了中國文學跟西方文學的“文學性”呈現為兩種不同的形態,而且也導致了漢語思想跟西方思想之間的巨大分別。[12]所以我們在對漢語文化文本做“話語分析”的時候,需要更多地注重“字形”中隱含的指涉關系。
注釋:
[1]【英】斯圖爾特·霍爾編:《表征——文化表象與意指實踐》,徐亮、陸興華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44頁。
[2]參見陳永國:《話語》,載趙一凡主編:《西方文論關鍵詞》,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231頁。
[3]【蘇】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載《巴赫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0頁。
[4]拉克勞和墨菲在《領導權與社會主義戰略》中借助于話語理論對國際社會主義政治進行了分析和總結。參見Ernest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co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s Politics,London Verso,2014.
[5]【法】米歇爾·福柯:《何為啟蒙》,載杜小真編選:《福柯集》,顧嘉琛譯,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年版,第528-543頁。
[6]《規訓與懲罰》法文原文書名是Surveiller et Punir,福柯自己建議英文譯為Disciplne and Punish。這里的“discipline”一詞主要意思是“紀律”,另一個意思就是“學科”。華勒斯坦等人的《學科·知識·權力》中文譯本將“discipline”一詞直接譯作“學科規訓”,此譯法跟福柯的本意相吻合。參見I.華勒斯坦等:《學科·知識·權力》,劉健芝等譯,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12頁。
[7]【法】米歇爾·福柯:《作者是什么》,載王潮選編:《后現代主義的突破:外國后現代主義理論》,逄真譯,敦煌出版社1996年版,第270-292頁。
[8]“法國理論”(French theory),英美學界以此指稱后結構主義思想,大多數法國學者都被歸于此名下,如福柯、德里達、巴特、利奧塔、拉康、德勒茲、克里斯太瓦等等。F.杰姆遜最早在The Cultural Turn(1998)提出此稱謂,伊格爾頓的After Theory(2003)以“理論”為名對所謂“法國理論”做了鏡像式的描述。一般說來,“法國理論”致力于反對本質主義、中心主義和普遍主義,這批知識分子熱衷于描述個人性、異質性、他者性、差異性以及不確定性的意義經驗。
[9]【美】T.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李寶恒、紀樹立譯,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0年版,第19頁。
[10]【澳】艾倫·盧克(Allan Luke):《超越科學和意識形態批判——批判性話語分析的諸種發展》,載陶東風等主編:《文化研究》第五輯,吳冠軍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11]艾偉先生認為漢語的意義表達機制是以書寫筆劃的構型形成視覺聯想,它稱之為“形—義關系”,這一點是漢語區別于英語拉丁語等拼音性文字體系的最為顯性的特征。關于此論述,可參見艾偉:《漢字問題》,中華書局1949年版。
[12]漢語跟“句本位”的西方語言在表意機制方面的最大差異在于漢語是一種“不完全形式化”的符號系統,它以“字形狀物”的方式訴諸視覺聯想形成指涉邏輯,因此隱喻在漢語中必然演化為一種普遍的表意策略。關于此一論說,參見馮黎明:《狀物與文學性》,《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