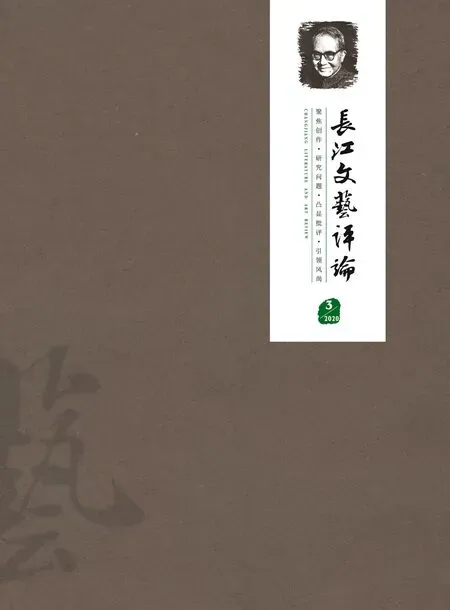話語研究的可喜深化
——以王彬的《從文本到敘事》為例
◆梁鴻鷹
話語是文學創作中的一個重要的課題。
文學工作者打交道的文學是一種特殊的話語樣式,一種有別于常態的交流方式,如何交流得好,把人性揭示好,把故事講好,運用好話語是極端重要的。我們鼓勵文學創作,研究文學現狀,評論宣傳文學作品,培養文學人才等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文學到底是什么,文學的敘事方式有哪些規律?我們卻研究得不夠,多年來我們以為文學只要反映了社會生活,成為火炬和號角就可以了,但這還不夠。如果只強調題材而忽視敘事策略,不關注、不研究,那就大錯特錯了。文學的本質到底是什么,什么樣的文字才能稱之為文學,文學有哪些規律,有哪些可能性,這些有待進行深入的探究與思索。
一、自由直接話語與亞自由直接話語
王彬的敘事學研究內容豐富,有趣的話題之一就是他關于話語的研究。他在新近著作《從文本到敘事》中用了三章的篇幅討論話語問題,即《小說中的自由直接話語與亞自由直接話語》《變異話語》與《漫溢話語》。王彬認為,小說就話語而言是由敘述語與變異話語組成。敘述語來自敘述者,轉述語來自小說中的人物。轉述語依據常規分類有四種形態:直接話語、間接話語、自由直接話語、自由間接話語,王彬認為還應該有一類,即亞自由直接話語。
王彬指出直接話語的形態,比如:他沉吟了一會,他說:“我明天一定來。”在轉述語之前,設置了主語、謂語、引詞(冒號、引號),構成轉述語的敘述標記。由于這些標記的存在,轉述語與敘述語分離,從而在轉述語中出現了第一人稱。如果把口中所“說”改為心中所“想”,便轉化為內心活動,二者在表述上是一樣的。自由直接話語的形態,比如:他沉吟了一會,我明天一定來。轉述語之前無任何敘述標記,但是在轉述語中出現了第一人稱。相對于自由間接話語,可以理解為此時的轉述語是對敘述語的改造。易而言之,在本來應該是敘述語的地方出現了轉述語,這樣的表述便是典型的內心獨白。而這種內心獨白如果是隨機式的聯想,便演化為意識流。自由直接話語為內心獨白與意識流提供了表述形式。
除此以外,還有一種轉述語的形態,即:亞自由直接話語。襲用上面的例子表述——他沉思了一會,他說,我明天一定來。相對于自由直接話語,增加了主語與謂語,敘述標記變了,將冒號與引號的敘述標記改為逗號,在轉述語中仍然出現了第一人稱:“我明天一定來。”[1]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自由直接話語與亞自由直接話語在當下小說創作中大范圍出現,已經成為中國當下的小說與西方小說在寫作手法上的一個顯著不同。而這樣的自由直接話語和亞自由直接話語,王彬認為實質是殘缺的轉述語的形態,而這種形態的轉述語在《論語·憲問篇》中找到例證: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2]
孔子認為如果國家的政治清明,官員可以領取俸祿;但是,如果政治黑暗,官員再領取俸祿就是恥辱了。原憲問:“沒有好勝、自夸、怨恨、貪心的人,可以謂仁嗎?”孔子回答:“能夠達到這樣程度的人也就難能可貴了,但是認為這樣的人便是仁,我并不贊同。”楊伯峻說:“可以為仁矣——這句話從形式上看應是肯定句,但從上下文看,實際是疑問句,不過疑問只是從說話者的語勢來表示,不藉助于別的表達形式而已。”[3]
從轉述語的角度看這種缺少主語與謂語的轉述語形式,既不屬于自由直接話語,也不屬于亞自由直接話語,屬于異常殘缺的轉述語形式。
當下的作家為什么如此熱衷于這種形式?王彬認為,五四以后的小說形式(敘述語+轉述語)實質是對話劇劇本的模仿。劇本由人物對話與背景說明組成,前者屬于直接話語,后者相當于敘述語。在劇本中,敘述語與轉述語的界限十分清晰,不存在混淆的可能。但是,如果我們把表示背景與對話的敘述標記刪略,加上適當的連接語,便很容易改造為傳統小說的模樣。同樣,如果我們把傳統小說按照背景說明與人物對話的模式進行簡單加工,也很容易改造為劇本。從這個角度看,傳統小說是一種對劇本模仿的“類腳本”。作家為了達到“類腳本”的效果,一定要通過完整的敘述標記,把敘述語與轉述語區別開來。而自由直接話語與亞自由直接話語的大量出現,則顛覆了“類腳本”傳統,“使作家的寫作更加得心應手,避免了在兩種話語之間跳來跳去,無論是轉述語還是敘述語統統變成了敘述語,小說只剩下敘述者一個人在講述,從而保證了敘事流暢的最大可能,促進了小說文本的解放。廣大讀者之所以接受這種小說的原因也在于此,閱讀時避免了在敘述語與轉述語之間跳來跳去的麻煩,有什么理由不接受這樣的文本?”[4]只是在接受中,王彬憂慮的是“不要忘記了我們接受的不應該只是轉述語的姿態,還應該包括轉述語的質地,否則只能是買櫝還珠”。[5]
二、小說中的漫溢話語
王彬認為話語與故事在小說中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話語要為故事服務,反過來故事也應該為話語服務,如果處于后一個階段,話語便會漫溢,甚至出現話語自足狀態,此時的話語或者不再為故事服務,或者不再為前面的、有可能生成故事的主題服務,而是旁逸出來形成另一個故事,進而改變小說的主題。
為此,他以莫言的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卜》為例進行分析。《透明的紅蘿卜》是莫言的代表作,講述人民公社時期的故事。黑孩的母親死了,黑孩被派出工,小石匠總是照顧他,小鐵匠則對他很不友善。小鐵匠讓小男孩從田里拔蘿卜,結果蘿卜被小鐵匠丟進河里。凌晨時分,幾只早起的鴨子站在河邊,有一只大膽的鴨子耐不住了,顢頇著朝河里走。之后是關于鴨子的描寫,在鴨子的注視下,走來一個老頭,老頭的背駝得很厲害,脖子像天鵝一樣伸出來,之后是一個光背赤腳的小黑孩,看到這個孩子,公鴨子跟身邊的母鴨子交換了一下眼神,意思是說,上次這個孩子把水桶撞翻滾下河,差點沒把麻鴨子砸死。母鴨子連忙回應:是呀是呀是呀,麻鴨那個討厭的家伙,天天追著我說下流話,砸死它倒利索……[6]
從單純性的故事角度說,鴨子與蘿卜的描寫均可刪掉,莫言不刪顯然有其原因。對此,滿足于故事的讀者可以不讀,有雅趣的讀者則可以品嘗故事之外的味道。總之,關于鴨子的漫溢話語,是可以刪略,也可以不刪略的。
山西作家蔣韻的《紅色娘子軍》則不是這樣,在這篇小說中,簡單的漫溢話語演化為一種顛覆策略,將前面的看似中心的故事轉化為后面故事的附庸。
小說的開頭是:那天,他們三人陪“我”丈夫游新加坡河。“我”丈夫是先生,“我”是愛人的妻子,從一個妻子的角度講述故事。陪先生游覽新加坡河的有三個當地人:大黃先生、小黃先生與駱先生,他們都是用華語寫作的華人。大黃先生年輕時主編一份激進的刊物,他與一個叫唐美玉的女孩談戀愛,大黃先生住這邊樓上,唐美玉住那邊樓下。每天夜里唐美玉便煮一碗甜品,到固定的時候,大黃先生從自己的窗口垂下一只栓繩子的竹籃,唐美玉便把甜品放在籃子里讓大黃先生吊上去。忽然有一天,大黃先生被捉進監獄,唐美玉為了尋找他而精神失常了,每夜都手捧一塊芋頭糕,尋找垂著竹籃的窗口。最后唐美玉投海自盡了。十一年以后,大黃先生刑滿出獄,聽到唐美玉的結局時,一夜間就像伍子胥過文昭關般徹底白了頭。
一天,從中國來了一家芭蕾舞劇團,表演《紅色娘子軍》。看完節目,兩位黃先生去喝啤酒。當他們走到路燈下時,大黃先生戛然站住:“手扶著燈柱,慢慢滑下去,一蹲身,然后小黃先生就聽到了一聲撕心裂肺的、泣血的長嚎。他蹲在地上,嚎啕痛哭。”[7]“入獄、出獄,十一年的監禁歲月,四千多個被海浪吞噬的黑夜,甚至,聽到鮮花般的唐美玉蹈海的死訊,他都沒有哭過,人人都以為,他骨鯁如鐵。”[8]但是看了《紅色娘子軍》以后他卻嚎啕大哭。小說至此結束。如果是這樣,也是一篇不錯地折射新加坡曾經的時代與激進人物的悲劇。然而,如果是這樣,這篇小說也就沒有什么可以分析的特殊價值。
這篇小說的特殊價值在于大黃先生故事中間的漫溢話語。在大黃先生的故事中鑲嵌了一個“我”在“文革”的經歷,從而將故事從大黃先生的故事轉變為“我”的回憶。“我”原來是聽,聽小黃先生講述大黃先生的故事,現在“我”進入往昔的時光隧道,“我”成為故事的介入者了。“文革”中的一天,“我們”在樓上排練《紅色娘子軍》中的斗笠舞,突然聽到有人喊:“葛華你爸跳樓了!”“我”從窗口向下望,看到一個男人“身體攤成一個‘大’字,臉親昵地緊貼著土地”,一個小女孩——就是那個死者的女兒,“分開人群沖進來,呆呆地,遲疑了一會,只一小會,突然氣壯山河沖著那血泊中的死者‘呸——’地吐了一口唾沫。人群中有人鼓起了掌,還有人喊口號。”那一聲“葛華你爸跳樓了”的尖叫,讓“我”記住了那個陌生女孩兒的名字,而她向血泊中的親人啐出那口唾沫,子彈一樣射進了“我”尚還柔軟的心。[9]
“我”的《紅色娘子軍》回憶與大黃先生的悲慘人生經歷,泛射出不同的人生經驗,是兩個國度兩個人的不同的故事,唯一相同的是“紅”的底色。我的回憶位于大黃先生故事中間靠后的位置,是因他的故事而起,屬于后面的故事,但是在指向上,后面的故事卻顛覆了前面的故事,故事在這里發生了變異,也就是漫溢。這是從故事的角度而言。從話語的角度,講述后面故事的話語并不為前面故事服務,易言之,話語在前故事的后面漫溢開來,從而出現了漫溢話語。
與莫言不同,蔣韻的《紅色娘子軍》不是簡單的漫溢話語,莫言《透明的紅蘿卜》仍然可以完整,而《紅色娘子軍》則不可以,因為“回憶”已經升華為小說的中心,大黃先生的故事其實是為后面漫溢服務。同樣是漫溢話語,運用的方式不同,小說的形態也自然發生了不同的質地變化。
所有的話語在文本上可以分為三類:一是科學話語,比如理論文章、科研文章;二是日常生活的應用話語;三是文學家使用的文學話語,王彬指出其實質是變異話語,而變異話語則是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的一個重要的無法取代的鮮明標識,駕馭文學話語需要有技巧,掌握詞語組合的規律,因為話語是與文學作品的水平和質地緊密相連的,這種問題是涉及什么是文學的大問題。
眾所周知,文學的第一個層次是話語,人們從話語進入文學,這與電影不一樣,電影首先是畫面、音響、場景,文學首先從話語進入,從怎么說、怎么講、怎么講得出色便可以看出作品的水平高下。怎么敘事、怎么描寫、怎么對話,如何起承轉合,一般人不深究,而像王彬這樣的有心人,卻從中梳理出一些規律。而這些規律對我們的文學創作和文學的鑒賞及審美感悟能力的提高,肯定極有意義。
王彬依照文學規律梳理出許多話語規律,除上面所討論的自由直接話語、亞自由直接話語,關于語感問題王彬也有深入的探討。他認為,語感是需要認真研究的。語感的問題就是你寫的東西到底能不能訴諸人的感官,能不能夠給人風格化的享受的問題。語感的提出升華了我們對文學的感悟,我們以前沒有從這些角度去考慮,相當于我們在欣賞文學的路途中遺失了許多東西,把文學本身的花朵和露珠遺漏了。看了王彬關于話語的論述,你會獲得一些新的感受,包括詞匯的選擇、控制詞匯之間的節奏、不同句型的組合等等。這些構成語感的部分是衡量作家語言能力的重要標志。文學是一種富于美感的、進行了特殊變異的創作活動(實際上是經過作家反復加工的結果)。王彬這方面的研究,對我們認識敘事具有重要意義。不管是文學創作,還是文學評論,缺乏感染力和魅力,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不把文學創作當成一個技術活,當成一個有技巧的、有規律的、有巨大的獨創性的事業來對待,注定是不能長久的。我國在小說敘事方面有良好的傳統,有大量的審美經驗,中國傳統的文學經典一直是標尺,但我們從未從話語角度進行鑒賞、品味、研究。王彬的話語研究恰恰提供了一個新的維度,因而值得我們認真思索。
注釋:
[1]參見王彬《從文本到敘事》,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7-208頁。
[2][3]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145頁。
[4][5]王彬:《從文本到敘事》,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26頁。
[6]莫言:《透明的紅蘿卜》,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182頁。
[7][8][9]蔣韻:《紅色娘子軍》,《收獲》,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