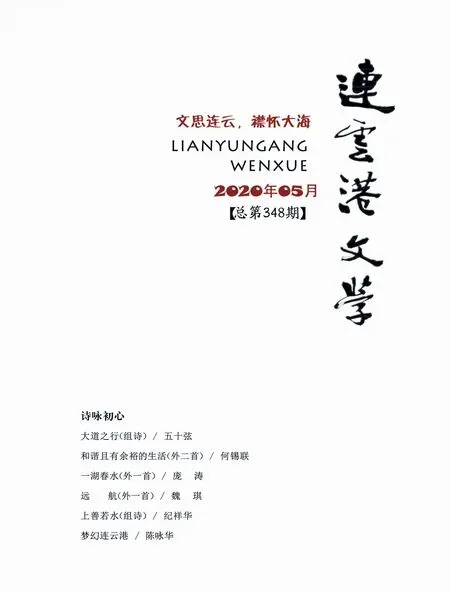麥收季節
回了趟老家,映入我眼簾的是黃色的海洋,成熟的麥子像被檢閱的士兵,整齊劃一地挺立在一望無際的田地。我知道麥收的季節又要到了。說不清為什么,每到這個季節,我的心底總要涌動一種莫名的情愫。往事就像水壩被挑開似的,一個勁地流出來。
我對麥收季節最初的印象是好玩。我很小的時候土地還沒有承包到戶,一切都還是屬于集體勞動。麥子成熟了,生產隊就組織全體社員割麥子,等麥子全部運完之后就會把麥地開放。記得男女老幼都圍坐在大田周邊的土埂上,就等隊長最后宣布“放門”,也就是允許人們到田里撿落下的麥穗,撿到的就歸個人所有了。那時,我大約五六歲,小姑就帶著我揀麥穗。奶奶說了,只要我撿回麥穗,就會獎勵我麥餅吃。這個獎勵還是挺有誘惑力的,那個時代吃到麥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和小姑坐在禁區之外的溝渠上,那些護麥的人大多是我小姑同學,可能我顯得可愛吧,他們特別喜歡逗我玩,把我的草帽搶過去高高舉起,讓我踮起腳搶。但我從不慍惱,搶不到也不著急。混熟了,他們竟給我特權,允許我先進去揀麥穗。六月的太陽是火辣的,這阻擋不了我撿麥穗的熱情,一個小人兒,格外珍惜這個“特權”,小手不顧麥茬扎人,把那些藏在麥草里的麥穗揀出來。汗水順著我的小臉滴落下來,太陽的炙烤讓我感到臉熱得燙人。等到麥地面向大家開放時,我已撿了好大一堆,以致回去時小姑背那些麥穗很吃力。奶奶沒有食言,把這些麥穗曬干捶下粒子,用自家的小磨磨成麥糊,攤成的麥餅吃起來格外香。這種香味深深烙在我的記憶深處,多年之后回想起來依然口中生津。
生產隊的麥子都堆放在打谷場上,脫過粒的麥秸堆成高聳的草堆。晚上,大人們都喜歡拖來席子在場上乘涼。而小孩子們就不安生了。在場上東奔西跑,盡情玩耍。小伙伴們最喜歡捉迷藏,把草堆掏出洞來,鉆了進去,把洞口偽裝好,真的很難找。也許當時我們是受電影《地道戰》的啟發吧。不過藏在洞里的滋味真的不好受。本來天氣就熱,洞里悶得讓人喘不過氣來。有人受不住自己就鉆了出來,但有人為了“最后的勝利”,堅持不出,每每聽到尋找自己的小伙伴從身邊走過的腳步聲就會格外得意。甚至有的人藏久了,在麥洞里睡著了。害得小伙伴們實在找不到嚇壞了,告訴家長。在大人的呼喚聲中醒來的伙伴迷迷糊糊鉆了出來,屁股上挨了大人的巴掌才徹底清醒。
這樣的日子很快過去了。后來土地都分到了各家。農民們的熱情被充分地激發出來。每到麥收時節,是農民們最忙的時候。到了小滿,家家都要忙著買些鐮刀、草叉、耙子、草帽、揚場锨等農具。農村有句老話叫“黃金鋪地,老少彎腰”,麥收季節家家沒有閑人,農民們必須搶收搶種。
那時我已經讀書了,但還是放假回家幫助家里農忙。無論大人還是小孩,腳步都是匆匆的。鐮刀被磨得鋒快。獨輪車被裝上用四根棍綁成的架子,便于運輸更多的麥子。整個田野里,人們星星點點分散在自家的麥田里。為了節省時間,中午是不回家的。早上已經備好了單餅,咸菜,水壺里裝滿了開水。
我也加入收麥的行列,一刀下去,就剜了一個小洞。望望前面,還是遙不可及。再看母親,弓著腰,一聲不吭,鐮刀揮起一道弧線,一片片麥子在嗤嗤聲中整齊地成堆鋪在地上。這些麥子好像成心跟我過不去似的,我很快就落在母親的后面。我幾乎割幾下就要歇會,時間長了,腰酸疼得幾乎直不起來。那火爐一樣的太陽無視我是個學生娃,曬得我汗流浹背。麥芒扎得人膀子上起了很多紅疙瘩,汗漬順著臉上、背上、胳膊上流下來了,浸得人又疼又癢。手又不能抓,否則破了更難受。我甚至用上衣把自己的頭包起來,只留下眼睛。但這無濟于事,反而憋悶得更難受。尤其無風的日子,世界幾乎窒息,那種滋味讓我永生難忘。
麥收季節最害怕下雨。有一年麥子剛剛成熟,雨就淅淅瀝瀝地下了起來,仿佛天上被捅了個窟窿,一直就沒有停下來的意思。麥穗在水中泡得久了,有的都發了芽。我奶不停地念叨,不知誰得罪老天爺了,害得大家都跟著受累。終于有點放晴,人們趕快涌入麥田搶收。由于麥田里有水,不能把麥子平鋪在田地里。我母親在前面抓緊收割,父親跟在后面把麥子扎成捆,然后麥穗向上,便于太陽蒸曬。地里泥濘,車子無法進入,還得一捆一捆往外抱,每走一步都很艱難,有時一腳踩下去,泥漿飛濺,衣褲處處是斑點不說,還會弄個大花臉。這種辛苦沒有親身體會的人真的無法感受。每每看到變天,黑云翻滾而來,人們就急急忙忙把麥子堆成垛,然后蓋上塑料布,等雨走后,再打開晾曬。反反復復,把人折騰得精疲力竭。即使這樣,那年的麥子還是受了罪,磨成面粉后,做的餅難以成形,黏嘴。賴以土地生存的農民,那時真的要靠天吃飯。
并不是麥子收了就萬事大吉,運到家里還得脫粒。最早的脫粒靠人工,就是把麥穗朝上扎成一把一把,然后向板凳上摔或者是用木棍敲擊。在麥子少的情況下才能這樣做,因為這樣的效率是極其低下的。記得當時每家門前都整出一塊場地,先擔水把地澆透,撒上草灰晾曬后再用碌磙碾壓平整好。這就是自家的打谷場了。運來的麥子堆在場上,全家人齊上陣,揮動草叉,把成捆的麥子抖散,那些打上死結的還需要動手撕開,盡量把麥子平整放好。然后用牛拖著碌磙碾壓,這樣就比人工提升了很多效率。我祖父是趕牛的好把式,戴個破草帽,左手牽著牛的韁繩,右手舉著一根柳條鞭子,在麥場中轉起來。祖父并不著急,哼著小調,鞭子只是偶爾在半空中揚一下,牛就不敢懈怠,加快了腳步。祖父打場的麥粒總是脫得很干凈,而且麥草也很整齊,便于保存下來喂牛。
后來有了手扶拖拉機,無論是運麥還是脫麥,效率都發生了質的飛躍。手扶拖拉機開進地里,后面的車廂四周綁上長長的木棍,形成一個四方的架子。白天用來收割,晚上才來運麥子。女人孩子抱麥子,男人們用草叉把麥子推在架子上,就像一座小山。幾畝地的麥子,手扶拖拉機幾趟就運完了。我特別喜歡爬在這些小山的上面,蹲在洼處,手里拉緊繩子,任車顛簸搖晃,像蕩秋千似的。尤其是晴朗的夜晚,那些閃爍在蒼穹的像寶石似的星星讓人心生遐想,讓你忍不住奮力抬手,想觸摸那深邃的天幕,體驗手可摘星辰的感覺。在這樣一種愉悅的情境中,一天的疲累就會煙消云散。
麥子運回家已經不再用牛來碾了。把手扶拖拉機后面扣了兩個碌磙,我二叔右腳踩著扶手,讓扶手與座位形成弧形的角,這樣手扶拖拉機就能在圓形的打谷場上對麥子進行碾壓。這樣脫粒的速度很快,半個小時就能脫一場。不過,拖拉機軋一會兒就得翻場。就是把麥子翻個身,因為鋪得厚,得把底下的麥稈翻起來。不要小看這項工作,也挺累人。全家人一字排開,拿著草叉,地毯式翻麥。從奶奶到我們這些小孩,全都要上陣。翻場不是那么簡單的,把麥草叉起來,還要把里面的糧食抖落,然后再把未打凈的翻在上面。由于白天要搶收,所以晚上得加班脫麥。大家白天已經累得骨頭要散了架,晚上更是疲累。手臂酸痛,草叉讓人感覺有千鈞重。有時翻著翻著,竟然握著草叉睡著了。麥場打完了,要叉去麥草,把糧食抖落下來,最后堆成堆。往往會忙到夜里十一點左右,睡覺時根本顧不上洗漱,就和衣而臥了。
“田家少閑月,五月人倍忙。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婦姑荷簞食,童稚攜壺漿。相隨餉田去,丁壯在南崗。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白居易的《觀刈麥》準確描寫了麥收季節農民們的辛苦勞作。每次麥收,對于我來講都會脫層皮,人被曬得烏黑,連鼻孔里面都是灰。甚至,吐出的痰都是黑的。麥收的日子,是我無法抹去的記憶。
現在的麥收季節,已經沒有過去的繁忙和漫長了。收割機得到普遍使用,鐮刀也不見蹤影了,村莊早已不見了麥秸垛。拿著鐮刀彎腰割麥,想看看牲口拉著碌磙碾麥,已成了奢侈、已成為歷史。現在的孩子聽大人講這些往事的時候,臉上滿是惘然和好奇,那些在金黃的麥穗前各種姿勢擺拍的女孩,哪里知道這些麥穗后面的汗水。好想帶著孩子在兒時的麥場上,享受著夏夜的涼風,聽著老人講離奇的故事,在無盡的幻想中進入夢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