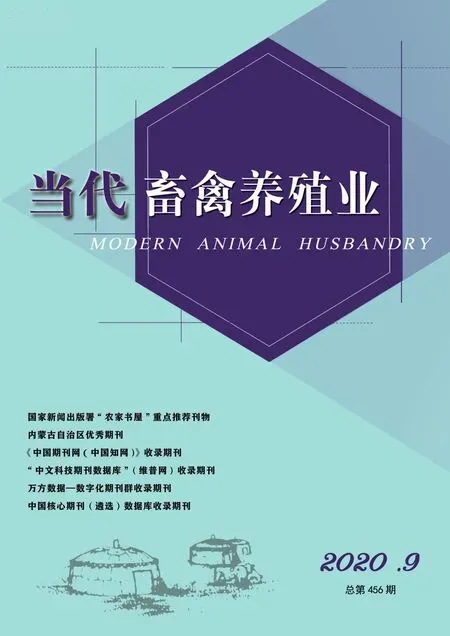草原畜牧業降成本提效益問題研究
其其格
(內蒙古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1 研究背景
長期以來,草原畜牧業的主要經營特點是以天然草場為主要基礎資料,以逐水草而遷徙的手段來抵御自然災害的古老而科學合理的傳統經營模式。這種被部分現代人稱為“方式落后、手段粗放”的生產經營方式,實際上在獨特的人文環境和歷史背景下,尊重大自然的天然稟性,把自己的行為與大自然緊密聯系在一起,實踐了“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和“人―草―畜”的動態平衡效果。然而,從20世紀80年代“草畜雙承包制”全面實施以來,草原畜牧業傳統生產模式由定居(半定居)和舍飼(半舍飼)方式所替代,牧民的生產、生計和生活也隨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1980年,Dyson—Hduosn等人在《人類學年鑒》上指出:“關于游牧的浪漫神話已粉碎,游牧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正在消失,即將成為純粹的歷史。自然環境的演變不足以解釋游牧社會的興衰,周圍世界對游牧社會有決定性的影響。還沒有一種理論能完美地解釋游牧現象,因為游牧并不是一種統一的適應模式,因時因地而變化多端。因此靜態研究正在被動態研究取代,大量宏觀、中觀及微觀理論正在涌現,強調游牧或畜牧社會的變化過程而不是靜止或僵化的模式。他們預言到20世紀90年代,游牧民雖未完全消失,但都實現了不同程度的定居,典型的游牧將不復存在”[1]。他們的預言如今果真變成了現實,放眼我國所有的草原牧區,基本上已經形成定居或半定居生產、生活模式,甚至出現了更多的半農半牧地區。從原古社會到封建王朝,再到現代人類文明,草原民族、草原人民、草原文化、草原經濟和草原生態等所有與“草原”有關的人類活動、經濟結構和自然環境一直在變化和發展。當前,草原牧區經濟社會已進入到了重大調整階段。這里所指的調整,主要體現在草原地區傳統畜牧業生產模式的轉變和隨之而來的牧民生活方式的改變上。事實上,日益惡化的草原生態環境和高消耗、低效益的生產經營方式使草原畜牧業可持續發展已難以為繼,而要實現從“量”的增長向“質”的提升,這必然會關系到草原畜牧業“降成本、提效益”這個核心問題。
近年來,草原牧區正在面臨著生態和發展雙重壓力,草原傳統畜牧業也面臨著必須要實現轉型升級的現實問題。這個轉變同時也意味著草原牧民的傳統生計方式也將要隨之發生一定程度的變化。然而,這些變化很多都是“被動性”的,準確地說,草原牧區的傳統文化、傳統產業和傳統生活等諸多傳統因素也正在面臨著更多的挑戰和困難。其中,一直依賴于天然草原放牧的牧區傳統畜牧業向舍飼和半舍飼方式的轉變,這在很大程度上使草原畜牧業的生產成本大幅上升。在實地調研中了解到,牧區畜牧業生產成本主要包括牧草成本、勞動力成本、燃料成本、基礎建設和牲畜防疫等多個方面。
2 草原畜牧業生產成本
2.1 牧草成本
牧民畜牧業生產成本逐年上升的客觀因素較多,其中包括自然災害、物價和勞動力成本、牲畜舍飼圈養的棚圈圍欄等基礎設施,以及牧草需求量增多等。其中,飼草料支出是牧民大宗生產性支出之一,在所有剛性支出中占據著較高比例。牧草支出的大幅上升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是氣候變化和自然災害的因素。近年來部分草原牧區連續多年干旱(或白災)導致天然草場不能滿足正常放牧,而補飼對牧草需求日益增多,尤其是過冬對飼草料需求量更大。其次,因草原地區生態環保政策(如圍封轉移、禁牧、草畜平衡等)的全面實施致使牧民對牧草的需求不斷上升。隨著舍飼和半舍飼的推行和購買牧草支出的大幅上漲,畜牧業的綜合成本不斷提升。在大部分草原牧區,因沒有自給自足過冬草料(干草)的草場和條件,牧民過冬所需飼草料絕大部分只能從外地購買。遠距離運輸和中間商的加價使牧草成本不斷上漲,尤其遭遇自然災害年份價格會更高。牧草是畜牧業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也是支撐草原畜牧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物資。然而,近幾年因干旱少雨等自然災害和超載過牧等人為因素導致草原“三化”現象嚴重,草畜矛盾突出。造成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歸根到底就是飼草不足。長期以來,畜牧業生產中人們過度強調草地的生產功能,而忽視了它的生態功能,草地生態功能和生產功能配置不合理,導致系統功能耦合機制失調,天然草地大面積超載過牧而導致“人―草―畜”關系失衡,草地大面積退化[2],隨之而來的是牧草的更加緊缺和價格的上漲。因此,牧民最大的需求是牧草,牧草(尤其是過冬草料)的短缺和其價格的居高不下是制約草原畜牧業可持續發展和影響國家生態保護工程能否順利實施的關鍵因素,同時也是草原畜牧業整體生產成本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
以內蒙古草原畜牧業主產區之一的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為例,近年來因持續干旱導致牲畜飼養成本大幅上升。冬春季每只羊每月飼草料支出高達68.4元,喂養期按5個月計算共計342元。2018年,蘇尼特右旗一直到6月底都沒有降雨,舍飼時間從冬季到夏季長達9個月,一只羊飼草料支出達到了615.6元,中等收入戶按300只羊計算,2018年冬春季飼草料總支出高達184680元。再加上其他支出和人工費,牧民基本沒有收入,甚至是虧損。多數牧民因現金不足而靠銀行貸款或民間借貸解決購買飼草料資金。銀行的利率分為幾個不同等級,但大多數為8厘左右。按8厘試算,有300只羊的牧戶以全額貸款購買草料,光一年貸款利息就高達17729元[3]。如果借民間高利貸,利息會更高。2015年,整個呼倫貝爾市牲畜過冬飼草料缺口約19×104t;2016年,受嚴重旱災影響,牲畜過冬飼草料缺口高達67×104t[4]。受災地區,有些賣草料的中間商為了追逐更高利益,把飼草料以遠高于市場價賒銷給從銀行貸不到款的部分牧民,到第二年再加高額利息回收貨款。類似高價格、高利息的雙高行為惡意盤剝困境中的牧民,使他們在債務泥潭中越陷越深。在內蒙古傳統牧區調研時發現,畜牧業飼養成本(尤其是過冬飼草料)大幅上升是多數牧民負債累累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一個內蒙古傳統牧業旗——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左旗洪格爾蘇木W嘎查,課題組隨機入戶調研了6戶牧民。他們當中有富裕戶,也有中等戶和相對貧困戶。位于中蒙邊境線上的W嘎查在整個蘇尼特左旗人均草場面積相對較多(人均210 hm2),草原生態保護得較好,牧民生活水平也較高,屬于純牧業的邊境嘎查。然而,人均草場面積雖然較多,但不具備自行生產過冬干草的條件,現實情況是當地的牧草(尤其是過冬牧草)依舊嚴重短缺,牧民每年的牧草剛性支出占據家庭總收入的較高比例(見表1)。
調研數據顯示,購買飼草料支出是牧戶最大的剛性支出。蘇尼特左旗大部分草場以干旱、半荒漠化沙地為主,牧草長勢差、密度低,不具備自產過冬草料(干草)的基礎和條件,而大量的過冬飼草料只能依靠從外地購買。遠距離調運和中間商的加價導致飼草料價格大幅上漲,牧民生產成本也隨之上升。入戶調查的6戶牧民2018年度牧草支出(包括租用草場)中最多的一戶高達10.7萬元,而最少一戶也2萬元,加之棚圈建設、圍欄修建、雇用羊倌和家畜防疫等剛性支出,牧民養殖成本明顯上升。
2.2 勞動力成本
“互助合作”理念是歷來草原地區牧民自發組織的民間合作方式。如早期的“古列延”、“阿寅勒”等合作組織以及后來的“蘇魯克”制度等,它是草原牧民團結互助和群體精神的最佳體現,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和時代背景。其中,像“古列延”和“阿寅勒”等牧民合作方式的最初形成背景是草原民族為了依靠團體的力量去應對嚴酷的自然災害和戰爭威脅等不可預知的風險。實際上,當時的互助模式除了明確的奴役或雇傭關系以外,普通牧戶之間的協作關系一般是平等的,也是不計勞動成本的互助行為。而“蘇魯克”制度則是游牧民族畜牧業經營過程中形成的一種互助方式和經營模式。它的主要特點是牲畜多的牧民將其所有(或部分)牲畜出租給需要租養牲畜的牧民,而牲畜少或沒有牲畜的牧民則通過“放蘇魯克”的方式獲得牲畜、仔畜以及畜產品等生產生活資料[5]。這種“放蘇魯克”方式,實際上是草原牧民之間互助模式的一種,同時也是有效利用牧區剩余勞動力和幫扶弱勢群體(無畜戶或貧困戶)提升生活水平的最佳體現。

表1 W嘎查樣本牧戶2018年度牧草支出統計
自20世紀80年代“草畜雙承包制”實施以來,以戶為單位的“小牧”經濟的迅速崛起和牧區草場承包到戶等因素,牧區傳統互助合作模式逐漸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直接雇傭勞動力等市場化模式。在牧區,雇用的勞動力主要集中在收割牧草、基礎建設和放養牲畜等基礎勞動者,而雇傭者一般都是牧業大戶、合作社或部分家庭勞動力短缺的普通牧戶。
在草原牧區調研中了解到,在內蒙古傳統牧區雇用羊倌的牧戶非常多。如錫林郭勒盟東烏旗滿都胡寶拉格鎮M嘎查,超過80%的牧戶都在雇傭羊倌。2019年,課題組在M嘎查進行了實地調查,在隨機入戶調研的20戶牧戶當中,有18戶正在雇傭羊倌,而雇傭羊倌的原因分別是家庭勞動力不足、選擇城鄉結合生活;戶主年老體弱及家庭成員進城陪讀子女等(見圖1)。
調查數據顯示,大部分牧戶雇傭羊倌是因為家庭勞動力不足,而勞動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家庭成員進城陪讀子女。在草原牧區,因“撤點并校”政策的實施,大量牧區中小學和幼兒園被撤并集中在城里,這使多數牧民只能選擇進城陪讀子女。事實上,大量牧民進城陪讀子女不僅加重了他們的家庭經濟負擔,更重要的是分散了家庭勞動力。因此,雇傭羊倌是多數牧民的無奈選擇。此外,部分牧民是因年老體弱等原因雇傭勞動力。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子女在城里就業或務工,而自己卻不愿意進城投靠子女,堅持經營傳統畜牧業。在牧區,老齡化現象非常嚴重,大多數年輕一代不愿意回鄉務牧,而大部分老年人也不愿意跟隨子女進城。他們因年老體弱,無法承受繁重的體力勞動,從而只能雇傭羊倌等勞動力。此外,還有少部分牧民是因為在城里經營商業、餐飲業等實體生意,因自己沒有時間和精力而雇傭勞動力。
在費用方面,內蒙古傳統草原牧區雇一名羊倌一年的工資支出約為5~6萬元,而雇傭夫妻兩人工資會更高(在牧區一般會雇用夫妻兩人)。從成本上計算,飼養牲畜數量較多的牧業大戶雇用羊倌相對比較劃算,因為分攤到羊只數上成本會有所下降,但飼養300只羊以內的中低收入家庭雇傭羊倌的成本明顯偏高。通過調研了解到,近年來雇傭勞動力成本占牧戶生產支出較高的比例,有些牧戶甚至把一年的牧業純收入全部給羊倌發了工資。現實情況是,因家庭勞動力被分散而有些牲畜少的牧戶也不得不雇傭羊倌,從而使家庭經濟負擔進一步加重,這也是他們的無奈之舉。
2.3 其他成本
除了牧草支出和勞動力成本以外,牧民生產成本還包括基礎建設、牲畜防疫、牧業機械和燃料油料等諸多剛性支出。其中,飲水設施、棚圈和圍欄等基礎建設也是牧民較大的生產支出之一。近幾年,各級政府部門對牧區基礎建設上的扶持力度大幅增加,在牧區棚圈修建及人畜飲水工程等牧民大型基礎項目上,政府將負擔大部分的費用。但是,上述工程花費較大,雖然政府負擔了大多數費用,但牧民自己也要承擔一部分。如蘇尼特左旗大部分牧區,水資源嚴重短缺,人畜飲水問題是當地政府亟需解決的關鍵問題。在當地,打一口深水井大約需要10萬元的費用,其中牧戶自己需要承擔3萬元。當然,上述各種政府扶持項目并不是人人都能申請到的。因地方政府的配套資金所限,每年批下來的指標并不多,根據牧民的申請和結合實際情況,從嘎查開始逐級上報審核,最終只能批準少數幾個牧戶。
此外,燃料支出是牧民家庭又一項大宗生產支出之一。隨著機械化的普及和牧民掌握各種機具能力的提升,牧民家庭現代化機械設備擁有量也大幅增加。機械化設備和新技術在草原地區的廣泛應用和普及是傳統牧區向現代化邁進的特征之一。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的現代化程度是生產力發展的關鍵因素,生產技術的變革是推動生產方式轉變的首要、也是最基本的要素之一。但是,這一切設備的使用都離不開一個關鍵物質—燃油。調查數據顯示,草原地區的燃油消耗量正在逐年成倍增長。同時,國家成品油價格的居高不下使機械化設備的使用成本不斷上升。在蘇尼特左旗X嘎查調查樣本戶中,2018年度人均燃油消費高達1700元左右,其中個別牧戶甚至超過了3萬元。
3 畜牧業降成本、提效益舉措
2017年中央1號文件明確提出,大力發展草原畜牧業,突出優質、安全、綠色導向,強化品牌保護,提質增效。畜牧業作為大農業的一部分,在農牧業結構調整、糧食轉化增值、安全食品生產、農牧民增收、吸收農牧區剩余勞動力等方面起到了主導作用[6]。眾所周知,不同的地理、氣候及歷史條件決定了人類不同的社會分工,但無論是生活方式、生產模式還是傳統文化,畜牧業有著自己獨特的歷史背景和人文環境,與農業或其他產業有著截然不同的本質區別。事實上,畜牧業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出其脆弱的一面,如對自然條件、氣候變化及生態環境的高度依賴性和對成本上升、價格波動等外在市場因素的極度敏感等。除此之外,國家對草原生態保護政策(如禁牧、草畜平衡)的全面實施,對草原傳統畜牧業的可持續發展提出了更嚴格、更具體的要求。在此背景下,降低畜牧業生產成本和提升效益問題成為了傳統畜牧業向綠色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
3.1 降低牧草成本是畜牧業發展的關鍵環節
牧區經濟發展的首要難題在于生態優先、綠色發展背景下因地制宜、科學合理地轉變牧民的傳統生產結構與生計方式,從而改善牧民生活水平。這無疑要觸及到牧民傳統生活習俗和世代相傳的傳統游牧文化。作為牧民生計的基礎,牧區生態保護與畜牧業發展不可偏廢其一。將生態保護、經濟發展與牧民生計相融合將更有利于牧戶生計的多元化選擇。牧區經濟發展離不開牧戶這一微觀群體,牧民生計狀況是牧區經濟發展的最終體現。生態工程建設承載了牧民生活與牧區經濟發展的雙重重任,在微觀與宏觀層面均有重要意義。畜牧業發展過程中必須考慮的是如何取得生態保護與牧區經濟社會發展之間權益平衡問題,解決好這個問題,才能達到草原生態恢復和牧區同步發展的良性循環。天然草場放牧的減少和舍飼圈養時間的延長,牧民對牧草的需求量大幅上升,在此背景下,降低牧草成本成為提升畜牧業效益的主要舉措之一。
3.1.1 農牧業互補方式。農耕和游牧自古以來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對立、相互排斥的人類分工模式和生存方式。然而,隨著人類生存所需的大生態系統遭到人為破壞和反復無常的自然災害等外部因素及物質循環、能量循環的經濟發展規律,使農村和牧區相互間產生了前所未有的互補性和依賴性,尤其是農牧交錯地帶和半農半牧區這種現象更為明顯。實際上,不同的生產方式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和產業上的優勢互補是現代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農村地區豐富的飼草料可有效彌補牧區的短缺,而牧區的肉、奶制品和牛羊糞肥料是農區所需要的。農村和牧區加強合作、資源互補、協同發展是農牧業互補模式的最佳體現。除此之外,近年來我區部分傳統牧區牧民自發組織的冬季“轉場越冬”實例效果顯著。如2016年,呼倫貝爾市牧區遭到百年一遇的旱災,市政府通過上年引導牧民轉場的經驗,出臺了許多優惠扶持政策,鼓勵和引導牧民牲畜異地轉場越冬。災情期間牧區共有29.4萬頭牲畜到農區越冬,節省飼草15.6×104t,按2016年飼草價格計算,節約資金約1.8億元左右[7]。2017~2018年,課題組在興安盟科右前旗滿族屯鄉滿族屯嘎查進行了“轉場越冬”為專題的跟蹤調研,發現該嘎查2017年冬季到農區 (大部分牧民選擇到黑龍江省或吉林省農業主產區跨省區轉場)“轉場越冬”的牧戶數達到總牧業戶的80%左右。從過冬成本和效果上分析,當地牧民“轉場越冬”與原地過冬相比,1只羊至少可節省90~170元飼草料成本,如有300只羊的中等牧戶可節省至少3~5萬元飼草料支出,這對牧民降低過冬牧草成本、提高牧業收入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3.1.2 政府介入方式。牧草安全關系到牧區畜牧業可持續發展和廣大牧民的基本生計,甚至關系到國家對牧區生態保護政策的實施效果。畜牧業是我區傳統支柱產業,尤其是近年來擺脫對資源經濟的過度依存、調整牧區經濟產業結構大背景下更為重要。從目前情況來看,內蒙古草原牧區牧草的供應和流通完全實現市場化運營,這雖然符合市場經濟規律,但同時也伴隨著諸多其他問題的出現,如牧草價格波動大、牧民購買牧草渠道單一、牧草產量不穩定等。其中,牧草價格的上漲將直接影響牧草市場的消費者主體—牧民畜牧業生產成本的大幅上升。因此,為了保障牧區牧草的安全、穩定、低價供應,各級政府應當對牧草的市場流通、產品調度、價格體系、交通運輸、市場調節、產業扶持、牧草種植、技術推廣、制度規則和供需規劃等關鍵環節進行科學化管理。由政府部門主導干預解決牧草問題是提升牧區畜牧業戰略安全和實現生態環保任務的重要保證。這并非簡單意義上的倒退到“計劃經濟時代”,而恰恰相反,市場疏導、資源整合和供需調節等關鍵環節只有政府的行政及法制手段才能起到決定性作用。這里所說的政府干預并非全方位干涉市場經濟體制,而是以疏導、鼓勵、調節和補貼等形式調節市場供需平衡和保障牧草資源的低價、安全供應。
3.1.3 其他方式。解決草原牧區牧草短缺問題,除了上述農牧互補、政府介入等方式以外,還有遠距離調運、人工種草、種養結合和國外進口等多種方式可以采取。但是,不同類型的草原牧區的地理、氣候、土壤植被和水利資源等先天性自然條件各不相同。因此,無論哪一種方式也絕不能盲目實施或“一刀切”,而必須要注重“因地制宜”的重要性。比如,曾備受質疑的內蒙古“開墾飼料地”政策,在水資源較豐富的部分農牧交錯地帶和半農半牧地區取得了較好的實際效果,但對于干旱、半干旱草原地區反而起到了極大的負面作用。土壤植被極度脆弱的大面積荒漠化草原被開墾種植,因土壤肥力不足和水資源嚴重短缺而最終導致大部分飼料地被荒廢。然而,這些被荒廢的飼料地,一部分成為了“三化”現象較為嚴重的荒漠化沙地。事實上,無論哪一種方式或方法,終極目的是為了解決牧區最短缺的牧草問題。保持生態平衡的前提下,解決牧草短缺問題是牧區畜牧業可持續發展的先決條件。因此,牧草問題的妥善解決是草原畜牧業降成本、提效益的關鍵舉措之一。
3.2 草原畜牧業增效益舉措
草原畜牧業的可持續發展,除了降低生產成本以外,提升產業效益也是使牧民增收的重要手段。比如引進優良品種、完善生產銷售產業鏈、集約化規模化經營、發展品牌化效益和提升畜產品附加值等。但是,從草原牧區目前的經營現狀來看,牧戶聯營的大型合作社、個體專業養殖大戶等規模化、集約化、產業化經營的民間實體相當少,基本上屬于分散經營、單打獨斗的零散狀態。多數牧區畜產品銷售渠道也過于單一,嚴重依賴當地冷庫經營者和外來二道販。因規模小而經營分散,對市場份額和價格影響力不大,市場主導地位和定價權不在自己手里,對銷售價格只能被動接受。相關畜產品的深加工和高附加值程度也相對較低,品牌意識不強。實際上,如著名地方品牌“蘇尼特羊”的市場認可度和需求量很大,但當地牧民基本上沒有受益于品牌效益,原因是商標注冊者、開拓市場渠道和高附加值深加工等產業化經營的企業主體大多并不是當地民間組織和牧民群體,而是少數外來企業和商家。他們從牧民手里收購的活羊價格壓的很低,與其他地方的收購價并沒有區別。因此,對牧民來說,他們只是扮演著整個產業鏈當中最低端初級生產者的角色,而不是最大受益者。這也是草原地區廣大牧民雖然增產但不能增收的主要原因之一。
3.2.1 引進優良品種是草原畜牧業提升效益的重要舉措。在牧區,因品種不同而牲畜的出售價格差別很大。如同樣的一頭牛,飼養成本差別并不大,但本地牛和改良牛的出售價卻完全不在一個檔次。在牧區調研過程中發現,多數牧民對畜種品種的改良意識逐漸增強,他們認為,改良優質品種可有效降低生產成本的同時大幅提高牧業收入,是真正實現從“量”向“質”的實質性轉變。當然,還有一部分牧民對此持有謹慎的態度,原因是前幾年在內蒙古部分牧區盲目從國外直接引進“西門塔爾”奶牛而遭受較大經濟損失有關。當時,在引進條件和設施不具備,沒有進行前期科學論證的情況下,呼倫貝爾市和錫林郭勒盟部分牧區大量引進了國外品種—“西門塔爾”奶牛,結果因氣候太寒冷和飼養條件及喂養飼料不符合標準等多種原因導致引進的奶牛大量死亡,購買的牧民遭受了較大的經濟損失。因此,引進或改良外來品種時一定要進行前期調研和科學論證,必須重視“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則。課題組在內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B蘇木調研時發現,當地引進的法國品種“西門塔爾”肉牛就卻很好地適應了本地的自然氣候和飼養條件,受到當地牧民高度認可,并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如從2019年底市場價來看,同樣的兩歲牛,本地牛能賣到9000元左右,而法國“西門塔爾”品種能賣到15000元。在同樣的飼養條件下,不同品種的出售價格差距如此之大,這對草原畜牧業提質增效具有積極的意義。
3.2.2 向規模化、產業化、品牌化發展是必然趨勢。建設和完善覆蓋廣大牧民群體的“抱團取暖、打造品牌、開拓市場”的畜牧業產業鏈對草原畜牧業實質性提升產業效益和牧民增收至關重要。轉變當前牧民單打獨斗的零散經營模式,逐步向集約化、規模化和產業化方向發展,以地方品牌和綠色產品主打中高端市場,堅定不移地向有機、綠色、原生態的“高品質、高附加值、高盈利”中高端畜產品跨越,努力占據市場主導地位和提高產業、產品的影響力,提升附加值和知名度,改變草原畜產品“優質不優價”的現狀和廣大牧民目前的最低端廉價原材料供應者的角色。品牌化效益是草原畜牧業未來的發展方向,而且發展潛力巨大。如內蒙古“科爾沁紅牛”“阿拉善駝肉和駝奶”寧夏“鹽池灘羊肉”青海“茶卡羊肉”等我國不同草原牧區的知名地標品牌對當地畜牧業和地方經濟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促進作用。推進草原畜牧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將地標品牌畜產品轉化為市場競爭優勢,破解畜產品低質競爭、綜合效益低等發展困境,推動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相適應,實現草原畜牧業發展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的有機統一[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