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沈從文小說連環畫改編的詩性建構
趙樹勤 路詩瀅
沈從文小說被譽為“鄉土抒情詩化小說的集大成之作”[1]楊義:《二十世紀中國小說與文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第197頁。,其詩性的散文化敘事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獨樹一幟。隨著圖像時代的來臨,許多現當代文學名家的經典之作都陸續被改編成豐富多彩的連環畫,深受讀者的喜愛與歡迎,并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和探究。遺憾的是,有關沈從文詩化小說連環畫改編的探討卻幾近闕如。實際上,迄今為止已有十余位畫家參與了沈從文小說的連環畫改編,他們將其10篇小說改編成了13個不同版本的連環畫,其中不少版本曾榮登數屆全國大型畫展,并屢次斬獲國家級榮譽獎項,這一圖像改編現象,無疑是一個饒有興味而又極具學術價值的研究課題。
一、矛盾:沈氏原則與改編傾向的博弈與出路
沈從文小說融敘事、抒情、狀景于一爐,因其行文間展現出田園牧歌式的鄉土風情畫卷而成為藝術改編的“香餑餑”,其中涉及影視、戲劇、連環畫等諸多領域,改編的方法莫衷一是,改編的結果也不盡如人意,究其原因,相當程度上是因為沈從文的作品屬于典型的詩化小說,其語言文字是散文化、跳躍式的,而情感表達又是意象化、隱喻式的,因此,故事情節具有碎片化和片段式的特質,與傳統圖像敘事所要求的情節連貫發展不盡符合。在改編過程中,如果完全尊重原作,會因過于詩化而難以引起讀者的共鳴;若是舍棄小說中寶貴的詩意氛圍,又面臨著改編失敗的危險。因此,要將如此充滿“詩性氣質”的沈從文小說進行成功的圖像改編絕非易事。
一直以來,大多數沈氏小說的圖像改編嘗試都存在著一個缺憾——二次創作對原著詩意氛圍的淡化和消解。這個缺憾首先暴露在影視改編上,同時也引起了作家本人的關注與介入。1953年,導演嚴俊將《邊城》改編為電影《翠翠》,沈從文閱片后大失所望,他認為影片在畫面和視聽語言上喪失了小說的詩韻,并對此評價道:“(改編者)主要是看不懂作品,把人物景色全安排錯了……應當作一個沅水流域畫卷來處理,才會成功”[1]沈從文:《沈從文全集》(26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136頁。。有了前車之鑒,1983年凌子風導演在二度改編《邊城》時,就特別邀請了沈從文親自參與劇本審閱,并請其寫下大量修改意見,以確保影片能夠盡量忠于原作。然而,盡管導演做了很多努力,仍有學者指出:“小說輕故事情節,重主觀、重情緒、重印象的詩化風格,被電影轉換成了重起承轉合、重故事流暢的傳統好萊塢風格”[2]李美容:《從詩化小說到詩電影——論電影〈邊城〉之改編》,《湖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第100頁。,可見改編后的作品依然具有“詩性氣質缺失”這一通病。針對這一點,沈從文在與友人往來的信件中反復強調,希望將小說“當成個抒情詩畫卷般處理”[3]沈從文:《沈從文全集》(26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288頁。,不僅僅指《邊城》,還包括許多其他作品,如《貴生》《蕭蕭》《丈夫》等[4]參見沈從文:《沈從文全集》(26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403頁。。后來,小說《丈夫》在1986年被導演黃蜀芹改編成電影《村妓》,《蕭蕭》在1988年被導演謝飛改編成電影《湘女蕭蕭》,但遺憾的是,兩位導演均摒棄了沈從文在小說中極力營造出的詩情畫意,使改編走向商業化、政治化的道路,幾近丟失了原著的神韻。
回溯沈從文對作品影視改編的介入,不難發現,他對自己小說被圖像改編的心態十分復雜。一方面,他深懷隱憂,無法接受背離寫作本意的二次創作,認為不被改編也許是幸事[5]參見沈從文:《沈從文全集》(26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80頁。;另一方面,他又對改編的傾向進行了細致的思考,他借用好友汪曾祺的話語表明:“不必側重在故事的現實性,應分當作抒情詩的安排”[6]沈從文:《沈從文全集》(26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149頁。,堅持要絕對尊重原作“抒情詩畫卷般處理”,這是他對于改編的底線所在。
無獨有偶,在沈從文小說的連環畫改編中,也存在著與影視改編相似的問題,且集中表現為:傳統連環畫“重故事性”與沈氏原則堅持“抒情詩化”相矛盾。一般來說,當小說被改編成連環畫時,其文學腳本的編撰往往不同于小說原著,它有著一套合乎自身藝術規范的編寫原則,強調“故事性強”“要有連續性”“盡量把情節展開”“心理描寫要受到一定的限制”[7]白宇:《談連環畫腳本》,《美術》1958年第7期,第31頁。等。因此,沈從文的詩化小說在被編排成連環畫的文學腳本時,將面臨著“去詩化”的選擇。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沈從文小說在被改編成連環畫后,其敘事中的詩性氣質必定會走向消解,因為連環畫的圖像作為故事畫,本身即是敘事的圖像,能夠表現小說敘事的內容與風格,正如萊辛在《拉奧孔》中言:“詩(文字)和畫在摹仿真實時所使用的媒介符號不同,前者是時間性的藝術,后者是空間性的藝術”,但兩者可以相互轉化[1][德]萊辛:《拉奧孔》,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90-92頁。,錢鍾書則把這種轉化稱作“出位之思”,他指出“藝術家總想超過這種限制,不受材料的束縛,強使材料去表現它性質所不容許表現的境界……詩跟畫各有跳出本位的企圖”[2][日]淺見洋二:《距離與想象 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13頁。,這是在說:作為空間性敘事媒介的圖像,可以“跳出本位”去表示時間性敘事媒介的語言。因此,當沈從文小說被改編成連環畫時,圖像的內容可不必局限于文字腳本,還可拓展到存在于原作中的故事,這表現為圖像對小說文本的摹仿,從敘事學的角度上看,小說是對現實或想象中生活的一種敘事,那么其圖像便是對文本的再敘事,即敘事中的敘事。
此外,連環畫家尤勁東認為,可以通過連環畫的圖像敘事來構筑一種新的“連環”。他指出:“繪畫是‘虛幻的空間’……而連環畫正是這種‘虛幻空間流’,它的特征是‘流’,即一種連續性。這種連續性不意味著只是合乎某一文學情節(故事)或某一事件的產生、發展、終結的過程,而更重要的是藝術家的思維、情感的流衍過程”[3]尤勁東:《連環畫要擺脫文學的束縛》,《美術》1985年第9期,第51頁。,李晨作為熱衷于沈從文小說連環畫改編的畫家之一,他與尤勁東的觀點不謀而合:“何為‘連環’?一定是單純的故事情節的‘連環’嗎?畫家尤勁東曾提出‘連環’為‘表現’過程,也是思維、情緒、造型的變化過程……”[4]李晨:《連環畫將迎來柳暗花明》,《中國美術館》2010年第4期,第72頁。在把沈從文小說改編成連環畫時,李晨就試圖以一種新的形式來構筑詩化小說的“連環”,他將這種“連續性”灌注于圖像敘事之中,通過圖畫里意象、空間和思維的連綴,來表現時間的線性流動與人物的情緒變化,這恰恰為解決連環畫改編“重故事性”與沈氏原則要求“抒情詩畫卷般處理”的矛盾提供了一種可行的出路。
綜合來看,在13個沈從文小說的連環畫改編版本中,有5個版本較為巧妙地做到了“詩性”與“連環性”的融合,在一定程度上還原了其小說“原汁原味”的詩意氛圍,呈現出抒情詩畫的良性互動,它們分別是畫家李晨版《邊城》《蕭蕭》和《雨后》,畫家廖正華版《邊城》以及畫家董英杰版《丈夫》,因此以下論述主要就這五個有典范性的連環畫改編版本進行探討。

圖1 李晨連環畫版《蕭蕭》 圖幅21
二、敘事:“空間之并置”展現情節故事線
約瑟夫·弗蘭克在《現代小說中的空間形式》中寫道:“現代小說家把他們的對象當做一個整體來表現,其對象的統一性不是存在于時間關系中,而是存在于空間關系里”[1][美]約瑟夫·弗蘭克:《現代小說中的空間形式》,秦林芳編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第Ⅱ頁。,沈從文的小說頗具“空間敘事”的特征,在敘事上呈現出弱化時間,強化空間的特點。譬如:《邊城》不是傳統的時間性敘事結構,而是借由不同空間的轉換來推動情節的演變,通過爺爺和翠翠常出現的小屋、渡船、河街、吊腳樓等不同空間的切換來實現情節的發展。
連環畫的圖像敘事也是典型的“空間敘事”,畫家依照文本繪制出多幅連續的圖畫,再依據情節線索重新排列形成一個個敘事片段,由于繪畫是隸屬于空間的藝術,組合圖畫也就是將多個空間進行時間排序,通過多張圖像里物體的空間轉換就能實現故事情節的變化發展。通常,小說在改編成連環畫時,繪者都會采用一幅圖像對應一個空間的形式,讓多幅圖像的多個空間排列組合,形成整個敘事架構中的某一個情節事件,然而這并非是處理圖像空間表現的唯一指向,富有創造力的畫家會根據沈從文小說獨有的藝術特點進行自覺探索,通過重組空間的排列組合方式——或為分解、或為并置,來突顯原著文本的敘事特質,豐富連環畫的敘事手段。
在李晨版《蕭蕭》的連環畫改編中,畫家摒棄了傳統連環畫里單幅圖像對應單個空間的繪圖方式,創造性地采用了“三聯一體”的構圖格式,以“一面多幅”的并置空間進行敘事,將想要同時表現的情節限制在同一畫幅里,通過空間的交替、切換、對比,強化出更為生動豐滿的故事情節。小說敘述中蕭蕭在懷孕后欲離家出走卻被識破,童養媳與他人珠胎暗結是件不得了的大事,婆家便請了眾鄉親說理評判。李晨在圖幅21里(見圖1)巧妙地繪制了三個分割的不同空間,又將它們并置到一起:最左側是特寫——婆家人豎目叉腰,怒氣沖沖;最右側是近景——蕭家人手足無措,背上的嬰兒嘟嘴皺臉,仿佛在為蕭蕭的處境難過;中間是拉遠的中景——鄉親們聞訊趕來,聚集在外指指點點。這一組畫面的空間組合是一個由兩側向中間拉遠的過程,事件的受害方婆家與蕭家是近景,而與此事利益無太大關系的眾鄉親是中景,這種空間并列切換的方式,便形如約瑟夫·弗蘭克為解釋“空間并置”的概念時所說:“并非只簡單一個詞的組合或一則軼聞的片段,而是作為一個整體的情節的各層次的組合”[1][美]約瑟夫·弗蘭克:《現代小說中的空間形式》,秦林芳編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第3頁。。畫家通過并列放置故事情節里不同人物的神情和反應,使這些元素相互統一,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敘事片段,這種新穎的組合形式既能讓讀者體會到各方當事人迥異的心情,又能使空間敘事變得更為緊湊、連貫。
同樣的處理方法不止這一處,李晨在圖幅16里也圍繞小說情節,主動分割了單幅圖像中的空間,把孕后的蕭蕭找二狗對質時兩人截然不同的神態動作并置到一起,兩側為中景,分別是:二狗倉皇無措、蕭蕭掩面痛哭,中間則是近景特寫:蕭蕭殷切地望向二狗,二狗卻低頭回避。讀者可以通過人物神色的差異來揣摩他們的思維性格與行為邏輯,并在腦海里推測出情節的最終走向,這也就形成了讀者與畫本之間良性的思維互動。
不得不說,畫家將多個空間并置于同一畫幅,通過空間的切換來展現情節線性流動的做法,是一種極其精巧的處理方式,不僅打破了傳統連環畫一幅圖像對應一個空間的敘事傳統,豐富了單幅圖像的故事情節,節約了連環畫圖幅的數量,還圓滿契合了沈從文詩化小說“強空間性”“弱時間性”的敘事特點,使得線性敘事在空間表現中層層遞進、重點突出,進一步顯示出連環畫改編者在藝術創作中的想象力與創造力。
三、抒情:“詩之意象”連綴情緒思維流
詩人鄭敏說過:意象之于詩歌,猶如情節之于戲劇和小說[2]參見鄭敏:《中國詩歌的古典與現代》,《文學評論》1995年第6期,第81頁。,可見“意象”是詩歌的基礎組成單位,也是詩性氣質最為顯著的體現。在現代文學作品中,沈從文小說因其意象化的表達而頗具“詩意”,有學者曾評論他的小說真正實現了“觀念和象征意蘊、情節和意象的水乳交融”[3]龍慧萍:《沈從文詩化小說的敘事學研讀》,《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5期,第47頁。。的確,沈從文的詩化小說往往能兼顧意象與情節,他擅長創造小說故事分支的“副文本”,以雅淡的意象取代曲折離奇的情節,成為主人公情感世界外化的重要標志,真正做到了“以優美而哀傷的情致動人”[4]龔剛:《論〈邊城〉的“詩語”風格與結構模式——基于形式主義與結構主義視角》,《中國文學研究》2020年第1期,第121頁。。譬如,在《邊城》中,作者多次用“虎耳草”的意象來寄托翠翠對儺送沒有宣之于口的情思,汪曾祺在追憶沈從文時曾聊到他與“虎耳草”的羈絆:“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種在一個橢圓形的小小鈞窯盆里。很多人不認識這種草。這就是《邊城》里翠翠在夢里采摘的那種草,沈從文喜歡的草”[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 四 散文卷》,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61頁。,由此可見,沈從文有將生活中物象轉化為小說中意象的習慣,他將對湘西言之不盡的復雜情感寄托于《邊城》里“白塔”“渡船”“虎耳草”等諸多意象之中,這些意象在不同時段、不同場景中的反復呈現恰恰透露出作家在藝術創作中的詩性思維。

圖2 廖正華連環畫版《邊城》 圖幅102
廖正華對《邊城》的連環畫改編就很好抓住了“虎耳草”的意象,他在圖幅74、圖幅101、圖幅102中分別繪制了翠翠在夢中攀崖采虎耳草、翠翠借口到后山偷摘虎耳草、翠翠編織虎耳草頭飾戴在頭上這三幅圖像(見圖2),畫面中“虎耳草”是中心物象,它的反復出現使得翠翠本應平常的動作有了非同尋常的意義,構成了小說的分支情節,畫家正是通過描摹翠翠三次對待“虎耳草”時做出的不同情態,來遞進暗示她對儺送悸動的愛戀。
除此之外,董英杰版連環畫《丈夫》也試圖用意象來側面表現主人公的情緒流變。小說《丈夫》講述的是一個鄉下丈夫到縣城看望以做妓女謀生的妻子,在當時湘西鄉下的貧困家庭中,婚后女人去到船上做“皮肉生意”,得來的錢能夠給夫家補貼家用,是所謂“名分不失,利益存在”的行為,被視為正常的營生手段。然而,對于男主人公來說,將妻子的身體給予船上人來人往的他者去享用,就相當于讓度了自己作為丈夫的部分權利。由于這是鄉里多年來約定俗成的潛規則,男主人公此前并沒有深入思考過“丈夫”與“妻子”的身份觀念與權利意識,沈從文在小說中多次寫道:蝸居后艙的丈夫不得不直面妻子在前艙一次又一次用身體接客的殘酷現實,他試圖通過這種對“權利喪失”的直面暴露來引出丈夫與妻子心態上的變化,進而引發他們對自我身份意識的覺醒。
在董英杰版連環畫《丈夫》中,就通過“胡琴”這一意象重點表現了夫妻兩人情緒變化的過程。丈夫在得知妻子今晚要接客時,曾憤怒地表示要立刻離開,但妻子隨后將集市上買來的“胡琴”送給丈夫,讓他覺得妻子心里還有自己,便沒有立即回去。在圖幅30中,妻子為丈夫調好了琴弦,丈夫拉琴后愉快地笑了,然而這種和諧沒能持續太久。醉酒的兵士上船大吵大鬧,叫嚷著要讓拉琴人出來唱曲;在畫幅34中,丈夫挾著胡琴躲到后艙,而妻子卻被迫出去賠笑臉,“胡琴”作為妻子贈予的禮物,雖然象征著關心與愛,但是這種“身體自主權利喪失”的愛對于丈夫來說不過是一種幻象,當他人可以光明正大地享用妻子的身體時,自己卻只能帶著“胡琴”躲躲藏藏,這種充滿諷刺意味的反差與情緒上的失落,從圖幅34丈夫倉皇狼狽的背影中可見一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丈夫剛想同哄完醉鬼的妻子說一些家常私話,卻又被大娘提醒接下來妻子要去接待干爹水保,丈夫的情緒徹底爆發了。在圖幅50中,他把妻子做“生意”得來的錢票撒到地上,像孩童般嚎啕大哭。緊接著圖幅51里,妻子也感知到這種身份錯位的荒誕,她抬頭望向船梁上的“胡琴”沉默不語(見圖3)。在小說原著里,作者可以通過大量的對話和動作描寫來書寫丈夫與妻子情緒上的變化,然而改編成連環畫后,文學腳本的重編限制了這些描寫的篇幅,詩性語言的表達也在不同層面上被削弱,此時畫家很聰明地在圖像繪制上融入了詩性思維,以物象為載體把夫妻二人的心理情緒外化,讓樸素的物象變成抒情的心象,在需要傳遞情緒的情節中,用圖像凸顯出灌注主人公情感的意象。“胡琴”意象的反復出現連綴了妻子與丈夫的心理變化,從兩人彈奏“胡琴”獲得愉悅體驗到妻子獨自望著“胡琴”沉默失語,巧妙暗示了兩人對自我身份意識的覺醒,畫家通過圖畫中典型意象的連綴,成功展現出丈夫對船妓舊俗從接受到質疑,又從反思到反抗的心理變化過程,可以稱得上是一次較為圓滿的改編嘗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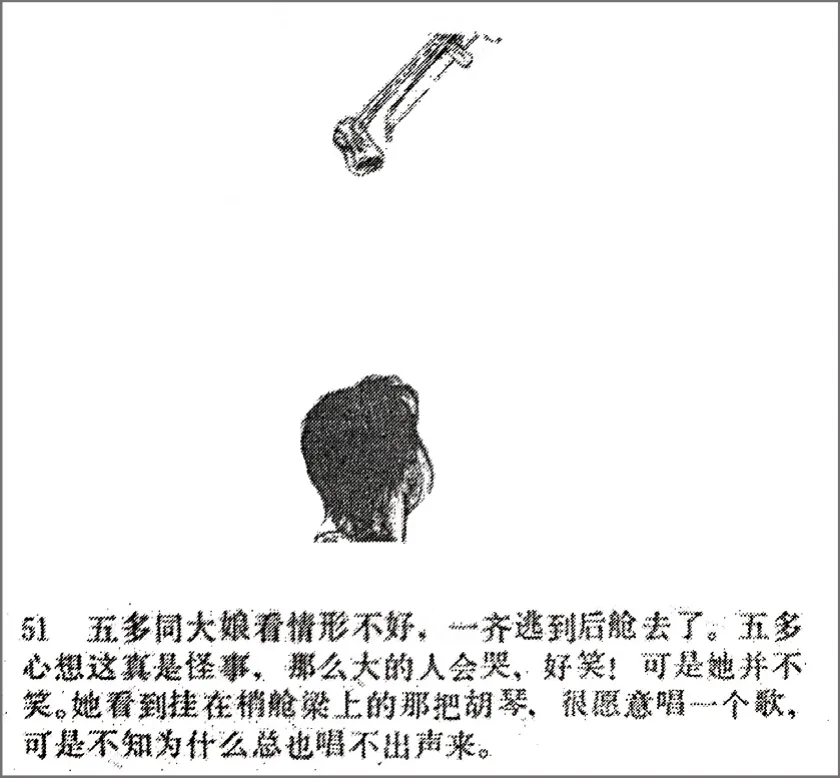
圖3 董英杰版連環畫《丈夫》 圖幅51
由上可得,這些連環畫改編后的作品重點描摹了小說中反復出現的經典意象,將人物的情緒變化寄托于物象中,使簡單的物象演化為復雜的心象,不但沒有丟失沈從文詩化小說里“重意象化”詩性表達的神韻,還在某種層面上實現了故事情節、人物情感的“連環性”發展,讓作品兼具連環畫連續流暢的閱讀體驗以及沈氏風格獨有的審美意蘊。
四、狀景:“語之留白”生成閱讀聯想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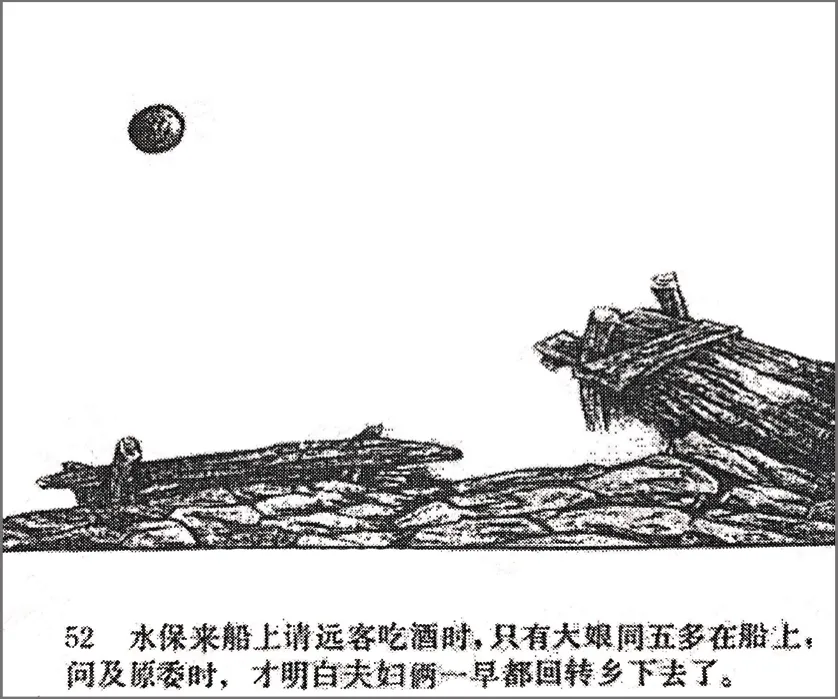
圖4 董英杰版連環畫《丈夫》 圖幅52
眾所周知,小說三要素是人物、情節和環境。傳統小說往往以情節的曲折離奇取勝,而沈從文卻大反其道,其筆下人物、情節所占故事的比重并不大,他似乎有意識地在這些其他作家用心耕耘的板塊留下大量的藝術空白,去填充他想要書寫的面貌——湘西風情,這與中國傳統繪畫中“留白”的技法有異曲同工之妙。笪重光在《畫筌》中言:“虛實相生,無畫處皆成妙境”[1][清]笪重光:《畫筌》,《藝林名著從刊》,北京:北京市中國書店,1983年,第9頁。,就是在說國畫的留白處往往是全局的關鍵,不僅襯托了畫面的主體,擴大其自由活動的空間,同時也成為主體形象的延伸,拓展了畫面的意境。
沈從文在創作短篇小說時,就傾向于將繪畫“留白”的技巧融入寫作中,“尤其重要處,便是那些空白處不著筆墨處,因比例上具有無言之美,產生無言之教”[2]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16卷 文論》,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505頁。。譬如,小說《邊城》最后寫道,“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沒有明確點明翠翠與儺送的結局;《雨后》的結尾“雨已不落了。她還是躺著,看天上的云,不去采蕨……”同樣沒有揭示阿姐與四狗在魚水之歡后的故事,他似乎有意將后續的發展在小說中省略,使之留下空白,以此來激發讀者的聯想與再創造。沈從文對情節的語言表達是模糊化、空白化的,看似平淡卻飽含深刻的思想意蘊,這種虛實結合、有無相生的留白藝術,既能彰顯出小說的詩情畫意,又能使讀者產生意猶未盡的閱讀體驗。
畫家們在對沈從文的小說進行連環畫改編時,自然也注意到了小說“重環境描寫”和“重敘事留白”的藝術特點。他們將兩者結合,在為文學腳本繪制對應的圖像時,便有意識地將人物剔除在外,把筆墨揮灑在其周邊場景環境的白描上,使得整個圖景猶如湘西山水畫卷,只現物景不見人像,言已盡而意無窮,形成藝術上的留白。李晨版連環畫《雨后》中畫幅15所對應的情節是:四狗的手在阿姐身上“撒野”,畫家沒有直接繪制出人像與動作,反而只描摹了這件事發生的場景:小船停靠在石頭鋪就的河岸邊,不遠處有一個草搭的棚子,他們便是在這草棚下唱歌嬉戲、共赴巫山。董英杰版連環畫《丈夫》中畫幅52(見圖4)對應著小說的結局:水保到船上吃酒時被告知夫婦倆一早就回到鄉下去了,畫家沒有根據腳本描摹出任何一個人物,整個畫面除去上方的太陽以及下方無船只停靠的河岸,其余皆為空白。畫面看似簡單,卻暗含無限深意:妻子隨丈夫走了,以后還做船妓嗎?她不做了,其他丈夫的妻子呢?若都回鄉了,這片河岸的船妓是不是都不再有了……讀者通過發揮主觀能動性,反復品味畫面的空白之景,可以在聯想和再創造中構建出一個完整的故事圖景,為敘事留白的小說文本生成新的意義與內涵。
除此之外,畫家也試圖通過再現小說里的自然風光來構建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并借自然環境中的物象暗示情節的推演,以還原其敘事上留白的特點。小說《邊城》的高潮部分由一場醞釀許久的雷雨拉開序幕:在雨夜的電閃雷鳴中,爺爺走向了生命的終點。然而,沈從文沒有把敘述的重點放在爺爺身上,對他的描寫僅寥寥數筆——“原來這個老年人在雷雨將息時已死去了”,他將更多筆墨放在雷雨夜的環境描寫上:電光從屋脊掠過,緊接著大雨傾盆,河溪洪流滾滾,渡船脫離纜繩,白塔業已坍塌……學者劉進才將這種景物描寫稱為“非情節因素的空間化”[1]劉進才:《京派小說詩學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68頁。,指的是那些不參與小說情節發展的敘述或描寫。他認為這是京派作家在文本內部對空間形式的藝術追求,京派小說更看重環境,而沈從文小說里對自然環境的描寫和民情民俗的展示恰恰就是他最想要突顯的部分。李晨版連環畫《邊城》對這段情節的處理很好地還原了小說的詩化風格,也兼具留白的藝術美,他似乎與沈從文先生秉持著同樣的審美意趣,沒有直接繪制出爺爺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情態,反而是描摹了兩個具有暗示意味的自然物象:碩大的閃電劃破黑云直擊大地(見圖5),湍湍流水席卷磚石向河岸涌去……閃電破空、河水奔流、白塔坍倒、渡船離去,它們將爺爺和翠翠的分別推向了生命的另一個階段,這些自然物象在沉默中爆發出強大的審美潛能與藝術張力,繪畫藝術上的留白也帶給讀者可以反復咀嚼、無限品味的空間。

圖5 李晨連環畫版《邊城》 圖幅84
總而言之,部分繪者在連環畫改編中與作家志趣相投,同樣追求“留白”的含蓄美。雖然他們所采取的藝術媒介不盡相同,但最終仍是殊途同歸,不論是在圖像里留下大片可填充的空白來映襯小說敘事的“言已盡而意無窮”,還是通過描摹自然風光以渲染環境氛圍,傳達主體情緒,都是畫家對沈從文筆下詩情畫意的抒寫與再創造,使得作品在文畫互動中實現了“詩性”的解放,給讀者帶來全新的閱讀審美體驗。
綜上可見,改編者們努力掙脫以往詩化小說圖像改編難以與原作風格有機契合的拘囿,有意識地將沈從文作品的“詩性氣質”融注于連環畫創作,建構了一個富有“連環性”的詩意世界。
五、啟悟:在開放與創造中探求新生
在傳統連環畫日漸式微的今天,重新檢視與思考沈從文詩化小說連環畫改編的成功案例,為當今讀圖時代的連環畫及相關圖像改編提供了積極的啟示,即在開放與創造中探求新生。
回顧沈從文小說連環畫改編的歷程,我們看到,改編者們一直以開放的姿態,積極借鑒其他藝術門類的敘事技法,促使傳統連環畫向現代轉型的方向努力。當代影視動漫的敘事手段豐富多樣、造型動作新穎夸張,能滿足時下大眾的審美情趣。沈從文詩化小說連環畫改編的創作者從中得到啟悟,在繪制圖像時利用視點轉移、時空交錯等影視敘事技法來敘說故事,從“三聯一體”的空間并置到“聚焦特寫”的鏡頭表現,畫家將沈從文小說的情節段落重新分解組合,以富有內在邏輯的空間切換來詮釋小說中的湘西世界,使得連環畫本呈現出電影蒙太奇敘事般的質感,不但沒有破壞連環畫一氣呵成的閱讀體驗,還恰到好處地營造出了沈從文小說獨特的詩意氛圍,彌補了過去影視改編時“詩性氣質”缺失的遺憾。從這點上看,沈從文詩化小說的連環畫改編無疑是一個值得學習的改編典范,這意味著新興連環畫的創作觀念與技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哺影視。這種繪畫、影視及動漫技藝的互補交融,為圖像敘事的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藝術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