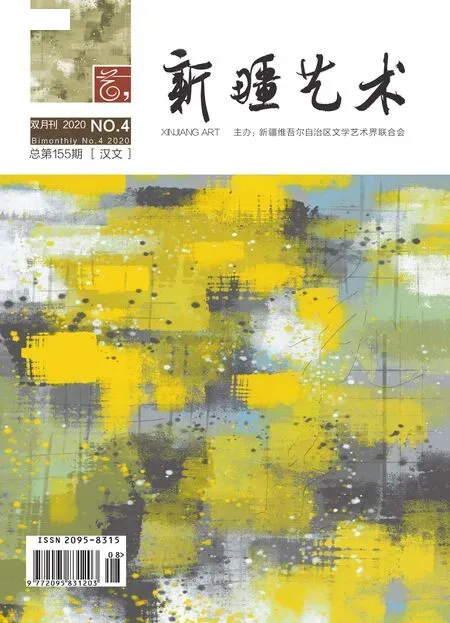《遠去的牧歌》:民族心志與歷史宏圖的詩意言表
□ 喬 慧

電影《遠去的牧歌》劇照
《遠去的牧歌》以四季流轉的散文詩意記錄了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新疆哈薩克牧民在生存與生活、生態的糾葛中,告別遷徙轉場邊牧的古老傳統生活,在矛盾與不舍中終于融入安居興牧的現代化新生活的故事。電影以史詩氣魄記錄一個民族的變遷與國家改革開放以來的繁榮發展,深描其民族傳統,并對整體民族風貌做宏大而典型的“民族志”書寫。悠遠瑰麗的民族詩意精神,彌漫于精致巧思的電影詩意語言之中。
《遠去的牧歌》由天山電影制片廠導演迪夏·夏熱合曼與周軍耗時三年聯合拍攝的一部少數民族題材巨幕影片,以春夏秋冬四季變換為結構方式,展現哈薩克游牧民族從遷徙轉場到定居生活方式與思維方式的轉變,同時投射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少數民族的興旺發展人事變遷,蘊含對傳統民俗與現代文明的理性思考。該電影作為2019北京國際綠色電影周的揭幕電影,以其詩意風格與精美制作廣受關注,獲得第十五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優秀作品獎。與此同時,這部電影基于對行將消失的哈薩克游牧民族轉場的保存需要而拍,以其全景式搶救紀錄片的性質承擔起民族志電影的作用,其內容立意與影片風格、審美品質,都“展現了新疆題材電影、少數民族題材電影、重大題材電影的新可能、新空間、新境界①”。
一、民族心志:深描真實與語境強化
《遠去的牧歌》是游牧民族融入現代文明的一次紀錄。電影在哈薩克族游牧與定居、消耗與保護、傳統與現代、生存與生活各種二元選擇中探究經濟發展現代文明對哈其民族生活方式與思維方式的影響,在其遷徙轉場景觀消弭之際回望四十年歷史,梳理并重演這一段歷程中從拒斥到融入到欣然享受現代文明的民族心態與民族生活演變,電影擔起讀圖時代直觀呈現與保存記錄哈薩克族民族圖景的“影像民族志”的功能。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定義一般來說學界定義“民族志”為“關于民族/族群社會文化的記述與描寫,其研究對象就是民族或族群”②。馬力諾夫斯基認為,成其“志”的首要要求是長時間的“浸泡”觀察,以實現真正對該民族世界的科學、客觀、嚴謹的真實摹寫,以其真實性開拓影像對民族志“寫文化”的形式延伸。兩位導演迪夏·夏熱合曼與周軍雖然相對哈薩克人來是文化與族群的“他者”,但長期生活于新疆,工作于天山電影制片廠策劃部,對新疆風土與哈薩克民情有著長期的觀察與由此積淀得來的理解,在長達三年的創作時間中概括提煉這一民族的全景歷史境遇,深描這一民族的風俗、儀式、情懷。
在拍攝這部搶救復現紀錄片的三年里,兩位導演耗費三年與牧區人民一起生活,充分田野作業觀察他們的生活細節還原真實情感。根據長時間的觀察,按動物群居與覓食習慣做分析記錄,并據此繪制好拍攝用的話筒與攝像機的布局圖,繪制好動物行走路線跟蹤圖。所以駱駝、羊群、馬匹多方向運動與多方面的展現,鏡頭充足而多樣,生動不局促。導演組在羊圈里埋下錄音器材長時間待機,所以電影里可以聽到羊群立體環繞一樣的呼吸,甚至可以聽到羊的咳嗽聲。四次遷徙,一次婚慶,一次誕辰禮,一次納吾魯孜節,其民族氣氛與民族習俗得到精致典型的呈現。醇厚濃烈、堅韌不移、熱情洋溢、悲天憫人的少數民族俗世文化體系之中蘊含令人贊嘆的普世人情,電影對這群生活于落后經濟中的人民,做了詩和樂一樣的歌詠,四十年生死詰問,一年四度轉場求生,最終遠離故土遠離邊牧,以其離散故土但事實上“反離散”的獨特民族演進道路構成一部民族文化與民族生活契合時代之變的壯闊民族志。
《遠去的牧歌》在真實與虛構的衡量上,其實是采用了半記錄半搬演的方式,也是最近幾年紀錄片學者們探討的“虛擬民族志”的成分因素參與其中。有意識拉長的時間跨度,扭轉了之前民族志紀錄片記錄時間短、從細節著手難以掌控大局觀、有現狀無過往有共時無歷時的缺憾,巨幕寬景與四十年里的四個季節,真正以“志”的高度構建完整的時空關系和世事衍變。影片以1980年代中期的冬、1990年代中期的春、2000年代中期的夏與2010年代中期的秋四十多年的時間里的四個季節構成極具寓意的一年時節,十年為期做一個民族演進史的典型概括濃縮,四季流轉之間人事皆非,而其情其志不改。民族團結友愛,善良有大局觀有生態觀,歷經生死磨難不改,不改故鄉依戀卻也不抗拒新生活的降臨。這樣一場民族歷史變革在長時間的鋪墊紀錄與水到渠成的接受里寧靜而漸進地發生,自省性超越性地完成一場民族進步。我們無法說這種四季劇情是標準真實的“寫志”,但是羅伊佐斯認為“‘語境強化’才是民族志電影最強大的力量之一:“不應懼怕讓電影拍攝的過程來主導一場調查,只要不讓它改變隱喻、誘導證人、迷惑觀眾③”。電影在開頭三五分鐘的時間里接連講博蘭古麗的“生”與哈山的“死”,生命與生存的詰問如山呼海嘯令人震驚。提純的典型與濃縮的時間有其不可替代的全面觀和震撼力,更好在短短一部影片里呈現歷史變化與牧民生活意識變化的多級多層。正是這種充滿意蘊的修辭、恰當的發展間距和散文故事化的構思,展現了民族志在對人類學知識的描述與參與歷史表征的后現代轉向與更強大的功能。

電影《遠去的牧歌》劇照
二、歷史宏圖:離散美學與現代認同的另一種可能
影片的主要敘事脈絡是記錄游牧文明向定居生活的演進。現代性的核心和離散,是與傳統的斷裂,是一種線性的、向前的、進步的時間觀念和發展態度。但是《遠去的牧歌》處理離散敘事的特點在于,雖然將游牧放置于現代性的對立面,卻不將其放在現代性文明的對立面。哈薩克族的穹頂帳篷如世外桃源,牧民淳樸真誠,另一種人文與自然景觀被一再強調,記錄下歷史的痕跡,搶救下文化的流傳。
《遠去的牧歌》不單單是為哈薩克游牧民族的過往作傳,在牧民們或艱難或愜意的日子里,都可以映見另一條歷史脈絡:國家強盛與現代文明的發展。美國民族志詩學家詹姆斯·克利德福認為形成民族志有兩大節點,分別是國家體系的形成時期和世界政治經濟發展時期。開始于1978年的改革開放,帶來的不僅僅是經濟的復蘇與繁榮,更多的是現代文明與現代生活方式現代思維方式的沖擊。這種沖擊在電影里表現為一種遞進滲透的而非速成的、反思進化的而非盲目崇拜的改進。比如胡瑪爾靠經驗判斷天氣選擇遷徙時機,并不盲目將政府通知與廣播天氣預報拒之門外;博蘭古麗不被約束追尋知識,求學去了北京并與里亞斯開車帶兒子回歸牧區,在爺爺的老馬走散之時也可以縱馬揚鞭;發展的陣痛也是不被避諱的,糞便堿性太大的山羊受到擴大化的養殖,冬蟲夏草與貝母的利潤促使人們在草原上挖開一個又一個瘡痍一樣的坑洞。對故鄉的回望有其深沉愛意留存的理由,對新文化的接受有其猶豫不決的根據,過去與未來,留守或遷居,構成了一種迥異于世界離散美學審美程式的、和現代認同的,另一種可能。
“離散文化表現為離開母體文化而在另一種文化環境中生存的文化現象,并引發了離散個體精神世界的文化沖擊與抉擇、離散者對文化身份認同和追求等各種問題④”。《遠去的牧歌》是極具離散文化特點的,胡瑪爾反問“我們哈薩克人還怕轉場?”認為只有“騎到馬背上,才能看的夠遠”,甚至認為搬到安居點后自己就會變成一個沒有用的人。但是未來生活的美好,以免于轉場中人的犧牲與動物的死亡為最大的生存之需,將對家園的離散悲傷轉化為可以期待的憧憬,以暖意包裹別離民族歷史的悲傷,將以往的“離”改寫為哈薩克族牧民走向現代文明、努力開創美好生活的“歸”,此歸與故鄉故文明習俗殊途,但回歸國家經濟建設與生態保護的懷抱更有崇高的美感意義。
影片以“冬”“春”“夏”“秋”四季結構了近40年改革開放中新疆哈薩克民族精神世界發生的深刻嬗變。“冬”寒象征著傳統的游牧生活轉場的天災人禍給牧民的生存危難,為牧民放下民族傳統融入現代生活的轉變做生存剛需的鋪墊;“春”暖象征著伴隨著改革大潮對傳統游牧生活的震蕩給老、中、青牧民價值取向、生活方式、道德觀念帶來的沖撞和變化,堅冰融化的蒙太奇鏡頭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對撞,并昭示了新季節新生活的勢不可擋;“夏”熱象征著改革巨浪推動的令傳統游牧文明必然向現代文明過渡轉化的歷史發展趨勢,新一代茁壯成長而他們將帶來民族生機絢爛盛放;而“秋”實則象征著改革開放結出取得豐收果實,牧民定居于新村,安定美滿各得其樂。影片結尾胡瑪爾在客廳中摁下遙控器選擇收看電視臺對新家園蔬菜種植與奶牛養殖的報到,新家電的嫻熟使用與滿面笑容,充滿新的詩意棲居的意味。影片著眼于宏大視角,卻立足于鄉情敘事。對胡瑪爾哈迪夏兩家的世代關系和對羊皮別克的對立關系的交代,又使文化展現與國家建設的大情懷落足于價值的具象化與故事的個體化。游牧文化的結束不單單由于文明進程與經濟發展,而是細致交代了牧場貧瘠、轉場艱難,游牧之鄉的“故土”對其居民的“先行背棄”,在之后的告別中,塑造了城市之“新居”的接納,“無家生存”的現代性存在困境無縫隙無劇變輕松過渡,證實了這場不同于傳統“離散”的美感而不是告別之殤。
三、《遠去的牧歌》作為詩意記錄片的詩意言表
聶欣如教授在其《思考紀錄片的詩意》中將紀錄片的詩意劃分為四個層次,分別是:影像的詩意——序列排列、話語的詩意--使用詩歌散文、敘述的詩意——敘事邏輯傳達思想以及詩學的詩意——追問存在意義。這四個層次逐層遞進,包裹了從視覺到敘事到思想的各種組成。《遠去的牧歌》是非戲劇性結構的,借用散文“形散神不散”之形式成其敘事之詩意,以航拍、俯拍、大全景、景深構圖成其影像之詩意,以獨具民族感悟包含民族經驗的對白成其話語之詩意,以拒斥或皈依、轉場或安居、傳統與現代各種矛盾的拉扯選擇與反思成其詩學之詩意。
(一)影像的詩意
《遠去的牧歌》對其所呈現出來的視覺效果是極為講究的。春夏秋冬四季變換。分別以風雪之白、草色之青、繁花之彩、秋葉之黃為大色塊的基調,展現四季邊疆自然風貌并對應人生得失境遇。哈迪夏家母駱駝死去,極高的俯拍鏡頭下駝尸躺倒,生命的逝去令人驚心,動物死去被表現以一種儀式性的場景,以主觀性的情感鏡頭還原了哈薩克民族對生態、對動物的熱愛,激發對所有生命一視同仁的生命敬畏;巴彥與杜曼兄弟爭吵,馬與摩托作為傳統與現代兩種文明的代表并列置于前景,兩人滾成一團成為模糊的后景,爭斗的是生存理念,可以淡去的是兄弟糾葛。影片中這樣精心構思的鏡頭比比皆是不勝枚舉,如散文詩電影一樣美麗雋永,對全貌摹寫時尤愛航拍技術支持下大俯拍鏡頭與舒緩音樂的聯合使用,靜觀不躁,動情不哀。
(二)敘述的詩意
以“冬”“春”“夏”“秋”四季結構,分四個章節,每個章節十年的敘事節奏。采用“散點式和詩化”的敘事風格和視聽語言,通過紀錄電影的方式,以全景視角,以“天之高遠,地之渾厚”為基調,依托畫面的視覺沖擊、人物情感的沖突、富有哲理地意境化處理,深沉而樸素地整體營造一種哈薩克游牧民族原生態的生活質感。敘事沒有集中爆發的沖突點,沒有三一律的限制,四季流淌生活成為事件本身,也就避免了用傳統的戲劇結構壓縮詩意情調詩意境界的生存空間。戲劇結構的起伏波折起承轉合會對詩意表達產生限制,而散文化的處理則將詩意延續從始至終不被分割,從而有助于觀眾形成同條共貫的詩意享受。
(三)話語的詩意
電影對話極具深意,諸如哈迪夏年老時教育孫子“樹沒了,鳥就不來了;鳥不來了,蝗蟲就多了;蝗蟲多了,草就沒了;草沒了,那些羊吃什么”對于生態鏈的深入思考與顯明表達,與胡瑪爾“搬遷好是好,這個我知道,保護草原對,可是沒有別的辦法了嗎”對矛盾情感的概括陳述以及對影片主旨的明確揭示,都有詩化了的哲理韻味。在電影描繪少數民族風情并令人沉浸于其民族淳樸與民族習俗的同時,“現代化”的進程切入卻讓人很難不產生拒斥的距離感,這顯然又會與影片主題背道而馳。如何平衡這種感傷而達到告別過去歡欣進入未來的共情,《遠去的牧歌》無疑在這種詩意話語的深層意義中找到了如伽達默爾所說的“共通感”:即,將政府倡導的、哈薩克人民堅守的、現代人認同的生態保護意識編織入其民族文化符碼,并形成電影敘事的主要推動力,成為一個不被情感敘事遮蔽的主題。
(四)詩學的詩意
這部少數民族風格的影片在很大程度上能看出對漢文化“賦比興”修辭借用的影子。寬幅場景抒情如賦,寓意場景凝練深意如比興:初次以保護燕窩將其放置于拴馬樁關聯對生命的愛護以及對家園的眷戀保護;二次以驅逐老鷹暗含傳統禁錮終將被破除,未來自由融入新生之義。在一定程度上,胡瑪爾和哈迪夏兩家的牽絆,是對生命意義的一種探討寓言:哈山為胡瑪爾兒媳生產推遲轉場遭遇危險喪生;胡瑪爾兒子為救哈山兒子墜崖喪命,兩位老人同命相憐放下恩怨“有我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第三代結為姻親延續了兩個家族的生命。在恩怨未了之時,當胡瑪爾扭傷腳踝,哈迪夏也暫時放下喪夫怨恨趕來幫忙醫治。楊義認為“時間觀念上的整體性和生命感,是中國人采取獨特的時間標示的表現形態……由此他們以時間整體性呼應著天地之道。并以天地之道賦予部分以意義”⑤,生死接續,匯成生生不息的民族史詩。
作為一部搶救性史詩性的民族志電影,導演在拍攝之處就確立了詩意表達的方法風格,如此既要保證對過往四十年民族苦難與國家發展的客觀真實性的記錄,又要符合觀眾尤其是其他華夏民族觀眾對共通之美的追求和情感需要。四十年風云變幻四季更迭,《遠去的牧歌》做到了在盡量減少對客觀現實“破壞”的基礎上,滿足觀眾的審美需求的詩意言表。在這“志”與詩意中,所映射出的對生命輪回的探索、對自然的熱愛與敬畏和對中國生態觀大局觀的贊頌通過詩意化手段得以極致呈現。《遠去的牧歌》展示“游牧文化”的歷史、人文情懷和豐厚內涵,以游牧轉場為線索,從人的生存方式、對自然的敬畏、對生命的尊重,以及當下草原所面臨的文明變革、生態危機與休牧拯救等,多方面揭示一個民族作為“人”和作為族群的精神存在和心理變化過程,兼顧展示現代文明給傳統文明帶來巨大沖撞時的堅守與無奈,以及牧民最后順應時代潮流、告別傳統走向新生活。影片將視聽形式與審美感情同構形成內外審美的協調,并將蘊藏在審美之中的終極追問形成詩意表述。
注釋:
①康偉:《〈遠去的牧歌〉:一部不會遠去的“藝術大片”》[N],《中國電影報》2019年5月1日第002版。
②劉玉皚:《民族志導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8年版第11頁。
③LOIZOS P.Admissible Evidence? Film in Anthropology[M}.In film as Ethnography.Ed.Peter Ian Crawford,David Turton.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
④張敏:《黃宇杰經典研究:流散研究·性別研究》[J]2009年當代外國文學學術研討會綜述.《當代外國文學》.2009(4)。
⑤楊義:《中國敘事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