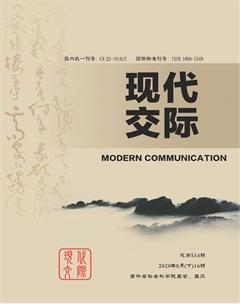評價理論視域中《生死疲勞》英譯的翻譯批評
曾圣潔
摘要:自2012年中國當代小說家莫言斬獲諾貝爾文學獎以來,中國文學作品開始越來越多地走入西方讀者的視野。莫言的翻譯葛浩文及其英譯作品也廣受不少中國專業讀者群的關注,由此產生了相關的翻譯批評活動。以葛浩文英譯本《生死疲勞》為例,管窺基于價值學的評價理論體系中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翻譯批評活動,從活動涉及的主體、客體和中介著手分析隱藏在背后的力量,以合規律性、合目的性為參照,客觀分析翻譯批評活動。
關鍵詞:評價理論 主體 客體 翻譯批評活動 《生死疲勞》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20)16-0096-03
文學作品一直是體現民族文化底蘊的代表之一,是各個國家在不同社會和時代變遷的結果。由于文學作品的虛構性,文學文本同現實之間產生了一些距離美,創造出了一個似真非真的世界,并通過翻譯活動,拉近了世界人民之間的距離。2012年,我國文學作家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一時間中國不少著名文學作家的作品開始進入西方讀者的視野,翻譯莫言作品的美國翻譯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及其英譯作品也成為不少學者的關注對象。國內外讀者和媒體對于葛譯本的評價褒貶不一,他們分別從文學作品的文字描寫、諾獎背后的政治因素、英譯本是否忠實于原著等方面展開了熱烈討論。然而,對于這些討論,我們并不需要給出一個正確與否的結論,而應該用客觀的評價去闡釋翻譯活動或者翻譯評價活動的影響因素,以成功的英譯作品為出發點,從更加客觀的角度看待中國文學“走出去”。
一、評價理論中的主體、客體和中介
翻譯批評活動從內部講,是不同個體根據自己的理解指出譯文的忠實與否、風格一致與否或者譯文通順與否,這與翻譯理論息息相關。而從翻譯批評活動外部來看,研究的是文本如何形成以及文本形成的影響因素等,這一點是基于評價理論的(屬于價值學范疇)分析。既然涉及“價值”范疇,就需要了解這一領域中的主體和客體。價值是客體屬性對主體需要的滿足。人類一切社會實踐活動都是價值性活動,包括翻譯,如人們為什么翻譯,翻譯什么,如何翻譯等。在評價一部翻譯作品或者解釋翻譯活動時,首先需要清晰明了這部譯作或者翻譯活動是否滿足了社會需求、人的需求或者具有何種積極意義,其次才著手看譯文本質,要將合規律性和合目的性兩個價值學關注的因素考慮在內,才能更加客觀、有效地開展評價。
這里需要進一步明確評價理論中提及的主體與客體。在以往的翻譯實踐中,譯本被視為研究客體;而今,“客體”的所指廣義上不僅包括譯文,還應包括翻譯現象以及翻譯批評活動所涉及的“文本”。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譯本和翻譯現象作為有機整體,是在翻譯理論指導下研究的,而對文本的理解,它其實涉及了文本的理解和解釋,是基于評價理論開展的分析研究。
客體具有一定的客觀屬性,穩定性較高;而言及主體,問題就比較復雜了。主體具有個體性和差異性,他們的需求是多樣多變的,而且主體的視域也各有不同,主觀能動性較強。當然,評價主體認識的對象除了譯本、翻譯現象這樣具有自在客觀屬性的客體以外,還因包含這類客體對主體需求達到滿足的性質和程度(如翻譯批評活動的外部評價,包括對文本形成過程的思考及其成因等,都有人為因素),因此這樣的客體中也包括了主體內容。除此之外,無論是原文還是譯文,文本本身都不是實存性客體,而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主體對實存客體進行抽象、概括,以符號形式表現出的客體。
除了評價理論中涉及的主體和客體,人類一切社會實踐活動都需要經過中介,將主客體連接在一起。既然翻譯活動屬于社會實踐活動,那么翻譯活動的中介就是語言,即連接主體(作者、譯者、讀者)與客體(原文本、譯本、翻譯現象以及翻譯批評活動)的重要紐帶。從功能上講,語言既有自指性,也有指向外部世界的能力。從翻譯研究角度看,自指性主要指語言的內部結構和使用規則,而指向外部世界,則要更多地思考與語言使用主體相關的作者意圖、社會現實等因素。
二、基于評價理論的社會交往行動三要素
充分理解了評價理論(價值具有多元性)中的主體、客體和中介的具體意義,我們才能客觀地分析翻譯批評活動。翻譯活動作為一種社會實踐活動,實質上也是人類社會交往活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與生活世界中的文化、社會和個人因素密不可分。根據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這里的文化是指知識儲備(從翻譯批評活動出發,可以理解為主體的前視域);社會是指一種合法的秩序(從翻譯批評活動出發,可以理解為主體的意識形態);個人是指主體說話、行動以及理解的能力(從翻譯批評活動的評價出發,可以理解為主體和客體在語言中介的連接下展開的互動)。
三、莫言《生死疲勞》葛譯本的翻譯批評活動價值背后的因素
從評價理論出發,首先需要了解莫言作品《生死疲勞》葛譯本翻譯批評活動中的主體和客體。主體包含《生死疲勞》的作者莫言、英譯者葛浩文以及《生死疲勞》英譯本的讀者群。由于主體有一定受限性,不是完全自由的個體,而在翻譯活動這個社會實踐中產生了社會交往,主體之間具有主體間性。因此,分析三個主體(也是生活世界的個人因素)是首要任務。
莫言是中國著名的文學家,著有《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勞》《透明的蘿卜》《師傅越來越幽默》等長中短篇小說。出生在山東的農村家庭,雖然只接受過五年的正規教育,但十分熱愛讀書,在西方現代主義文學(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下,憑借著自己豐富的想象力和洞察力,結合中國經驗、本土化與民間資源進行文學創作,并以一種詼諧、自由的表現手法,借助中國特色的鬼怪形象,揭示一些現實現象。2012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葛浩文是美國著名的漢學家、翻譯家,從事中國文學、文化研究近40年,享有一定聲譽。在此期間,他翻譯了蕭紅、賈平凹、蘇童、莫言等在內的20多位作家的文學作品,對中國文學“走出去”做出了貢獻。葛浩文自1993年翻譯中國文學作品以來,經歷了翻譯的初期、探索期和黃金時期三個階段。在整個翻譯實踐過程中,他一方面致力于傳播中國傳統文化,另一方面將西方讀者的價值觀、意識形態等因素放在重要位置。盡管如此,他的譯作收到兩類讀者的不同反饋:一類是同一價值體系的西方讀者,一類則是通曉英漢雙語的讀者(專業人士)群。
針對西方讀者和中國讀者對于葛浩文譯本的不同反映,我們可以將社會交往活動(翻譯活動)中涉及的文化和社會因素結合起來,展開綜合分析。
根據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這里的文化指的是知識儲備。西方讀者對葛浩文譯本的接受度良好,這離不開葛浩文文本選擇以及對中西文化差異的深入理解。葛浩文是莫言文學作品的讀者,又是譯者,他把自己的主觀意識、審美情趣或國家的社會文化因素糅合到一起,經由他的評價,再翻譯成另一種語言。這時他的譯文已經不能等同于原作者對作品作的價值判斷了,這是譯者加工后的第二層價值判斷的結果。那么在這一過程中,葛浩文成了翻譯活動的價值主體。中外讀者群對葛浩文譯作進行分析評價時,又產生了一個新的價值關系,讀者群成了評價的主體,而譯作成了價值客體,由此構成了第三層價值判斷的結果。因此,對于任何譯本、翻譯現象和翻譯批評活動的評價都是圍繞主體—客體的動態關系展開的,同時需要以規律性為指導,以目的性為依據。因此,這里的客體既包含《生死疲勞》英譯本,還應包含整個“文本”分析。具體實例如下:
例1:
原文:西門歡天生不是個讀書的孩子,他在這五年里做過的壞事難以盡數。進縣城第一年他還有所收斂,從第二年開始,他就成了南關一霸,他與北關劉小羅鍋、東關王鐵頭、西關于干巴壞名相齊,是縣公安局都掛了號的“四小惡棍”之一。(莫言《生死疲勞》,2006)
譯文:Ximen Huan was not student material;hed caused more trouble and created more mischief during those five years than anyone could count.The first year he was relatively well behaved,but then he took up with three young hooligans,and in time they became known by the police as the “Four Little Hoods”.(Goldblatt,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2008)
例2:
原文:但一個二十多歲就當了縣級領導干部的人,和農村姑娘結婚的可能性幾乎是零,無論她貌如西施還是色比嬋娟。(莫言,《生死疲勞》,2006)
譯文:There was no chance that a leading county-level cadre in his twenties would ever actually marry a pesant girl,no matter how pretty or fetching she might be.(Goldblatt,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2008)
例3:
原文:“你什么都不要說,”她打斷我的話,平靜地說,“無論是爬刀山還是跳火海,我都跟隨著你!”(莫言,《生死疲勞》,2006)
譯文:“Dont say anything.”She stopped me.“I dont care if its climbing a mountain of knives or swimming a sea of fire,”she said calmly,“Ill be there with you.”(Goldblatt,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2008)
據分析,例1原文中的“北關劉小羅鍋、東關王鐵頭、西關于干巴”并沒有直接翻譯出來,而是采用了減譯的方法,直接將這三者概括翻譯為“three young hooligans”。譯者可能考慮到西方讀者對于這三個人物及背景并不理解,如果將三個陌生的名字全部翻譯出來,會顯得突兀。其實這三人就是流氓、惡棍的代名詞,只需直接翻譯出內涵意義即可。例2原文中的“貌如西施還是色比嬋娟”采取了意譯的手法,譯為“how pretty or fetching she might be”,并沒有將“西施”“嬋娟”這樣具有意象性的名詞翻譯出來,更沒有對相應的典故進行解釋說明,譯者可能考慮到這類名詞翻譯與解釋在文中并不重要,原文只想借此表達姑娘的美麗程度,譯者想讓西方讀者能夠直接領會文字大意。與前兩例不同,例3原文中的“爬刀山還是跳火海”譯為了“climbing a mountain of knives or swimming a sea of fire”,譯者此時并沒有尋找西方讀者熟悉的意象或者熟語進行替換,而是直接將“刀山”和“火海”翻譯了出來。前文提到,葛浩文翻譯中國文學作品的目的之一是為了努力讓西方讀者了解中國文化,豐富西方文學和文字。
就中國讀者群而言,大多是會英文的學術人士,對葛浩文英譯本的見解也是褒貶不一。有的學者認為葛浩文的翻譯并不忠實,刪減了原文的大量語句,沒有將莫言文學作品中字里行間流露出的文化特色傳遞給西方讀者。然而,筆者查閱相關文獻發現,葛浩文在翻譯莫言的每一部作品之前,都會與莫言通郵件、電話,請教不懂的文字和表達,由此可見他對翻譯實踐的嚴謹態度。那么就葛譯本“不忠實”的原因,除了表面的文字符號的轉換有所增減以外,可能還源于從事翻譯理論研究的學者受到自身前視域影響,對中國借鑒西方的翻譯理論范式有著不太全面的理解。具體而言,有的學者從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翻譯理論出發,認為語言是封閉的,文本有確定意義,只關注兩種語言的轉換規律,將“等值性”作為譯本好與不好的評價標準。“等值論”是把主體因素排除在外,將對主體懸置,認為語言是要遵循客觀規律的,僅以此標準來評價譯本。從語言學角度分析,語言系統并非封閉自足的。語言始終在變化或者連續變化,既有外部因素影響,也有內部因素影響。另外一些學者則從解構主義譯學范式出發,認為一切意義都是在對話中產生的,不同視域融合帶來不同意義,宣稱“作者”已死。這一范式否定了作者的主體性,只強調位于非中心主體(譯者)的主觀能動性,完全釋放了原本中心主體制約下的翻譯活動,將個體差異性得到最大化體現,卻忽略了任何個體都是社會這個大主體的,任何個體需求都在潛移默化地反映著社會發展的整體需求。任何個體不可能無限制地展開完全自由的選擇,在個體關系與社會關系的牽制下,個體主體的選擇會受到社會規范的約束。從價值觀考慮,評價理論是不可能完全擺脫社會意識形態影響下的中心主體因素而存在的。
除了上述提到的文化和個人因素,社會因素對于我們展開翻譯批評研究也十分重要。其一,文化因素(知識儲備)會影響個人的思考及實踐活動的開展;其二,在社會交往中,每個人又會和外部世界的各種社會因素發生聯系。
在葛浩文翻譯莫言的《生死疲勞》作品之前,有諸多社會因素需要考慮在內。第一,西方讀者的接受度。前文提到了莫言文學作品的創作模式,這與中國大多數文學家的創作方式不同,他本人深受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特別是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因此,他擅長運用世界性的敘事技巧,將富有中國本土特色的神話鬼怪等意象創造性地融入作品中。對于西方讀者而言,莫言的這一文學創作方式和文學作品中表達的內容確實表現出了人類共同的價值和普遍意義,以這種“以人為本”的共識建立起了共通價值與情感的橋梁。盡管如此,我們在做文本分析時,還要考慮到西方文學的整體特征。西方大部分讀者,特別是美國讀者,他們對于自己本國的文學作品信心十足,很少會去接納中國的文學作品。即使莫言的作品在寫作技巧上有世界格局,善于創造性地將中國小說在藝術上進行改造、提升,并充分表達中國性的民間情懷,但如果沒有葛浩文幾十年來潛移默化的英譯作品影響,短時間內也很難讓西方讀者有所接受。第二,隱形主體的存在價值。對于《生死疲勞》的翻譯活動而言,顯性的主體是原文作者、譯者和讀者群,但隱形主體的存在也具有非凡的價值。這里的隱形主體是指中外文學作品贊助商、出版商和文學代理人。比如《生死疲勞》的英譯本由美國巨頭出版商之一的拱廊出版社(Arcade Publishing)出版發行。拱廊出版社的創始人理查德·西維爾(Richard Seaver)讀了《酒國》后,對莫言贊賞有加,拱廊又相繼出版了包括《生死疲勞》在內的其他幾部英譯作品。此外,莫言在中國的“伯樂”——北京精典博維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董事長陳黎明,也對莫言文學作品的市場開拓大有助益。
因此,任何一部翻譯作品的誕生絕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翻譯活動。既然翻譯活動屬于社會實踐活動,那么它所處生活世界中的文化、社會和個人因素應作為評價一部譯作的組成要素。
四、結語
任何翻譯活動或者對翻譯批評活動的評價,都離不開翻譯的本質研究,需要從在場的形式(包含外在形式和內在形式)中去挖掘不在場的意識形態,不能脫離任何一個因素去研究。而評價的標準,是以評價理論為基礎確定的,需要考慮價值學中的主體、客體和中介。盡管世間價值觀包羅萬象,只要始終以合規律性、合目的性為參照進行評價判斷,就能更加客觀地研究不同的社會實踐活動。葛浩文《生死疲勞》英譯本的翻譯批評活動,讓我們更加全面地了解了影響譯本誕生的諸多顯性和隱性因素,能更加客觀地對翻譯活動進行批評;也讓我們從價值觀的內在和外在目的性出發,深刻思考譯者在翻譯時除了滿足自身對作品的愛好需求與表達,想把喜愛的作品推廣出去,還需考慮外在目的,即該譯作對目的語社會的進步是否有推動作用或者有積極影響。
參考文獻:
[1]呂俊,侯向群.翻譯批評學引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9.
[2]莫言.生死疲勞[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3]YAN M.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M].New York:Arcade Publishing,2008.
[4]陳千颯.基于語料庫的《生死疲勞》熟語英譯研究[J].重慶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1):105.
[5]張琦.“創造性”叛逆:莫言《生死疲勞》英譯特點及啟示[J].上海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4):327.
[6]黃衛峰.葛浩文的文學翻譯忠實觀及其實踐[J].杭州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1):59.
[7]李文靜.中國文學英譯的合作、協商與文化傳播:漢英翻譯家葛浩文與林麗君訪談錄[J].中國翻譯,2012(1):57.
[8]許鈞.關于文學與文學翻譯:莫言訪談錄[J].外語教學與研究(外國語文雙月刊),2015(4):611.
責任編輯:趙世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