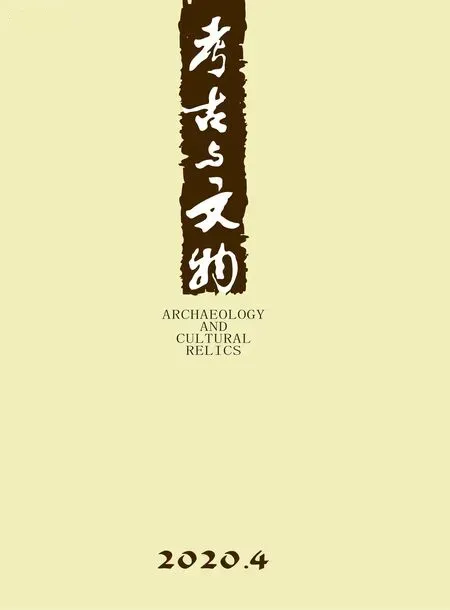漢代“盤鼓舞”圖像再考訂—側重于考古材料的梳理與解析
王 菁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
“盤鼓舞”是漢代樂舞中廣為流行的一種以盤與鼓為基本舞具,舞者隨節拍跳踏其上的獨特舞蹈類型,且在傳世文獻與考古材料中有豐富印證。肇始的研究可追溯到上世紀50年代,以王仲舒《沂南石刻畫像中的七盤舞》與馮漢驥《論盤舞》為先導[1],對盤鼓舞的文獻記載做了清晰而詳盡的梳理。嗣后的學術跟進則時有拓展,以近年的研究為例,較具新意的有閆艷《釋“七盤舞”》[2]、李淼《漢畫盤鼓舞解析》[3]、潘岷《河南博物院藏東漢盤鼓舞畫像磚考略》[4]、杜樂《漢代“盤鼓舞”初探》[5],以及張晗《動靜之美—南陽畫像石“盤鼓舞”表現手法研究》[6]與韓博雅《基于文獻與圖像的盤鼓舞藝術風格研究》[7]等,其中也多有注意到對零星考古新材料的利用。然而,總體考量以往的研究,似大多受限于對考古新材料晚出或不易搜集,而稍顯單薄且體系不整,亦即未見有納于圖像資料平臺框架下對于“盤鼓舞”圖像類型與要素及其整體圖像的綜合梳理與解析,因此本文欲嘗試從一個新的角度給予補充和考訂,并據以從“圖像學”的視角來進一步認知漢代社會生活與歷史文化。
一、考古材料所見“盤鼓舞”圖像
欲梳理“盤鼓舞”圖像的基本要素,則先需厘清名稱上的混淆。鑒于目前研究中出現的名稱在術語專詞上的凌亂,我們依據朱青生《南陽漢畫畫面描述所用的術語與專詞》一文框定于古名、主要道具、主要動作并借用現代樂舞用語所厘定的標準,將此類舞蹈圖像的名稱術語歸為“盤鼓舞”“七盤舞”“踏盤舞”三種[8],當然它們在廣義的舞種上都屬于一個大類,僅在“踏器”的舞具上稍有區別而已。其實揆諸考古材料上的呈現,古人的圖像表述往往是簡約和象征性的,譬如“七盤舞”的名稱最常鑒于漢晉時期的詩賦,如《文選》所見張衡《七盤舞賦》“歷七盤而屣躡”,王粲《七釋》“七盤陳于廣庭”,以及陸機《日出東南隅行》“丹唇含九秋,妍跡陵七盤”和鮑照《數詩》“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鐘”等等,誠可謂淵源有自。但實際上可能只是以七盤的數量居多,而在圖像的表現上卻并不完全契合七盤的數目,有少于七盤的,也有多于七盤的,多以“七盤舞”為泛稱。“盤鼓舞”的名稱亦始于漢代,顧名思義即有盤亦有鼓,如張衡《西京賦》“振朱屣于盤樽,奮長袖之颯纚”與傅毅《舞賦》“眄般鼓則騰清眸”等即是明證。而對于“盤鼓舞”最為形象的描寫,則是三國時期卞蘭的《許昌宮賦》:“振華足以卻蹈,若將絕而復連。鼓震動而不亂,足相續而不并。婉轉鼓側,逶迤丹庭。與七盤之遞奏,覲輕捷之翾翾”。因此“盤鼓舞”實則是涵蓋了“七盤舞”更廣義的名目,也就是說“七盤舞”中并不排除會有鼓的舞具出現,當然通常是盤多而鼓少。而“踏盤舞”則應是“七盤舞”與以盤為主的“盤鼓舞”的簡稱或別名,雖然在某種場合可能只有盤而無鼓[9]。
至于另有一種相對于“踏盤”的“踏鼓”舞蹈,則多見于山東地區,如嘉祥武梁祠左石室第三石與前室第七石以及宋山小祠堂東壁畫像石上的舞者持桴踏鼓形式。那么“踏鼓舞”與“盤鼓舞”是否同種?尚需區別認識。因為“踏鼓”中的舞者常常手中執有鼓桴,從而與擊鼓融為一體,另外還多呈以手撫鼓做倒立雜技狀,這就與兼具足踏盤、鼓二要素的“盤鼓舞”在形式上有所區別[10],而若只是有鼓而無盤的“踏鼓”舞蹈形式,或許亦可視為“踏盤”的同類,僅不過是踏具單一而已。由此,在正名上似應以“盤鼓舞”與“七盤舞”和“踏盤舞”為同類而別名,“七盤舞”與“踏盤舞”則又應納入廣義的“盤鼓舞”中,至于“踏鼓舞”雖然也是以足踏器物為舞,所本之源大抵相同,演出場合亦固不可分,且就圖像表現與功能而言也甚為相似,則或可有所區別的視為“盤鼓舞”大類中的旁門。如此解析與釋名,雖屬一孔之見,卻比較易于對應圖像要素,一目了然且不致發生本質的混淆。基于此,則本文以“盤鼓舞”而統稱之。
隨著考古發現的推進需要重新建立一個盡可能完備的圖像庫。(表一)對29種漢代各類考古資料中的盤鼓舞圖像建立了一個初具規模的圖像資料庫,本文所關注的主要元素是盤與鼓的數量、排布方式、舞者性別、服飾特征以及舞蹈形式等,其次也擬延伸探究“盤鼓舞”所處的場域,亦即整體表演環境的歷史文化背景,以期勾勒出“盤鼓舞”在圖像學上的完整敘事。
二、考古材料所見“盤鼓舞”圖像解析
1.“盤鼓舞”圖像要素解析
依據表一中“圖像要素”一欄的描述,筆者對盤鼓數量、排布方式、舞者性別、舞者衣冠與舞蹈形式等圖像要素進行統計與解析。
盤鼓數量:盤與鼓略無定數,鼓有一鼓與二鼓,盤有一盤、二盤、三盤、四盤、五盤、六盤、七盤甚至十盤,而若拘泥于圖像的表述,則又不排除有盤而無鼓的情形。以此分析,可知盤鼓舞是以盤為主而以鼓為輔,亦可能是以鼓為節拍,而以盤為展示舞姿的主要載體。
排布方式:大多為無規則排布,或菱形,或前后數排,且通常為盤鼓相間,以便于騰挪跳躍、掌控節奏與舞姿多變。至于盤與鼓的數量多寡與排列變化,或可能取決于舞者技巧的高低與場地的制約等因素。另外,盤的放置通常為盤口向下,僅有山東歷城黃臺山漢墓盤鼓舞畫像石1例為盤口向上(圖一),恐在穩定性上不合常理。實際以常識而論,為獲得足夠的承托力,盤皆倒扣于地面,所見圖像絕大多數亦是如此。而盤口向上的案例,除此以外,也有一例是四川郫縣一號石棺的盤舞圖像也呈盤口向上,但這未必表示一定存在著“盤口向上”的盤鼓舞形式,是否有繪刻者“誤刻”的可能性,尚需存疑。
舞者性別:男性舞者僅見于“沂南石刻畫像”“成都羊子山一號漢代磚室墓石刻畫像”和“安徽定遠縣畫像石”三例,可見盤鼓舞者實以女性為主。

表一 考古材料中所見盤鼓舞圖像要素(畫像石、畫像磚、銅鏡、陶俑等)

續表一

圖一 山東歷城黃臺山漢墓畫像石盤鼓舞圖拓本

圖二 四川彭縣天平鄉百祥村東漢墓盤鼓舞畫像磚

圖三 山東東平后屯M1漢墓前堂南壁宴飲圖壁畫中的盤鼓舞

圖四 河南南陽新野后崗村漢墓盤鼓舞畫像磚

圖五 洛陽七里河漢墓盤鼓舞俑
舞者衣冠:女性舞者多梳高髻,另有雙髻或戴巾幗者,男性舞者則戴有介幘之冠。女性舞者以著廣口長袖居多,又以雙層袖為主(當是漢服中的雙層曲裾深衣,內層衣袖較長),另有少數為持巾而舞者,如“彭縣畫像磚”“麒麟崗畫像石”“安徽定遠縣畫像石”及“成都羊子山二號漢墓畫像磚”。女性的長袖與高髻,無疑是最與“盤鼓舞”妍跡颯纚的曼妙舞姿相和諧的衣冠特色。
舞蹈形式:既有女性或男性的獨舞,亦有女性或男性的雙人舞,還有男女結合的對舞及三人舞。可知盤鼓舞的形式是隨著盤鼓數量或所處場合而變的。至于真實的舞蹈技法,限于靜態的圖像刻繪而無法傳達,只能看到或一足踏盤,或一足踏鼓,或雙足踏鼓,或雙足踏盤等定格的寫照。

圖六 寧夏固原市北塬東漢墓出土搖錢樹盤鼓舞圖像
還有一點值得留意,如山東地區常見手腳倒立而以手撫鼓的“踏鼓舞”形式,而在陜北地域的漢畫像石中所呈現的盤鼓舞圖案(圖七),畫面中常有打斗如擊劍持弓等人物形象,盤鼓的數量也無規律,這是否是特定地區對于格套傳統得以長期維系而又不失旨趣的巧工變化?從而具有著特殊的組合方式與含義,抑或是無特殊意義的隨機組合?容再推究。也有學者認為“如果更深一層看,當時不少喪家對畫像的內容可能并沒有特定的主張,只求合乎身份,隨俗成禮。如此,富有經驗和名氣的石工畫匠就有了較大左右畫像安排和設計的機會”[41],或亦有其道理。
2.“盤鼓舞”圖像的表演場域解析
從表一所提示的盤鼓舞圖像要素以及追溯其原本所處的整體圖像環境,可以發現盤鼓舞通常是與世俗百戲、宴飲慶賀乃至祈望升仙的場景結合在一起的,以下試舉三例:

圖七 綏德四十里鋪漢畫像石門柱盤鼓舞圖

圖八 河南滎陽陶倉樓彩繪盤鼓舞圖
(1)河南滎陽河王水庫漢墓出土的彩繪陶倉樓[42],在倉樓正面繪有盤鼓舞圖像(圖八)。其整體圖像為上下兩欄,盤鼓舞位于下欄,上欄另有五人,從左至右為:兩位紅衣者,左側紅衣者躬身向右,戴進賢冠,手執一文書狀物;右側紅衣者身形較大,佩劍,戴高冠,似為通天冠,應為圖像中地位最高者;中間跪拜者著黑衣,戴進賢冠,持一文書狀物;右側二白衣者,一人束發露髻、手持食奩,一人戴白巾。按一般陶倉樓圖像,白巾者應持一糧袋,復原時蓋未細查,因糧袋與白衣俱為白色而混沌繪出[43]。結合一般陶倉樓彩繪圖像內容,此應為糧食豐收后的對賬場景。盤鼓舞在此陶倉樓上的出現,當理解為一種對豐收的慶賀。

圖九 山東諸城前涼臺漢墓畫像石盤鼓舞線描圖
(2)山東諸城前涼臺漢墓畫像石上的盤鼓舞圖像[44],整體圖像為樂舞百戲場景(圖九)。頗為奇特的是,此石上段另繪有一幅拷打用刑圖,受刑者正被削發、鉗頸,亦即鉗髡之罰。同一石上,上段刻繪慘烈的鉗髡場景,下段卻是盛大的樂舞百戲場面,對比鮮明,也因此頗使觀者困惑。諸城地區出土的漢墓畫像石多刻繪俗世場景,甚少見仙神圖像[45]。此墓“宴客圖”畫像石上有題銘曰:“漢故漢陽大守青州北海高密都郷安持里孫琮字威石之郭藏”,可見墓主乃是一位太守[46]。結合墓主身份,或可認為,此石上段反映的乃是太守孫琮的“工作場景”,展現的可能是為官政績[47],下段則是“娛樂場景”,展現的可能是為官期間太平安康的日常生活場面。值得一提的是,此圖上的盤鼓舞圖像亦“規規矩矩”地刻畫出七盤,與文獻相合,或可反映出此墓畫像石制作的精心。
(3)米脂官莊M2漢墓后室南壁橫楣畫像石上的盤鼓舞圖像,其整體圖像內容龐雜,且儼然是一幅仙境場景(圖一〇)。《米脂官莊畫像石墓》一書所謂“盤鼓舞圖右刻助興表演隊伍……上方五位舞伎……面向西王母跪地起舞……下方面朝西王母跽坐五位說唱、鼓吹樂手”的說法似乎不確[48],應為拜謁同觀樂舞表演的臣屬隊伍。上方所謂“舞伎”者,并不見舞姿,更類于朝見拜謁的姿態,中間四位或為所謂牛首、雞首人身像,此類形象元素多見于魯南、蘇北、陜北及晉西北畫像石。而牛首、雞首人身像所扮演的角色,觀其身姿形態,也應是表現朝見、拜謁西王母之意。故盤鼓舞在此場景中的出現,應與整體圖像融為一體,具有“娛仙”通神的功用。

圖一〇 米脂官莊M2墓室南壁橫楣畫像石盤鼓舞圖拓本
3.“盤鼓舞”圖像性質
考量“盤鼓舞”圖像發現其常與漢代百戲雜藝中的跳丸、角抵、疊案、擲劍等形成組合關系,這表明盤鼓舞在漢代樂舞中應是一種更注重技巧的特殊性舞蹈,同時也是一種更為民間娛樂場合所接受的大眾化、世俗化舞蹈,雖然這種舞蹈也有出現在表演宮廷樂舞的宏大莊重的高雅場域中,如前舉漢魏詩賦里涉及到宮廷的盤鼓舞描寫。又從前述表演場域來看,還有著如拜謁西王母場景一類的升仙意義以及日常生活中慶豐與娛樂的文化內涵與時代精神,當然也不排除有因地域不同而呈現的不同特征等等。因此亦可認為“漢代的‘盤鼓舞’不僅是宮廷、民間喜聞樂見的娛樂舞蹈,其本身亦蘊含著漢代的宗教信仰,在‘手舞足蹈’中體現了漢人羽化登天的思想和愿景,是漢代獨有的一種宗教舞蹈”[49]。至于有研究分析七盤舞之數或與漢代道教甚至北斗信仰的“斗極觀念”與“步罡踏斗”之說可能有所聯系[50],但以道教在東漢中晚期方始成其為宗教且有教團產生并影響于民間而推之,則這種觀點或許還值得商榷。總之,基于上述解析,對于“盤鼓舞”的性質的定義或許更普遍的是類同于朝野間流行的百戲的文化屬性與社會屬性。
三、“盤鼓舞”圖像意義的再認識
以圖證史的“圖像學”研究近年來在學界漸成風氣,其本就是“左圖右史”的古代學術傳統,也契合近代以來注重新材料的“二重證據法”的研究模式,惟其不僅可以擴張史料來源,更能憑藉生動具體而獨具感染力的形象來彌補文字難以傳遞的信息。亦即對于圖像的研討,可以從關注分析圖像所呈現的自然與常規意義,進而去解讀并透見其所蘊含的時代與文化的本質。而基于對諸多品類考古材料所見“盤鼓舞”圖像的梳理與解析,同樣可以挖掘歷史本身的敘事以盡量貼近歷史的真相,從而為揭示漢代社會生活與文化精神以及民間信仰等提供富有學術意義的根據。
“盤鼓舞”圖像無疑具有著再現漢代生活情狀的寫實性,從其通常出現在享受生活安泰的歡樂和迎接豐收富足的喜悅的場景層面來看,正能揭示人們對社會安定與生活富足的祈望與希冀。“盤鼓舞”圖像的載體包羅了畫像石(磚)、壁畫、陶俑、銅鏡、搖錢樹等諸多品類,大多與墓葬文化相關聯,可憑此探究當時人的“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的生死喪葬觀念,亦即對生命長久的懷戀和對往生幸福的寄托。從思想文化的精神傾向來看,與“盤鼓舞”圖像相伴生的西王母與東王公形象也在多種考古材料中不乏出現,這又為研究寄托著長樂未央與長生無極心愿的漢代民間信仰風尚提供了可靠信息。而這種大量呈現于墓葬材料中的“盤鼓舞”之類的歡樂舞蹈場景,實際上就是彼時特定文化背景下人們思想意識形態的真實反映,其不僅僅具有揭示現實生活情景的世俗功用,同時也常常寓意著一種類似于宗教意義上的祈望升于仙界的神化內涵[51]。
[1]a.王仲舒.沂南石刻畫像中的七盤舞[J].考古通訊,1955(2).b.馮漢驥.論盤舞[J].文物,1957(8).
[2]閆艷.釋“七盤舞”[C]//漢語史研究集刊(15).成都:巴蜀書社,2012.
[3]李淼.漢畫盤鼓舞解析[J].中州學刊,2017(8).
[4]潘岷.河南博物院藏東漢盤鼓舞畫像磚考略[J].江漢考古,2017(6).
[5]杜樂.漢代“盤鼓舞”初探[J].大理大學學報,2019(6).
[6]張晗.動靜之美—南陽畫像石“盤鼓舞”表現手法研究[D].北京:中國美術學院國畫系,2014.
[7]韓博雅.基于文獻與圖像的盤鼓舞藝術風格研究[D].青島:青島大學音樂學院,2017.
[8]朱青生.南陽漢畫畫面描述所用的術語與專詞[C]//古代墓葬美術研究(第三輯),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15:79.
[9]蕭亢達.漢代樂舞百戲藝術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207-208.
[10] 馮漢驥.論盤舞[J].文物,1957(8):9.馮漢驥稱踏鼓與盤鼓舞并非一類,其文注釋六云:“武氏祠左石室第二石上所刻者,乃系‘踏鼓’之戲,不可與盤舞相混。”又,成都華通博物館藏東漢踏鼓舞俑亦可為證。
[11]同[10]:9-12.現藏于四川博物館。
[12] 山東省沂南漢墓博物館.山東沂南漢墓畫像石[M].杭州:西泠印社,2003:66,42-43.
[13] 岳鳳霞,劉興珍.浙江海寧長安鎮畫像石[J].文物,1984(3):50.
[14] 趙成甫.南陽漢代畫像磚[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圖61、96。現藏于河南博物院。
[15] 王建中,趙成甫,魏仁華.中國畫像石全集(第6卷)[M].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0:165.
[16] 湯池.中國畫像石全集(第5卷)[M].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101.
[17] 榆林市文物保護研究所.米脂官莊畫像石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141.
[18] 焦德森.中國畫像石全集(第3卷)[M].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141.
[19] 蔣英矩.中國畫像石全集(第1卷)[M].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91.
[20] 陳長山.南陽麒麟崗漢畫像石墓[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171.
[21]同[16]:173.
[22] 高文.中國畫像石全集(第7卷)[M].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0:96-97.
[23]同[15]:27.
[24]同[15]:98.
[25]同[22]:52-53.
[26]《中國音樂文物大系·總編輯部》.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四川卷[M].鄭州:大象出版社,1996:167.
[27]楊桂榮.東漢“七盤舞”雜技畫像鏡[N].中國文物報,1988-9-23(3).
[28] 金秋.中國傳統文化與舞蹈[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102.
[29]梅原末治.紹興古鏡聚英[M].東京:桑名文星堂,1939:圖13.
[30] 劉東升.中國音樂史圖鑒(修訂版)[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8:46.
[31] 姜生.漢帝國的遺產:漢鬼考[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414.
[32]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滎陽河王水庫漢墓[J].文物,1960(5):60-68.
[33]同[17]:87.
[34] 信立祥.中國畫像石全集(第4卷)[M].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0:160.
[35]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東平后屯漢代壁畫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152.現藏于山東博物館.
[36]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研究所,靖邊縣文物管理辦公室.陜西靖邊東漢壁畫墓[J].文物,2009(2):32-43.
[37]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靖邊縣文物管理辦.陜西靖邊縣楊橋畔梁樹壕東漢壁畫墓發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2017(1):3-27.
[38] 孔祥星.中國銅鏡圖典[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437.其中有介紹文字稱:“內區四枚乳釘紋將紋飾分為四組:一組為一馬駕車……一組二人甩長袖起舞。地下似有盤,當為盤舞內容。主紋外圈帶銘文:尚方作竟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直徑19厘米,河南淇縣出土。”唯諦審畫面,應為盤鼓舞,非盤舞。此鏡今藏河南博物院.
[39]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鑒耀齊魯: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出土銅鏡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330,422.
[40]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市原州區文物管理所.寧夏固原市北塬東漢墓[J].考古,2008(12):23-38.
[41] 邢義田.畫為心聲—畫像石、畫像磚與壁畫[M].北京:中華書局,2011:55-56.
[42] 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隊.河南滎陽河王水庫漢墓[J].文物,1960(5):60-68.
[43] 賈峨.滎陽漢墓出土的彩繪陶樓[J].文物參考資料,1958(10):16-17.同出的另一座陶倉樓的圖像亦有大致相似的圖像內容,位于同一位置者則清晰可見持一糧袋.
[44]任日新.山東諸城漢墓畫像石[J].文物,1981(10):14-21.
[45] 譬如此墓中出土的十三塊畫像石中,還有的刻畫著庖廚圖、謁見圖、宴飲圖、莊園庭院圖等,皆為世俗場景的描繪。
[46] 王恩田.諸城涼臺孫琮畫像石墓考[J].文物,1985(3):93-96.
[47] 同[46].王恩田認為鉗髡圖“所反映的是孫琮生前所在漢陽郡內處置羌族戰俘的情景”,可備一說。
[48] 榆林市文物保護研究所.米脂官莊畫像石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85.
[49]同[5].
[50] 張素琴.“斗極觀念”影響下的漢代盤鼓舞與道教“步罡踏斗”淵源考[J].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12(3):37-41.
[51]同[31]:412-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