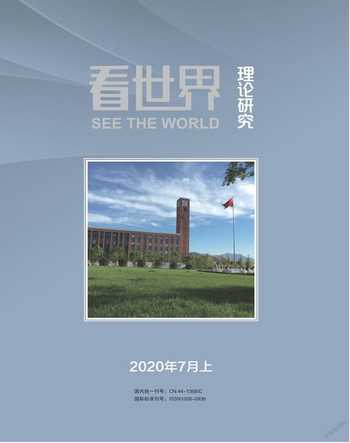維柯詩性智慧的形而上學基礎
尚啟睿
摘要:詩性智慧是維柯《新科學》中的重要思想。詩性智慧思想的形而上學基礎要追溯到維柯早在《論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中確立起來的“真理與創造相同一”的原則。本文試圖分析,維柯如何通過“真理與創造同一”原則,完成想象力的真理性確立和對屬的改造,以奠定作為詩性智慧產生前提的“想象的類概念”的理論基礎。
關鍵詞:維柯;詩性智慧;真理與造物同一;想象的類概念
詩性智慧是維柯《新科學》中的重要思想。維柯將整個人類文明都放置在了詩性智慧之上。通過詩性智慧,維柯確立了感覺與想象,以及詩與藝術的自主性和真理性。以至于在思想史上通常被作為歷史哲學家看待的維柯卻被克羅齊評價為“美學科學的真正建立者”。維柯詩性智慧的邏輯前提則來源于其在《論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以下簡稱為《古代智慧》)中就確立的“真理與創造相同一”的形而上學原則。“真理與創造同一”原則通過兩個方面構成詩性智慧的重要支撐。人類要通過感官和想象力建立起先于哲學和科學的“詩性玄學”,也就要首先創造一種不同于抽象共相的“想象的類概念”即詩性的形象。因此,一方面想象力必須首先獲得其可靠性。根據“真理與創造相同一”的原則,人類的感覺能力與想象力被維柯確立為創造性的能力從而具有其確定性。感性能力不再被看作混亂的,而是通過創造其對象從而獲得真理性。另一方面,事物的屬應當作為事物的形式而被理解。這一觀點不僅是維柯對于“真理與創造同一”原則的語源學佐證,同時也是該原則的重要推論。通過對于拉丁語中屬和形式同義的語源學證明,維柯將屬歸結為在完美方面無限的形式而非普遍共相,使得屬作為類概念而具有了構造和創造的性質,而非流于共相的抽象和空泛。“真理與創造相同一”原則通過這兩個方面,為人類知識所由誕生的“想象的類概念”的真理性提供了基礎。
一、“真理與創造相同一”原則
十七和十八世紀的歐洲處于一個由笛卡爾開啟的理性主義和邏輯主義的時代。但維柯卻在笛卡爾的理性主義原則中看到了虛無主義的種子,因此他稱他所處的時代“是被分析的方法,被一個公開宣稱窒息源于身體的靈魂的所有官能特別是窒息今天那個被痛斥為萬惡之源的假想官能弄得思想纖弱的時代”;是“凍僵美妙詩篇所有寬容雅度的智慧時代”[1]。于是在《新科學》中維柯找到了詩性智慧以對抗笛卡爾所確信的理性的確定性。笛卡爾以“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 sum)作為其形而上學的第一真理,同時也是一切知識之最堅實的基礎。笛卡爾認為,人們可以懷疑他是否感知,是否活著,是否有形體,世界是否存在,最終懷疑自身是否真的存在,但人們唯一不能懷疑的便是他在思維,因而也不得不確實地得出結論,即他存在。維柯則站在笛卡爾的對立面,公開反對笛卡爾的形而上學第一真理,從而反對笛卡爾所使用的分析方法。維柯向經院哲學借來了“真理與創造相互轉化”(verum et factum convertuntur)的表達,并將其轉化為“真理與創造相同一”(verum idem ac factum)的觀點,有時維柯也將其表達為“真實就是創造本身”(Verum esse ipsum factum),以此作為同時對抗笛卡爾主義者的武器。維柯認為,笛卡爾的錯誤就在于沒有認識到,除了“真實之標準就是做成它本身”[2]外,并無其他通向真實的道路。對原因的把握包括了一切屬和一切形式,因而這種對原因的把握就是第一真實,而這只能是上帝。上帝在認識中創造真實,“在神的知識中,所謂神認識真實,就是說他從永恒中內在地(ad intra)產生真實,在時間中外在地(ad extra)創造真實”[2]。因此上帝的認識與上帝對真實的創造相同一。上帝采集事物的所有元素,同時他自身就表現了事物的一切元素,因而神能夠通曉(intelligentia)一切事物,而人只能思維(cogitatio)事物,因為人的心靈是有界限的,它只能匯集事物最外在(extrema)的元素。“打個比方來說,神的真實是事物的立體像,正如塑像;人的真實則是素描或平面像,猶如繪畫”[2]。因此對于人來說最確定的知識,只能是在運作上肖似于神的知識的知識,即我們只能夠知曉我們自身創造出來的東西。因此人能夠認識和把握的真實是這樣的,“即真實之元素由我們自己、并為我們自己而創造,且包含在我們之內,然后我們根據假設,將其延伸至無限;并且在我們結合真實之元素的同時,我們就創造了我們在結合的過程中知曉的真實;通過上述這一切,我們也就把握了我們借以創造真實的屬或形式”[2]。在《古代智慧》中維柯認為,根據“真理與創造同一”的原則,這種知識應當是幾何學和算術的知識。而在《新科學》中維柯更進一步,看到了人類真正創造之物是人類自己的歷史。因為歷史實踐的世界較之抽象的形式世界更加確實。人類歷史處理現實事務,數學則處理抽象事物,而一切抽象都后于在歷史活動中誕生的詩性形象而產生。
二、想象作為創造的能力
在維柯看來,詩性智慧是人類文明的源泉,是人類的一切“制度”得以產生的根源。詩性的智慧是一種根源于身體的強旺感覺力和生動想象力的智慧,是最原始的,而知性智慧包括哲學和科學的智慧是派生出來的。從這種智慧中,既產生出了對世界的認識,又產生出了詩和藝術的創造。人類起初對世界的認識就通過這種根源于感覺力和想象力的智慧,因為人類要認識外部世界就不得不首先通過感官同外部世界接觸。“人類本性,就其和動物本性相似來說,具有這樣一種特性:各種感官是他認識事物的唯一渠道。”[3]維柯還引用了亞里士多德《論靈魂》中的論斷來佐證自己的觀點。亞里士多德稱“凡是不先進入感官的就不能進入理智”[3],因而由詩性智慧誕生出來的知識就要先于哲學和科學的知識。維柯認為,最初的人仿佛就是人類的兒童。兒童的記憶力最強,所以想象力生動。拉丁人把memoria(記憶)稱作收集通過感覺而來的各種知覺作為營養儲備營養儲備的能力。回憶(reminiscentia)就是提取這些知覺。它同時也意味著一種形成意象的能力,希臘人稱為phantasia,也就是想象力。想象力只能構想我們通過感覺對其有知覺,并且記憶下來的事情,“沒有一位畫家曾經畫出過自然沒有產生的植物或生物種類,就算是那些半鷹半馬的有翅獸和半人半馬的怪物,實際上也只是自然事物的荒誕混合”[2]。“因此,在希臘人的神話傳說中,作為想象力德性代表的繆斯女神就相傳為記憶女神的女兒”[2]。由于想象力的強大和抽象能力的薄弱,原始人類還不懂得“共相”或者可用理智理解的“類概念”,因此他們就有必要去創造“想象的類概念”。例如,兒童凡碰到與他們最早認識到的一批男人、女人或事物類似的男人、女人或事物,就會依最早的印象來認識他們,依最早的名稱來稱呼他們。他們的辦法就是“制造出某些范例或理想的畫像,于是把同類中一切和這些范例相似的個別具體人物都歸納到這些范例上去。”這種“想象的類概念”(imaginative class concepts)也就是詩性的形象,是創造性的想象。那么想象如何能夠獲得其可靠性呢?
維柯指出,在拉丁文中能力(facultas)一次如同faculitas,從這個詞演變出facilitas(容易,靈巧,熟練),也就是一種純熟的(expedita)或者成備的(exprompta)創造才能。因此,維柯否定了經院哲學家們將顏色、味道、聲音和觸覺等等都認作處于物體之中的看法。他認為“假如各種感覺都是能力的話,那么我們就是在看中創造創造事物的顏色,在嘗中創造事物的味道,在聽中創造事物的聲音,在觸中創造事物的冷熱”[2]。同樣,維柯稱“想象力(phantasia)是一種確實之極的能力,因為我們在運用想象力時,就構造了事物的意象(imago)”。如此,想象力與人的感性能力一同,在真理與創造的原則下,與理性主義劃分了界限。人的感性認識能力與想象力不再是混亂的和低級的能力,人通過這些能力成為自己作品的上帝,從而“做出了真理”[2]。
三、屬是在完美方面無限的形式
人類通過詩性智慧所首先形成的詩性的形象如何才能獲得其真實性?從想象中產生的形象如何能夠表現事物的本性,成為事物的屬或類概念?這就要求必須將屬理解為具有創造性的形式。事物通過特有的形式而被創造,因而該事物的本性就要通過創造該事物的形式來考察。通過詞源的考證,維柯指出,拉丁人談論genus(屬)時意指形式(forma),而且genus在詞源上確有生成、產生的意思。因此這一考證就符合維柯論證“真理與創造相同一”原則的訴求。并且維柯認為,如果真實與創造是同一的,那么事物的屬就絕不是經院哲學家所講的共相,而只能是形式。同時并非是在外延(amplitudine)方面無限的形式,而是在完美方面無限的形式。將屬理解為形式而不是共相的意義在于,形式作用于構造和創造,而共相則只能來源于比較和反思的抽象。“那些交代了事物所由生成的屬或方式的藝術,與那些并不交待事物所由生成的屬或方式的推測性藝術相比,要更確實地導向其自身所設的目標。前者例如繪畫、雕塑、造型、建筑等,后者例如修辭術、政治、醫學等。前者之所以交待了事物生成的屬或方式,是因為這些藝術遵循已經包含在人的心靈之內的事物原型(prototypos);后者之所以不能交待,是因為人在自身之內并不包含著所要推測的事物的任何形式”[2]。通過心中已有的形式進行創造比起無形式的推測,要更明確的導向目標,因而這樣的知識就及其確定。知識和藝術如果建立在共相的種屬觀念的基礎上,就會變得宏觀普泛且無用,因為它只在事物中抽出普遍的共相,而不創造出新的東西。維柯舉了法學和醫學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在法學中,人們并不尊重這樣的人,即他僅僅通過博聞強記,從而掌握了實在法(ius theticum)或一般法規總匯,而是尊重那些人,他們憑借著敏銳的判斷,能在諸多案件中看到各種因素的最終情況(peristases)或細節(circumstantias),因為那些情況適合援用公平原則或者例外原則,通過這兩種原則來規避一般法律”[2];“在醫學中,誰如果徑直依據醫學理論而行醫,那么他就會更關系避免破壞其體系,而不是治愈病人。”[2]而在由摹仿構成的例如繪畫、雕刻、詩歌等各門藝術中,即使原型(archetypum)取材于自然,優秀的藝術家們也能用“非同尋常的、新穎而令人驚嘆的細節將其烘托出來;或者即使這個原型已為其他藝術家所表現,它們也要用更好的獨有的細節與之相區別,將其打造成自家的東西”[2]。這就是因為藝術家在創作時,心中已經知曉其作品所由生成的形式或方式。而如果藝術創造所遵循的原則是由事物抽象而來的普遍原則或規律,則或者創造失去其誕生新事物的意味,或者創造活動與美的原則相分離。
在拉丁語中,智慧(sapientia)一詞指恰當適度的能力(solertia decori)。而solertia的意思是聰睿、準確、靈敏等能力。也就是要使言行符合具體情況,而不是遵從普遍標準。因此智者才能憑借這種智慧“在任何新事物和新情境中都能言行自如,并且無論如何都再恰當不過”[2]。而在普遍的屬(共相)中卻不能預見到任何新穎或出人意料的事物。certum(確定)這個詞有兩個意義,一個是明確的、無疑的,另一個是特定的(peculiare),而這與共通(communi)是相對的。這可以說明,“特定的就是確定的,而共通的則是含混的”。將屬理解為共相會導致多義語(aequirocis)的產生,也就是同一個詞意指多個事物,因此就造成含混。例如一個男孩被吩咐去叫提蒂烏斯(Titium)但未被加以區分,而提蒂烏斯有兩個。所以他自然就要確定要叫這兩個提蒂烏斯中的哪一個。一切哲學、醫學和法學中的派別之爭,在維柯看來都是由于將屬理解為共相所引起的。因為它帶來一語多義的普遍名稱,致使這些用語都是及其寬泛的。
維柯要打破唯理性主義為人類帶來的價值虛無,就要說明人類的認識遵循從感性認識發展到理性認識的次序,并將感性認識確立為一種切實可靠的認識。原始人類通過想象力創造出的詩性形象具有普遍性,但又并非概念的普遍性。將屬理解為形式也就為說明作為一切詩性智慧之基礎的“想象的類概念”即詩性形象的可能性打開了道路。
四、“想象的類概念”
通過“真理與創造相同一”原則,想象力被維柯看作為一種創造性能力,因而確立了想象對于人類認識的確實性。同時,通過該原則,事物的屬自然而然地應當被理解為事物在被創造的過程中所依據的形式。由此,人類在產生反思和推理的能力之前,才能夠運用想象力創造出具有普遍性的感性形象。“想象的類概念”即是把不同的人物、事跡或事物總括在一個相當于一般概念的具體形象中。也就是通過想象的創造,將一個就其自身而言是特殊的形象,通過表現和代表其他同類的事物,而成為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形象。并且“人類在認識不到產生事物的自然原因,而且也不能拿同類事物進行類比來說明這些原因時,人們就把自己的本性移加到那些事物上去,例如俗話說:磁石愛鐵”[3]。因此人類在無知的階段,就把自己當作萬物的尺度。以自身的形象為標準,通過理想化的方式創造出詩性的形象。從一切民族都創造出了類似“天帝約夫”(即關于自然力量的人物形象,多被想象為拋擲電光弩箭)的天神形象就能夠說明這一點。原始的人類將天空的雷電看作像自己一樣的龐大巨人的咆哮和暴怒。詩的形象就是人們按照自己的觀念創造出的理想的、完美的形式,借以表達其他同類事物。在抽象思想隨著推理力的發展出現以前,原始人們就以詩的方式思考。
通過“真理與創造相同一”原則,維柯找到了想象力與詩性形象的真理性,從而確立了詩性智慧的地位。雖然維柯無論在《古代智慧》還是《新科學》中都并未明確表現出其建立美學學科的自覺性,但通過“真理與創造”原則,維柯賦予了感性能力與藝術以不同于鮑姆嘉通以來的“感性學”美學的獨立性地位。因此維柯這位“思想史上的失蹤者”的思想中,蘊藏著深厚的美學價值。
參考文獻:
[1][意]克羅齊.美學的歷史[M].王天清,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2][意]維柯.論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從拉丁語源發掘而來[M].張小勇,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3][意]維柯.新科學[M].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
[4]武茜佳.《新科學》的美學反思[J].品味經典.2019(06):1-7.
[5]席格.論維柯思想的美學史價值[J].中南大學學報.2015(4):13-19.
[6]朱立元.重估維柯思想的美學內涵[J].文藝理論研究.2012(4):86-93.
[7]李靜.真理與造物同一——維柯克服虛無主義的嘗試[J].哲學動態.2019(12):77-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