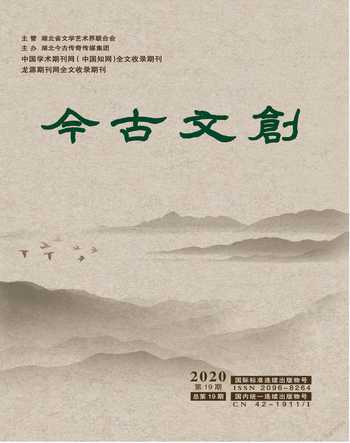論蘇童《妻妾成群》的悲劇意識
劉珂彤
【摘要】 蘇童,當代作家。本文從愛情的悲劇矛盾、人性的悲劇色彩、意象的悲劇意蘊三個標題來探究蘇童《妻妾成群》的悲劇意識。通過對蘇童《妻妾成群》悲劇意識的分析,蘊含著對封建禮教的批判、對人性泯滅的哀嘆。
【關鍵詞】 蘇童;《妻妾成群》;悲劇意識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0)19-0025-02
蘇童,原名童忠貴,中國當代文學先鋒代表作家之一。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江蘇分會駐會專業作家、江蘇省作協副主席。代表作有《紅粉》《妻妾成群》和《碧奴》等。蘇童發表了《1934年的逃亡》而一舉成名,同洪峰、格非等一起成為先鋒小說的領軍人物之一。小說《妻妾成群》講述了陳家大院里的四房姨太太在封建禮教的壓迫下互相殘殺,身心俱傷的故事,揭示了封建制度對人性的摧殘。
一、愛情的悲劇矛盾
愛情是文人墨客書寫的一個重要主題,小說《妻妾成群》通過對大院里不同角色的愛情故事的講述,展現了在封建禮教的壓迫下,不同的人生所經歷的不同的愛情悲劇,而這些愛情也引導了他們的命運。
三太太梅珊是一個灑脫到有些離經叛道的女人。但是梅珊的兒子飛瀾并沒有在個性上遺傳梅珊太多,飛瀾身上現出更多的是和哥哥飛浦一樣的懦弱和冷漠。當父親迎娶了新妻子時,飛瀾是緘默的;當母親因為偷情被抓去死人井時,飛瀾是冷漠的。一個童真的形象被賦予了冷漠的性格,這與人們思維定式中的孩子形象是相悖的,這種扭曲體現了大院冷漠的氛圍,襯托了單純的頌蓮在大院中舉步維艱的境地。“蘇童在剝離人性的同時,生命在非理性的人性陰暗面中凸顯了個體價值的狂歡,肯定了個體生命的價值。”飛瀾是受過初級西方新式教育的孩子,他與頌蓮的不同就是他還沒有被封建禮教的腐朽思想所荼毒。飛瀾代表著一股嶄新的西方意識正在成長,而這股力量在與封建禮教思想對抗的同時,在原生家庭的無愛環境下,滋生出了一種冷暴力,而他沉默的反抗最終也只能變成為封建禮教發展推波助瀾的毒手。
頌蓮的長簫是影響她情感變化的重要意象,簫的存在與否也是頌蓮是否真正融入大院的標志。當簫在頌蓮身邊時,她對飛浦產生了感情。通過賞菊,頌蓮與飛浦之間建立了一種無言的默契;簫的消失,是陳佐遷在陳府中權力的體現。頌蓮與飛浦的感情糾葛表現了女性在封建思想和本性欲望之間的拉扯,在封建思想的壓迫下,成年男女的本性欲望在野蠻生長,生成一種近乎瘋狂的力量,但就是這樣瘋狂的力量,卻依舊被殘漏的封建禮教所壓制。
陳佐遷看似只是一個配角,但實際上他掌握著真正的生殺大權。在陳佐遷的眼中女人都只是廉價的生育機器,他遷經常會提到大院里的一切都是老祖宗留下的規矩。這樣的規矩逼著大院的女人們互相廝殺,逼著她們爭寵,逼著她們臣服在絕對權力之下。可悲的是,沒有人有異議,所有人都漠然地生活著。這種規則中的愛情不止束縛著大院里的女人們,也反噬了享受這種規則帶來的權利的陳佐遷。陳佐遷在掌握著院女人命運的同時,也為女人們的鉤心斗角感到頭疼不已,他意圖通過身體上的放縱回避這種精神上的折磨,但是就是身體上的放縱,帶來了更深層的精神上的折磨,這種輪回式的宿命悲劇正是纏繞著陳家的最沉重的枷鎖。
二、人性的悲劇色彩
作者塑造了封建牢籠里四個性格截然不同、命運卻極為相似的女人,她們正是社會上不同的女性的縮影。姨太太們身上所體現的人性的悲劇正是封建制度的壓迫下人性被迫扭曲的悲劇現實。
毓如作為原配太太,終日被養在院子里,失去了姿色,失去了丈夫的寵愛,也失去了往日的權勢。從踏入陳家大院開始,頌蓮的命運就已經開始改寫為悲劇。“這種家庭意外變故的‘偶然性’打開了頌蓮悲劇的大門,而其自身內在的傳統本能,使得其成為徹底的‘必然性’悲劇。”對于擁有新思想的頌蓮來說,她是主動踏入舊社會的牢籠中的,雖然這種主動是迫于現實,但這種自我毀滅令已經深受封建禮教殘害的毓如扼腕嘆息。毓如在陳家的地位十分尷尬,陳佐遷厭棄她,兒子也認為她是一個固執呆板的女人,她是一個被封建禮教侵蝕迫害至遍體鱗傷的封建女性,她信奉著封建禮教規定的男尊女卑和三從四德,她人性的悲劇體現在一種墨守成規的依附性,她的人生都是依附于陳佐遷而展開的。毓如人性中的悲哀是一種無欲無求帶來的虛無感和面對頌蓮產生的怒其不爭的無力感,而她的存在感就在這種矛盾中被抹殺了。
卓云和梅珊、頌蓮的命運都被陳佐遷的一喜一怒牽動著,在男權的壓制下,她們只能將不滿和郁悶發泄在彼此身上。“痛苦的四個女人,在痛苦中一齊拴在一個男人的脖子上,像四顆枯萎的紫藤在稀薄的空氣中互相絞殺,為了爭奪她們的泥土和空氣”。這種爭寵意識并不只體現在陳家的女人身上,這是整個封建社會中女性的共識,正是這種共識性,增添了太太們作為被封建制度壓迫的女性典型的悲劇性。從頌蓮被迫加入女人們的戰爭開始,女學生頌蓮就死了,封建禮教把一個單純的女學生變成了滿腹心計的怨婦,悲哀的是,工于心計竟成了頌蓮能在大院中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徑。“生存在陰郁、窒息的環境中為了自我生命的自由, 他們進行了無數次逃亡與找尋的嘗試。”梅珊不能保證牢牢拴住陳佐遷的心,所以她勾搭了醫生,嘗試通過與醫生偷情逃離封建禮教的約束。無論是作為傳統封建牢籠的陳家,還是偽善惡毒的卓云都容不下梅珊放蕩自由的靈魂,所以梅珊的死既是偶然被卓云捉奸所致,也是自由靈魂無法逃脫封建禮教束縛的必然結局。“‘新女性’頌蓮在覺察到丫鬟雁兒給自己造成潛在威脅時,根本絲毫沒有運用其本該有的新氣息來哀憐女人終究是傳統禮教的犧牲品”頌蓮在懲罰雁兒吃下草紙的時候,已經完全是以陳家四太太的身份在懲罰自己的丫鬟了。頌蓮已經被封建禮教改造成了一個以“夫權”為中心生活的封建女性。包括頌蓮在內的所有太太們,都已經被封建禮教摧殘得無法對女性同類的悲慘遭遇產生共情了。如果說頌蓮是逼死雁兒的元兇,那么其他太太們的默認就是無形之中推動了雁兒的死亡。在男權的壓制下,女性們互相爭斗,最后三太太死,四太太瘋,大太太和二太太又迎來了年輕貌美的五太太,沒有人是贏家。
三、意象的悲劇意蘊
意象在小說中有渲染氣氛,表達人物性格,喻示劇情走向的作用。出現的意象都體現了死亡意識與悲劇性,它們對于情節發展,人物性格變化起到了導向甚至決定性的作用。
小說中的菊花意象主要出現在頌蓮與飛浦的交往中。因為菊花代表的是頌蓮對愛情的向往,人性中的純潔。當頌蓮遇見飛浦的時候,她對愛情的向往是強烈的,她沉溺于自己營造的一種曖昧的假象;當頌蓮安心地做陳佐遷的太太時,她為陳佐遷顧忌其他太太是否吃醋而生氣,“頌蓮的內心是矛盾的,一面想要追求人格的獨立,在陳佐千面前表現出與眾不同的品格,卻又發現陳佐千是這大院里唯一能做主的,沒有什么能夠改變他。”一個受到新思想教育的女學生徹底淪為封建禮教的祭品,頌蓮人性中那些被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領導的奴性被激發,她不再為爭寵而努力,她變成了像所有被封建禮教改造過的女性一樣的沉默和順從。菊花象征著封建社會女性群體的反抗意識,在數千年封建禮教的壓迫下,女性為了人性解放,人權獨立進行了無數次的嘗試。但每一次從怒放到凋零的過程都是一次失敗的嘗試,象征著女性最終只能被封建勢力吞噬的悲慘命運。美好事物終將毀滅的悲戚,推動著頌蓮最終走向瘋癲的深淵。
紫藤花這一意象其實代表的是頌蓮的潛意識。如果說頌蓮就是一朵紫藤花的話,那么嫁人之前,父親就是粗壯的藤架,藤架倒后,花就飄零著,直到有一口深井在接應她。紫藤以為找到了可靠的歸宿,但其實深井才是吃人不吐骨頭的地方。頌蓮絕不是被迫出嫁,她甚至主動要求找個好人家,說明她雖受新思想的教育,但骨子里還是傳統保守的,所以她注定要墮落。頌蓮嫁入陳家不僅是一種自甘墮落,另一方面這代表著西方意識向封建思想妥協。面對身世飄零的頌蓮,沒有人表現出對弱者患難的共情,這種對于死亡、毀滅等現實的漠然體現了封建社會對于女性人性的摧殘。梅珊和頌蓮是完全不一樣的人,梅珊毫不掩飾自己的叛逆,不受寵就找別的主去依靠。頌蓮沒有別的主可以依靠,她只身來到陳家,像漂泊的紫藤,遇見了枯槁的井也覺得溫暖。梅珊與頌蓮的不同在于,梅珊具有堅定的自我意識,她不拘泥于順從的生活;但頌蓮表面上是具有清高品格的“菊”,實際上她是隨風飄零的“紫藤”,在陳家的斗爭中逐漸喪失了自己矜貴的性格。
井是死亡的象征,是整個陳氏家族中的女人命運輪回的象征。文本中描述的死亡的宿命感來源于井。井的存在說明,歷代陳氏家族中出現過像梅珊一樣,將自我凌駕于一切之上、敢于反抗男權至上的女性。井不僅是封建禮教對敢于反抗的女性的強硬束縛,井的存在更是一種對美的扼殺。小說中鮮活的、積極的元素都毀滅于井,反倒是陰狠的卓云和冷漠的毓如作壁上觀,逃避了被井毀滅的命運。井是整部小說中最陰暗,最壓抑的元素,它承載了一個時代的女性們的恐懼。作者在小說中對傳統死亡意識顛覆的同時,賦予死亡以新的內涵,即殉葬。梅珊的死和頌蓮的瘋,是女性在新思想與舊文化的斗爭中做出的有意義的犧牲。
四、結語
綜上所述,論文從陳家大院四房太太的愛情婚姻經歷出發,分析了愛情矛盾、人性的悲劇及悲劇的意義和價值,挖掘了女人的互相殘殺,制度的摧殘及死亡的解脫,讓悲劇有了深度。結合先鋒小說中的死亡意識,蘇童創作中的悲劇敘述等概念挖掘了小說《妻妾成群》中所體現的悲劇意識。蘇童通過講述人物的悲劇,講述男性和女性的人格扭曲、道德淪喪,他們只能通過互相殘殺、互相迫害的方式尋求靈魂解脫,用血與淚凝聚成了一曲悲歌。
參考文獻:
[1]周夕楸.論蘇童小說中的創傷書寫[D].成都:四川師范大學,2019:3.
[2]劉虎.淺析蘇童《妻妾成群》中的“人性(女性+男性)”悲劇[J].名作欣賞,2018,(32):109.
[3]龍夢.濁世里的菊——淺談蘇童《妻妾成群》里的頌蓮悲劇[J].藝術科技,2017,30(03):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