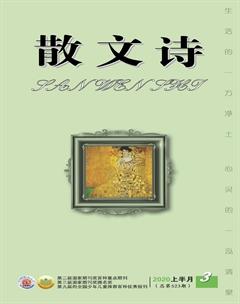世界散文詩:在思想的隱喻里展開或釋放(八)
2020-09-02 06:34:23黃恩鵬
散文詩
2020年3期
黃恩鵬
讓我們再看尼加拉瓜詩人魯文·達里奧的《腦袋》:
整個晚上,耳朵里裝滿奧迪安劇院的音樂、阿斯托爾廣場的演說、馬路轉彎處的汽車噪音和玉米餅販子凄涼的叫賣聲,做夢者面對著書桌上一疊紙,等待他寫上長短句和十四行送給寵愛的女人。
什么長短句!什么十四行!抒情詩人的腦袋里是色彩和聲音的大雜燴。他的頭顱里回響著獨眼巨人的敲擊、洪亮的定音鼓頌歌、雄壯的銅號、清脆的笑聲、小鳥的啁啾、拍翅聲和親吻的爆響,各種瘋狂的復雜節奏。種種色彩擠挨著,像種在一個盆子里的許多不同的花,也像畫家調色板上斑駁的油彩……
這是一章有著明顯喻象的文本。“做夢者”與“抒情詩人”是同一個人。他在一個晚上想寫一首“長短句”或“十四行”給“寵愛的人”,可是他的腦袋里無法除去眾多聲音的攪擾。那些聲音龐雜擁擠,絡繹不絕,惑亂了心緒。詩人以“聲音”的混亂,來說明這是一個不適合寫純情詩的時代。一些純真于人類情感的感受,早已經被日益躁烈的喧囂擊傷或毀滅。作為一個內心有美好愿望的人,是無法獲得寧靜平和的自由人生的。或者說,現代社會無法容許一個人有著美好的憧想了。它擄奪了人最本質的生存理想。腦袋,便不再是自己的腦袋,而是被社會左右了的復雜的腦袋。人的腦袋成了被社會“戲劇場”或“舞臺場”牽引的物件。
魯文,達里奧讓聽著的、發出聲音的同時呈現。印證現實生存之眾生本相:一個吵嚷著的、沖突著的、戕殺著的生存艱辛和尋歡作樂的欲望世界!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