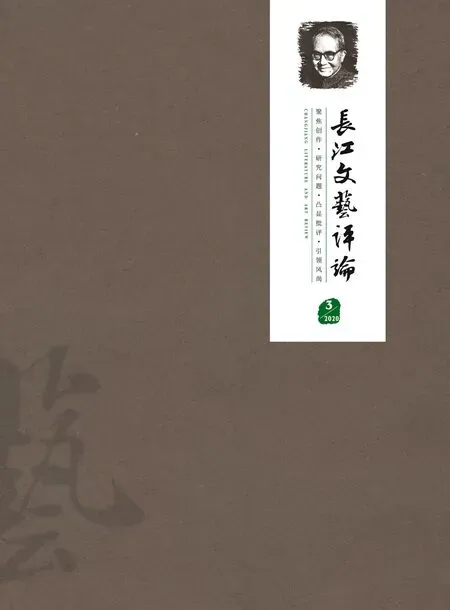造像記
——《烈焰青春》創作志
◆焦興濤
具象寫實技藝的傳承與教授是當代中國雕塑教育中最為完整的體系,由此決定了這一體系將始終是我們不斷研究的對象和討論的話題。不獨如此,整個人類雕塑史上絕大部分的經典篇章都誕生于這個系統之中。
在藝術觀念多元化的今天,關于具象寫實雕塑至少有兩個角度可以深入:一是“具象寫實”概念的重新梳理和再命名的可能;二是“技術”除了作為實現藝術意圖必須的“手段”,是否還有別的意義和價值?布洛克在其《現代藝術哲學》中寫道:“每一個社會都對‘現實’有著獨特的理解,根據這種解釋,它自然會覺得只有自己對現實的再現才是‘寫實’的,其他時代或區域的再現,則是非寫實的。換句話說,任何現實主義都是相對的,隨著文化環境的不同而不同。”具象藝術是人類對于自身形象最直接的解讀和認知,是把握現實世界最重要的視覺方式和工具,盡管經歷了各種視覺藝術經驗的革命,但至今我們依然以各自不同的理解延續著這樣的視覺傳統。如果“寫實”只是某種文化和傳統的結果,也就不存在一成不變的“寫實標準”,新的觀看方式不僅必然要出現,而且毫無疑問地屬于這樣一個傳統之中。作為一個雕塑家,就是要學會在偉大的傳統里努力睜大眼睛重新“觀看”,并期待著新的啟示和意義的驚鴻一瞥,這是我們主動而現實的選擇。
我常常喜歡去回顧揣摩中國雕塑的奠基人和開拓者們的作品。在劉開渠先生的《川軍抗日》紀念碑雕塑中,剪影般弓腰前行的輪廓內斂而堅定,造型樸質端方,充滿真實內在的力量,遠比夸張的姿態、昂揚的動作更能打動人。在曾竹韶先生的《轟炸》中,在集體創作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中,都能感受到對現實生活和真實經驗的直接把握和呈現。一種質樸、單純而強烈的氣息撲面而來,雕塑的形體處理沒有太多的風格矯飾,構圖單純簡潔,人物形象可信,拒絕“戲劇化”的情緒。這讓我想到黑格爾所定義的“嚴峻的風格”——它堅守描寫的客觀簡樸性。由此看來,那種沒有被過分“主題化”的主題美術創作,往往具有真正直擊人心的美和感染力——這恰恰是今天的雕塑家們需要好好體會和學習的。
去年年初因為參加一個政府會議,在會議大廳的轉角處,我突然撞見兩位嚴陣以待的消防員,全副裝備,為了警戒發生概率極小的危險,目不斜視,一動不動地值守在那里。這原本是重要會議的基本措施,但我不禁為之一動。因為日常,所以沒有夸張的姿態,一切源自職責,所以顯得平靜。這不是新聞和網絡中的英雄,他們就在日常生活之中,但卻和“日常”如此不同。消防戰斗服所特有的厚重感和美感,平添了氣勢。制服對于人格有著很強的塑造作用,它不僅僅是一種身份和職業的象征,也讓穿上制服的人獲得很強的歸屬感和使命感,從這個角度上講,制服塑造并強化了人的價值觀,具有很強的象征意義。這種強烈而震撼的感受,隨著四川涼山消防官兵的犧牲變得愈加強烈。平凡中的偉岸,無言中的絕響——呈現這種直接而強烈的情感的沖動變得越來越強烈。
七月的重慶,烈日爍金,在一個火熱的下午,我來到了附近的消防中隊,體驗他們的訓練生活并了解人民消防的歷史。很快,年輕的消防隊員們在閑聊中與我成為朋友,他們20歲出頭,干凈、整潔,挺拔。說到訓練,有條有理,如數家珍;談到生活,撓頭咧嘴,如鄰家男孩。英武的氣概與大男孩的生澀間或隱現,崇高的職責與飛揚的青春融為一體,著實令人印象深刻!實在令人難以忘懷!此時此刻年輕的“這一個”是最緊要的。典型固然完美,但是如果沒有生動如火的性情的融入,難免流于符號和表面。
具象藝術之所以被過去或現在的人們看作“反映了客觀現實”,并不是它本身必然是寫實的,而是因為它和過去或現在用來描述現實的藝術傳統相一致。所以,理論上講只有與今天視覺文化現實相一致的表達方式,方能“寫”今天之“實”,“具”此時之“象”。否則,對既有傳統表達方式的簡單套用,很可能成為藝術表達上的“刻舟求劍”或“緣木求魚”。

在緊接著的小稿創作中,我反復推敲、猶豫不定的是雕塑的構圖和人物動態的選擇。到底應該選擇一個“逆火前行”的勇士形象,還是懷抱嬰兒的守護天使或是疲憊不堪躺倒在路邊的戰士,還是莊嚴誓師的最可愛的人?在一開始,到底是表現消防員的群體還是具體發生的事件,我很猶豫。因為每一個戰士都是這樣的鮮活,每一個現場都是如此的險峻,每一次搶險都是那樣的可歌可泣,但是如若這樣,環境清晰了,氣氛出來了,情節也豐滿了,但真正打動我的東西卻消失了。對于場景和事件的描述讓作品的精神性退隱了,而寫實創作的關鍵恰恰在于對人物精神的凝練和表現。這時候一張攝影照片吸引了我:一個消防戰士從火線下來,剛剛摘下頭盔,仰頭的一瞬間,幾道污跡在年輕白皙的臉上像深深的劃痕,表情平靜而深邃——就是這種感覺!沒有激烈的動作和夸張的表情,淡定自然中透出堅毅決然的底色。很快,我便確定了單人立像的構圖。幾經反復,最終雕塑的構圖確立為一個站立的姿態。這是“他”剛從搶險救災的火線上下來,稍事休息之后,再次全副武裝,帶上各種裝備,準備重返火場的一個瞬間。上身披掛了較多的工具和器械,繁復的視覺效果帶來強烈的重量感,由此強化了人物的力量感,下裝適當加強褲腿褲腳的體量,以獲得穩定的視覺感受。靜中有動,穩中求變,以此來呈現人物心中淵渟岳峙般的磅礴與大氣。
形象具有的經典意義往往超越簡單的場景摹寫。毫無疑問,人物的基本關系和動態極為重要。在隨后的大泥塑的塑造過程中,反復調整兩條腿的位置,以獲得微妙的人物動態的變化,將行未行,希望能獲得動作轉換瞬間的運動感,同時又不失穩定的端厚沉穩氣質。特意微微調整了頭部的比例,借此與整體的身姿體量形成對比,試圖營造出平凡中的偉岸和雕塑特有的紀念碑感。我選擇了一個年輕挺拔的消防員為原型,在綜合其他因素的基礎上,特別強調個性的形象:寸頭,方臉,單眼皮,平靜而篤定的眼神,抿得緊緊的嘴唇,粗壯結實的脖子,年輕而且有些俊美的臉上所呈現的某種崇高的光輝尤其動人。在塑造過程中正是對雕塑“紀念碑”性的追求,讓我選擇放棄事件性、情節性的構圖方式,專注于人物的塑造,在“一個”之中,充分展現群體的價值和時代的回響。一個活生生的英雄就是這個時代的紀念碑。
如今,雕塑家們越來越傾向于借助群像的方式來創作,在戶外紀念碑雕塑中群像塑造尤其受到重視,架上雕塑創作也受此影響,強調氣氛、環境和多個人物的關系。毫無疑問,這有利于表現宏大的場面和具體的事件。然而,我常常感到希臘雕塑所具有的“靜穆的偉大”,中國雕塑中呈現的“意向性”審美特質,都在提醒雕塑家們不要忽略了雕塑藝術最重要的特質:內容的概括性、表現的紀念碑性。羅丹的不朽名作“地獄之門”完美地呈現了但丁神曲的意境,人物眾多,關系復雜,氣勢磅礴,不過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卻是“思想者”“亞當”“夏娃”這樣的單體作品。一方面是因為它們本身塑造得十分精彩,另一方面也有單體雕塑特有的象征性、完整感和表現力,讓這些雕塑獲得了獨立的審美價值,正所謂“以一當十”,與中國美學意境中的“少即是多”有異曲同工之妙。
雕塑是空間和材料的藝術。從這個意義上講,一件雕塑的材料選擇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雕塑作品的成功與否。如何能夠在材料語言上找到契合主題表現的特有方式,怎樣才能呈現材料在視覺象征上的張力和沖突,把現實的敘事和材料的邏輯完美結合,一直是我在考慮選擇雕塑材料的依據。《烈焰青春》血與火的主題讓我想到了熟悉的木材。木材可以在上面進行燒灼和炭化,十幾年前,我在木雕作品中就做過類似的嘗試,具有強烈的視覺和心理的張力,為什么不可以在主題性創作中進行運用呢?五年前完成的同樣風格材料的雕塑《逐夢》,也讓我對再次選用這一材料和手法增添了信心。仔細一想,燒灼的方式對于“火”的主題是一種最為直接的詮釋,木材之于火的關系正好隱喻了“浴火前行”“以身犯險”的壯烈。
選定了材料也就決定了語言的方式。在東西方悠久的雕塑傳統里面,木雕因其獨特的表現力和感染力而源遠流長,而當代的木雕作品在表現方式上則有了更多的創造和嘗試,然而等大的木雕創作并不多見。為了解決合適的材料問題,我決定用木材鑲嵌粘接來替代整塊原木雕刻成型的方式來完成作品。這樣做不僅僅是因為木材本身的限制,還因為“拼接”作為一種當代的材料語言,同樣可以成為主題性雕塑創作的觀念構成,同時,在技術上拼接的木雕更不容易開裂。等到雕塑雛形一出來,我便根據外形掏掉了木雕內部的一部分木料,再在拼接的木材之間加上螺栓進行拉緊和加固,這樣既合理地控制了重量,又強化了木雕整體的牢固。處理好材料的基礎工作,后面的造型終于開始變得得心應手了。時間慢慢過去,隨著雕塑從體量巨大的木方中一點點顯形,在電鋸的嘶響中,期待的心情如同火苗一樣一天天竄了起來,創造的愉悅與快樂如同陽光下的木屑,混合著柏木的幽香,漸漸充滿了工作室的小屋。
“藝術品一定是某種人工性的結果”。傳統藝術依靠技術和技藝來獲得這種人工性,今天,我們是不是可以嘗試把這種“人工性”的獲得,看作是藉由“技能”“技巧”為載體的一種命名方式,它不僅需要挑戰身體和時間(持之以恒的雕塑過程絕對是對身體和意志的考驗),還需要以技巧和技能為憑借——前提是,只有把它與特定的藝術意圖聯系起來的時候,其中所蘊含的過程性和命名方式的意義才可能呈現。時間的介入賦予了雕塑一種內斂的氣質、一種精神的張力和征服空間、征服材料的力量,同時也意味著對雕塑家最大的挑戰之一就來自材料,而應對的武器就是技巧和時間。
毋庸置疑,人物的面龐五官及情緒是刻畫的重點。在精雕細刻的過程中,我保留小圓刀隨著形體起伏的刻痕,將藝術情感通過技藝作用于木質的過程予以充分的呈現。好的技藝不是為了顯示技藝本身,而是展現藝術家對于形象的控制和分寸。服裝所具有的質感和體積感是整個雕塑的視覺重點所在,在木頭上捕捉衣服的皺褶溝壑,并賦予這些形體空間以視覺的節奏,這是一件微妙而令人興奮的樂事。濃墨重彩精雕細刻的時候,提醒自己須點到為止;大刀闊斧切削剁砍的關頭,需反復斟酌方能做到舉重若輕。做到感覺細膩而不“油膩”,刻畫充分卻非面面俱到,這樣的挑戰讓我每一天都如履薄冰卻樂在其中。

雖然雕塑事實上從來就沒有離開過色彩,但木雕的著色依然是一個值得不斷嘗試的領域。在觀察中國傳統建筑上面的木質浮雕,或者寺廟里面那些為數不多的木質造像時,它們表面因顏色脫落而露出的木頭本色與斑駁色彩構成的時間的印記,其隱隱的歷史感和年代感呈現出一種特別的魅力,吸引著我,讓我嘗試著在創作中轉述這種美感。當代的木雕著色,往往講究輕、薄、透,以呈現原木本身的質感;又或者強調藝術家的主觀感受,色彩的敷設刻意保持著和真實的距離,以呼應木雕本身的材質肌理,由此形成了今天特有的木雕色彩審美模式。在《烈焰青春》這件雕塑上,我恰恰想呈現與現實更加接近的真實感,我需要用大紅大黑去釋放木雕著色一貫的謹慎和克制,在布滿刀痕的木材表面上涂抹橘紅的丙烯,敷設鮮紅的油漆,讓濃烈的色彩和被燒灼的木頭一起去唱響血與火的青春之歌。于是我在木雕大形完成后就開始上色,然后繼續雕刻,再繼續上色,反反復復,讓色彩參與到雕塑材料成型的過程之中,由此形成豐富的層次、特有的滄桑感和時間感,讓雕塑的形體與色彩飽滿而強烈、自然而有機地交融在一起。
作品創作的過程就是一段充滿意外和驚喜的旅程,其中所經歷的興奮、快樂、激動、猶豫、手足無措和柳暗花明都是藝術賜予我們的珍貴禮物。在今天,當代雕塑多元跨界發展的狀態下,再次完整體會研習具象雕塑創作,感慨良多。毫無疑問,當代雕塑在形式語言上表現得更加多元豐富和歷久彌新。在材料的使用上,傳統雕塑材料在不斷被重新解讀的同時,新的材料不斷進入;技巧的進步不斷刷新對“真實”的經驗感受;與環境密不可分的現場展示方式充分顯示了當代藝術對雕塑的影響;而同時,色彩幾乎成了當代雕塑作品的標簽。當代具象雕塑創作只有進行主動地選擇和改變,才能回應今天的文化語境和現實。除了服務于國家重大文化建設的要求,對具象雕塑創作語言的再認識是此次創作活動的一個收獲。如果無法呈現真實生活中不斷涌現的新的視覺經驗和激情,寫實就有可能成為一種“熟悉的經驗”,觀眾很難通過模式化的呈現來體會寫實所特有的“逼近”審美體驗和強烈的感染力。寫實不應該僅僅是某種慣熟的“流暢的手法”和“既定的模式”,強烈的視覺和情感形式不應該被“愉快的風格”所稀釋,回到寫實就是回到真實的塑造,回到遭遇真實的現場,然后心無旁騖地呈現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