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創(chuàng)造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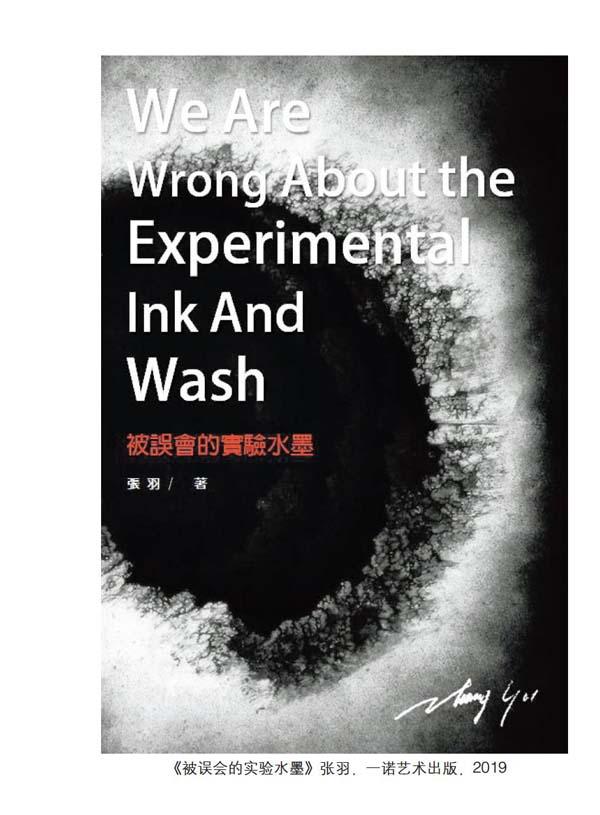
創(chuàng)造藝術(shù)/超越時代
時代往往是一個巨大的陷阱,于是討論當代藝術(shù)的前提是超越你所處的時代,你的行為不依附于你所處的時代,不與其同步并保持距離,對其具有一種警惕。以確保自己獨立思考,這種理智便是一種當代認知。
事實上,改革開放40年來的藝術(shù)實踐及理論思考的積累,水墨的發(fā)展已經(jīng)有了一個清晰的答案。“水墨創(chuàng)造論”是我對水墨發(fā)展做的一次梳理與論證的階段性總結(jié)。首先,需要認清一個問題,無論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還是最好的時代,我們已然深深地陷在當下景觀社會大雜燴的處境中。當下的學術(shù)研究或藝術(shù)創(chuàng)作,表面上多元其實隱含的是缺失前進方向、喪失精神追求、魚龍混雜的大雜燴關(guān)系。而這種大雜燴的現(xiàn)實竟成為當下潮流,這就是如今的時代,也正因有如此經(jīng)歷更讓自己明晰了時代與時代間的進程關(guān)系,辨清了一路上具有意義和價值的來龍去脈。
全球化是當今討論任何議題都要面對的,這就要求我們必須以新的視角重新審視中國現(xiàn)當代藝術(shù)在改革開放以來這40年是怎樣的路徑,歸納起來有兩條比較明確的線索:
一、在經(jīng)歷了20世紀“文革”十年浩劫后的“傷痕美術(shù)”到“85美術(shù)思潮”的走向西化,出現(xiàn)了一條模仿西方藝術(shù)史藝術(shù)的,以西方藝術(shù)方法論講述中國故事的線索。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社會政治、社會形態(tài)符號的“政治波普”“玩世現(xiàn)實主義”“公寓藝術(shù)”“艷俗藝術(shù)”“卡通一代”。這以后再沒有出現(xiàn)更具有影響的藝術(shù)現(xiàn)象。
二、同樣經(jīng)歷了“文革”十年,從“形式美”1到“85美術(shù)思潮”西化路線,從水墨出發(fā)以中國繪畫史作為基本依托,沿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西合璧之路模仿西方形式主義之后,漸而擺脫西化形式主義方向,以水墨作為工具的中國敘事。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末,從“現(xiàn)代水墨畫”“現(xiàn)代水墨”“實驗水墨”到新世紀“極多主義”2“念珠與筆觸”3“意派”,4以及“存在藝術(shù)”5“覺知藝術(shù)”6的線路。
這兩條線索從80年代發(fā)展至今,是完全不同路徑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從兩條線路的發(fā)展結(jié)果看,可以確認它們都具有向外開放的視野,但對開放的認知卻不在一個起落點。第一條線索就藝術(shù)本體而言,是西方藝術(shù)史藝術(shù)的方法論關(guān)系,以中國社會圖像構(gòu)成在中國現(xiàn)當代藝術(shù)發(fā)展史上幾種繪畫風格的藝術(shù)樣式。第二條線索與西方藝術(shù)史若即若離,但有著明確的現(xiàn)代主義的東方主義認知,這與日本“前衛(wèi)書法”“具體派”“物派”,韓國“單色繪畫”具有相關(guān)性,可以看作中日韓東亞線索的現(xiàn)代主義的東方主義路線。這條路徑不在于確立怎樣的藝術(shù)風格,重要的是呈現(xiàn)了中國現(xiàn)當代藝術(shù)的發(fā)展方向。
這不僅可以看到水墨發(fā)展的結(jié)果,更可以意識到從水墨出發(fā)的中日韓現(xiàn)當代藝術(shù)的關(guān)聯(lián)性發(fā)展,可以視為東亞藝術(shù)共同體在建立現(xiàn)代主義的東方主義體系,如何走向當代藝術(shù)認識的發(fā)展方向,關(guān)鍵是這一東方主義并不單純指水墨如何,而是打開水墨及任何媒介的表達。
現(xiàn)代性/當代/不只是水墨結(jié)論
厘清水墨的進程,就有了水墨發(fā)展每個階段的結(jié)果及水墨結(jié)論,這個結(jié)論的價值不只是水墨的結(jié)論,而是如何認識藝術(shù)的結(jié)論。現(xiàn)代性、當代并不是糾結(jié)水墨,而是使水墨進入藝術(shù)問題對創(chuàng)造藝術(shù)的追問。在這個起點上我更愿意將中國、日本、韓國看作一個同源的藝術(shù)共同體來討論水墨的發(fā)展進程,如此才會清楚我們能給予世界什么,以及我們?nèi)绾蜗蛭鞣剿囆g(shù)史提問。
基于這兩條線索,我們進一步追問:水墨何去何從?這也是對創(chuàng)造藝術(shù)的追問:
1.將前人開辟的傳統(tǒng)書畫之應物相形的書寫筆墨視為不變的、永遠真理的保守主義。從古代繪畫到唐代詩人王維用“水”將“墨”渲淡,以“水法”“墨法”入畫,墨分五色的文人畫書寫;到晚明八大、徐渭之書寫筆墨的大寫意;近代黃賓虹以形忘形的書寫筆墨境界;再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借洋興中、西法中用、中西合璧之徐悲鴻、林風眠及之后齊白石大寫意、張大千潑墨、潑彩;再到改革開放80年代中期普遍西化后出現(xiàn)的一場筆“墨中心主義”的討論,一方面批評家郎紹君與臺灣現(xiàn)代水墨畫家劉國松革中鋒用筆展開的激烈論爭,另一方面持筆墨中心主義的批評家們力推當時在書寫筆墨具有代表性的畫家。事實上,書寫筆墨路線的具象表現(xiàn)主義繪畫樣式,歐美的大師比比皆是,如果從繪畫維度看是不可超越的。像蒙克、馬蒂斯、畢加索、德庫寧等有一大串大師名單,他們沒有給后人留下任何可以逾越的空間。即使你用水墨媒介畫到相似而又能如何呢?因此,表現(xiàn)主義最后的出路是與抽象藝術(shù)合流,進入康德的純粹美學,剔除具體的形象及文學性情節(jié)。
2.途徑千年中國傳統(tǒng)書畫乃至文人畫應物相形的書寫筆墨征途,至明末八大、徐渭的大寫意,到近代黃賓虹書寫筆墨的得意忘形,遺憾的是黃賓虹沒有意識到自覺忘形,只差一步?jīng)]有實現(xiàn)書寫筆墨的獨立價值。如果黃賓虹時代進入抽象藝術(shù)完成筆墨獨立價值,藝術(shù)史的發(fā)展在此將是一個拐點。然而黃賓虹一步之遙卻又后繼無人,成為文人畫書寫筆墨的終結(jié)點。
“二戰(zhàn)”后的日本則在“前衛(wèi)書法”的領(lǐng)域下,其變革取得驚人的突破,最終井上有一成就于將漢字書法躍出書畫實現(xiàn)了書寫筆墨的獨立價值,進入一種表現(xiàn)主義的抽象。這無疑是書寫筆墨向抽象發(fā)展的拐點。在日本“前衛(wèi)書法”“具體派”的影響下,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臺灣“東方畫會”“五月畫會”的東方式抽象啟開了水墨畫現(xiàn)代性探索。60年代中期以后至70年代日本“物派”韓國“單色繪畫”崛起,禪宗、水墨及筆墨性被攜帶。此刻港臺及大陸幾位抽象水墨畫家蕭勤、劉國松、呂壽昆、王無邪、趙春翔繼續(xù)著水墨的東方抽象之路。
橫在他們面前的問題是,能否別于西方抽象藝術(shù),探索東方抽象的現(xiàn)代主義的東方之路。雖然他們沒能完成這一課題,但努力了。
時間到了80年代,美國學者、哲學家阿瑟-丹托提出“藝術(shù)終結(jié)論”之時,中國“85美術(shù)思潮”的中西融合之現(xiàn)代水墨運動蓬勃興起。隨著90年代中期“實驗水墨”群體另辟蹊徑以中西之上的認知崛起,掀起了探討走出水墨進入當代的藝術(shù)實踐與理論研究,創(chuàng)造了一種別于西方抽象的水墨圖式的當代表達。進入21世紀后,實驗水墨又創(chuàng)造了以行為、裝置呈現(xiàn)的“極多主義”“念珠與筆觸”方法論,從而進入“意派”的討論中。在對“意派”反再現(xiàn)論的重重質(zhì)疑聲中“意派”并未構(gòu)成對西方藝術(shù)史的有效質(zhì)疑。2015年之后以全球化視野沿中西之上的“存在藝術(shù)”“覺知藝術(shù)”的研究悄然啟動,其目的是向西方現(xiàn)有藝術(shù)史及藝術(shù)發(fā)問,擺脫當下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一直處于瓶頸的現(xiàn)狀。在我看來,瓶頸的原因是藝術(shù)史藝術(shù)對創(chuàng)造藝術(shù)的追問始終停留于語言的形式主義層面,預想通過身體或肉身的體驗表達真實存在,指出創(chuàng)造語言不是藝術(shù)的核心價值。企圖將水墨單純地作為工具,通過方法或方式進入一種轉(zhuǎn)換機制,成為藝術(shù)史中的藝術(shù)。
以上兩條線索已經(jīng)昭示著水墨發(fā)展的兩種必然結(jié)果,也彰顯出梳理此線索的切入方法。前者基于書寫筆墨的結(jié)局,書寫主義處于一種被擱置狀態(tài)。其實,這是水墨畫畫種處于死亡的臨界點。后者不再如以往那樣簡單地去擁抱西方,而是通過水墨畫種的消亡,在現(xiàn)有藝術(shù)史抽象表現(xiàn)主義節(jié)點及后現(xiàn)代的關(guān)系上,面對如何突圍語言的形式主義,構(gòu)成提問的可能性,這一可能性就是通向全球化格局的創(chuàng)造藝術(shù)路徑。這是不中斷歷史的且具有世界主義的路徑。
現(xiàn)代主義/東方主義/藝術(shù)史中的水墨
只有將水墨納入藝術(shù)史中討論,才能認識水墨與藝術(shù)的關(guān)系,才能使水墨獲得創(chuàng)造藝術(shù)的可能。從前衛(wèi)書法、具體派、物派、單色繪畫、實驗水墨、存在藝術(shù)的東亞現(xiàn)當代藝術(shù)發(fā)展的現(xiàn)代主義的東方主義,看西方現(xiàn)當代藝術(shù)史是怎樣建構(gòu)現(xiàn)代主義的東方主義關(guān)系,印象派與日本浮世繪,野獸派與日本裝飾主義繪畫,抽象表現(xiàn)主義與中國書法,激浪派與禪宗。顯然是兩條不同路徑的現(xiàn)代主義的東方主義,是形式主義與觀念藝術(shù)兩種方法論生成的。
從水墨出發(fā)的這條線路:水墨畫由于是一種書寫筆墨與繪畫的關(guān)系,唯有進入表現(xiàn)主義這條路徑。當書寫與西方表現(xiàn)主義匯合,書寫也就走向了盡頭。顯然,水墨的發(fā)展會走向抽象,但這并不意味進入抽象就可以解決問題,而是向抽象提問,獲得穿越抽象進入藝術(shù)史的路徑。
讓水墨穿越抽象的起點是消解水墨畫種,步入綜合材料的“現(xiàn)代水墨”為第一步。1996年后掀起的“實驗水墨”運動是第二步。這一步的目的是擺脫西方抽象繪畫的現(xiàn)代主義樣式,探尋現(xiàn)代主義的“東方主義”表達。于是,我再三強調(diào)實驗水墨并非抽象水墨問題,而是呈現(xiàn)一種開放的立場和態(tài)度,其意圖是對水墨的認知超越畫種。將水墨、行為、裝置、影像并置作為呈現(xiàn)表達的工具,我們可以從“物派”“單色繪畫”的現(xiàn)代主義的東方樣式中看到這種關(guān)系。事實上,當“實驗水墨”生發(fā)了“極多主義”“念珠與筆觸”的方法論,理論闡釋上并沒有躍出“物派”“單色繪畫”幾許,但實驗水墨的藝術(shù)實踐卻遠遠超越了“物派”及“單色繪畫”,已經(jīng)挑戰(zhàn)了西方藝術(shù)史藝術(shù)。
這里,我們簡單回顧一下西方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主義的關(guān)系,印象派借鑒日本浮世繪,野獸派借鑒日本裝飾主義繪畫,抽象表現(xiàn)主義借鑒中國書法,激浪派借鑒禪宗。前衛(wèi)書法關(guān)聯(lián)著中國千年的書法及文人畫,物派關(guān)聯(lián)著意大利貧窮藝術(shù)與禪宗,單色繪畫關(guān)聯(lián)著歐美抽象主義、抽象表現(xiàn)主義及中國水墨。
中國繪畫史的進程由于在晚明和近代及民國三次錯過切入現(xiàn)代主義的最佳時機,到80年代中后期以現(xiàn)代水墨為開端,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的“實驗水墨”運動完成了現(xiàn)代主義的補課,這一補課與日韓相差30年。從這幾層關(guān)系看現(xiàn)代主義的東方主義發(fā)展,是一個非常具有意義的話題。西方的現(xiàn)代主義隱含著與東方的關(guān)系—現(xiàn)代主義的東方主義。而中日韓的現(xiàn)代主義的東方主義,實際是一個同源的藝術(shù)共同體。那么,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東方主義與東亞現(xiàn)代主義的東方主義是一種并行關(guān)系,這種關(guān)系構(gòu)成一種世界藝術(shù)共同體的整體現(xiàn)代主義關(guān)系。于是,突圍現(xiàn)有藝術(shù)史藝術(shù)的發(fā)展是我們的共同課題。
由此,我們可以達到一種共識,如果從中國繪畫史看水墨,這個水墨是建立在水墨畫的畫種基礎上,也就是在書寫筆墨的規(guī)范中演化,它是一個封閉系統(tǒng)。如果從整體藝術(shù)史進程看,就要從與日韓、歐美的關(guān)系中認識水墨。這個關(guān)系是從華夏千年書畫及更久遠的書法的演進與日韓水墨的發(fā)展,水墨的認識是逐漸抽離出來的。
我與實驗水墨十年間的實踐就是實現(xiàn)水墨轉(zhuǎn)型,使水墨具有本身的媒介性、工具性、審美性。簡言之,讓水墨成為藝術(shù)表達中的一種帶入關(guān)系,從而進入創(chuàng)造藝術(shù)的藝術(shù)史中。
在藝術(shù)發(fā)展進程中,創(chuàng)造藝術(shù)舉步維艱,體現(xiàn)著藝術(shù)史藝術(shù)發(fā)展的困境。事實上,這是遭遇了一百年的困境,我們誤以為塞尚將創(chuàng)造藝術(shù)推向創(chuàng)造語言的形式主義之路,使藝術(shù)一直處于語言形式主義多樣性是有效的,忽略了對藝術(shù)核心價值到底是什么的追問。達達主義的出現(xiàn),我們再次誤以為杜尚橫掃藝術(shù)本體是創(chuàng)造了奇跡,從否定繪畫形式到現(xiàn)成品形式,藝術(shù)就這樣走了一百年。什么都是藝術(shù),什么都不是藝術(shù);人人都是藝術(shù)家,人人都不是藝術(shù)家。藝術(shù)到底是游戲,還是對精神的追問。
終于,我在創(chuàng)作《指印》系列時棄筆、棄墨的,這一不是之是的圖像清零啟示了我,放棄圖像就是剔除圖像預設。棄筆的關(guān)鍵不在于如何背離毛筆,而是手指蘸水摁壓的指印,通過肉身與宣紙的觸碰獲得那一刻的自我真實存在,讓我躍出了所有關(guān)于水墨的思考。我重新面對薩特、海德格爾、雅斯貝爾斯、克爾凱戈爾的存在主義。我從一個新的維度反思并重新觀看藝術(shù)史,顯然,存在于時間性中的自我真實存在,打開了藝術(shù)史藝術(shù)一直對語言形式追問的死結(jié),顛覆了我對現(xiàn)有藝術(shù)史藝術(shù)一直認知的語言的形式主義發(fā)展框架。從“指印”的核心關(guān)系看到指印不是單一地對形式的突圍,關(guān)鍵是肉身之手的手指摁壓宣紙的一刻,藝術(shù)家作為創(chuàng)作主體的真實我在。存在于時間性中的自我真實存在,實際上是個體人追問的一種存在價值,即人生存的核心意義及價值。這一點,顯然是創(chuàng)造藝術(shù)的藝術(shù)核心的價值。
從這個角度我認識到現(xiàn)有藝術(shù)史是藝術(shù)家的自我存在史,那么藝術(shù)史藝術(shù)的藝術(shù)家又是如何表達自我真實存在的呢?其實,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藝術(shù)史中的藝術(shù)并沒有意識到追問創(chuàng)造藝術(shù)的核心精神價值,而是始終追問語言的形式問題。
回顧塞尚,當他面對古典繪畫提出怎樣畫比畫什么更重要,這一探求語言的形式主義本體論的現(xiàn)代藝術(shù)。杜尚似乎更為徹底,直接否定繪畫這種藝術(shù)形式,用現(xiàn)成品完成藝術(shù),以達達的前衛(wèi)藝術(shù)觀念瓦解藝術(shù)本體。事實上,杜尚根本沒有給出創(chuàng)造藝術(shù)的邏輯,他以歷史虛無主義的激進主義將繪畫形式換成現(xiàn)成品形式。本質(zhì)上仍然是形式主義。就這樣,現(xiàn)代藝術(shù)的語言形式主義與前衛(wèi)藝術(shù)的觀念主義構(gòu)成了歐洲藝術(shù)史進程的兩種方法論,影響至今。這一百年來整個西方藝術(shù)史的藝術(shù),都是這兩種方法論的產(chǎn)物。這就是一百年來藝術(shù)發(fā)展的現(xiàn)實,對創(chuàng)造藝術(shù)的追問被語言形式的多樣性所遮蔽,似乎藝術(shù)家們情愿被杜尚愚弄,早已忘記了對藝術(shù)核心價值的追問。解決當代藝術(shù)發(fā)展的停滯不前,唯有開啟追問藝術(shù)核心價值的創(chuàng)造藝術(shù)才有可能使藝術(shù)獲得發(fā)展,而水墨也只有放在這個全球化語境中尋求出發(fā)。2016年初“存在藝術(shù)”的研究啟開了破解一百年來藝術(shù)發(fā)展新的研究方向,水墨被有效地攜帶于這場討論中向前推進了一步。
書寫終結(jié)/水墨畫種論消亡
從水墨作為畫種到水墨作為工具,從水墨畫到水墨的發(fā)展進程其學術(shù)價值顯而易見。從千年歷史的傳統(tǒng)書畫改稱為中國畫、水墨畫,伴隨著歷史及時代的變遷而變化:中國畫(水墨畫)→現(xiàn)代水墨畫→現(xiàn)代水墨→實驗水墨及創(chuàng)造藝術(shù)的藝術(shù),構(gòu)成一條具有問題性效率的鏈接及藝術(shù)發(fā)展史的邏輯。
水墨畫種的消亡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它是藝術(shù)發(fā)展進程中學理、學術(shù)對藝術(shù)推進的必然結(jié)果,書寫筆墨的終結(jié)自然是畫種的消亡。
水墨作為水墨畫畫種千年的書畫歷史,從王維用“水”將“墨”渲淡,以“水法”和“墨法”墨分五色,起始于書畫的筆墨進程,以宣紙、毛筆、墨、水的關(guān)系構(gòu)建書寫筆墨規(guī)范系統(tǒng)。從以書寫為源頭的應物相形之筆墨體系的文人畫路徑,直到明末八大、徐渭的大寫意至近代黃賓虹的得意忘形的書寫筆墨抵達書畫巔峰之后走向了衰敗。主要體現(xiàn)在黃賓虹成就之后,這條線索再沒有出現(xiàn)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畫家。在我看來,黃賓虹的筆墨線索最有可能進入水墨現(xiàn)代主義,最可能走向抽象。假如如此,中國的水墨現(xiàn)代主義至少前提半個世紀。
之后徐悲鴻、林風眠到齊白石、張大千、潘天壽等均沒有達到黃賓虹的成就。就是說,書寫筆墨的成就在中國繪畫史既是開始也是結(jié)束,換言之,書寫筆墨沒有走出中國繪畫史。
“二戰(zhàn)”后日本前衛(wèi)書法的井上有一的書寫筆墨實現(xiàn)了筆墨的獨立價值,使書法及書畫的書寫筆墨走出原本的價值體系,與美國抽象表現(xiàn)主義相會。這是水墨走向現(xiàn)代的重要轉(zhuǎn)折點,中國的水墨畫受到日本具體派、前衛(wèi)書法的影響開始走向抽象繪畫風格。20世紀50年代中國臺灣“東方畫會”“五月畫會”的蕭勤、劉國松等開始探索東方抽象的彩墨畫。
水墨在中國大陸的轉(zhuǎn)折是從20世紀“85美術(shù)思潮”開始,1985年李小山的“中國畫之我見”的中國畫窮途末路,激起現(xiàn)代水墨畫運動。隨后的現(xiàn)代水墨對綜合材料的引入動搖了書寫筆墨水墨畫畫種的邊界。1996年是一個根本性的轉(zhuǎn)折點,張羽策劃的“走向21世紀的當代水墨藝術(shù)研討會及作品觀摩展”在廣州召開,錢志堅提出“水墨畫消亡論”。71997年實驗水墨崛起,將行為、裝置、影像帶入水墨表達中,這使王維開創(chuàng)的水墨畫漸漸地逼向尾聲。雖然,書寫是20 世紀以來東方與西方都在挖掘這一貫穿古今的亞洲源頭的元素,無論是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東方主義,還是東方現(xiàn)代主義的東方主義,書寫及筆墨語言的形式主義探討都已完成了歷史使命。
在實驗水墨決定走出水墨畫種離開千年書寫筆墨僵化固守的戒律,不只是書寫筆墨的水墨畫無力表達當代訴求而結(jié)束,還有其喪失了藝術(shù)發(fā)展的效率,畫種也就必然消亡。畫種的消亡實質(zhì)是取消書寫作為水墨的中介,而解放水墨自身的直接承載價值,也就釋放了水墨媒介物質(zhì)屬性的價值,使水墨自身獲得創(chuàng)造藝術(shù)的源起,從水墨的原點思考創(chuàng)造藝術(shù)。使“水墨不等于水墨畫”獲得水墨的水+墨8之和或分離,作為自由的物質(zhì)被選擇,可以在新的需要下產(chǎn)生重新觀看的表達。行為、裝置及其他方式可以自由轉(zhuǎn)換水與墨進入創(chuàng)造藝術(shù)的表達,水+墨之和或分離帶來的是我們對創(chuàng)造藝術(shù)的重新思考,我們在經(jīng)歷了水墨概念三十余年的多次反轉(zhuǎn)之后,終于清醒地理解水墨轉(zhuǎn)型中何為水墨的意義。
邊界的取消,水墨不再是固定在狹隘不變的一種工具模式,而是可變化的動態(tài)關(guān)系,可以隨時被表達攜帶進入作品。水墨從而真正意義上獲得參與世界的對話,暗喻著尋求切入西方現(xiàn)有藝術(shù)史藝術(shù)提問的可能。
進入21世紀的棄筆、舍墨之“零媒介”9成為認識、表達的新話題,水墨不等于水墨畫成為現(xiàn)實。從水墨畫到當代藝術(shù)的進程,結(jié)束了千年以來水墨只作為畫種的時代。
觀念之后/唯水墨成為藝術(shù)
觀念之后,水墨離開了毛筆、離開了平面、離開了架上、離開了千年的水墨畫種。從此水墨被行為、裝置、影像帶入當代藝術(shù)表達中,開始了水墨新的篇章。2000年后,我再次棄筆以行為呈現(xiàn)《指印》,隨即棄墨只蘸清水摁壓指印,既剔除了毛筆與宣紙的關(guān)系,也剔除了墨與宣紙的關(guān)系,只余下創(chuàng)作者作為主體的肉身與宣紙的真實存在關(guān)系。最終超越平面、超越水墨、超越繪畫、超越抽象。2004年劉旭光以影像呈現(xiàn)《墨滴》,通過高清攝影機記錄滴在過濾紙上的一滴墨水,從光韻的墨珠到墨色干枯的墨質(zhì)變化。2013–2016年,我以行為裝置呈現(xiàn)《上水》,藝術(shù)家用一把水壺將水上滿一萬只白色瓷碗內(nèi),隨后水在自然中蒸發(fā),自然的雨水再為其上滿,再蒸發(fā),循環(huán)往復生生不息。這不僅反映以開放的思想面對未來,關(guān)鍵是何為全球化視野下的認知觀念。
綜上所述的整個歷程,都是圍繞著水墨如何創(chuàng)造藝術(shù)演進的。事實上,讓水墨成為藝術(shù)的關(guān)系建立在西方藝術(shù)史、東亞藝術(shù)史、中國繪畫史的三重關(guān)系上。通過對這三條線索的線性梳理,再將三條線索重合起來看。再將中國書法史、中國繪畫史看作中日韓藝術(shù)發(fā)展的原點,就有了將東亞現(xiàn)代主義的東方主義之東亞共同體的成果放在西方藝術(shù)史中觀看,這顯然是西方藝術(shù)史不能覆蓋的成果。
水墨畫的消亡與西方繪畫的消亡雖然有著不同的線索及關(guān)系,但都證明了單一媒介的藝術(shù)形式表達無法承載當今世界發(fā)展的豐富性、復雜性,難以創(chuàng)造出新的藝術(shù)。當我們認識了現(xiàn)有藝術(shù)史是一部語言的建構(gòu)史,而語言的形式主義早已無法前行,就是說語言的形式主義是藝術(shù)發(fā)展的死結(jié)。當然,我也認識到現(xiàn)有藝術(shù)史是一部藝術(shù)家自我存在史。那么,藝術(shù)史藝術(shù)又是怎樣呈現(xiàn)自我存在的呢?我要問的是自我真實存在的藝術(shù)在哪里?我想《指印》的答案是明確的。這將關(guān)系到我們應該為世界提供怎樣的藝術(shù)認知,我們能否突圍現(xiàn)有藝術(shù)史。
總之,世界的演化改變著我們的思維、認知及觀看,觀看的視覺邏輯已從二維進入多維的時間與空間。多維的視覺邏輯迫使水墨唯有成為一種動態(tài)的可變化的工具,帶入創(chuàng)造藝術(shù)表達中的有效生成機制中。換句話,當水墨拒絕了二維關(guān)系,水墨自身必須獲得再生關(guān)系,唯有讓觀念將水墨帶入轉(zhuǎn)換機制使水墨再生。簡言之,水墨唯有成為藝術(shù)問題才是問題。我相信會有不少人對“唯水墨成為藝術(shù)”感到疑惑,水墨不是藝術(shù)嗎?這個疑問恰恰是打開視水墨為藝術(shù)的誤解。事實上,水墨只是漢語區(qū)域的一個具有文化關(guān)聯(lián)的媒介代碼,與藝術(shù)沒有實質(zhì)關(guān)系。水墨成為藝術(shù)需要置入一種轉(zhuǎn)換機制,傳統(tǒng)書畫是以書寫作為中介進行轉(zhuǎn)換的。對創(chuàng)造藝術(shù)而言,視水墨為藝術(shù)其實只是一棵救命稻草。
結(jié)論:“水墨創(chuàng)造論”即解構(gòu)水墨的創(chuàng)造論—藝術(shù)創(chuàng)造論。換言之,水墨創(chuàng)造論并不是水墨一定能夠創(chuàng)造奇跡,而是水墨畫種如何消亡才是討論創(chuàng)造藝術(shù)的前提,如果水墨不能創(chuàng)造新的藝術(shù)呈現(xiàn),水墨也就自然消亡。
吳冠中.繪畫形式美[J].美術(shù),1979.5.
見“中國極多主義”藝術(shù)展,高名潞策劃,北京,中華世紀壇藝術(shù)館,2003.
見“念珠與筆觸”藝術(shù)展,栗憲庭策劃,北京,798“東京北京工程”畫廊,2003.
見“意派:中國抽象三十年北京觀摩展”,高名潞策劃,北京墻美術(shù)館,2007.
見“存在藝術(shù)”項目研究展,張瀟雨策劃,北京,798“第零空間”畫廊,2016.
見“覺知超限:覺知藝術(shù)—對存在與時間性的言說”,張羽策劃,上海,明圓美術(shù)館,2019.
錢志堅.假設的可能性—現(xiàn)代水墨畫的虛擬狀態(tài)[A].張羽.二十世紀末中國現(xiàn)代水墨藝術(shù)走勢[C],第3輯.哈爾濱:黑龍江美術(shù)出版社,1997: 138-139.
胡震.張羽—念力-心印[J].張羽. 藝術(shù):做我自己—張羽訪談錄[C].長沙: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 2014:336-371.
巫鴻對話張羽“零媒介:水—由水墨引發(fā)的思考”[A].張羽.基本原來:張羽視覺進化論.北京:中國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 2017:339-3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