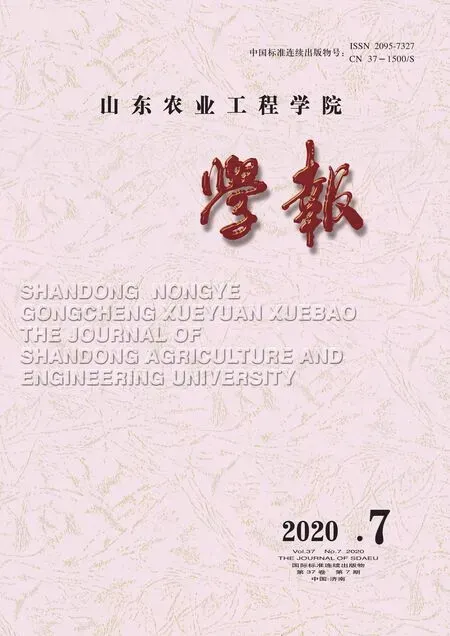從社會保障獲得視角透視農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皖江工學院 水利工程學院,安徽 馬鞍山243002)
一、引言
在城市定居是農民工城鎮化進程中的向往目標,農民工如何能夠融入到城市之中,需要政府制定精準有效政策。假設該群體在城市沒有居住的地方,那么會引發系列治安問題,不利于和諧社會構建[1]。正因如此,學術界對農民工居住問題進行系列相關研究。如:部分研究者將農民工的住房消費置于中國城鎮化建設中,探討住房分配機制向住房市場轉型過程中如何影響農民工群體城市定居決策[2];還有學者從社會建構視角分析農民工城市定居選擇,提出城市居住作為一種消費行為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住宅使用差異體現了社會階層隔離、種族隔離以及貧富隔離[3]。對農民工定居意愿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已有較多成果,如:個體因素,包括其人口特點變量的年齡、性別、婚姻狀態、戶口類型以及受教育程度[4]等;農民工家庭特征方面:如家庭的社會資本擁有度、家庭成員經濟狀況考察等[4]。縱觀已有研究,社會保障對城市居民住房已經產生顯著影響,但社會保障因素對農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影響關注較少,尤其是從社會保障總體視角與分類視角探討對農民工定居的影響。因此,從社會保障獲得視角透視農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是值得關注的課題,故文章運用CSS2011調查數據,分析農民工社會保障獲得對其城市定居意愿影響。
二、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文章采用的是CSS2011調查數據①,研究對象是農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文章中的農民工是指具有農村戶籍,在城市從事非農工作的勞動者,再排除不合格樣本量,得到有效樣本量為3784個,文章構建定量模型,擬用STATA統計軟件進行分析。
(二)變量選擇
對農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實證分析,所研究的對象是農民工社會保障與城市定居意愿關聯。因此,被解釋變量是農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核心解釋變量是社會保障獲得。具體相關變量處理過程如表1所示:
第一,被解釋變量(Y)。模型的被解釋變量是農民工城市定居意愿,被解釋變量選取及操作化過程為“您家有定居打算嗎”,回答的答案有:“打算一年內購買”,“打算兩年內購買”,“打算三年內購買”,“有定居的想法,但暫時不打算購買”,“沒有購買住房的想法”以及“不好說”等,由于文章關注的農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答案為“不好說”不在研究范圍之內,故應刪除。選項為“打算一年內購買”,“打算兩年內購買”,“打算三年內購買”以及“有定居的想法,但暫時不打算購買”操作化為愿意定居,用“1”表示,“沒有購買住房的想法”選項操作化為不愿意定居,用“0”表示。
第二,解釋變量。文章核心解釋變量是社會保障獲得,文章試圖從兩個層面進行操作化,一個是從總體層面,另一個是從分類層面。總體層面:操作化為社會保障擁有度,通過6個問題進行測量:“您目前有沒有下列社會保障?”,選項為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以及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如果有則賦值為“1”,沒有則賦值為“0”。由于社會保障擁有度是復合型變量,因此需要通過主成分分析由這6個題目得到社會保障擁有度指標,于是本文通過使用SPSS軟件的因子分析功能來進行研究。結果顯示,KMO值為0.79,且Bartlett球形度檢驗的P值小于0.01,由此可知這6個變量可以進行主成分分析,得出僅有一個大于1的特征根,由此可知主成分的個數為1,由成分矩陣可得特征向量,從而得到主成分得分系數矩陣,為便于分析,根據極值點和均值點將變量社會保障擁有度離散化所得到變量進行如下處理:當0<社會保障擁有度≤平均數的時候,賦值為“0”,表示社會保障擁有度低;當平均數<社會保障擁有度≤最大值的時候,賦值為“1”,表示社會保障擁有度高。分類層面:操作化為6個問題,分別是您是否擁有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以及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如果有則賦值為“1”,沒有則賦值為“0”。
(三)模型選擇
由于因變量是農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是二分類變量,基于此,假定農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是以自己效應最大化原則進行,文章建立二元Logit離散選擇模型:

(1)式中y表示農民工城市定居意愿;xi表示影響農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體因素,γi是等待估計的參數項;μ是隨機誤差項。對等式兩邊取e的指數得:

(2)式中,eγi為發生比率(odds ratio),它提供了自變量變動一個單位時,發生比變動的倍數。即自變量變動一個單位所帶來的發生比變動的百分比為(eγi-1)×100%,這對回歸系數的解釋較有意義。
三、結果分析
面對幾個模型的實證結果做簡要分析(如表2所示)。職業變量由就業形態和就業能力構成,從表2模型1中可以看出,農民工就業形態變量是由“自雇”和“他雇”構成,在控制其他不變的條件下,與農民工是“他雇”就業形態相比,“自雇”形態的農民工在城市定居意愿顯著增加0.49倍(e0.4-1)④。社會距離感對農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有顯著負向影響,也就意味著農民工與城市居民社會距離感越大對其城市定居產生負面效應。身份認同也是社會距離感另一種呈現,身份認同變量通過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與身份認同為農村人相比,身份認同為城市人的農民工群體在城市定居意愿顯著增加了1.43倍;總體來說,農民工對未來生活抱有樂觀想法的人,對城市定居意愿有顯著影響⑤。模型2中,從社會保障作用機制上看,如果農民工群體的社會保障制度越完善,將有利于農民工抵御未來不確定因素導致預期收入減少,從而對農民工群體城市定居意愿產生正向激勵作用。該論述也在模型2中得到驗證,如果在控制其他變量不變的條件下,相對于社會保障擁有度低的農民工群體而言,社會保障擁有度高的農民工群體在城市定居意愿顯著增加1.19倍。

表1 變量定義及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2 社會保障獲得對農民工城市定居意愿估計結果
(二)分組樣本估計結果與解析
在表3模型3到模型8表示農民工社會保障獲得類別對其家庭城市定居意愿影響。各控制變量的系數與模型1基本保持一致,體現模型的穩健性。從模型2中驗證了社會保障擁有度越高就有利于農民工抵御未來收入減少、預期支出增加風險,對農民工城市定居選擇呈現正相關,但從表3模型3到模型8中估計結果總體上來看,有無養老保險和生育保險對農民工城市定居選擇沒有顯著影響,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這兩項險種覆蓋率低、保障力度不足,從表1中也可以看出,農民工參與養老保險均值為0.287,近七成農民工都沒有參與養老保險,生育保險參與率更低,其均值為0.031。失業保險對農民工城市定居雖沒有顯著影響,但該變量系數為負數,意味著農民工如果處于失業狀態多數不會選擇在城市定居。農民工參與醫療保險變量預期對農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產生負面影響,但估計結果與預期影響方向相反,也就是說,在控制其他變量不變的條件下,與沒參加醫療保險農民工相比,參加醫療保險農民工城市定居意愿顯著下降,這一現象可能解釋是,醫療保險參與中存在逆向選擇,多數身體健康農民工不愿意參加,從表1中醫療保險均值為0.125也能得到體現,反而農民工感知身體狀況較差會積極參加醫療保險,從而出現上述現象。農民工參與工傷保險變量系數為-0.39,且通過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在控制其他變量不變的前提下,與沒有參與工傷保險農民工而言,參與工傷保險農民工城市定居意愿顯著下降了0.33倍(1-e-0.18),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農民工群體工傷保險的參與率較低,在表1中可以看出,參與工傷保險的均值為0.051;二是農民工群體多數工作在建筑行業,工作面臨意外風險較大,其單位愿意為該群體購買工傷保險,多數參與工傷保險農民工群體從事高危工作,面臨風險更高,預期收益不確定性和可能醫療支出增加,從而抵消了工傷保險正面效應,對城市定居產生了負面影響。農民工擁有最低生活保障變量對其城市定居選擇影響與預期方向一致,擁有最低生活保障的農民工會顯著減少城市定居動機。

表3 社會保障獲得對農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分組估計結果
四、結論與進一步討論
文章采用CSS2011調查數據,運用Logit選擇模型,考察農民工社會保障獲得對其城市定居意愿影響。主要結論如下:第一,總體來說,農民工生活水平預期提升,對其在城市定居有顯著的正向推動作用,而生活水平預期為最低對城市定居有負面效應。同時發現,就業能力強、城市居民身份認同、社會距離感等控制變量對農民工城市定居有顯著影響。第二,從社會保障總體獲得來說,農民工社會保障擁有度越高對其城市定居意愿產生正面效應,而社會保障擁有度越低不利于其城市定居。第三,從社會保障分類層面來說,農民工參與醫療保險、工傷保險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對農民工城市定居有顯著影響,而農民工參與養老保險、失業保險以及生育保險對其城市定居沒有顯著影響。
文章從農民工社會保障獲得角度研究其城市定居選擇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并把社會保障從總體層面和分類層面進行細分來研究對農民工城市定居影響,是對農民工住房保障理論研究進一步深入和發展。當然,本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定居意愿的形成是一個動態復雜的變化過程,而文章從CSS2011數據出發,難以控制具體流動經歷、社會保障獲得路徑以及變動對農民工城市定居的影響,現實生活中,更強的城市定居意愿并不意味著必然有實際的定居行為,因此,對于農民工城市定居選擇行為進一步研究空間較大,有待于對相應跟蹤調查數據的收集和解析。第二,文章對于社會保障分類采取的是常規的測度測量指標,相對來說比較相簡單,為進一步探討社會保障對農民工城市居住選擇的影響機制,應該考慮進一步豐富社會保障測量的指標,同時,CSS2011數據也缺少住房公積金測量,這需要進一步展開研究。第三,隨著進城農民工中新生代農民工比例日益增高,且新生代農民工與老一代農民工的進城動機和目標已經產生了變化,因此,在未來的研究中,可以從代際差異視角分析社會保障制度對農民工城市定居選擇影響。
注釋:
①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 (Chinese Social Survey,縮為CSS),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發起的一項全國范圍內的大型連續性抽樣調查項目,目的是通過對全國公眾的勞動就業、家庭及社會生活、社會態度等方面的長期縱貫調查,來獲取轉型時期中國社會變遷的數據資料。調查采用概率抽樣的入戶訪問方式,在全國的128個縣(區),256個街道(鄉、鎮),512個居(村)民委員會開展調查,每次調查全國樣本量約為7000-8000個家庭。
②就業形態變量是“自雇”和“他雇”構成。問卷中測量方式是:“您現在的就業身份屬于哪一種?”答案選項包括雇員、工薪收入者、雇主/老板、自營勞動者以及家庭幫工,將雇主/老板和自營勞動者視為“自雇”,將雇員、工薪收入者以及家庭幫工視為“他雇”。
③社會距離的測量是根據博格達斯社會距離量表,我們選擇本地居民是否愿意與農民工交往來考察本地居民與農民工的社會距離,具體測量問題是:“您是否愿意與農村人成為朋友?”答案選項為很愿意、比較愿意、不太愿意、不愿意以及不好說,故文章把社會距離的變量操作化為虛擬變量,當受訪的本地人很愿意和比較愿意時賦值“0”,表示社會距離小。不太愿意、不愿意或者不好說時賦值為“1”,表示社會距離大。
④為了進一步證明職業變量對農民工城市定居有影響,文章用另一個測量變量是就業能力,通過在就業單位中的職位來反映農民工就業能力,問卷選項是高層管理者、中層管理者、低層管理者以及普通職工,前三項操作化為管理者,后一項操作位非管理者,該變量均值是0.061,在模型1中可以發現如果農民工是管理者的崗位,則顯著影響其城市定居意愿。
⑤具體來說,生活水平預期上升變量系數為0.61,且通過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在控制其他變量不變的前提下,相對于生活水平預期下將的農民工而言,生活水平預期上升農民工定居意愿顯著增加了0.84倍(e0.61-1)。同時在模型1中也發現,生活水平預期略有上升和生活水平預期中等的農民工對城市定居都有顯著正向影響,生活水平預期提高不僅給農民工帶來積極績效反饋,同時農民工自身也在奮斗中獲取自我肯定以及對自己未來有樂觀的預期,從而有利于城市定居意愿。但是生活水平預期略有下將變量對農民工城市定居雖沒有顯著性影響,但該變量的系數為-0.45,系數為負,原因是生活水平下降對農民工產生了非常消極的情緒,降低城市定居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