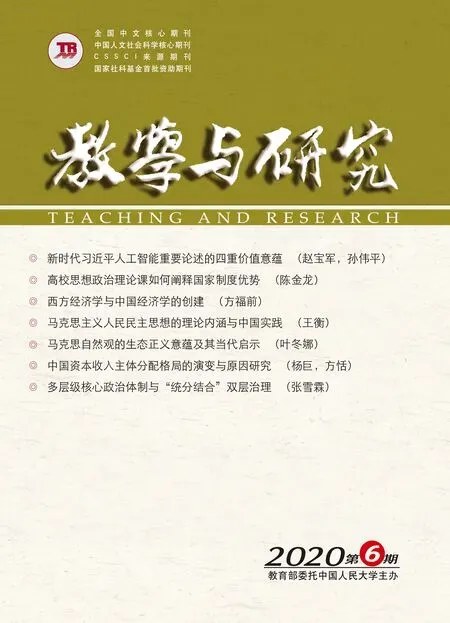中國資本收入主體分配格局的演變與原因研究*
較長時間以來,學者們給予了勞資分配以足夠的重視,然而,在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格局中,勞資分配只是其中的一個維度,資本收入分配和勞動收入分配同樣值得特別關注。根據鮑爾斯等人的論述,剩余產品由誰控制和如何被使用,是理解不同的經濟制度如何運行變革的關鍵所在。(1)[美]塞繆爾·鮑爾斯、理查德·愛德華茲、弗蘭克·羅斯福:《理解資本主義: 競爭、統制與變革》,孟捷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0年,第109-111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需要利用企業部門的利潤再投資和利潤再創新,推動經濟體持續發展,同時,我們也需要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拓寬居民財產性收入渠道,構建長效的資本收入分配機制,讓住戶部門持續共享經濟發展成果。因此,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已經浮現出來:在過去較長的時間里,企業部門、住戶部門等不同主體之間的資本收入分配格局到底發生了什么變化,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種變化,本文試圖回答這兩個問題。
與我國資本收入分配主體格局相關的文獻可以分為兩類:第一,要素收入份額是資本收入分配的基礎,因此需要回顧要素收入份額相關文獻。此類研究關注要素收入份額變動的原因與影響,現有研究發現,產業結構、技術偏向、市場因素、制度質量、統計規則等因素影響了中國要素收入份額。(2)Luo C, Zhang J,“Declining Labor Share: is China’s Case Different”,China & World Economy, 2010,18(6): 1-18;白重恩、錢震杰:《誰在擠占居民的收入——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5期;羅長遠、張軍:《經濟發展中的勞動收入占比:基于中國產業數據的實證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4期;文雁兵、陸雪琴:《中國勞動收入份額變動的決定機制分析——市場競爭和制度質量的雙重視角》,《經濟研究》2018年第9期;王林輝、袁禮:《有偏型技術進步、產業結構變遷和中國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經濟研究》2018年第11期。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文獻中普遍認為,所有制結構變化、勞動者地位的下降、政府沒有發揮應有作用等原因造成了資本收入份額上升。(3)Qi H,“The Labor Share Question in China”,Monthly Review, 2015,65(8): 23-35;Qi H,“Power Relations and the Labour Share of Income in China”,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0,44(3):607-628;齊昊:《勞動者報酬比重下降的“非典型”事實:馬克思主義的解讀》,《當代經濟研究》2011年第10期;喬榛、曹利戰:《我國初次收入分配結構變遷:一個馬克思經濟學視角的經驗分析》,《經濟學動態》 2012年第10期。關于要素收入份額變動的影響,現有文獻主要基于后凱恩斯主義的巴杜里-馬格林模型以及該模型的擴展,(4)Bhaduri A, Marglin S,“Unemployment and the Real Wage: the Economic Basis for Contesting Political Ideologies”,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0, 14(4): 375-393;Stockhammer E,“Wage-led versus Profit-led Demand: What Have We Learned? A Kaleckian-Minskyan View”,Review of Keynesian Economics, 2017,5(1): 25-42.利用該模型,現有文獻研究了中國要素收入份額變動對消費水平、總需求和生產率等宏觀變量的影響。(5)臧旭恒、賀洋:《初次分配格局調整與消費潛力釋放》,《經濟學動態》2015年第1期;鄒薇、袁飛蘭:《勞動收入份額、總需求與勞動生產率》,《中國工業經濟》2018年第2期。
第二,財產性收入是資本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需要回顧財產性收入相關文獻。1988—2009年,中國城鎮居民財產性收入增長速度較快,從人均7.5元上漲到人均238元,但是財產性收入在居民總收入中的比重仍然非常低,從1988年的0.4%上升到2009年的0.9%,2007年最高,但是也只有1.7%,同時,財產性收入來源呈現多元化趨勢,財產性收入差距較大,財產性收入基尼系數從0.571上升到0.745。(6)Chi W,“Capital Income and Incom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2, 40(2): 228-239;國家統計局城市司、廣東調查總隊課題組:《城鎮居民家庭財產性收入研究》,《統計研究》2009年第1期;遲巍、蔡許許:《城市居民財產性收入與貧富差距的實證分析》,《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2年第2期。1995—2015年,農村人均財產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都在3.5%以下,中西部地區農民財產凈收入大大低于東部地區,農地“三權”分置改革導致農民財產性收入加速增長,同時也使得農民財產性收入依賴于資源稟賦而呈現收入分化。(7)陳曉楓、翁斯柳:《 “三權”分置改革下農民財產性收入的特點和發展趨勢》,《政治經濟學評論》2018年第2期。造成我國居民財產性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包括學歷背景、政治身份、地區差異和金融約束等宏觀因素。(8)寧光杰:《居民財產性收入差距: 能力差異還是制度阻礙?——來自中國家庭金融調查的證據》,《經濟研究》2014年第1期;寧光杰、雒蕾、齊偉:《我國轉型期居民財產性收入不平等成因分析》,《經濟研究》 2016年第4期。
與這些研究相比,本文主要有如下創新:第一,不同于現有關于資本收入份額或者居民財產性收入的文獻,本文研究了資本收入在非金融企業部門、金融機構部門、政府部門和住戶部門等主體之間的分配格局,經濟體的資本收入分配實際上可以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資本收入在各主體之間的分配;第二個層次是資本收入在各主體內部的分配,現有關于資本收入份額的文獻把各主體當成一個整體,而現有關于居民財產性收入的文獻只是集中分析住戶主體內部資本收入分配的一個方面,因此本文的研究是對現有文獻的補充。第二,借鑒馬克思的思想對資本收入分配主體格局變動進行了原因分析,由于不同部門具有不同的資本收入變化趨勢,現有關于總體資本收入份額的影響因素分析自然無法完全適用于不同部門的分析,因此本文的原因分析是對現有文獻的擴展。本文接下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基于資金流量表考察了資本收入分配的主體格局,第三部分進行了原因分析,最后進行總結和展望并提出政策建議。
一、中國資本收入分配的主體格局:2000—2017年
《中國統計年鑒》資金流量表分為實物交易(非金融交易)表和金融交易表,其中,實物交易表提供了增加值、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和財產收入等數據,涉及非金融企業、金融機構、政府和住戶等多個部門,這些數據可用于資本收入分配的主體格局分析。在當前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部門增加值等于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固定資產折舊和營業盈余四者之和,現有文獻一般將固定資產折舊和營業盈余之和定義為資本收入,(9)白重恩、錢震杰:《國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統計數據背后的故事》,《經濟研究》2009年第3期。到目前為止,資本收入尚未進行財產收入分配,因此可以將此時資本收入在不同主體之間的分配狀況界定為財產收入分配之前的資本收入主體分配格局。接下來,各部門基于投入的資本類型進行財產收入分配,如借貸資本所有者獲得利息收入,股權所有者獲得紅利或參與利潤分配,自然資源所有者因出讓自然資源而獲得地租等,在各部門完成這些財產收入分配之后,可以將此時資本收入在不同主體之間的分配狀況界定為財產收入分配之后的資本收入主體分配格局。
具體來說,從部門增加值中扣除勞動者報酬和生產稅凈額可得到部門資本收入(前),即固定資產折舊與營業盈余之和,將部門資本收入(前)除以四部門合計資本收入可得到部門資本收入占比(前),從而形成財產收入分配之前的資本收入主體分配格局。接著,從部門資本收入(前)中加上財產收入凈流入(即應收財產收入減去應付財產收入)得到部門資本收入(后),再除以四部門合計資本收入而得到資本收入占比(后),從而形成財產收入分配之后的資本收入主體分配格局。現有《中國統計年鑒》提供了1992—2017年的資金流量表,然而1992—1999年和2000—2017年前后兩個階段的編制方法存在較大差異,因此本文只采用后一個階段的資金流量表,所考察的數據區間為2000—2017年。(10)《中國統計年鑒2012》提到,根據財政部提供的全口徑財政收支詳細資料、國家外匯管理局修訂后的國際收支平衡表數據,以及部分交易項目編制方法的調整,系統修訂了2000—2009年實物交易資金流量表。1992—1999年資金流量表正在修訂之中。經過比較,我們發現修訂后的資金流量表和原資金流量表存在較大差異,因此只采用了修訂后的資金流量表。
值得特別說明的是住戶部門。在資金流量表中,住戶部門之所以有增加值和勞動者報酬的運用(11)非金融企業部門、金融部門和政府部門是勞動者報酬的“運用”部門,住戶部門既是勞動者報酬的“來源”部門,也是勞動者報酬的“運用”部門。等指標,就是因為住戶部門的統計中包含了個體工商戶。(12)李揚、殷劍峰:《中國高儲蓄率問題探究——1992—2003年中國資金流量表的分析》,《經濟研究》2007年第6期。除此之外,基于國家統計局城鄉住戶調查,《中國統計年鑒》“人民生活”篇還提供了居民工資性收入、經營凈收入、財產凈收入、轉移凈收入等居民收入指標。這些居民收入指標與資金流量表關于住戶部門的統計有何關聯呢?基于文本分析和調查了解,我們整理了兩種統計口徑的聯系和區別。第一,對于個體工商戶來說,資金流量表先計算個體工商戶的增加值,然后采用分劈的辦法計算增加值構成項目,(13)住戶部門個體經濟的勞動者報酬一般按照特定比例分劈計算,行業不同計算方法也存在差異,具體參見《中國資金流量表編制方法》附件一“機構部門增加值測算方法”。即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固定資產折舊和營業盈余,而城鄉住戶調查則將凈收入(經營收入-經營費用-生產性固定資產折舊-生產稅)計入居民“經營凈收入”,(14)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統計指標解釋,經營凈收入是指“住戶或住戶成員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所獲得的凈收入,是全部經營收入中扣除經營費用、生產性固定資產折舊和生產稅之后得到的凈收入”,計算公式為:經營凈收入=經營收入-經營費用-生產性固定資產折舊-生產稅。可見“經營凈收入”中沒有區分“勞動者報酬”和“營業盈余”。第二,對于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和具有法人資格的私營企業(15)私營企業包括私營獨資企業、私營合伙企業、私營有限責任公司和私營股份有限公司等四種類型,其中,私營有限責任公司和私營股份有限公司均屬于企業法人,根據《中國私營經濟年鑒》(2008.6—2010.6),截止2010年6月30日,這兩類法人企業的戶數占私營企業總戶數的比例為83.1%,分支機構比例為95.1%,投資者比例為90.3%,雇工人數比例為83.0%,注冊資本比例為94.0%。等法人單位而言,資金流量表將高管和員工工資記入“勞動者報酬”,將居民從企業獲得的利息、紅利等財產收入記入“財產收入”,未分配利潤屬于企業部門,而城鄉住戶調查則將高管和員工工資記入“工資性收入”,居民所獲財產收入記入“財產性收入”,未分配利潤也屬于企業部門。第三,對于不具備法人資格的私營企業來說,資金流量表仍然按照法人單位處理,而城鄉住戶調查則將員工工資記入“工資性收入”,將居民所獲財產收入記入“財產性收入”,如果住戶是私營企業的所有者并且參與了經營,那么該住戶所獲利潤分配記入“經營凈收入”,未分配利潤依然屬于企業部門。(16)考慮到企業需要資金用于再生產,國家統計局不會將私營企業所有利潤劃歸居民“經營凈收入”。
可以看到,雖然資金流量表的住戶收入統計和城鄉住戶調查的居民收入統計存在著比較復雜的對應關系,但是有兩點是比較確定的:第一,對于個體工商戶來說,因為不采取企業形式,個體工商戶與住戶之間沒有界限,個體工商戶完全屬于住戶部門;第二,對于企業來說,無論采取何種具體的組織形式,企業與住戶之間都存在著比較清晰的界限,住戶能夠從企業獲得工資、利息、紅利等收入,但是企業的固定資產折舊、營業盈余或者未分配利潤等收入仍然屬于企業部門。因此,我國的資本收入分配確實可以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資本收入在各主體之間的分配,第二個層次是資本收入在各主體內部的分配,本文對于第一個層次的分析有助于架起從總量資本收入到各主體內部資本收入分配之間的橋梁。
政府部門也需要特別說明,資金流量表所界定的政府部門不同于通常意義上的黨和國家政府機構,后者只是前者的一個組成部分。根據《資金流量表編制方法》,政府部門由各種類型具備法人資格的常住行政單位事業單位組成,這種單位一般屬于全額預算單位或者差額預算單位;根據《中國經濟普查年度資金流量表編制方法》,政府部門增加值包括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研究和試驗發展等8個行業的全部增加值和教育、衛生等5個行業的部分增加值,(17)根據《中國經濟普查年度資金流量表編制方法》,政府部門增加值=與政府部門對應的產業部門增加值之和=(1)研究和試驗發展+(2)地質勘查業+(3)水利管理業+(4)環境管理業+(5)公共設施管理業+(6)社會保障業+(7)社會福利業+(8)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9)專業技術服務業×80%+(10)科技交流和推廣服務業×80%+(11)(教育增加值-教育個體經營戶增加值)×80%+(12)(衛生增加值-衛生和福利業個體經營戶增加值)×80%+(13)(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增加值-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個體經營戶增加值)×50%。其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包括中國共產黨機關、國家機構、人民政協和民主黨派等子行業。以這些標準為基礎,資金流量表提供了政府部門增加值、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財產收入等指標。
(一)財產收入分配之前的資本收入分配主體格局
圖1呈現了財產收入分配之前的資本收入主體分配格局。總體上,非金融企業部門獲得了最多的資本收入,其次是住戶部門、金融機構部門和政府部門。2000—2017年,非金融企業部門資本收入占比(前)在62.2%~69.6%的區間波動并且看不出明顯的趨勢,如果取三年移動平均值,則從65.0%小幅上升到66.4%;金融機構部門則呈現快速上升的趨勢,從2000年的0.9%上升到2017年的12.4%,累計上升11.5個百分點;2000—2017年,政府部門的資本收入占比(前)在2.3%~4.2%的區間波動而且也看不出明顯的趨勢,如果取三年移動平均值,則從3.2%小幅下降到2.9%;住戶部門資本收入占比(前)也有所波動但能看出明顯的趨勢,從2000年的33.2%下降到2017年的17.4%,累計下降多達15.8個百分點。這些數字表明,在財產收入分配之前,非金融企業部門在整個時期都獲得了較多的資本收入,金融機構部門在時期開始時獲得的資本收入較少,但在整個時期之內,越來越多的資本收入快速流入了金融機構部門,政府部門資本收入始終較少,住戶部門在時期開始時獲得了相對較多的資本收入,占據著資本收入的重要地位,但在整個時期內,越來越多的資本收入流出了住戶部門。

圖1 財產收入分配之前的資本收入分配主體格局(2000—2017年)注:除非特別說明,本文圖表數據均來源于2000—2017年中國資金流量表
(二)財產收入分配之后的資本收入分配主體格局
將部門財產收入凈流入除以四部門合計資本收入得到財產收入凈流入比率(表1)。2000—2017年,在所有年份里,非金融企業部門的財產收入流入都小于財產收入流出,財產收入凈流入比率從-9.2%下降到-12.2%;在大部分年份里,金融部門財產收入流入大于財產收入流出,財產收入凈流入比率有所波動但總體保持不變;政府部門從-1.1%上升到4.1%;住戶部門財產收入凈流入有所波動且看不出明顯趨勢,如果取三年移動平均值,總體從5.1%小幅上升至6.2%。這些結論表明,財產收入從非金融企業部門流向了金融部門、政府部門和住戶部門,非金融企業部門支出的財產收入有所增加,住戶部門獲得了最多的財產收入,但是絕對水平偏低且沒有明顯增長,此外,政府部門所獲財產收入有所增長。

表1 財產收入分配的主體格局(2000—2017年)

圖2 財產收入分配之后的資本收入分配主體格局(2000—2017年)
圖2呈現了財產收入分配之后的資本收入主體分配格局。總體上,非金融企業部門仍然獲得了最多的資本收入,其次是住戶部門、金融部門和政府部門。由于非金融企業部門為財產收入凈流出部門,其余三個部門為財產收入凈流入部門,因此非金融企業部門資本收入占比(后)小于資本收入占比(前),其余三個部門的資本收入占比則相比之前普遍上升。2000—2017年,非金融企業部門資本收入占比(后)仍然有所波動,如果取三年移動平均值,則從55.4%下降到53.6%,總體小幅下降1.8個百分點,正是由于非金融企業部門財產收入凈支出的增加,導致財產收入分配之后的資本收入占比有所下降;金融部門變動趨勢非常明顯,從2000年的2.3%上升到2017年的13.5%,累計上升11.2個百分點,上升幅度與之前基本持平;政府部門的變動趨勢也較為明顯,從2000年的2.5%上升到2017年的7.0%,累計上升4.5個百分點;住戶部門下降趨勢依然非常明顯,從2000年的38.8%下降到2017年的23.8%,累計下降幅度仍然多達15.0個百分點。可以看到,正是由于財產收入從非金融企業部門流向了金融部門、政府部門和住戶部門,導致后三個部門資本收入占比(后)的絕對水平提高,但是財產收入分配并沒有明顯改變原有資本收入分配的主體格局,金融部門仍然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資本收入占比,住戶部門仍然獲得了越來越少的資本收入占比。唯一有所不同的是政府部門,在財產收入分配之后,政府部門資本收入占比有所上升。
二、中國資本收入分配主體格局變動的原因分析
前面的測算結果表明,資本收入分配的主體格局在過去十來年中發生了明顯變化,而且財產收入分配也沒有在根本上改變這種變化趨勢,那么我們就需要回答,在財產收入分配之前,資本收入分配的主體格局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變化?特別是,為什么金融部門資本收入占比快速上升而住戶部門快速下降?
(一)資本收入占比變動的原因分解
利用部門資本收入占比(財產收入分配之前,下同)的定義公式,通過簡單變換,可以表示為部門資本收入份額、部門增加值比率和總資本收入份額倒數的乘積。
(1)
其中,c為部門資本收入占比,s為部門資本收入份額,z為部門增加值比率,u為總資本收入份額,p為部門資本收入,m為國內各部門合計資本收入,a為部門增加值,v為國內各部門合計增加值。
我們對(1)式求變化率,得到(2)式。

(2)
根據(2)式,我們得到了表2,可以看到:在財產收入分配之前,非金融企業部門資本收入份額總體保持不變,而增加值比率年均增長0.6%,總資本收入份額年均增長0.3%,導致資本收入占比年均增長0.5%,可見非金融企業部門資本收入占比之所以小幅上升,是由于部門增加值比率有所擴大,而不是源于總資本收入份額的下降或者部門資本收入份額的提高;金融機構部門資本收入份額年均增長12.5%,增加值比率年均增長4%,扣除總資本收入份額的負向影響,導致資本收入占比年均增長16.6%,可見金融機構部門之所以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資本收入,首要原因是部門資本收入份額的上升,次要原因是部門增加值比率的擴大;政府部門資本收入份額年均下降1.6%,而增加值比率年均增長0.6%,加之總資本收入份額的負向影響,導致資本收入占比年均下降1.3%,可見政府部門資本收入占比之所以小幅下降,主要是因為部門資本收入份額的下降和部門增加值比率的上升;住戶部門資本收入份額年均下降1.2%,增加值比率年均下降2.3%,和總資本收入份額一起導致資本收入比率年均下降3.7%,可見住戶部門資本收入占比之所以快速下降,原因是部門增加值比率和資本收入份額的“雙降”。在此過程中,總資本收入份額對所有部門均有所影響,但皆不是最主要的影響因素。就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來說,以上的原因闡述仍然是不夠的,還需要就深層原因展開分析。

表2 資本收入主體分配格局及影響因素年均增長率(2000—2017年)
(二)深層原因分析
首先來分析總資本收入份額。第一,現有研究發現,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勞動收入份額開始快速下降,資本收入份額開始快速上升,那么為什么本文所計算的總資本收入份額年均增長率只有0.3%呢?實際上,我國勞動收入份額自2008年開始觸底反彈,(18)趙峰、陳寶林、章永輝、季雷:《收入分配、需求體制與經濟增長——基于“馬克思-凱恩斯-卡萊茨基”理論的經驗研究》,《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8年第10期。在我們所考察的區間內,總資本收入份額先上升后下降,從2000年的35.2%上升到2008年的39.6%,然后下降到2017年的37.0%,2017年比2000年僅僅高出1.8個百分點,自然會導致資本收入份額年均增長率較低。第二,現有政治經濟學相關文獻認為,總資本收入份額代表了所有制結構變化、勞動者地位和政府作用等反映階級力量對比的因素,在考察時間段的前期,國有經濟比重的下降、勞動者組織力量下降、政府較少地維護勞動者利益等因素都會導致總資本收入份額上升。有研究發現,2007年以來,由于工會組織覆蓋范圍提升、新生代農民工集體行動能力提升、城市工人工資與農民工工資比例的減小、非正規就業比重的下降、國有經濟比重下降速度減小、社會保障覆蓋面提升等原因,工人組織力量和結構力量得到提升,(19)李怡樂:《工人力量的變化與中國經濟增長——基于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據的分析》,《政治經濟學評論》2016年第2期。總資本收入份額因此開始下降。在所考察的整個時間段內,總資本收入份額的總體變動幅度較小,導致其對資本收入主體分配格局的影響較小。
再來分析部門增加值比率。一般來說,部門增加值比率的變動反映的是不同資本之間的動態競爭與結構演變。第一,經濟體產業結構演變會導致服務業增加值和金融業增加值上升,進而引起政府部門增加值和金融機構部門增加值上升。隨著經濟總量不斷擴大,產業結構也不斷變遷,在考察時間段內,正處于服務業不斷上升的階段,金融業比重自然不斷上升。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提供各行業增加值數據可計算出,2000—2017年,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從37.8%上升到51.9%,我國金融業增加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從4.8%上升到8.0%。在資金流量表中,劃歸政府部門的行業均屬服務行業,而金融業增加值則完全劃歸金融機構部門,因此政府部門增加值和金融機構部門增加值都會上升。(20)根據《中國經濟普查年度資金流量表編制方法》,金融機構部門增加值=銀行部門增加值+證券部門增加值+保險部門增加值+其他金融機構部門增加值,其中,銀行部門增加值=GDP生產核算中的銀行業增加值,證券部門增加值=GDP生產核算中的證券業增加值,保險部門增加值=GDP生產核算中的保險業增加值,其他金融機構部門增加值=GDP生產核算中的其他金融活動增加值。非金融部門、住戶和政府等部門增加值及構成項的統計均不涉及金融行業。第二,除了產業變遷導致部門增加值比率變動之外,還需要注意不同規模資本之間的動態競爭。馬克思談到,企業之間的競爭會導致優勝劣汰,進而導致資本集中和資本集聚。一般來說,非金融企業部門的企業規模較大,住戶部門個體工商戶規模較小,大中型企業往往能夠利用其規模優勢壓縮個體經濟的市場規模和生存空間,進而導致住戶部門增加值比率下降,非金融企業部門增加值比率上升。
最后來分析部門資本收入份額。之所以放在最后來考察,是因為在解釋部門資本收入份額的時候需要特別謹慎。如上所述,總資本收入份額取決于所有制類型、勞動者地位和政府作用等勞資力量對比因素,那么部門資本收入份額是否也能夠如此解釋呢?
第一,非金融企業部門是 “實體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上述影響總資本收入份額的因素也會影響非金融企業部門。正是由于這個原因,非金融企業部門資本收入份額和總資本收入份額呈現大體相同的變化趨勢,非金融企業部門資本收入份額與總資本收入份額的相關系數達到了0.846,在我們所考察的區間內,非金融企業部門資本收入份額先上升后下降,從2000年的39.3%上升到2008年的44.9%,然后下降到2017年的40.3%,2017年比2000年高1.0個百分點。在整個考察時間段,非金融企業部門資本收入份額變化幅度并不大,自然也不是部門資本收入占比變動的主要原因。
第二,金融部門資本收入份額迅速上升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在考察時間段內,金融部門資本收入份額從2000年的7.8%迅速上升到2008年的59.1%,而后緩慢下降到2017年的57.8%,也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表明金融部門的資本收入份額也受到了所有制類型、勞動者地位、政府作用等因素的影響。但是,在整個時期內,相對于非金融企業部門,金融部門資本收入份額變化幅度非常大而且異常特殊,從而需要進行詳細的考察。
首先,在考察時間段的初期,金融部門資本收入份額極低。我們認為有兩個原因:一是銀行體制不健全導致銀行不良債務高啟。2000年左右,我國銀行部門面臨極高的不良資產率,即使在不良資產已經開始處置的情況下,2001年末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債權仍然達到了貸款余額的25.37%,(21)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在2002年3月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宣布了該數據,援引自吳敬璉:《銀行改革:當前中國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世界經濟文匯》2002年第4期。意味著此時銀行部門盈利能力極弱,2000年四大國有銀行的平均資本利潤率僅為2.8%,平均資產利潤率僅為0.1%(參見圖3),進而表現出極低的資本收入份額。二是資產流量表采取了特殊的處理辦法計算銀行部門增加值與構成項目,(22)見后文進一步的說明,關于金融部門增加值和財產收入等指標統計的特殊性也可參見白重恩和錢震杰的分析。白重恩、錢震杰:《誰在擠占居民的收入——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5期。極高的不良率必然對應于極低的服務質量和服務產出,進一步表現為非常小的增加值和非常低的資本收入份額。其次,2000—2008年,金融部門資本收入份額提升速度非常快,2004年超過非金融企業部門之后持續攀升,兩者的差距持續拉大。我們認為也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我國國有銀行不良率過高,我國于1999年成立了四大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專門負責剝離和處置四大行的不良貸款,當不良貸款被剝離時,四大行的盈利能力在短時間之內迅速攀升(參見圖3);二是我國金融部門以銀行為主,而商業銀行能夠享受國家法定的固定利差,較低的存款利息和較高的貸款利息給商業銀行帶來了較高收益,同時也抬高了實體企業的財務費用,壓縮了實體企業的財務收益,(23)陸岷峰、張惠:《金融產業資本與實體經濟利潤合理分配研究》,《經濟學動態》2012年第6期。使得商業銀行具有較強的價值轉移能力,體現為金融部門資本收入份額迅速提升。再次,2008—2017年,金融部門資本收入份額絕對水平較高,年均絕對水平比非金融部門高出16個百分點,而且下降幅度明顯小于非金融企業部門,這段時間內只下降了1.3個百分點。我們認為這種變化態勢與經濟金融化趨勢有關。2008年以來,我國非金融企業杠桿率迅速增加,表明中國存在較為明顯的經濟金融化趨勢,(24)譚小芬、尹碧嬌、楊燚:《中國非金融企業杠桿率的影響因素研究: 2002—2015 年》,《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田佳禾:《當前中國經濟金融化的水平和趨勢——一個結構的和比較的分析》,《政治經濟學評論》2015年第3期。經濟金融化趨勢與仍然存在的息差優勢相結合,非金融企業需要將越來越多的利潤用于支付利息,從而有效保證了金融部門的價值轉移能力,金融部門資本收入份額表現出非常強的“韌性”。因此我們認為,由于銀行不良貸款剝離、固定息差優勢和經濟金融化趨勢等因素的共同作用,金融部門盈利能力總體快速提升,最終表現為銀行部門資本收入份額總體大幅提高。

圖3 四大行平均資本利潤率和平均資產利潤率(2000—2017年)注: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金融年鑒》,四大行平均資本利潤率=四大行凈利潤之和/四大行凈資產之和,四大行平均資產利潤率=四大行凈利潤之和/四大行總資產之和,四大行是指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
第三,在資金流量表的統計中,住戶部門擁有的是個體工商戶,個體工商戶實行自我雇傭和自我組織,沒有雇傭勞動也就不存在與雇傭企業相類似的勞動者報酬,住戶部門沒有實際存在的勞資雙方,因此資本收入份額自然也就不能反映勞資雙方的相對地位。在考察時間段內,住戶部門資本收入份額的變化趨勢與總資本收入份額存在明顯差異,住戶部門資本收入份額先從2000年的36.4%下降到2008年的32.0%,接著繼續下降到2017年的29.9%。實際上,住戶部門勞動者報酬都是按照特定比例分劈計算的結果,雖然行業不同分劈計算方法亦存在差異,但是只要分劈方法不隨時間變化,那么計算方法本身就不會是資本收入份額變動的主要影響因素。我們傾向于認為,在考察時間段的前期,在與雇傭型企業的激烈競爭中,個體經濟還能憑借靈活性和便利性而在小區域內占據優勢,個體經營者自我雇傭明顯優于受雇于其他企業,個體工商戶具備較強的盈利能力,從而表現出個體經營者資本收入份額較高,但是在考察時間段內,隨著信息技術特別是移動互聯網產業技術的飛速進步,大型在線購物網站快速發展,全國高效物流快遞網絡逐漸形成,許多個體經濟競爭力快速下降,這些經營者逐漸發現自我雇傭已經無法明顯優于受雇于其他企業,個體工商戶盈利能力減弱,最終表現為個體經營者資本收入份額明顯下降。
第四,政府部門資本收入份額呈現出和總資本收入份額類似的變化趨勢,表明政府部門也受到了相同因素的影響,同時,在資金流量表的統計中,劃歸政府部門的單位普遍具有較弱的營利性,導致政府部門資本收入份額的絕對水平偏低。在考察時間段內,政府部門資本收入份額從2000年的16.2%上升到2008年的17.9%,然后下降到2017年的12.3%。由于資金流量表關于政府部門的統計中包括了教育、醫療等進行過市場化改革的部門,所以政府部門資本收入份額也受到了市場化程度、勞動者地位和政府作用等因素的影響,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同時,市場化改革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市場化程度總體前期較低后期較高,導致相對于非金融企業部門,前期上升幅度較小而后期下降幅度基本持平。還需要看到,就絕對水平而言,政府部門資本收入份額的絕對水平較低,比非金融企業部門資本收入份額平均低28個百分點,盡管一些政府部門進行過市場化改革,但是相對于完全的市場化部門來說,政府部門的公益屬性相對較強而營利性相對較弱,進而表現出較弱的“盈利能力”和較低的部門資本收入份額。
把這些表現“連結”起來,大概可以呈現如下的“故事”:住戶部門的個體工商戶與非金融企業部門的大中型法人企業在市場上展開競爭,無論在規模上還是企業形式上,個體工商戶都處于相對劣勢,加之新經濟對個體經濟的沖擊,個體工商戶的市場份額逐漸被非金融企業部門蠶食,導致住戶部門資本收入相對下降;然而,非金融企業部門只是獲得了更多的市場份額,所獲資本收入卻沒有明顯提升,重要原因就是金融部門能夠從非金融部門轉移較多的利潤,經濟金融化趨勢加強了金融部門的價值轉移能力。與此同時,政府部門提供了越來越多的增加值,但是由于市場化改革進程、勞動者地位等因素的共同影響,最終導致所獲資本收入有所下降。在整個過程中,由于勞動者力量的前降后升和社會保障覆蓋面在后期擴大等原因,導致總資本收入份額和非金融企業部門資本收入份額在整個考察時間內的變化幅度并不大,自然也無法成為主要影響因素。
(三)進一步的說明
1.個體經濟發展情況的其他證據。
相對來說,住戶部門個體工商經濟由于數據缺乏而沒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因此個體工商經濟的發展情況似乎需要更多證據。采用2000—2017年資金流量表提供的住戶部門增加值作為個體經濟增加值,從中扣除生產稅凈額得到個體經濟凈增加值,再通過《中國統計年鑒》獲得全國個體經濟就業人數,個體經濟增加值除以個體就業人數得到個體經濟人均增加值,個體經濟凈增加值除以個體就業人數得到個體經濟人均凈增加值;將全國GDP除以全國就業人口得到就業人員人均GDP;通過《中國統計年鑒》直接獲得全國就業人員平均工資數據,最后利用這些數據計算兩個相對比率:個體經濟人均增加值/全國就業人員人均GDP和個體經濟人均凈增加值/全國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參見圖4)。可以看到,2000年個體經濟人均增加值達到了全國就業人員人均GDP的4.58倍,意味著個體工商戶的確創造了較多的社會價值,然而這種情況持續下行,到了2017年,個體經濟人均增加值與全國就業人員人均GDP的比率下降到1.17,意味著個體工商戶的價值創造能力已經逐漸回歸到全國平均水平;2000—2017年,個體經濟人均凈增加值與全國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的比率也一路下滑,2017年下降到1.67,個體工商戶是一種自我雇傭和自我組織的生產模式,意味著個體工商戶所能獲得的包括自我雇傭勞動者報酬、固定資產折舊、自我雇傭利潤等收入在內的全部收入僅僅為全國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的1.67倍,說明無論如何劃分凈增加值,個體工商戶已經不能獲得較多的資本收入。

圖4 個體經濟發展情況分析(2000—2017年)數據來源: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2.金融部門財產收入凈流入比率較低,為什么資本收入占比會快速上升?
金融部門財產收入凈流入比率在-1%和0.5%之間波動(參見表1),似乎意味著金融部門并沒有通過存貸款等金融業務獲得較多的利潤,然而無論是否考慮財產收入分配,金融部門資本收入占比均快速上升(參見圖1和圖2)。之所以產生似乎自相矛盾的結果,根本原因是資金流量表的編制方法。以非金融企業部門從金融機構貸款為例,在資金流量表中,非金融企業部門貸款利息支付=非金融機構實際應付貸款利息-對其從金融機構得到貸款分攤的虛擬服務費,而金融機構貸款利息的獲得=金融機構實際應收利息-對金融機構貸款的虛擬服務費,其中金融機構貸款的虛擬服務費=金融中介虛擬服務產出×金融機構實際應收利息÷(金融機構實際應收利息+金融機構實際應付利息)。(25)參見國家統計局:《中國資金流量表編制方法》,中國統計出版社, 1997年,第17-18頁。簡單來說,資金流量表的計算方法將一部分貸款利息收入算作了金融部門的服務費,一方面導致金融部門財產收入流入的下降,另一方面導致金融部門增加值的增加和資本收入的增加。如果非金融企業部門在金融部門存款,資金流量表則將在存款利息之上加上虛擬服務費,導致金融部門財產收入流出的上升。資金流量表之所以采用這種編制方法,是因為金融部門中介活動的價值主要通過利息收支來體現,如果將利息收支全部看作財產收入,那么就無法準確體現金融部門的增加值。所以我們才會看到,金融部門財產收入凈流入比率較低,資本收入占比卻快速上升。
三、結論、展望和政策建議
關于資本收入分配,以往文獻普遍研究資本收入份額或者財產性收入分配,而對資本收入分配的主體格局缺乏足夠的關注。本文基于資金流量表考察了2000—2017年我國資本收入在非金融企業部門、金融部門、政府部門和住戶部門等主體之間的分配格局與變動情況,發現在財產收入分配之前,最為明顯的特征是住戶部門資本收入占比快速下降和金融部門資本收入占比快速上升,財產收入分配導致住戶部門資本收入占比提高了5-6個百分點,但沒有改變原先的變化趨勢。基于資本收入占比的定義公式進行原因分解,發現住戶部門資本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個體工商戶增加值比率和盈利能力的“雙降”,根本原因是互聯網經濟的沖擊和大中型企業的競爭,金融部門所獲資本收入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盈利能力與增加值比率的“雙升”,主要原因是銀行不良資產的剝離、固定息差優勢的存在和經濟金融化趨勢的加強。
本文對于后續研究可能具有重要意義。第一,除了分析全國和地區層面的要素收入份額和居民財產性收入分配之外,還可以關注資本收入分配的主體格局。剩余產品的支配和使用問題非常重要,因此需要關注哪些主體擁有資本收入,各自擁有的資本收入數量,以及如何使用這些資本收入等,可能都是理解中國經濟運行的重要切入點。第二,居民財產性收入差距和居民資本收入差距容易被低估。在現有的統計框架中,企業和居民之間存在著清晰的界限,較多的資本收入并沒有進入居民收入的統計范圍內,從而容易低估居民收入差距。目前,很多微觀數據提供了居民收入指標,這些數據對于經營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等居民收入指標的界定并不相同,研究者可能需要關注這些差異。第三,金融部門的國有比重較高,這給資本收入的公平分配留下了較大的空間。金融部門獲得了較多的資本性收入,我們需要分析金融和實體的協調發展機制,將金融部門的利潤率與實體經濟的發展壯大緊密結合起來;同時,我國金融部門由銀行部門主導,而銀行部門由國有銀行主導,這就給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和收入差距的改善留下了較大的空間。
本文也有一些比較緊要的政策建議。第一,處理好國有企業做大做優做強與國有企業利潤共享之間的關系。黨和政府的多次重要會議都提到,要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會提高居民收入,而居民財產性收入差距較大可能會擴大居民收入差距,能夠權衡好這兩個方面的可行選擇是國有企業的全民利潤共享,既能夠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還能改善居民收入差距。根據本文的研究,特別需要將四大行等金融國企納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并且要將更多比例直接轉入社保基金或用于民生支出,全面落實并合理提高國有股權劃歸社保基金的比例要求。同時,加強國有企業的利潤共享并不能“舍本逐末”,持續高水平利潤共享的前提仍然是不斷發展壯大國有企業,因此需要兼顧國企發展壯大與國企利潤共享。第二,提高銀行理財能力,健全直接資本市場,使投資者獲得穩定的投資回報。當前居民所獲凈財產收入只占到全部資本收入的6%左右,毫無疑問這是個比較低的水平,因此要加強銀行的規范經營,提高銀行為客戶特別是普通客戶理財的能力,同時努力建設直接資本市場,使得投資者能夠通過股票和債券投資獲得穩定的合理回報。第三,保護住戶部門個體工商業。由于個體工商業的非剝削性質,我國在1982年《憲法》中就已經確認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迄今為止已經出臺了許多針對個體工商戶的優惠政策,(26)2008—2013年,政府連續出臺相關減免行政事業性收費的文件,其中為個體工商戶減免的費用多達25項;2019年最新相關政策規定,對月銷售額10萬元以下的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免征增值稅。參見汪海粟、姜玉勇:《個體工商戶的行業分布、生存狀態及其或然走向》,《改革》2014年第4期。個體戶生產稅凈額占增加值的比率從2000年的3.6%下降到2017年的2.8%,然而個體經濟的生存空間仍然被壓縮。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個體工商戶以靈活見長,但是無論是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個體工商戶都沒有優勢,在企業內部也已經形成了分化趨勢,大企業和大資本一般更有可能在競爭中勝出。當前,要實施更具有照顧性和偏向性的優惠政策,鼓勵商業銀行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給個體戶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