鄰居,最熟悉的陌生人
劉晗

《后窗》劇照。
壓力巨大、檔期全滿、信息透明……這一系列的城市化進程使噓寒問暖、閑時尬聊的傳統鄰里關系成了過去式,層出不窮的社會騙局與陷阱造就了不少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這些在無意中為自己設下心理防線的人,究其背后的社會問題不無原因。
近在咫尺,殺機四起
據《鏡報》報道,新冠肺炎疫情隔離期間,俄羅斯中部發生了一起槍擊案,一名30多歲的男子用獵槍殺死了自家樓下的5個鄰居和路人,起因是這名男士嫌鄰居太吵而怒起殺意。幾乎是同一時間,泰國《民族報》也刊出了當地兩鄰居因噪音過大而發生爭執,導致一人被槍殺身亡的消息。諸如此類同在一個屋檐下、積怨已久醞釀殺機的新聞不勝枚舉。是什么原因讓見面相視一笑的鄰居演變成一言不合大打出手,甚至升級為相互殘殺的仇家?那些余音繞梁的詭秘“兇音”勾起了壓抑已久戾氣的升騰,加之忍無可忍的浮躁情緒,噪音侵犯到了自家領地,無異于對心煩意亂負能量爆棚的鄰居火上澆油,同理心也就此失效,沖動的魔鬼便附上身來。
當鄰居成了“惡魔”,藝術家從那一扇扇窗口看出了端倪,故事便就此展開。最有名的當屬希區柯克執導的經典懸疑電影《后窗》,攝影記者杰弗里斯傷病修養在家,偷窺窗前鄰居們的日常生活消磨時光。鏡頭里搭建的住所,正是一個令局外人可以一窺他者生存現狀的局面,每一個窗口似乎都有一雙眼睛盯著,杰弗里斯就是其中一個。住在對面公寓二樓的珠寶推銷員拉爾斯與長期臥病在床的妻子安娜之間的爭吵吸引了他的注意,在一個下雨的晚上,杰弗里斯看見拉爾斯提著箱子多次出入,翌日又看到他用報紙包裹一把鋸和一把刀外出,而妻子安娜從此時起就再也沒了蹤跡,職業性的好奇讓杰弗里斯起了疑心,他懷疑安娜早已被杰弗里斯殺害并且分尸。然而,杰弗里斯并沒有目擊案發現場,便開始了探尋之旅,隨著真相的呼之欲出,一切卻昭然若揭。
杰弗里斯像是瓦爾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筆下的“游蕩者”,由于傷病暫時與城市脫離了關系,卻因這一扇窗又與社會產生了某種聯系。作為客觀冷靜的觀察者,他有著自發的抵抗精神,來自于職業的慣性亦或是正義的初衷,他雖然無法漫游在城市的建筑物和人群之間,卻又身居于此。在他者看來,他是一個被邊緣化的人,卻深居簡出伺機觀察著周遭的一舉一動。正是這樣“游蕩者”的視角建構了城市現代生活的圖景,對秘而不宣的城市角落有了觀察的機會,在廢墟中挖掘出人性,冷卻下來毫無血性的東西,藏匿在暗處的蛛絲馬跡會在月黑風高之時發出驚聲尖叫。
身為“游蕩者”,杰弗里斯的視覺在方寸之地走馬觀花,且走且停,悠閑地看鄰居們各展其能:體態婀娜妖嬈的舞蹈演員身著性感內衣做著家務,忙于創作似乎永不停歇的作曲家,過著平淡無奇生活的夫婦倆……直到他目睹到了推銷員夫婦倆的生活,才將自己理智和反思的一面展現出來。作為鄰居,作為旁觀者,杰弗里斯用潛意識與想象力拼湊了真相,恐怖氛圍層層深入,這也是希區柯克“讀心術”的高明之處,不呈現血腥,反而在故事巧妙的搭建中傳遞給觀眾血腥的場面,“腦補”現場狀況,因此他的拍攝重點也在于醞釀感情與死亡的博弈,在這一點上,也正契合了身為局外人的鄰居的視角。
有的因個人恩怨而殺機四起,也有通過心理暗示大開殺戒的。2019年的一部火便全網的日劇《輪到你了》拉開了“交換殺人”的序幕。新婚夫婦菜奈和翔太搬進了一間公寓,原本對于未來充滿期待的二人卻被一場居民會改變了生活的走向,鄰居的一句“誰都有想殺某個人的瞬間”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眾人紛紛坦白各自心底的恨意,管理人床島提議,在座的每個人都公布自己想殺的人。不曾想到,這場即興游戲演變成了一樁樁撲朔迷離的兇殺案,前后30多人卷入其中。劇中鄰里玩的“交換殺人”游戲,就是每個人在紙條上寫下自己想殺的人,然后把紙條都放在箱子里,大家輪流抽到紙條,對紙條上所寫的名字采取行動。每一個即將死去的人都會收到一張寫有“輪到你了”的紙條,打著“每周都會有人死去”的暗號,不得不倒吸一口冷氣。
“交換殺人”的詭異之處在于真實的行兇者跟死者可能幾乎無任何交集,這大大加重了后期調查案件的難度,其撲朔迷離的程度直擊每個人復雜的內心世界,一旦游戲開始,便會一發不可收拾,參與者、執行者的命運就此失控,無法將真相公之于眾,更不能輕而易舉從中抽身。在現實中,這種類似“無差別殺人”的作案手法正是發源于日本,鮮為人知的案件當屬震驚世人的秋葉原殺人事件,犯罪分子加藤智大背負著即將被公司開除、交友不順等壓力,最終釀成了隨機殺人報復社會的悲劇。
萌生這種想法的人大多數是長期抑郁、精神受挫的年輕人,有被孤立的情況,在情感或者生存遭遇重創時就會有了作案的沖動,他們與受害人從未謀面,純屬因為對個人境遇的不滿而遷怒于社會,從而攻擊城市中的某一類人,可能是弱勢群體,也可能就近尋找目標,正如《輪到你了》對陌生人大開殺戒,歹徒兇殘令人發指,與此同時也給了觀眾和社會一定的警示作用。近年來,這類毫無防備的案子時有發生,隨著人們心理壓力的增大而越有飆升的態勢,從而成為一個形勢嚴峻的社會問題。每一個擦肩而過的陌生人都可能成為攻擊者,壓倒他們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是沉重的生存壓力,而是冷漠。遠親不如近鄰,如果社區或是鄰里在他心灰意冷之時送來溫暖,負能量就會得到扭轉。
浮想聯翩,情挑友鄰
城市是流動的,也是封閉的。在每一個房間里,藏著外人不知的秘密,作為最熟悉的陌生人,鄰居只能靠偶遇碰面、或者隔壁傳來的一言半語拼湊出他們生活的大致輪廓,而正是這些未知引發懸念,曖昧的人際關系不禁讓人浮想聯翩。《舊約·出埃及記》里寫道:“不可貪圖鄰人的房產。不可貪愛鄰人的妻子、奴婢、牛驢或他的任何東西。”《圣經》之中提出如此警示,也示意了在現實中涉足這類丑事者大有人在。
鄰人之妻,近水樓臺。美國電影《隔墻有心人》(又名《身為人母》)就描繪出了鄰居之間互生情愫的情節。故事發生在小城鎮的一個富人區,在家帶孩子的家庭主婦薩拉無暇顧及與丈夫理查德之間的關系,婚姻出現危機,在閑暇之時,她被居住在同一社區的有婦之夫布拉德所吸引,經常以帶孩子之名約會,發展了一段婚外戀。美國人類學家愛德華·霍爾 (Edward Hall) 在他的著作《隱藏的維度》中首創了空間關系學和私人空間的概念,他認為,人與人之間也可以像使用語言一樣,通過空間距離傳達信息,他以人們交往保持的距離劃定了4種關系,各種距離也暗示了關系的親密度:公共距離 (360-750厘米) 代表著非正式的聚會中人與人的距離;社交距離 (120-360厘米) 多見于工作職場之中;個人距離 (45-120厘米) 適用于親友熟人之間,也就是鄰居之間交往大致保持的距離,僅限于認識,沒有特殊的關系;親密距離 (0-45厘米) 也就是暗示著他們之間是夫妻及情侶關系。
事實上,人與人關系的遠近也與身處的環境相關,起初,薩拉與布拉德在社區里以鄰居的身份見面,微妙的分寸丈量出了人與人的遠近親疏。學生時期的莎拉是浪漫的文藝青年,還經常為爭取男女平等積極奔走,然而婚后才發現家庭主婦一無是處,老公更是沉迷于網絡色情,于是她對于生活的全部憧憬即刻崩塌。布拉德好強的妻子總是抱怨他不求上進,令他尊嚴掃地。隨著薩拉與丈夫、布拉德與妻子的關系惡化,他們之間近距離交流也越來越少,薩拉與布拉德才有了各自尋找更為親密關系的機會,從結識、互相吐槽到熟知,再到互生情愫,他們也上演了一出情挑友鄰的戲碼。愛人之間的關系就像是放風箏,太近了放不高,太遠了又怕飛了,只有保持一個不遠不近的距離,才是剛剛好的。薩拉的失望、布拉德的墮落放飛了風箏,卻又在轉角處情牽一線。
愛慕之情可以是互相吸引,但也可以是單相思的。作為日本映畫史上著名的情色電影大師,若松孝二擅長以黑白片的形式,呈現出政治與情色碰撞出的故事。他的早期作品《墻中秘事》就以鄰居間的偷窺展開敘事的想象,在平淡無奇的住所里,充滿著壓抑與沉悶。落榜的高中生內田春琴夜以繼日溫書復習,卻又難耐青春期的躁動,閑來無事拿望遠鏡窺視對面居民樓的男女。事實上,偷窺只是若松孝二洞悉戰后扭曲人性、孤寂生活的切入點,在末日陰影之下,戰爭的殘余令置身在逼仄空間里的人局限于單調的生活,監視與偷窺即是反抗精神的流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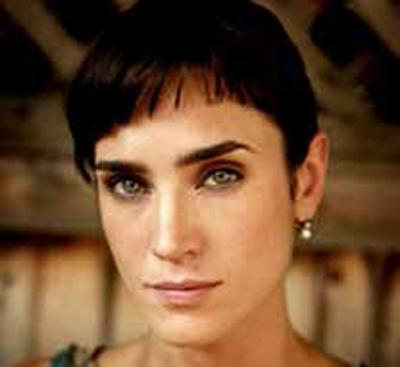



《為人之母》劇照。

《生活大爆炸》劇照。
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 (Michel Foucault) 在《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中寫道:“我們的社會不是奇觀社會,而是監視社會……我們既不在露天劇場,也不在舞臺上,而是在全景機器中,被它的作用力消耗,我們是自作自受,因為我們是整個機制的一部分。”如今,不見了眼前的圓形監獄和高塔,四通八達的互聯網時代實現了全景敞視,在自我暴露的同時,他者也在監控中不斷獲取我們的信息,當代人在逐漸適應了這種偷窺與被偷窺的共生關系,網絡熱搜、電視真人秀、帶貨直播讓人人都有了成為明星的機會,成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偷窺不再是藏在暗處的“小動作”,而是成為明目張膽的“打Call”,而且被偷窺的人也開始在表演中展示自我,在用盡出其不意的招數博取粉絲一笑,觀者則自主選擇偶像,以他人的生活取悅自己。正如社會評論家霍爾·涅茲維奇 (Hal Niedzviecki) 在《我愛偷窺》中所說:“窺視源于傳統社群生活的瓦解,以及取代共同社會之大眾電子娛樂的興起。監視同樣源于傳統生活的瓦解,也同樣基于科技進步。因此監視和窺視兩者關系盤根錯節,一點也不讓人驚訝。它們的運作機制是這樣的:我們日常生活中不斷增加的娛樂,實源于別人的生活。”
如此看來,在賽博時代,所謂“鄰居”的定義在擴大,它可能不再是一個實體的人,而是一些散布在社區住宅內的電子眼、監視器,甚至是手機上的攝像頭,它們注視著人們在每個場景下的所作所為。一方面,注重個人隱私的人對于自己無意間淪為偷襲的對象心有余悸;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在一個“刷存在感”的時代,大多數人害怕被遺忘,而且在動蕩不安的環境下,智能AI 像是一個如影隨形的朋友,隱形保護著自己,對這種真實生活片段的截取繼而亦有可能成為娛樂的素材。因此,曝光與掩護成了一對相互支撐的“伴侶”,正如傳統對鄰居的認知,麻煩與溫暖同在。
抱團取暖,患難見真情
瘟疫伴隨著人類的歷史進程,歷史客觀記載了災難下的死傷損失,卻鮮少記錄下那些處于疫情中人們的日常生活,在人人自危、惶恐不安之中,他們的細小舉動有可能帶來毀滅性的劫難。不幸之中有萬幸,這些都被擅于洞察的作家寫進了小說,當疫情結束,一切焦慮緊張的情緒都煙消云散的時候,所有虛構的細節拼湊出了我們未曾目睹卻又真實存在的影象。
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了原本平靜的生活,病毒的肆虐放大了人與人之間的生死情愛,在極端的生存環境下做出抉擇,也是對人性的考驗。身處困惑迷離的局面,城市災難如一面鏡子,照見了善惡美丑——有的人臨危不懼,成為“最美的逆行者”;有的人在孤獨中死去;還有人為了躲避災禍臨陣脫逃……活下來的人如何讓生活步入正軌,不幸染上重疾的人又如何有尊嚴地死去,這些問題都折射出了疫情之下的人情世故。14世紀的意大利作家喬萬尼·薄伽丘在他的作品《十日談》里勾勒出佛羅倫薩瘟疫流行時一所鄉村別墅里的避難場景。作為歐洲文學史上第一部現實主義巨著,薄伽丘親眼目睹了可怕的鼠疫大流行,“黑死病”奪去了上千萬人的生命。小說里,10名青年男女在鄉下躲避瘟疫,那里環境清幽,美酒花香相伴,完全與城里尸橫遍野兩重天。他們似乎忘記了當下的艱難,終日游山玩水,載歌載舞,還商定每人每天講一個故事,10天時間100個故事,從歷史傳說到民間故事,有的是“新瓶裝舊酒”,還有對當時社會教會黑暗的批判,贊美愛情向往自由的軼事,或諷刺或幽默。
他們在虛構的王國抱團取暖,給局限的社會空間打開了新的天地,他們跳出真實世界構建了一個想象的空間,既是對現實社會的延伸,也是對個人境遇的一種反思。福柯在《詞與物——人類科學的考古學》中提出了“異托邦”(Heterotopias) 的概念,在他看來,“在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文明中可能也有真實的場所——確實存在并且在社會的建立中形成,這些真實的場所像反場所的東西,一種的確實現了的烏托邦。在這些烏托邦中,真正的場所,所有能夠在文化內部被找到的其它真正的場所是被表現出來的,有爭議的,同時又是被顛倒的。這種場所在所有場所以外,即使實際上有可能指出它們的位置。因為這些場所與它們所反映的、所談論的所有場所完全不同,所以與烏托邦對比,我稱它們為異托邦……”不同于“烏托邦”的子虛烏有和遙不可及,“異托邦”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場域,唯獨要憑借個人的想象,或是依靠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去建構這樣一個空間。當正常的社區生活方式在極端的情形下被剝奪,人與人的交往傾向于“就地取材”,脫離尷尬境地,《十日談》之中每天由一個人擔任“國王”,在角色扮演的樂趣中剝離現實的冷酷與乏味。
男女共處一個屋檐下,最廣為人知的還是《生活大爆炸》 這部伴隨一代人成長的輕松搞笑肥皂劇引領的科學浪潮席卷全球,片中4個科學宅男謝爾頓 、萊納德 、霍華德 ?以及拉杰 ,與隔壁懷揣演員夢的餐廳女招待佩妮 ?碰撞出一場場意猶未盡的爆笑情節。劇迷們期待著這些科學怪人情感軌跡的變遷,謝爾頓與艾米、萊納德和佩妮、霍華德和伯納黛特如電荷一樣互相吸引有了情感歸宿,只有拉杰繼續唱著單身情歌。令人著迷的是,這4個宅男和佩妮居住的公寓樓,表面看上去和其他建筑并無二致——不時罷工的電梯,落后的配套設施甚至有些破敗的跡象,詫異的是房子的結構,網友們通過劇情展示的房間以及他者行動對未曝光空間的描述,大致勾勒出這座建筑的內部構造,細微之處見出房間的曲折變化。天馬行空的奇思妙想滲透到了日常場域之中,揭開了科學宅男生活中不為人知的一面,居室擺設、房子構造、服飾裝扮都迸發著科學的姿態、智慧的火花以及不可復制的個性。
科學怪人們平時是斗氣冤家,在患難之時則見出真情。他們雖然有過人的智商和各自的優勢,但他們也有難以啟齒的短板。拉杰患有嚴重社交障礙,一見到異性就說不出話來。這種社交恐懼癥中的選擇性緘默癥尤其在聚會時顯得頗為尷尬,在他一時語塞之時,其他人便出來插科打諢救場。有社交障礙的還不止他一人,謝爾頓的女友艾米也是如此——科學宅女卻不通人情的怪咖,生活死板而又無趣,直到加入了佩妮、伯納黛特的朋友圈才煥然一新,雖然在與朋友交流時經常貽笑大方,但她也有自己的可愛之處。在劇中還可以一窺美國人日常的社交生活,比如利用語義的歧義、夸張、雙關增加笑料,當雙方的觀點相悖的時候,一味的勸說可能會南轅北轍,還可能因此傷了感情,與其爭得不相上下,不如轉移話題,在避免尷尬的同時,婉轉地向對方滲透自己的觀點,這種交流方式在劇中比比皆是。在溝通中,他們看上去違背了會話的原則,但卻幽默風趣地傳遞出了他們所要表達的,不失為一種鄰里交往的話語秘訣。
(責編:常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