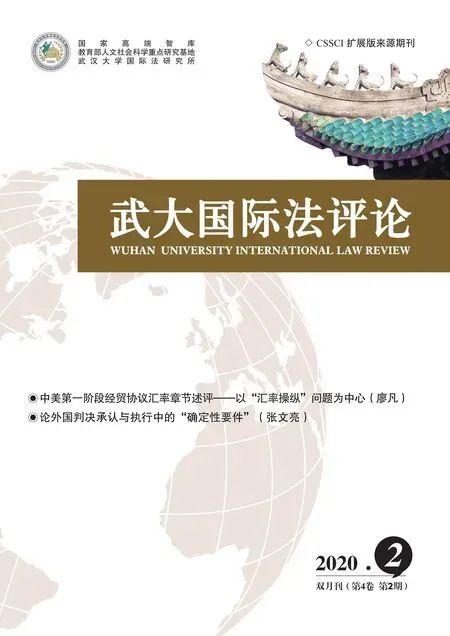論投資條約中最惠國條款的多邊化作用及限度
——基于同類規則適用的實證分析
蔣海波
據統計,98%的投資條約都規定有最惠國待遇。①See UNCTA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Navigator,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 al-investment-agreements/iia-mapping, visited on 8 October 2019.這些最惠國條款(以下稱“MFN 條款”)在投資條約實踐中引起了廣泛爭論,爭論主要圍繞投資條約中MFN條款是否可用于引入第三方投資條約的條款。MFN 條款要求締約東道國給予來自另一國投資者及其投資的待遇不低于該東道國給予第三國投資者及其投資的待遇,這種“最惠國”功能極易被用于突破現行投資條約體系的雙邊結構,而把該體系發展成為事實上的多邊體系。這對于該體系建立一個開放的、非歧視的國際投資市場具有重要意義。但另一方面,正如南部非洲發展同共體(SADC)雙邊投資條約范本起草委員會所指出的,MFN 條款會產生非預期的多邊化后果,對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帶來不可預料的風險。②See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C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Template with Commentary, https://www.iisd.org/itn/wp-content/uploads/2012/10/SADC-Model-BIT-Template-Final.pdf, visited on 8 October 2019.本文將在實證分析的基礎上闡明MFN 條款的多邊化作用及限度,以期改善投資條約中MFN 條款實踐的可預期性及正當性。
一、最惠國條款的多邊化影響
作為BITs 最初模板的《外國人財產保護公約草案》主要關注征收及其補償等投資安全問題,并沒有規定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等非歧視性待遇標準。后來,最惠國待遇條款開始出現在一些早期的BITs 中,并逐漸成為BIT 的標準條款。①See UNCTAD, Most-Favoured Nation Treatment: UNCTAD Series on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I, https://unctad.org/en/Docs/psiteiitd10v3.en.pdf, visited on 8 October 2019.不過,MFN 條款的出現在早期投資條約實踐中并未引起人們的注意。在相對待遇標準上,東道國更為關注國民待遇條款。因為,東道國主要顧慮外國投資對國內經濟社會的影響,主要關注如何利用外國投資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至于該投資具體來自哪個國家并不那么在意。例如,我國早期與瑞典、德國、法國等簽訂的BIT只規定有MFN條款,而沒有規定國民待遇條款。
隨著投資條約仲裁案件的出現,MFN 條款的多邊化功能開始被投資者開發出來,并得到了仲裁庭的肯定。在第一起投資條約仲裁案中,申請人試圖利用基礎條約中的MFN 條款(斯里蘭卡與英國的BIT)引入第三方投資條約中的損害賠償條款(斯里蘭卡與瑞士的BIT),仲裁庭并沒有否定MFN 條款的多邊化功能,只是認為第三方條約沒有規定申請人所謂的嚴格責任標準而駁回了該訴請。②See Asian Agricultural Products Ltd. (AAPL) v. Sri Lanka, ICSID Case No.ARB/87/3, Final Award, 27 June 1990, para.54.在后續的投資條約仲裁案件中,投資者逐漸開發出MFN 條款的多邊化潛能:從最初引入第三方條約的實體條款擴大至改變基礎條約的管轄范圍、避開例外條款以及引入爭端解決條款(ISDS條款)等。其中,墨菲基尼案(Maffezini)成為MFN條款多邊化作用受到廣泛關注的開端。在該案中,仲裁庭首次允許申請人援用MFN 條款引入第三方條約中更為優惠的ISDS 條款。③See Maffezini v. Spain, ICSID Case No. ARB/97/7, Decision on Objections to Jurisdiction, 25 January 2000, paras.38-64.對此,筆者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以下稱“貿發會議”)的資料列出了2010 年以前涉及MFN 條款的仲裁案例(見表1),這些早期案例基本概括了關于MFN 條款實踐的爭議問題。表2 是2016、2017年兩年所公布的關于MFN條款的案例,這其中出現了一些新變化。

表1 2010年以前涉及MFN條款訴請的投資條約仲裁案件統計表④ See UNCTAD, Most-Favoured Nation Treatment: UNCTAD Series on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I, https://unctad.org/en/Docs/psiteiitd10v3.en.pdf, visited on 8 October 2019.

續表

表2 2016—2017年涉及MFN條款訴請的投資條約仲裁案件統計表① 主要根據貿發會議關于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報告中的數據統計得出。See UNCTRAD,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Review of Developments in 2017, https://investmentpolicyhub.unctad.org/Publications/Details/1188,visited on 8 October 2019.
由以上統計列表可知,在投資條約仲裁中,投資者不斷利用MFN 條款試探投資條約多邊化的極限。在這一過程中,MFN 條款的多邊化作用及限度逐漸清晰。總體上,投資者試圖利用MFN 條款改變基礎條約管轄范圍以及避開其例外條款的訴請都被否決了。不過,對于MFN 條款是否可以引入第三方條約的ISDS條款,不少仲裁庭作出了不一致的裁決,這為MFN 條款實踐的可預期性蒙上了一層陰影。
二、最惠國條款多邊化作用的機制
(一)最惠國條款多邊化效力的基礎
雖然最惠國待遇被廣泛地規定在商業條約中,但是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該待遇標準已成為一項習慣國際法規則,“普遍認為,只有條約才是最惠國待遇的法律基礎”。①See UN, A/33/10(SUPP), 28 July 1978, Article 7.換而言之,任何國家都無權要求另一國給予最惠國待遇,除非該另一國承諾給予其他國家此類待遇。最惠國待遇的法律效力來源于規定該標準的基礎條約,即基礎條約的MFN 條款。在英伊石油公司案(Anglo-Iranian Oil Co. Case)中,國際法院明確指出:基礎條約確立受惠國與第三方條約之間的司法聯系,并給予受惠國第三方所享有的權利,而第三方條約沒有在受惠國與授與國之間產生任何法律效力,第三方條約屬于他人之間的行為(res inter alios acta)。②See Anglo-Iranian Oil Co. Case (United Kingdom v. Iran), Judgment, ICJ Reports 1952, p.109.而第三方條約的有關條款只是觸發基礎條約中MFN 條款運行的條件。最惠國待遇屬于相對性標準,其內容并不確定,而是取決于觸發基礎條約中MFN 條款運行的第三方條約中有關條款。MFN 條款的法律效力與第三方條約條款的內容相結合而產生授與國的具體義務。由此,該第三方條約的條款借助基礎條約中MFN 條款的法律效力實現了多邊化。至于第三方條約條款如何能夠觸發基礎條約中MFN 條款的運行,則須符合同類規則(ejusdem generis)的要求。
(二)投資條約中最惠國條款的主要類型
由上可知,最惠國條款的效力及范圍須根據基礎條約的具體規定而定,誠如麥克奈爾(McNair)所述:“嚴格意義上,不存在所謂的MFN 條款,每項條約須各自獨立地予以審查”。③A. McNair, The Law of Treaties 285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8).在投資條約體系中,主要有以下七類MFN條款:
1.MFN 條款只是簡單地提及給予投資者或投資不低于第三國投資者或投資的“待遇”。這類MFN條款在早期的BIT中很常見。④例如,我國簽訂的第一項BIT 中國—瑞典BIT 第2 條2 款規定:締約任何一方的投資者在締約另一方境內的投資所享受的待遇,不應低于第三國投資者的投資所享受的待遇。
2.MFN 條款提及“所有”事項。例如,阿根廷—西班牙BIT 第4 條2 款規定;對于本協定內的所有事項,這一待遇不應低于各締約方對第三國投資者在其領域內所作出之投資給予的待遇。①墨菲基尼案把該款規定的“所有事項”視為MFN 條款可以吸引其他條約ISDS 條款的理由之一。See Maffezini v. Spain, ICSID Case No.ARB /97/7, Decision on Objections to Jurisdiction, 25 January 2000, para.60.
3.“待遇”一詞涉及投資活動的具體方面,例如,美國2012 年范本第4 條規定:對投資者及其投資在投資設立、并購、擴張、管理、經營、運行、出售或其他處置行為方面給予最惠國待遇。
4.最惠國待遇涉及條約項下的具體義務,例如,俄羅斯—西班牙BIT 第5 條在規定公平公正待遇(FET)后,緊接著第2 款規定:第2 款所提及的待遇不應低于一締約方給予任何第三國投資者在其領域進行的投資所給予的待遇。
5.在MFN條款中規定“相似情況”等。例如,《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第9.5條規定,第14個注釋中明確規定“相似情況”應該根據總體情況,包括相關待遇是否基于合法公共福利目標來區分不同投資者或投資。
6. MFN條款似乎引入地域限制。一些仲裁庭在解釋MFN條款是否可以引入其他ISDS 條款時,認為MFN 條款規定有地域限制,而“國際仲裁是一項與被訴國領域沒有內在聯系的活動,仲裁地通常位于中立的第三國”,從而否決這種訴請。②ICS Inspection and Control Services Limited v. Argentina, PCA Case No.2010-9,Award on Jurisdiction, 10 February 2012, para.306.例如,ST-AD GmbH 案仲裁庭所適用的德國與保加利亞的BIT 第4 條5 款規定:就本條所涉事項,一締約方的投資者及投資在另一締約方的領域內所享有的待遇,不得低于第三方國家的投資者及投資所獲得的最優惠待遇。③該條款的英語原文是:“(5) In matters governed by this article, the investments and investors of either Contracting Party shall enjoy treatment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other-Contracting Party that is no less favourable than that enjoyed by investments and investors of those third States that receive most favourable treatment in this respect.”根據該仲裁庭的推理,在該條文中“in the territory”放在“treatment”的后面,因而作為對后者的限定詞。
7.MFN 條款明確規定“待遇”的范圍或含義。例如,中國與烏茲別克斯坦、坦桑尼亞、加拿大所締結的BIT明確規定MFN條款不適用于爭端解決條款。歐盟與加拿大的經濟與貿易全面協定(CETA)第8.7條(最惠國待遇)規定:該條款所指的“待遇”不包括其他國際投資條約和貿易協定規定的投資者—國家投資爭端解決程序;其他國際投資條約或貿易協定所規定的實體義務本身也不屬于“待遇”。《泛非洲投資法典草案》第7 條第5 款也作出類似CETA 的規定,并且其8 條還專門針對最惠國待遇規定了例外條款。
這些不同類型的MFN 條款在義務、范圍、涵蓋面和受惠者等方面的具體措辭有差異,因而其效力及范圍也會有不同。但是,正如施瓦茨伯格所言:“盡管不存在所謂的MFN 條款,但同樣有必要強調的是最惠國待遇標準確實存在。”④Georg Schwarzenberger, The Most-Favored-Nation Standard in British State Practice, 22 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04 (1945).不論具體如何表述,所有MFN 條款都具有相同的特征與總體目標,只是實現這一總體目標的方式會因具體措辭差異而不同。①See UN, A/70/10, paras.146-147.為外國投資者創建一個開放、非歧視的法律環境是所有投資條約中MFN 條款的總體目標,而MFN 條款的多邊化作用就是為此目標服務的重要機制。因為MFN 條款可以拉平東道國締結的所有與外國投資待遇保護有關的條約,使東道國與任何第三國達成的投資條約所規定的優惠待遇擴散至受惠國的投資者,從而破除雙邊主義的藩籬,確保來自不同國家的外國投資者在該東道國內獲得平等競爭的機會。
(三)同類規則規定了最惠國條款多邊化作用的機制
MFN 條款的多邊化作用是以更優“待遇”的名義引入第三方投資條約條款來實現的。在基礎條約MFN 條款法律效力支持下,代表更優“待遇”的第三方投資條約條款對作為該基礎條約締約方的東道國產生拘束力。而這一多邊化過程的實現需要滿足同類規則的要求。具體而言,主張更優“待遇”的投資者及其投資是最惠國條款所指定的或者是該條款主題所暗含的,并且所要求的權利也應處于該條款主題范圍內。至于MFN 條款的主題,在投資條約語境中,可能是投資促進、投資保護、投資自由化等。
國際法委員會在1978 年報告的《最惠國條款草案》(以下稱“1978 年草案”)指出,同類規則得到各國際法庭判例、各國內法院以及外交實踐等普遍承認。②See UN, A/33/10(SUPP), 28 July 1978, p.27.如今,雖然該草案報告的背景已經發生變化,但是正如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審議最惠國條款的2015 年報告(以下稱“2015 年報告”)所述:“MFN 條款的特性依然沒變,1978 年草案的核心規定仍然是今天解釋與適用MFN 條款的基礎。”③See UN, A/70/10, para.160.有學者認為,“MFN 條款的特性以及同類規則屬于與投資條約中MFN 條款有關的一般國際法規則”。④Facundo Pérez-Aznar, The Fictions and Realities of MFN Claus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112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Unbound)56 (2018).
究其實質,同類規則建立在最惠國待遇法律性質的基礎上,旨在限制MFN 條款的作用范圍,即只能引入具有相同主題的第三方條約條款,以免對授與國施加其從未預料的義務。基于本文的主題,筆者將根據1978 年草案,對同類規則的效力闡明以下三點:
1.根據同類規則,MFN 條款是通過基礎條約中的一套條款引入第三方條約中的另一套條款,而這兩套條款的主題應具有實質相同性。⑤See UN, A/33/10(SUPP), 28 July 1978, p.30.換而言之,MFN 條款不能引入基礎條約沒有規定的新權利或新待遇。例如,在基礎條約沒有規定ISDS 條款時,MFN 條款無法引入第三方條約的仲裁同意。在MMEA & AHSI 案中,申請人試圖利用GATS 中MFN 條款引入荷蘭—塞內加爾BIT 中的ISDS 條款,仲裁庭認為:GATS本身沒有規定國際仲裁或爭端解決,也沒有包含任何類型的仲裁同意,因此不能利用MFN 條款引入BIT 中的ISDS 條款。①申請人的母國盧森堡與塞內加爾沒有締結BIT。See UNCTAD,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Review of Developments in 2016,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diaepcb2017d1_en.pdf, visited on 12 December 2019.而各投資條約相同的結構以及大體相似的內容為MFN條款的多邊化作用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2.同類規則要求投資者與第三國投資者處于相似情況,“這一要求是MFN 條款運行的一項內置要素”。因此,MFN 條款是否提及這一措辭對其適用沒有影響。②See UNCTAD, Most-Favoured Nation Treatment: UNCTAD Series on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I, https://unctad.org/en/Docs/psiteiitd10v3.en.pdf, visited on 8 October 2019.就此而言,I?kale 案仲裁庭適用MFN 條款的推理令人質疑。該庭認為,由于MFN條款明確提及“在相似情況下給予(最惠國)待遇”,為了使“相似情況”(similar situations)這一措辭不至于無效,從而要求投資者應該與第三國投資者的事實情況相似。基于此,該庭裁定認為,申請人無權引入基礎條約沒有規定的實體保護標準,駁回了申請人引入第三方條約規定的FET,盡管該基礎條約的序言提及了FET。③See I?kale v. Turkmenistan, ICSID Case No.ARB/10/24, Award, 8 March 2016,paras.329-332.該裁決與Bayindir案裁決相矛盾。④Bayindir 案的仲裁庭裁定,在基礎條約序言中規定有FET 的情況下,MFN 條款可以引入第三方條約中的FET 條款,從而把序言中不具有拘束力的FET 提升為具有規范效力的標準。See Bayindir v. Pakistan, ICSID Case No.ARB/03/29,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14 November 2005, para.230.
3.當包含優惠待遇的協定存在或者被締結,因而第三國投資者有權獲得該優惠時,基礎條約中MFN 條款就開始運行,而不用等待該待遇被第三國投資者實際獲得才觸發MFN 條款運行。換而言之,受惠國的投資者不用等待授與國根據第三方條約義務采取國內措施之后才能獲得該待遇。在第三國投資者有權獲得該優惠時,這種待遇就無條件地、立刻擴散至受惠國的投資者,也不用后者主張要求該待遇,除非MFN 條款明確附加一些條件。⑤See UN, A/33/10(SUPP), 28 July 1978, p.44.在Garanti 案中,持少數意見的仲裁員認為:外國投資者必須首先與東道國處于爭端解決關系中才能使MFN 條款產生效力。該仲裁員的推理是投資者只有根據爭端解決條款提起仲裁后才有權主張最惠國待遇。對此,該庭的多數意見批判認為,這一時間順序的認定沒有任何法律根據。⑥See Garanti Koza LLP v. Turkmenistan, ICSID Case No.ARB/11/20, Decision on the Objection to Jurisdiction for Lack of Consent and Dissenting Opinion, 3 July 2013, paras.60-61.有學者把這一時間順序作為MFN 條款不適用于仲裁管轄權條款的理由之一。⑦See Zachary Douglas, The MFN Clause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Treaty Interpretation off the Rails, 2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353-371 (2011).由此可見,這一觀點站不住腳。此外,另有學者認為MFN 條款不能用于引入第三方條約條款的理由是:MFN 條款是初級規則,這一性質意味著該條款的適用過程僅限于比較有關待遇以確定是否違反該條款,若違反該條款,要求承擔國家責任即可。①See Facundo Pérez-Aznar, The Fictions and Realities of MFN Claus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112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Unbound) 56(2018).這種觀點實際上把MFN 條款的法律效力與違反該條款的法律責任混淆在一起,而且似乎也沿著前述錯誤的時間順序邏輯。MFN 條款的法律效力是把優惠無條件地、立刻擴散至受惠國的投資者,而違反該條款所產生的國家責任只是對這一法律效力的保障。
三、最惠國條款多邊化作用機制的運行:同類規則的適用
正如Al-Warraq 案仲裁庭所述,只要符合同類規則,MFN 條款就可以適用于引入其他條約條款。②See Hesham Talaat M. Al-Warraq v. Indonesia, UNCITRAL, Final Award, 15 December 2014, para.551.雖然同類規則的內容比較明確,但是該規則的實際適用遇到了許多難題。投資條約仲裁對此出現的分歧就是例證。總體上,投資條約仲裁對于引入實體條款的意見比較一致,而對于引入ISDS條款的分歧比較大。
(一)關于實體條款引入
根據同類規則,MFN 條款能否引入第三方投資條約的條款需要滿足兩項條件:其一,該引入條款所代表的更優“待遇”處于MFN 條款主題范圍;其二,基礎條約有一項與該引入條款的主題具有本質同一性的條款。誠如Teinver 案仲裁庭所述,MFN 條款能“提升”基礎條約中已有的條款,但不能創設新權利或待遇。③See Teinver SA and Others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ARB/09/1, Award ,21 July 2017, para.885. Hochtief 案仲裁庭也持相同觀點。See Hochtief AG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ARB/07/31,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24 October 2011, para.81.這也是同類規則對MFN 條款多邊化作用的限制。至于這兩項條件如何予以具體確認,則需要根據條約解釋的一般原則對所涉投資條約作出解釋。
1.第一項條件的確認
在上文歸納的七類主要MFN 條款中,第四類MFN 條款對其主題有比較明確的限制。所以,從該MFN 條款措辭的解釋中可以確認其主題的具體范圍。例如在Renta 案中,仲裁庭認為基礎條約(俄羅斯—西班牙BIT)把最惠國待遇規定在FET 條款項下,因而該MFN 條款只適用于引入第三方投資條約中FET 條款,從而駁回了申請人利用MFN 條款引入第三方投資條約中ISDS 條款的訴請。④See Renta 4 SVSA and Others v. Russian Federation, SCC Case No.24/2007,Award on Preliminary Objections, 20 March 2009, paras.105-106.Paushok案的仲裁庭也基于同樣的理由駁回了申請人利用MFN 條款引入其他投資條約中保護傘條款的訴請。①See Paushok and Others v. Mongolia, 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Liability, UNCITRAL, 28 April 2011, para.570.晚近出現的第七類MFN 條款也有比較明確的主題。然而,其他MFN 條款措辭并沒有對其主題的確認給出有效的指示。對此,需要結合所涉投資條約的上下文、目的與主旨確認所涉MFN 條款的主題。在投資條約仲裁實踐中,實體條款所代表的“待遇”一般都認為屬于MFN 條款的主題范圍。在這些仲裁判例中,MFN 主要被用于:(1)引入其他投資條約的FET 條款,例如Bayindir v.Pakistan, Al-Warraq v. Indonesia 等案;(2)引入其他投資條約的保護傘條款,例如 MTD Equity v. Chile, EDF and Others v. Argentina,Arif v. Moldova 等案;②See Arif v. Moldova, ICSID Case No.ARB/11/23, Award, 8 April 2013, paras.395-396.(3)引入其他投資條約的全面保護與安全條款,例如Teinver 案;(4)引入其他投資保護條款,例如White案。③在White 案中,仲裁庭允許申請人引入第三方條約中關于為投資者求償與權利執行提供有效手段的條款。See White Industries Australia Ltd v. India, IIC 529 (2011), Final Award, 30 November 2011, paras.11.2.1-11.2.9.
2.第二項條件的確認
就實體條款的引入而言,第二項條件在投資條約仲裁實踐中也被廣泛承認。例如,在Bayindir 案中,基礎條約(巴基斯坦—土耳其BIT)的序言提及FET;在White 案中,基礎條約(印度—澳大利亞BIT)的序言也包含與所引入條款具有相同主題的內容。而對于保護傘條款的引入,一些仲裁庭在確認基礎條約是否存在本質同一性的問題上出現了分歧。MTD Equity 案仲裁庭和EDF and Others 案仲裁庭把保護傘條款視為基礎條約中FET 條款的組成部分而允許引入。而在Teinver 案中,雖然基礎條約規定有FET 條款,但是仲裁庭認為基礎條約中沒有本質同一性的條款而駁回了申請人利用MFN 條款引入保護傘條款的訴請。Arif 案仲裁庭完全沒有談及第二項條件,只是簡單地提及當事雙方同意MFN 條款適用于實體義務就允許引入其他投資條約的保護傘條款。國際法學會在2013 年通過了一項關于“投資者根據國家間條約針對東道國政府訴諸仲裁的法律問題”的決議,其第12 條明確規定,在基礎條約沒有規定一項保護傘條款的情況下,MFN 條款不能引入第三方條約的保護傘條款。④See 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Legal Aspects of Recourse to Arbitration by an Investor against the Authorities of the Host State under Inter-State Treaties, www.idi-iil.org/app/uploads/2017/06/2013_tokyo_en.pdf, visited on 21 April 2019.這有助于投資條約仲裁對引入實體條款形成一致意見。
3.新近出現的不同觀點
近來,有兩位學者基于I?kale 案的裁決、第七類MFN 條款的出現以及NAFTA各締約國在NAFTA 仲裁中提交的有關意見等,對引入實體條款提出了一些疑問。①See Simon Batifort & J. Benton Heath, The New Debate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MFN Clauses in Investment Treaties: Putting the Brakes on Multilateralization, 111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873 (2017).其主要觀點是:絕大多數仲裁庭都把實體條款的引入視為無異議的,這種傳統看法是根據對MFN 條款一般特性的假定而得出的,忽視了各投資條約中MFN條款措辭的差異,從而致使解釋者不恰當地認為這些MFN 條款具有統一的功能。②See Simon Batifort & J. Benton Heath, The New Debate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MFN Clauses in Investment Treaties: Putting the Brakes on Multilateralization, 111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874 (2017).他們持麥克奈爾(McNair)的觀點,即不存在所謂的MFN 條款,每項投資條約都應根據《條約法公約》(VCLT)規則各自獨立地作出解釋。③See Simon Batifort & J. Benton Heath, The New Debate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MFN Clauses in Investment Treaties: Putting the Brakes on Multilateralization, 111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877 (2017).這種觀點不僅要推翻投資條約仲裁在實體條款引入上形成的一致意見,而且也否定1978 年草案條款的核心規定對投資條約MFN條款解釋與適用的相關性。
作為投資條約的一部分,MFN 條款的效力及范圍確實應該根據VCLT 規則善意地解釋其通常意義予以確定。而“投資仲裁庭卻時常把VCLT 規則視為一種自助餐,以從中選擇支持自己希望得出之結論的食料”,并沒有細致分析條款措辭。④See Donald McRae, Introduction to the Symposium on Simon Batifort and J.Benton Heath The New Debate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MFN Clauses in Investment Treaties: Putting the Brakes on Multilateralization, 112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Unbound) 41 (2018).Al-Warraq 案仲裁庭對MFN 條款的適用就是例證。該庭在分析基礎條約與第三方條約的序言后認為兩者的主題相同,即都是保護外國投資,進而認為申請人的訴請符合同類規則的要求,允許申請人利用MFN條款引入第三方條約的FET條款。⑤See Hesham Talaat M. Al-Warraq v. Indonesia, UNCITRAL, Final Award, 15 December 2014, paras.545-551.但根據1978 年草案報告,這種對同類規則的寬泛解讀是錯誤的。同類規則要求利用MFN 條款引入的利益與基礎條約的規定屬于同類,而不是基礎條約與第三方條約屬于同類。⑥See UN, A/33/10(SUPP), 28 July 1978, p.30.換而言之,該仲裁庭忽視了上文的第二項條件,該案所涉基礎條約的序言及條款都沒有提及FET。而該仲裁庭的寬泛解讀實際上把同類規則轉變為“同質化”東道國締結的所有投資條約條款的工具。事實上,這些投資仲裁庭在把VCLT規則視為自助餐的同時,也沒有嚴格適用同類規則。
即使強調按照VCLT 規則來善意解釋投資條約中的MFN 條款,我們也不能否定1978 年草案條款的相關性,更不能簡單地把它們視為“傳統觀點”而拋棄之,盡管該草案沒有成為正式的條約。事實上,該草案失敗的原因并不是各國當時對其核心條款內容存在分歧,而是該草案沒有排除關稅同盟等特殊安排,也沒有考慮發展中國家的優惠待遇問題。①See UN, A/CN.4/L.719, p.7.這種“傳統觀點”是關于“一項MFN 條款在國際法上的典型含義的一般背景知識”,在所涉MFN 條款缺乏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可以成為該條款的默認含義(default meaning)。②See Michael Waibel, Putting the MFN Genie Back in the Bottle, 112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Unbound) 60 (2018).在投資條約體系的七類MFN 條款中,只有第四類與第七類MFN條款的主題比較明確,而其他絕大部分MFN條款并沒有對自身的解釋與適用給出有效的指示。在此情況下,這些MFN 條款的解釋與適用不能與一般國際法背景脫離。另外,雖然一些當事國在投資仲裁中提交的辯護意見以及作為爭端第三方提交的意見都反對MFN 條款引入第三方投資條約的實體條款,但把這些反對意見脫離投資仲裁案件的具體語境,放到更廣泛的一般國際法層面所能產生的影響是極其有限的。有學者從更廣泛的層面實證分析了各國對投資條約中MFN條款的意見,并指出:大多數國家并不反對MFN條款對第三方投資條約實體條款的引入,所以這種“傳統觀點”沒有被推翻。③See Martins Paparinskis, MFN Clauses and Substantive Treatment: A Law of Treaties Perspective of the“Conventional Wisdom”, 112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Unbound) 49 (2018).2015 年報告也是國際法委員會廣泛征詢各國意見而得出的,其指出:1978 年草案核心規定仍然是當前解釋與適用MFN 條款的基礎。雖然CETA 等晚近一些條約對最惠國待遇的限制性規定完全排除了其MFN 條款被用于引入第三方條約條款的可能性,但是還不足以推翻該“傳統觀點”對解釋與適用其他類型MFN 條款的相關性。④See Stephan W. Schill, MFN Clauses as Bilateral Commitments to Multilateralism: A Reply to Simon Batifort and J. Benton Heath, 111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929 (2017).
(二)仲裁管轄的合意原則不應成為ISDS條款引入的障礙
從上述統計的投資仲裁案例來看,對于投資仲裁管轄,申請人利用MFN 條款引入第三方投資條約有關條款主要為了以下目的:(1)擴大“投資”或“投資者”定義;(2)改變基礎條約的屬時理由;(3)避開基礎條約的例外條款;(4)延長仲裁同意的時效;(5)在沒有規定ISDS機制或該機制已經失效的情況下,引入ISDS機制;(6)擴大仲裁受案范圍;(7)免除ISDS 程序條款對仲裁同意所附加的條件;(8)引入其他類型的ISDS機制。
前三項目的涉及整個基礎條約法律效力范圍的改變,明顯不可能實現。因為MFN 條款的法律效力建立在基礎條約上,所以,不處于后者法律效力范圍內的事項當然也不處于其MFN 條款的法律效力范圍內。從統計的案例來看,涉及這三項目的的訴請無一例外地都被駁回了。后五項目的涉及利用MFN 條款引入第三方投資條約中的ISDS 程序條款。根據同類規則,第四、五項目的不能實現,第六項目的、第七項目的需根據具體情況分析,第八項目的可以實現。這部分主要根據同類規則具體分析第七、八項目的,而其他幾項目的將在后文予以探討。
從一些投資仲裁案例來看,阻礙第六、七、八項目的實現的主要障礙是仲裁合意原則。Plama 案仲裁庭認為:仲裁合意應該明確、不含糊,這是法律上已被普遍接受的原則,通過MFN條款引入其他ISDS條款而達成的仲裁合意是不明確的,除非締約國引入ISDS 條款的意圖在投資條約中有明確的表達,例如,英國的BIT 范本。①See Plama Consortium Limited v. Bulgaria, ICSID Case No.ARB/03/24,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8 February 2005, paras.198-212.該庭對國際法院英伊石油公司(Anglo-Iranian Oil Co.)案判決的援引卻是斷章取義。國際法院的判決是:英國與伊朗的條約(基礎條約)是在伊朗發布接受國際法院強制性管轄聲明之前所締結的條約,不屬于該聲明效力范圍之內,所以對該條約引發的爭議沒有管轄權。而且,根據MFN 條款的法律性質,得出該條約所規定的MFN 條款與管轄事項沒有任何關系。由此可知,國際法院的判決并不是當然地否定MFN 條款與管轄權無關。而Plama 案仲裁庭卻斷章取義,只援引國際法院最后的結論。See Anglo-Iranian Oil Co. Case (United Kingdom v. Iran), Judgment, ICJ Reports 1952,pp.109-110.另外,該庭還基于仲裁條款的獨立原則而在MFN 條款適用上區別對待仲裁條款與實體條款。后來的一些仲裁庭也沿著這一推理方向,Telenor 案仲裁庭“完全支持Plama 仲裁庭的分析及其所表述的原則”,并指出,在沒有具體措辭或上下文表示相反的情況下,“應給予投資之待遇”這一措辭的通常語義指投資者的實體權利而不是程序權利。②See Telenor Mobile Communications AS v. Hungary, ICSID Case No.ARB/04/15,Award, 22 June 2006, paras.90-92.ICS 案和Daimler 案的仲裁庭還提出了同時期原則:阿根廷—英國BIT(基礎條約)締結于1990 年,在這一時期,學者與仲裁庭都主張仲裁條款應分割或獨立,從而保護投資者在東道國撤銷投資合同的情況下獲得賠償的權利。③See ICS Inspection and Control Services Limited v. Argentina, PCA Case No.2010-9, Award on Jurisdiction, 10 February 2012, para.290; Daimler Financial Services AG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ARB/05/1, Award, 22 August 2012, para.221.與仲裁條款獨立原則一樣,所謂的“同時期原則”也是為了進一步確立仲裁合意原則的阻礙作用。
在MFN條款適用上,把同一條約中的ISDS程序條款與實體條款依本身性質而區別對待是站不住腳的,除非締約國明確把ISDS條款排除在MFN條款主題范圍之外,或者對基礎條約進行合理解釋而可以明確地推斷出締約方排除ISDS條款的意圖。正如一些仲裁庭所言:ISDS條款應該與同一條約中其他條款一樣,既不能進行更具限制性的解釋,也不能作出更寬泛的解釋。④See Suez and Others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ARB/03/19,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3 August 2006, para.66.“原則上,MFN條款對包含該條款的條約所涵蓋的所有事項產生效力”,ISDS條款是投資條約的組成部分,自然也應該處于MFN 條款的主題范圍。①See Rudolf Dolzer & Christoph Schreuer,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20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因此,恰如席爾教授所言:設定一類特別的條款,使該條款本身就對被第三方條約中更優惠待遇所取代產生免疫,這一做法沒有任何理由,除非這些條款可以被解讀為MFN待遇的例外。②See Stephan W. Schill, The Multilater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146(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有些仲裁庭的裁決援用了席爾教授的這段話,例如,White Industries Australia Ltd. v. India, IIC 529, Final Award 30 November 2011, para.11.2.8.據此,在MFN條款可否引入第三方條約條款的問題上,ISDS程序條款應該與實體條款統一對待。
事實上,在符合同類規則要求的情況下,允許利用MFN條款引入其他ISDS條款并不違反投資仲裁合意原則。不同于一般商事仲裁,投資條約仲裁合意建立在“無默契仲裁”理論上。③該理論在投資條約仲裁實踐中被廣泛接受。See Jan Paulsson, Arbitration Without Privity, 10 ICSID Review 232-257 (1995).根據該理論,ISDS 條款被視為締約國對該條款規定的投資爭端給出仲裁同意,而后投資者提起投資仲裁的行為被視為對該仲裁同意的接受,并由此形成仲裁合意。根據上文分析,MFN條款的主題原則上涵蓋同一條約的所有事項,ISDS 條款所表達的仲裁同意自然也處于MFN 條款的主題范圍內。因此,這符合同類規則的第一項條件。就第二項條件而言,如果基礎條約規定了有效的ISDS條款,那么該條款就可以觸發同一條約中MFN條款的運行。MFN條款的具體作用機制是:當第三方投資條約中ISDS 條款包含更優惠的仲裁同意時,該ISDS條款被MFN條款引入,并在該MFN條款法律效力支持下成為約束基礎條約締約東道國的有效仲裁同意,而且這一更優惠的仲裁同意自該締約東道國締結該第三方投資條約之時起就立即擴散至受惠國的投資者,而不是在該投資者提起仲裁要求之后才能擴散。所以,MFN條款并不是在爭端提起之后再擴大基礎條約中ISDS條款授予的管轄權。④See Stephan W. Schill, Allocating Adjudicatory Authority: Most-Favoured-Nation Clauses as a Basis of Jurisdiction—A Reply to Zachary Douglas, 2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363 (2011).在此情況下,投資者獲得的有效仲裁同意建立在MFN 條款效力的基礎上,基礎條約中的ISDS條款效力被MFN條款推翻了。ST-AD GmbH案的仲裁庭認為,仲裁庭只有在滿足基礎條約中仲裁同意的所有條件獲得管轄權后才可討論MFN條款的適用范圍。⑤See ST-AD GmbH v. Bulgaria, PCA Case No.2011-06, Award on Jurisdiction, 18 July 2013, paras.397-398.這一推理誤讀了申請人利用MFN條款獲得優惠待遇的時間順序,也錯誤地把仲裁同意仍然建立在基礎條約的ISDS條款上。
就第八項目的而言,當基礎條約只規定一類ISDS 機制(例如UNCTAL 仲裁)時,或者當基礎條約規定有幾類ISDS機制時,其中部分ISDS機制對所涉投資者失去效力(例如Venezuela US 案)時,MFN 條款可以被用于引入第三方投資條約中更為優惠的其他類型ISDS 機制(例如ICSID),因為這也符合同類規則的兩項條件。在墨菲基尼案中,仲裁庭基于公共政策理由指出:在基礎條約具體規定了某一類ISDS 機制的情況下,MFN 不能引入其他類型的ISDS 機制。①See Maffezini v. Spain, ICSID Case No.ARB/97/7, Decision on Objections to Jurisdiction, 25 January 2000, para.63.實際上,該仲裁庭基于“公共政策”提出的例外情形并無法律根據。這種例外似乎僅僅建立在對締約國意圖的主觀推斷上,即從基礎條約對投資仲裁的一些“特別”規定中推斷出締約方把仲裁同意排除在MFN 條款主題范圍之外的意圖。因此,墨菲基尼案仲裁庭提出的這種例外情形缺乏說服力,受到不少仲裁庭的批判。②See Teinver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ARB/09/1,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21 December 2012, para.180.
至于第一種情形以及墨菲基尼案本身所涉及的利用MFN條款避開18個月等候期的情形,都與第七項目的相關,即利用MFN 條款引入對仲裁同意附加較少條件或者沒有附加條件的其他ISDS 條款。一般而言,這些附加條件是仲裁同意的組成部分。③See 駁回申請人利用MFN 條款避開18 個月等候期的訴請的Wintershall 案仲裁庭就持這種看法。 Wintershall Aktiengesellschaft v.Argentina, ICSID Case No.ARB/04/14,Award, 8 November 2008, para.160.換而言之,當申請人沒有滿足所附條件時,所涉ISDS 條款表達的仲裁同意對該申請人而言并未生效。因此,就該申請人而言,基礎條約不存在一項表達仲裁同意的有效條款。在此情況下,根據同類規則的第二項條件,申請人不能利用MFN 條款引入更優惠的其他ISDS 條款,盡管墨菲基尼案等系列案件的仲裁庭恰當地指出:ISDS 條款是投資保護的一部分,因而處于MFN 條款主題范圍內。④See Maffezini v. Spain, ICSID Case No.ARB/97/7, Decision on Objections to Jurisdiction, 25 January 2000, paras.54-56.不過,有些要求并非仲裁同意生效的條件。例如,Bayindir 案的仲裁庭恰當地指出,提起仲裁的通知要求是指示性的,而非仲裁管轄的必要條件。⑤See Bayindir v. Pakistan, ICSID Case No.ARB/03/29,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14 November 2005, paras.99-100.如此,申請人利用MFN條款引入其他ISDS條款的訴請就符合同類規則的兩項條件。
四、同類規則對MFN條款多邊化作用的限制
MFN 條款的法律效力建立在基礎條約上,所以基礎條約在屬人、屬物以及屬時方面的限制也將決定MFN條款的效力范圍。例如,Société案仲裁庭駁回了申請人試圖利用MFN條款擴大投資定義的訴請;Tecmed案和MCI案仲裁庭駁回了申請人試圖利用MFN 條款改變基礎條約不溯及既往適用的訴請。⑥See Société Générale v. Dominican Republic, LCIA Case No.UN 7927, Award on Preliminary Objections to Jurisdiction, 19 September 2008, para.41; Tecmed SA v. Mexico,ICSID Case No.ARB(AF)/00/2, Award, 29 May 2003, para.69; MCI Power Group LC and New Turbine Incorporated v. Ecuador, ICSID Case No.ARB/03/6, Award, 26 July 2007, paras.127-128.在統計的案例中,申請人試圖利用MFN 條款避開基礎條約例外條款的訴請也都被駁回了。這些都屬于MFN條款法律性質對其多邊化作用的內在限制。除此之外,同類規則對MFN條款多邊化作用也設置了限度。這主要體現在該規則包含的兩項條件上。
(一)第一項條件的限制
根據同類規則,MFN 條款引入的第三方投資條約條款所代表的更優“待遇”應處于MFN 條款主題范圍內。第四類MFN 條款,晚近出現的第七類MFN 條款,以及中國、俄羅斯等國家早期締結的BITs 中的ISDS 條款都對最惠國待遇的主題范圍有明確的限制。在此情況下,MNF 條款只能多邊化那些處于其主題范圍內的待遇保護條款。
1. ISDS仲裁受案范圍對最惠國待遇主題的限制
在中國、俄羅斯以及東歐國家早期締結的BITs 中,ISDS 條款限定外國投資者只能就征收補償數額等因一些特定條款產生的爭議提起仲裁。這意味著ISDS 條款把仲裁同意限制在一些特定條款上,從而把仲裁同意排除在MFN 條款主題范圍之外。因此,借用席爾教授的說法,這類ISDS 條款可以被視為最惠國待遇的例外。①See Stephan W. Schill, The Multilater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14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從統計的投資仲裁案例來看,涉及擴大投資仲裁受案范圍的訴請都被駁回了,除了RosInvest 案以外。但是,這其中大部分案例的仲裁庭卻把駁回訴請的理由建立在ISDS 條款與實體條款的區別對待上,而不是同類規則的限制。Plama 案所適用的基礎條約(保加利亞與塞浦路斯的BIT)第4 條第4 款明確規定投資者只能就征收補償數額提起國際仲裁。Berschader 案和ST-ADGmbH 案所適用的基礎條約中ISDS 條款也作出類似規定,而這兩個仲裁庭也都沿著Plama 案仲裁庭的推理方向,即把ISDS條款與實體條款區別對待。②See Berschader (Vladimir) and Berschader (Mose) v. Russian Federation, SCC Case No.080/2004, Award, 21 April 2006, para.202.該案適用的基礎條約是蘇聯與比利時的BIT,其第10 條規定投資者只能就征收補償數額或方式提起國際仲裁。See ST-AD GmbH v. Republic of Bulgaria, UNCITRAL, PCA Case No.2011-06, Award on Jurisdiction, 18 July 2013, paras.391-402.該案適用的基礎條款是德國—保加利亞BIT,其第4 條第3 款規定:征收補償數額爭議可通過仲裁庭解決。但是,這兩個仲裁庭駁回訴請的理由都是:只有基礎條約條款明確地、不含糊地規定MFN 條款涵蓋ISDS 條款或者可以明確地推斷出締約國有此意圖,才能允許申請人利用MFN條款引入其他ISDS條款。
在新近的兩個案例中,仲裁庭直接根據同類規則駁回訴請。在Anglia 案和Busta 案中,所適用的條約都是英國—捷克BIT,其ISDS 條款如俄羅斯以及其他東歐國家一樣規定:因第2(3)條(保護傘條款)、第4 條(對軍事沖突、內亂等造成損害的賠償)、第5條(征收)以及第6條(投資及收益的匯回)產生的爭端可提起國際仲裁。兩個仲裁庭都認為:所涉BIT 明確地把ISDS 機制排除在第3 條(MFN 條款)范圍之外,因此,申請人不能利用MFN 條款引入另一投資條約中更優惠的爭端解決條款……沒有必要再討論該MFN 條款的范圍(即“待遇”“根據東道國法律”,或者“管理、經營、使用、享有或處置”等措辭的含義)……也沒有必要探討提起仲裁是一項程序權利還是實體權利。①See Anglia Auto Accessories Limited v. The Czech Republic, SCC Case No.V 2014/181, Final Award, 10 March 2017, paras.191-192; I. P. Busta & J. P. Busta v.Czech, SCC Case No.V2015/014, Final Award, 10 March 2017, paras.166-167.
RosInvest 案仲裁庭的推論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該仲裁庭恰當地指出:提起仲裁是給予投資者保護的重要組成部分,至少在征收語境中,其與實體條款具有同等的保護作用,如果MFN 條款可以適用于實體條款,也應該可以適用于程序條款……其管轄權是建立在基礎條約中MFN條款與第三方條約中ISDS條款(丹麥—俄羅斯BIT)結合的基礎上。②See RosInvest Company UK Limited v. Russian Federation, SCC Case No.V079/2005, Jurisdiction Award, 1 October 2007, paras.130-132. 該案所適用的蘇聯與英國BIT 中的ISDS 條款規定:因第4 條(對軍事沖突、內亂等造成損害的賠償)和第5 條(征收)的賠償數額或支付、征收行為其他的后續事項、第6條(投資及收益的匯回)產生的爭端,可提起國際仲裁。但是,它沒有考慮BIT 中ISDS 條款已把其所表達的仲裁同意排除在MFN條款主題之外。換而言之,該庭無法回答如Daimler 案仲裁庭提出的一個疑問:雖然利用MFN 條款引入更優的ISDS 條款有利于投資保護,但這是以締約雙方所同意的那種方式來保護投資嗎?③See Daimler Financial Services AG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ARB/05/1,Award, 22 August 2012, para.259.所以,RosInvest案仲裁庭允許申請人利用MFN條款擴大投資仲裁受案的裁決是錯誤的。
綜上所述,當投資條約對ISDS條款的范圍作出限定而排除MFN條款時,申請人不能利用MFN 條款引入其他更優惠的ISDS 條款,這在投資條約仲裁實踐中得到廣泛的承認。而有些投資條約在限定投資仲裁受案范圍時并不排除MFN 條款,例如NAFTA 的修改版《美墨加協定》。作為該協定的附件(Annex14-D),美國與墨西哥的雙邊投資爭端協定規定,申請人只能就被訴國違反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征收及補償等條款提起仲裁。依此而言,該ISDS 條款包含的仲裁同意處于MFN 條款的主題范圍內。只是,該條款的注釋對最惠國“待遇”的含義作出了類似CETA 的限制性規定。所以在此情況下,申請人也不能利用MFN條款引入包括ISDS條款在內的其他條款。
2. CETA等晚近一些投資條約對最惠國待遇主題的限制
鑒于投資仲裁對MFN 條款解釋與適用的不一致性,晚近越來越多的投資條約為了防止MFN 條款帶來不可預料的多邊化風險而對最惠國待遇主題作出明確的限制。筆者對貿發會議網站公布的投資條約文本進行統計發現:在2018年1月至2019 年5 月期間,總計締結42 項投資條約,其中可獲得文本的投資條約28 項;在這28 項條約中,22 項條約的MFN 條款明確地把ISDS 機制排除在其主題范圍之外,6 項條約的MFN 條款沿用CETA 的限制性規定,2 項條約沒有規定MFN 條款。①See UNCTA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Navigator,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iia-mapping, visited on 8 October 2019.由此可見,對ISDS機制的排除已成為晚近投資條約中MFN條款實踐的常見做法。根據同類規則,這種做法將會排除MFN 條款被用于引入其他ISDS 條款的可能性。而CETA 對最惠國待遇的主題作出了更為嚴格的限制,即明確規定其他國際投資條約或貿易協定所規定的實體義務本身不屬于最惠國待遇的主題。根據同類規則,這意味著CETA 完全排除了MFN條款被用于引入任何第三方條約條款的可能性,從而完全限制了MFN 條款的多邊化作用。如此,MFN 條款只能適用于締約國的國內措施。從統計數據來看,這種做法在晚近投資條約實踐中還不常見(只占21%左右),主要被歐盟的投資條約所采用。實際上,這種做法并沒有否定同類規則的效力及內容,反而在一定意義上強化了同類規則對投資仲裁解釋與適用MFN 條款的指導作用。例如,歐盟與越南的貿易與投資協定中“投資章節”第2.4條(最惠國待遇)明確規定:本條款應該根據同類規則進行解釋。②See The EU-Vietnam Free Trade Agreement, Article 6.
這種做法的出現主要是因為:許多投資仲裁庭沒有嚴格地根據同類規則來解釋與適用MFN 條款。實際上,它們的裁決結果大多符合同類規則的要求,但是卻把裁決理由或多或少地放在對實體條款與程序條款的區別對待,以及對締約國意圖的主觀臆斷上。這不僅削弱了所涉裁決的說服力與權威性,而且在廣泛意義上侵蝕了投資條約MFN 條款的目的與價值。如前文述,MFN 條款的多邊化作用與投資條約體系的雙邊結構緊密相關,對建立一個開放的、非歧視的國際投資法律環境具有重要意義。CETA 式的做法大幅削減了MFN 條款對投資條約體系的積極效用。有些投資條約文件刪除MFN 條款的做法更是過猶不及,完全抹殺了MFN 條款的價值。事實上,基于同類規則對MFN 條款多邊化作用的限制,強化該規則對MFN條款實踐的指導并不會產生締約國無法預料的多邊化風險。
(二)第二項條件的限制
根據同類規則,MFN 條款引入其他更優條款的另一項條件是:基礎條約包含一項與該引入條款的主題具有本質同一性的條款。因此,在基礎條約沒有規定主題相似的條款,或者該主題相似的條款已經失去法律效力的情況下,MFN條款無法被用于引入其他更優的條款。晚近一些投資條約刪除了FET 條款、ISDS 條款等。③例如,南方共同體市場(Mercosur)成員國于2017 簽署的投資促進與合作議定書沒有規定ISDS 條款和FET 條款;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SADC)于2016 修改了金融與投資議定書,也刪除了ISDS 條款和FET 條款;See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7: Investment and Digital Economy 113-114,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wir2017_en.pdf,visited on 6 March 2019.MFN 條款的多邊化作用范圍也受到相應的限制。一般而言,當基礎條約中ISDS條款對仲裁同意附加條件時,若投資者未能滿足該條件,那么該仲裁同意并未生效。因此,基于第二項條件的限制,他也不能利用MFN 條款引入其他ISDS 條款。另外,有些投資條約對投資仲裁規定了時效。例如,中國與韓國、坦桑尼亞、烏茲別克斯坦、加拿大等締結的投資條約都規定了三年的投資仲裁時效。在超過該時效的情況下,投資者也無法利用MFN條款引入其他更優的ISDS條款。
在 Ansung Housing 案中,中國—韓國 BIT(2007)中 ISDS 條款第 9 條第 7 款規定:投資者首次知道或應該知道受損之日起超過三年,不得提起國際仲裁,而申請人試圖利用MFN條款引入中國的其他BIT以避開此項規定。仲裁庭駁回了此項訴請,其主要理由是:第3條第3款所規定的最惠國待遇是針對“投資和商業活動”的,所以對該條款措辭的直白解釋就是MFN 條款不適用于時效限制。筆者認為,“投資和商業活動”與“時效限制”之間并不是明示其一即排除其他的關系。假設MFN條款可以被用于延長時效,這對外國投資者的“投資和商業活動”而言難道不就是更優惠的待遇嗎?這種機械式的解釋就是道格拉斯教授(Douglas)所批判的“在(投資)條約解釋上對字典的迷信”。①Zachary Douglas, The MFN Clause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Treaty Interpretation off the Rails, 2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353-371 (2011).雖然道格拉斯教授這篇文章的主題是MFN 條款不適用于管轄權,但他對投資條約仲裁實踐中出現的這種解釋方法的批判是恰當的。在Garanti案中,雖然基礎條約(英國—土庫曼斯坦BIT)的MFN條款也規定締約一方就投資管理、維持、使用、享有或處置方面給予另一締約方的國民或公司以最惠國待遇,但是該庭認為:給予投資者更有利的國際仲裁就意味著給予該投資者在其投資管理、使用、享有和處置方面更優惠的待遇。②See Garanti Koza LLP v. Turkmenistan, ICSID Case No.ARB/11/20, Decision on the Objection to Jurisdiction for Lack of Consent and Dissenting Opinion, 3 July 2013, para.94.就此而言,Ansung Housing案仲裁庭的理由缺乏說服力。實際上,該庭完全可以根據同類規則駁回申請人的這種訴請,而不必做如此推論。
(三)相似情況或地域限制?
在一些投資條約仲裁案例中,第五類和第六類MFN 條款的有關措辭被解釋為對最惠國待遇多邊化作用的限制,可分別稱之為“相似情況”和“地域”限制。然而,進一步分析這些案例的推論以及所涉MFN 條款的措辭可以發現:這兩種限制都缺乏有效性。
在I?kale 案中,申請人試圖利用MFN 條款引入第三方投資條約中的公平公正待遇、全面保護與安全、非歧視、保護傘等條款。該基礎條約的MFN 條款屬于第五類。該庭認為:“相似情況”這一措辭是對MFN 條款適用范圍的限制,即要求對投資者投資的“事實情況”進行比較分析以得出該投資是否處于“相似情況”,因此,雖然第三方投資條約規定的投資待遇保護標準可能優于基礎條約的標準,但是可適用的法律標準上的差異并不構成“在相似情況下要求給予的待遇”,否則“相似情況”這一措辭也就失去意義。①See I?kale v. Turkmenistan, ICSID Case No.ARB/10/24(2016), Award, 8 March 2016, para.329.換而言之,“相似情況”的限制意味著:MFN條款只能被用于引入第三國投資者實際獲得的優惠待遇,而不能引入抽象的第三方投資條約規定的待遇保護標準。由此可見,該仲裁庭把“相似情況”解讀為類似CETA 第8.7 條對最惠國“待遇”含義的限制性規定。根據同類規則的效力,“相似情況”的要求是MFN 條款運行的內置要素。從某種意義上說,上述兩項條件就是為了把MFN 條款的多邊化效力嚴格限制在“相似情況”中,以免對締約國施加完全超乎意料的義務。所以,即使對“相似情況”沒有作出明確的表述,投資者也只能要求符合同類規則的最惠國待遇。②1978 年草案報告對同類規則也作出了類似的評論,不過,在當時國際經濟背景下,該評論針對貨物貿易。See UN, A/33/10(SUPP), 28 July 1978, p.31.因此,I?kale案仲裁庭基于“相似情況”的措辭對MFN 條款作出過度限制性的解釋是不恰當的。③Schill 教授批判性地指出,該案仲裁庭的推論有兩處錯誤,其中之一是:仲裁庭由MFN 條款中“相似情況”這一措辭得出該條款不能用于引入其他更優惠的實體待遇條款。See Stephan W. Schill, MFN Clauses as Bilateral Commitments to Multilateralism: A Reply to Simon Batifort and J. Benton Heath, 111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931-932 (2017).正如一位學者所言,我們有必要重視投資條約中MFN 條款的措辭,但是也不能過于強調文本中的細末差異而僵化條約的效力。④See Andrea K. Bjorklund, The Enduring but Unwelcome Role of Party Intent in Treaty Interpretation, 112 AmericanJ 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Unbound) 48 (2018).
在一些投資仲裁案例中,所謂的“地域限制”主要針對MFN 條款對其他ISDS條款的引入。例如,在北京城建公司案中,中國—也門BIT 第3 條第2 款后半部分規定“締約一方應依照其法律法規確保:對與他們投資有關的在其領域內的活動所給予締約另一方的投資者的待遇不低于最惠國待遇”。仲裁庭認為:這些措辭把最惠國待遇與發生在“領域內”的活動聯系在一起,這種地理上的限制使最惠國待遇不能擴展至國際仲裁,因為國際仲裁本身不是一項與被訴國領域有內在聯系的活動。⑤See Beijing Urban Construction Group Co. Ltd. v. Yemen, ICSID Case No.ARB/14/30,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31 May 2017, para.120.Berschader 案、ICS 案、Daimler 案以及 ST-AD GmbH 案等一系列案例的仲裁庭都把這種限制作為駁回申請人相同訴請的主要理由或者輔助理由。⑥See Berschader (Vladimir) and Berschader (Mose) v. Russian Federation, SCC Case No.080/2004, Award, 21 April 2006, para.185; ICS Inspection and Control Services Limited v.Argentina, PCA Case No.2010-9, Award on Jurisdiction, 10 February 2012, para.306; Daimler Financial Services AG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ARB/05/1, Award, 22 August 2012, paras.226-230; ST-AD GmbH v. Republic of Bulgaria, UNCITRAL, PCA Case No.2011-06, Award on Jurisdiction, 18 July 2013, para.395.例如,Daimler 案仲裁庭認為“在一項MFN 條款僅適用于東道國領域內的待遇時,符合邏輯的推論是東道國領域外的待遇就不處于該條款范圍內”。該推論確實符合邏輯,但是該推論的前提能否成立就令人質疑了。如果MFN條款的地域限制是針對“投資者及其投資”而不是“待遇”,那么該推論的前提就不能成立。就北京城建公司案而言,我國官方公布的中文版條文是:“締約一方應依照其法律和法規保證給予在其領土內的締約另一方投資者與其投資有關的活動的待遇······不應低于最惠國的投資者的待遇。”從該條文中,可以得出另一番解釋:只有適格的投資者及其投資活動才受MFN條款的保護,而處于締約一方“領土內”的另一締約方的投資者及其投資活動才是適格的。換而言之,“領域內”是對“投資者及其投資”的限制,而不是對“待遇”限制。這一解釋更符合投資條約的屬人和屬物效力。Impregilo SpA案仲裁庭認為:“領域內”這一措辭不能排除MFN條款適用于爭端解決機制。①See Impregilo SpA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ARB/07/17, Final Award, 21 June 2011, para.100.
綜上所述,這兩種限制都是有些仲裁庭對第五類、第六類MFN 條款作出道格拉斯教授所批判的機械式解釋而得出的。實際上,根據同類規則,這兩類條款并沒有對最惠國待遇標準的多邊化作用施加有效的限制。
五、結 論
在ISDS 機制的支持下,MFN 條款的多邊化影響日益受到關注,這主要與投資條約的雙邊結構有關。MFN 條款是以擴散更優惠“待遇”的名義而間接地多邊化體現該待遇的第三方投資條約條款。這一多邊化作用機制受同類規則的約束,只要符合同類規則的要求,MFN 條款就可以被用于引入其他更優惠的條款,除非所涉MFN條款明確地作出另外規定。而在投資條約體系出現的七類主要MFN條款中,只有第四類以及晚近出現的第七類MFN 條款規定了明確的限制,其他類型并沒有對最惠國待遇的多邊化作用規定有效的限制。
國際法委員會1978 年草案報告對同類規則的內容及效力有比較權威的表述。雖然該草案的背景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但其核心規定依然是解釋與適用MFN 條款的基礎,這在2015 年報告中得到進一步的確認。在投資條約的MFN 條款本身不甚明確的情況下,對該條款的解釋與適用不能與一般國際法規則脫離,而同類規則就屬于相關的一般國際法規則。根據同類規則,MFN 條款能否引入第三方投資條約的條款需要滿足兩項條件:其一,該引入條款所代表的更優“待遇”處于MFN 條款主題范圍內;其二,基礎條約規定有一項與該引入條款的主題具有本質同一性的條款。根據這兩項條件對投資仲裁案例進行實證分析后可以發現,同類規則支持絕大部分案例的裁決結果。但是,許多仲裁庭卻把裁決理由或多或少地放在對實體條款與程序條款的區別對待上:對實體條款的引入想當然地支持而沒有謹慎分析MFN 條款和同類規則,對程序條款就以仲裁同意原則為由要求有投資條約的明確規定。這其中,不少仲裁庭還把一些裁決理由建立在對MFN條款的主觀分析上,在語義貧瘠匱乏的MFN條款上以VCLT規則的名義主觀臆斷締約國的意圖或者機械地解釋某項措辭來支持自己先入為主的結論。這些理由不僅大幅削弱了所涉裁決的說服力與權威性,引發許多不必要的爭議,而且還嚴重侵蝕了最惠國待遇標準的價值與目的,使各國產生一種MFN 條款已失控的錯覺。實際上,同類規則不僅明確MFN 條款的多邊化作用機制,而且也劃出了該條款多邊化作用的限度。在此基礎上,各國可以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與發展需求在投資條約中對MFN 條款進行有效的定制,使該條款的作用及實踐朝著自己可期的方向發展。
總而言之,強化同類規則對投資條約MFN 條款實踐的指導,不僅可以改善投資仲裁實踐的正當性與可預期性,而且有助于MFN 條款價值與目的的實現,以推動一個開放的、非歧視的國際投資法律環境的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