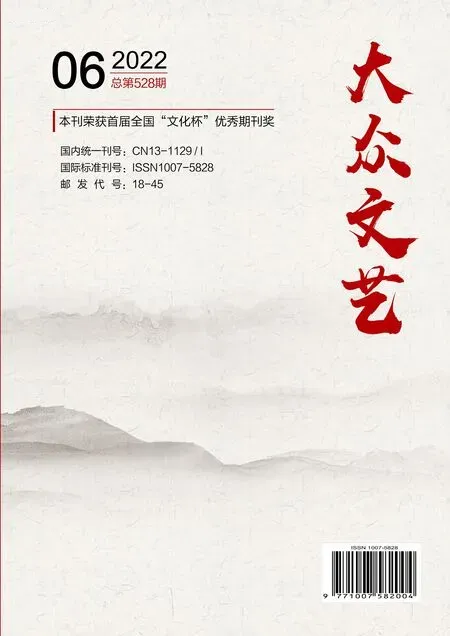列斐伏爾空間理論視域下網(wǎng)絡(luò)小說空間場景設(shè)定研究
(江南大學(xué)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工作坊 214000)
雷米·埃斯指出,20世紀(jì)70年代以來,亨利·列斐伏爾完成了由鄉(xiāng)村社會學(xué)到研究都市、空間與城市的轉(zhuǎn)變。自2000年以來,學(xué)界對于列斐伏爾的關(guān)注度不斷提升,閆超從建筑學(xué)的角度討論了列斐伏爾與20世紀(jì)70年代“享樂”建筑間的關(guān)系,林葉從城市人類學(xué)的角度論述了關(guān)于列斐伏爾空間理論的三元關(guān)系、空間視角與當(dāng)下都市實踐的再思考,陳慧平、李春敏分別就列斐伏爾的社會空間理論和空間生產(chǎn)理論進(jìn)行了探析。
目前學(xué)界對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跨學(xué)科研究、尤其與文學(xué)作品相結(jié)合研究的學(xué)者及論著較少,而實際上,文學(xué)作品中的人物無法脫離文本為他們構(gòu)建出的空間而活動。列斐伏爾在《空間與政治》一書中曾指出,“空間要么依靠一種先在的、至高無上的和絕對的,甚至是神學(xué)的邏輯;要么就是邏輯本身,是連續(xù)性的系統(tǒng);要么,最終,它在接受某種行動的邏輯的過程中,接受了這種連續(xù)性。在這里,人們發(fā)現(xiàn)了關(guān)于空間的不同觀點,要么作為范例,要么作為工具,要么作為中介。”近幾年流行的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寫手們更是熱衷于精心雕飾、設(shè)計他們的人物活動的空間場所,比如人物交流信息的酒樓、茶館、客棧,居住的皇宮,藏身的密室等。本文將立足于當(dāng)下頗受讀者歡迎的、改編為影視劇搬上銀幕的網(wǎng)文,以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為依據(jù),從“作為工具的空間”“作為范例的空間”以及“作為中介的空間”三個角度來論述網(wǎng)文中的空間設(shè)定。
一、作為工具的空間:茶館酒樓
在以古代社會為背景的網(wǎng)文小說中,茶館、客棧甚至妓院都或多或少在一定程度上承擔(dān)著信息交流與溝通傳遞的重要功能,這些場所中每天聚集著大量的來自社會各階層的人員,魚龍混雜、流動性強(qiáng)。因而,茶館、客棧、妓院的包間往往就具有了一定的隱秘性,大量的密謀與私會往往會被作者安排在這些場合中進(jìn)行。因此,酒樓茶館往往易被特權(quán)階級所利用,作為意識形態(tài)宣傳的工具性場所。而作為工具存在的茶館酒樓往往具有以下兩種功能:
(一)為主人公命運的轉(zhuǎn)折提供發(fā)生空間
列斐伏爾在《對空間政治的反思》一文中指出,“空間是政治性的”,在《空間與政治》序言中,他亦指出,“空間是戰(zhàn)略性的”。人物命運往往與他所處的意識形態(tài)環(huán)境聯(lián)系在一起,有時候,自己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個人命運往往與他所關(guān)系到的意識形態(tài)集體的利益而決定。因此,空間在某種情境下,就為意識形態(tài)改變個人命運提供了發(fā)生的場所。
《魔道祖師》中的夷陵老祖魏無羨在圍剿亂葬崗一戰(zhàn)中跌落懸崖而死,夷陵老祖的故事本該到此結(jié)束,而由于聶懷桑的精心安排與對莫玄羽的慫恿,而使得莫玄羽愿下舍身咒救活魏無羨,使得魏無羨在某種意義上獲得一種自我的重生。清河聶宗主安排一位說書人在茶館中說了三天夷陵老祖的故事,使得眾人相信以夷陵老祖的本領(lǐng)法術(shù),在某天重回于世是完全可能發(fā)生的事情,這樣的信息被說書人以故事的形式傳播開來,在茶館這種集散地、收容往來四海過客的地方傳播,無形中就將夷陵老祖重回世間的消息帶到了天下各處,為魏無羨的重生造足了勢。說書人的宣傳此時具有了“意識形態(tài)”性,為專門的意識形態(tài)的合法化起到了普及的作用。在《夢回大清》中,趙鳳初趙老板的臥底身份被十四懷疑以后,十四在酒樓請了十三觀趙老板之戲,期間,十四不斷用語言試探十三,稱“趙老板的每一場戲都能迎來觀眾的叫好”,這話暗示了十三,他已然懷疑甚至發(fā)現(xiàn)趙鳳初的身份。這里,酒樓為十三、十四分別代表的四爺黨與八爺黨這兩股勢力的相遇和交鋒提供了可能的發(fā)生空間。
(二)為人物的情感升溫提供場所
在《空間與政治》中,列斐伏爾指出,在被分割的空間中,“每個人都在一個抽象的空間上進(jìn)行操作,按照他自己的標(biāo)準(zhǔn)、自己的比例”,而要消除這些分割,就要“確定一個結(jié)合點”。按照列斐伏爾的說法,在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中,當(dāng)作品涉及到男女情愛線索的時候,要想讓男女主產(chǎn)生聯(lián)系,就要想辦法建立兩人之間空間的連接。而茶館、客棧往往為男女主人公相遇提供連接的可能。《知否知否應(yīng)是綠肥紅瘦》中,盛明蘭毀掉了顧廷燁娶余大姑娘的計劃,顧廷燁質(zhì)問盛明蘭為何毀他婚事,而盛明蘭則道出朱曼娘不安分守己、大鬧余府的事跡,提醒顧廷燁堤防小心曼娘,二人的酒館對話為顧廷燁看到明蘭的仗義執(zhí)言提供了場所,而之所以選擇酒館而非府邸等場所也暗示讀者此時顧廷燁對盛明蘭的好感還未得到認(rèn)可,是“非法”的,為顧廷燁之后為娶盛明蘭而做出的一系列行動提供最原始的理由與動力。
二、作為范例的空間:皇宮
“皇宮”作為專制主義社會特有的一種建筑和權(quán)力形態(tài),無疑具有一種典范性。在《空間與政治》序言中,列斐伏爾指出,“讓空間服從權(quán)力,控制空間,通過技術(shù)來管理整個社會”,在宮斗小說中,皇宮無疑是統(tǒng)治階級統(tǒng)治整個社會的工具,它具有“宗教或者政治性建筑的不朽性和重要性,以及相對于‘居住’的優(yōu)先性”。從2004年開始連載的《夢回大清》到桐華的《步步驚心》、匪我思存的《寂寞空庭春欲晚》,再到流瀲紫的《后宮·甄嬛傳》、瞬間傾城的《未央浮沉》,這些故事的展開自然要依托皇宮作為舞臺,甚至一種符號式的存在與標(biāo)志。
列斐伏爾指出,“整個社會生產(chǎn)出了‘它的’空間”。依托自給自足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而產(chǎn)生的專制主義集權(quán)政治的語境下催生出“皇宮”這一空間,皇權(quán)統(tǒng)治下產(chǎn)生的皇宮就像一座金色的囚籠,服從、服務(wù)于掌控它的皇權(quán),逐漸同化并生產(chǎn)出順從的嬪妃、皇后、宮人以及新的統(tǒng)治繼承人。
《后宮·甄嬛傳》中,甄嬛初入宮闈,在皇宮的碎玉軒和養(yǎng)心殿兩個主要空間中恩寵不斷,完成了她人生的“高光”時刻。用計回宮黑化后,入主永壽宮,鏟除異己,最終扳倒皇后,成為太后,“皇宮”幾乎承載了甄嬛大半的人生軌跡。而這樣一個具有反抗性的少女最終也是在皇宮中完成了她的異化,成為了世故毒辣的深宮婦人,成為了皇權(quán)機(jī)器中的最高捍衛(wèi)者。由此,以“皇宮”為依托書寫她的故事顯得合理而融洽。同為清穿三大鼻祖小說之一的《夢回大清》,講述的是現(xiàn)代女孩徐薔薇穿越回清朝康熙年間,無意卷入九子奪嫡的紛爭,并與十三皇子胤祥展開跨越時空的傳奇愛情的故事。小說中,回到古代的小薇,在德妃娘娘的長春宮中當(dāng)差、在皇宮中接受皇帝的賜婚、多次被康熙皇帝召見的情節(jié)都是依托皇宮展開,皇宮禁地使得情節(jié)的發(fā)展、爾虞我詐的上演有了合理性,也為小薇增添傳奇性的光環(huán),同時,也向讀者展現(xiàn)了宮闈之中,個人命運的身不由己,個人的無力感。
三、作為中介的空間:密室
密室往往與隱秘、不可告人、人性的陰暗面相聯(lián)系,它起到一種傳通的作用,為人物命運的進(jìn)行或轉(zhuǎn)折提供可能的空間。網(wǎng)文中,發(fā)生在密室中的情節(jié)往往帶有關(guān)鍵性、決定性,抑或預(yù)示著關(guān)鍵性情節(jié)的發(fā)生。
(一)關(guān)鍵人物的隱藏
密室作為藏身之處躲避追兵,是其最平常不過的功能。在《知否》中,當(dāng)太后黨與顧廷燁一黨展開最后的決戰(zhàn)之時,明蘭一家自然無法獨善其身,追兵將至,已是侯府主母的明蘭果斷決定打開家中的密室,讓常媽媽、榮姐兒、還有自己剛出生不久的兒子躲入其中,這時候的密室是一個保護(hù)的空間,起到正面而積極的作用,而密室的出現(xiàn)也暗示讀者,小說的最高潮部分已經(jīng)來臨,人物的決戰(zhàn)時刻即將到來。
密室隱匿的關(guān)鍵人物除了正面的、弱小的,便是危險的。在《未央浮沉》中,代宮王后青檸在被發(fā)現(xiàn)細(xì)作身份以后,便被薄姬囚禁在幽棄冷宮中,避免青檸為呂后傳遞信息,王后青檸在密室中飽受折磨卻依然要想出保護(hù)代王與讓呂后放心的萬全之策,她以口傳烏鴉、以鳥語傳信的卓越本領(lǐng)更是因為有了密室的烘托,才更顯傳奇色彩,而竇漪房在密室中密會青檸,目睹青檸為保代國而死的經(jīng)歷更是給了她很大的啟發(fā),直接啟示了竇漪房使用報假消息助代國韜光養(yǎng)晦的方法。
與之相似,在《魔道祖師》中,溫若寒操控陰鐵,以各大世家的子弟作為試驗品,煉就傀儡,而這些消失掉的世家子弟就被隱藏在了溫若寒的不夜天城中,某種程度上,不夜天城的大殿就相當(dāng)于密室,隱藏陰鐵的秘密、隱藏溫若寒稱霸各大世家的野心。
(二)“偷窺”視角的結(jié)合
“偷窺”的視點往往能夠為小說情節(jié)的發(fā)展提供可能的依據(jù)。“偷窺”的視角最早出現(xiàn)于西班牙流浪漢小說《小賴子》,近年來,我國影視劇的處理也愿意加入“偷窺”視點。比如,2018年上映的《影》,讓子瑜對鏡州起了殺心而必置他于死地的情節(jié)即是發(fā)生在密室中,子瑜通過門眼處的縫隙偷窺到鏡州霸占自己的妻子,潛意識中挑戰(zhàn)了自己權(quán)威的做法。密室里的視點突出了子瑜的陰險與狡詐,為情節(jié)的發(fā)展提供了合理性。
列斐伏爾在牛津、農(nóng)特爾等地的發(fā)言稿《空間》中,曾指出,“人們無權(quán)假設(shè)一種先在的系統(tǒng),比如一個社會的,或空間都市的系統(tǒng),從而將局部的因素納入其中,而這些局部因素的理性又來自這個假設(shè),又由整體演繹而來。”他又指出,“如果存在著一個系統(tǒng),那么就應(yīng)該揭露它,說明它,而不是把它作為出發(fā)點。如果人們由這樣一種假設(shè)出發(fā),那么人們就置身于一種虛偽的重復(fù)中了,因為他們僅僅是從這一假設(shè)中推演這些結(jié)果的。”
因此,這也就解釋了為何“密室”總與“偷窺”的視角相聯(lián)系。只有親眼窺探到密室里不可告人的秘密,才能把自己推測、假設(shè)的系統(tǒng)和空間真正地揭露和說明,使之脫離虛無,公之于眾。在《魔道祖師》中,金光瑤為了報仇,且左文自己仙都一位,在他殺死了聶明玦以后,將其頭顱藏在自己的密室中懸掛,這件事情做的極其隱秘,雖然魏無羨等人在聶懷桑的引導(dǎo)下,不斷加深了對于金光瑤的懷疑,可一切只是推測。要使魏無羨等人最終能夠揭穿金光瑤,就必須要有證據(jù)支持,這時,小說選擇了一個非常巧妙的方式——讓魏無羨做法術(shù),使得帶有魏無羨靈識的小紙人跑入金光瑤的密室,由此親眼看到金光瑤所犯罪行,而印證眾人推斷。小說巧妙地運用了“偷窺”的方法,使得小說帶上了玄幻的色彩,“紙人潛入密室”的處理方式巧妙地突出體現(xiàn)了魏無羨其人的古靈精怪與神通廣大,也化解了文本情節(jié)無法推進(jìn)的矛盾,而“密室”這一空間,則在印證魏無羨一行人的過程中,“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
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作為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興起的一種文學(xué)形式,空間的設(shè)計在網(wǎng)文中占據(jù)重要的地位,不同的空間承擔(dān)不同的功能,與它所在的文本融合成一個完整的整體,仍具有進(jìn)一步發(fā)掘與研究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