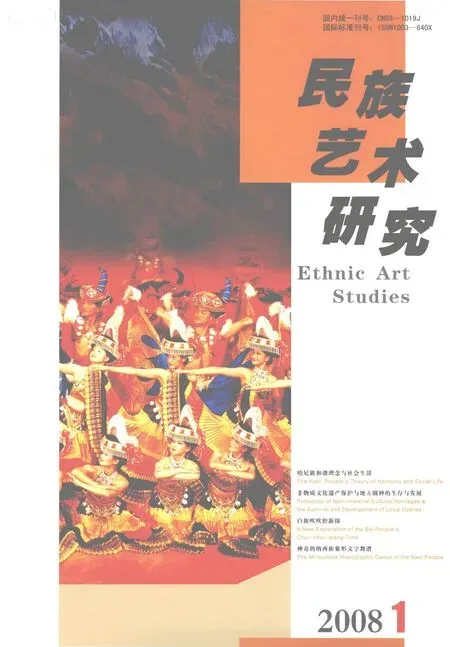中國古代藝術風格類型理論的早期形態
張蘭芳
中國古代藝術風格類型理論從先秦兩漢時期孕育萌芽,到魏晉六朝時期從審美意義上正式確立,經歷了相當長的發展過程。然而,目前相關古代藝術風格類型理論研究,大多從文藝學角度出發,著眼于文論批評相關文獻,認為 “魏晉以后才形成自覺的風格類型論”,①吳承學:《中國古典文學風格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頁。由此,中國古代藝術風格類型論的研究起點,主要是以魏晉六朝時期文論批評所積累的風格類型理論為研究對象,而對其他門類藝術理論批評相關 “風格類型”的文獻很少提及。眾所周知,魏晉六朝時期盡管社會動蕩、朝代更迭,但人的自我覺醒與精神自由,促進文學藝術發展走向自覺,其理論批評突破了政教倫理道德束縛,集中針對藝術自身及其美學問題進行思考,尤其是倡導主體個性張揚,促使這一時期的理論批評對 “風格”問題格外關注,除文論批評重視風格問題的理論概括外,其他門類藝術理論(如詩論、書論、畫論等)批評領域也有大量相關 “風格”的言論體例,其中包括對風格類型的劃分與思考。然而這些文獻卻一直未能引起研究者足夠的重視。
與此同時,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思考,那就是魏晉六朝時期各門類藝術理論批評涌現出諸多相關 “風格類型”的言論體例,絕非偶然。任何事物的出現,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風格理論也是如此。難道此前的理論批評沒有相關 “藝術”及其 “風格類型”的認識與劃分,還是由于研究者的忽視,尚未對魏晉六朝以前的藝術理論文獻進行考察、發掘?有鑒于此,本文擬從廣義 “藝術”層面出發,著重對先秦兩漢至魏晉六朝時期關涉 “藝術”及其風格類型的言論體例進行系統考察與綜合研究,旨在探究中國古代藝術風格類型理論的早期形態。
一、古代藝術風格類型理論的孕育萌芽
檢視古代藝術理論文獻,發現古人相關“藝術”的言論、批評,早在先秦時期就已出現,主要集中在 “樂”論方面。相較于造型藝術 (建筑、雕塑、繪畫、工藝)的理論探討,樂論不僅出現最早,而且數量相當可觀①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百家爭鳴,有關 “樂”的記錄、討論相當活躍豐富。在 《尚書》《周禮》《竹書紀年》《左傳》《國語》《論語》《老子》《莊子》《管子》等文獻中,包含諸多相關 “樂”的制度、篇目、見聞、形式、活動、評論等內容,在《墨子》《荀子》《呂氏春秋》設專篇探討音樂相關問題,甚至還出現了具有完整體系的樂論專著 《樂記》。,其中有些言論已關涉 “藝術”及其風格類型問題。
據古代最早的歷史典籍 《尚書》記載,上古時期,部落首領、君主貴族非常重視“樂”,將其納入貴族子弟教育體系當中②《尚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舜典》載 “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可見,“樂”在人類社會早期,不是僅指音樂,而是包括詩、歌、聲、律、八音在內彼此協調的綜合性藝術,這里的詩、歌、聲、律及八音都包含于“樂”活動當中,其表現形態與效果已初具“藝術”類型劃分的意味。
其后,西周貴族教育開設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③《周禮·地官·保氏》載:“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具體來看,“六藝”具體包括:“禮”指吉禮、兇禮、賓禮、軍禮和嘉禮等五種禮儀規范;“樂”指 《云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等六種樂舞;“射”指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等五種射技;“馭”指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等五種駕車技術;“書”指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形聲等六種漢字構造法;“數”指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腰等古代九種算術法。參見郭丹主編: 《先秦兩漢文論全編》,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12年版,第317頁。課程,其中 “樂”為大藝,屬大學的課程;孔子辦私學也仿照西周教育體制傳授 “六藝”,其中只有 “樂”是較為純粹的藝術活動,“書”與藝術有所關聯,其他各項都與藝術無關,或者說是 “技術”。某種程度上,“六藝”具有很強的實用性,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解決各種實際困難,完成各項社會事務所必須掌握的基本技能。在 “六藝”中,“藝”“技”是沒有區別的,這種將藝術與非藝術 “混雜”并列的分類理論,是以實用功能為標準的類型劃分,而非針對藝術本體的類型劃分,更沒有從審美角度論及 “藝”的風格問題。然而,這種 “混雜”現象,在某種程度上,卻對后世的風格類型劃分理論產生了一定影響。
就 “樂”活動的教學內容來看,其所包含的 “詩”“舞”“樂”中,已出現較為具體的劃分。如,“六詩”與 “六義”,《周禮·春官·大師》載:“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④《十三經注疏·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三,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10頁。后來,漢代 《毛詩序》將 “六詩”稱為 “六義”:“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⑤《詩大序》,載 《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卷第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頁。表面看來, “六詩”與“六義”包含的內容等同,但其出發點與表達方式卻不同。這可能是由于 “《周禮》和《詩序》的語言環境不一,表達方式不同使然。”⑥韓宏韜:《孔穎達對〈詩經〉“六義”問題的貢獻》,《理論月刊》2012年第6期。對此,孔穎達在 《毛詩正義》中解釋:“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大小不同,而得并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非別有篇卷也。”⑦《國風·周南·關雎》,載 《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卷第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3頁。現代學者也普遍認為,風、雅、頌指的是詩歌的體裁種類,而賦、比、興是指用于寫作風、雅、頌三種詩歌的藝術手法,《詩經》的藝術形態已初具文體風格的意味。相較于 “六藝”而言,“六詩”“六義”已經擺脫了藝術與非藝術的“混雜”問題,是專門針對詩歌、較為純粹的“藝術”類型劃分。
再如 “六樂”,作為 “六藝”之 “樂”的具體化,包括 《云門》 《大咸》 《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分別為黃帝、堯、舜、禹、商、周不同時期的大型樂舞,作為大司樂教授國子的內容,其功能主要在于教化,但因歌頌對象不同,其表現方式、整體風貌,乃至風格特點也一定有所不同。另外,先秦樂論有相關 “八音” “十二律”等劃分理論,已具體到樂器、樂律層面,雖未論及風格,但這種類型劃分是基于音樂自身的類型劃分,距離音樂 (風格)類型理論又近了一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荀子,他在 《樂論》中不僅對樂器種類作了區分,還關注到音聲的 “風格”特點: “聲樂之象:鼓大麗,鐘統實,磬廉制,竽笙簫和,筦鑰發猛,塤篪翁博,瑟易良,琴婦好,歌清盡,舞意天道兼。”荀子以極富審美性的范疇語匯 “大麗”“統實” “廉制” “發猛” “清盡”等對鼓、鐘、磬、竽、笙、簫、和、管、籥、塤、篪、瑟、琴、歌等十多種樂器的音聲、歌唱及舞蹈表演的風格特點或意象作了概括,這是荀子經過深入體會、仔細辨析所獲得的審美感受,表明他對不同樂器本體的音聲音色及風格特點的認識已進入較高層次,非常值得肯定。當然,荀子的這一分析是針對墨子 “非樂”的反駁,他不止一次強調 “樂者,樂也”,但他所謂的 “樂”并非純審美意義上的 “樂”,而是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受時代局限,荀子未能掙脫政治道德框架的束縛,從非功利的視角來認識藝術的審美娛樂功能。但荀子能以精煉簡潔的范疇語匯,從欣賞的角度對音樂自身的風格特點及類型進行區分概括,這在古代藝術風格類型史上尚屬首次,對后世風格類型理論無疑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此外,與 “藝術”相關的類型劃分,還有基于時代治亂之 “音”的區分。 《禮記·樂記》提出 “治世之音” “亂世之音”及“亡國之音”①《禮記·樂記》“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其后 《毛詩序》又做了進一步的發揮。②漢代 《毛詩序》:“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這些言論將音樂與時代治亂相聯系,認為不同時代的政治、道德、風俗等狀況對音樂 (詩歌)具有決定作用,很明顯這是儒家 “尚用”思想的體現,并非針對音樂(藝術)自身的類型劃分。
漢代,“賦”作為時代文學的代表盛極一時,內容上側重 “體物寫志”,形式上側重“鋪采摛文”,多以豐辭縟藻、窮極聲貌的溢美之詞大肆鋪陳,力求通過巨細宏微、細膩模擬的描繪,實現對世間萬物的把握與囊括,涌現出司馬相如、揚雄、班固等賦家。然而,理論批評領域相關 “賦”體類型區分,并未完全從文體自身出發進行審美觀照,而是特別強調儒家道統思想的核心地位。揚雄 《法言·吾子》提出 “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③[漢]揚雄撰、韓敬注:《法言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27頁。的觀點,他以 “麗”字對 “賦”體的整體風格特點進行概括,屬于形式美范疇。但在揚雄內心深處卻嚴格遵從儒家 “原道”“征圣”“宗經”的思想,因此在理論批評中,體現出對形式主義傾向的反對態度。他將賦分為 “詩人之賦”與 “辭人之賦”兩種類型,認為辭賦是 “童子雕蟲篆刻” “壯夫不為”④[漢]揚雄撰、韓敬注:《法言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25頁。,而詩賦之 “麗”才值得欣賞,但也不能過度,必須要受到 “則”的限制,遵循一定的規則法度。在揚雄看來,“麗以則”是值得提倡的,而 “麗以淫”卻是應堅決反對的。盡管這樣的批評言論是對文體自身風貌或特色的把握,已具有一定的 “風格”意識,但其理論出發點,依然未能脫盡儒家思想道德規范的制約。
先秦兩漢時期相關 “藝術”的理論批評,尚未出現專門意義上的風格類型理論探討,更多的是從實用功利或道德教化著眼,但相關批評語匯、分類方法等卻對后世藝術風格類型理論具有啟示作用,應視為古代藝術風格類理論的 “萌芽”時期。
二、古代藝術風格類型理論的正式確立
隨著社會歷史的演進與時代精神的變遷,尤其是各個門類藝術的各自獨立發展成熟,基于藝術自身的風格類型理論終于在魏晉六朝時期正式確立。顯著的標志是,這個時期人物品評對個性的崇尚,對美的發現,藝術創作實踐取得高度成就,涌現出大量風格迥異的名家杰作,促使理論批評的重心逐漸從藝術外部 “實用功能”轉向藝術自身 “審美價值”,表現出對 “風格”問題前所未有的關注。文論、詩論、書論、畫論等批評領域相關 “風格”的言論體例比比皆是,用以表達“風格”之意的概念也相當豐富,如“體”“體制”“體韻”“體法”“體格”“風格”“風”“風骨”“氣”“氣候”等①張蘭芳、田啟川:《廣義 “藝術”層面的古代 “風格”概念辨析》,載 《藝術學界》第18輯,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17年版,第57-65頁。,從多重角度對藝術自身的風格特點進行審美觀照。理論家不僅認識到個性風格的獨創價值,還圍繞風格的成因、類型以及品評等相關問題作了探討。就 “風格類型”理論而言,既有體式風格類型的區分,也有風格類型的審美概括,形成了一系列較為成熟的風格類型理論。
(一)“體式”風格類型
1.文論 “體式”風格類型
中國古代藝術風格類型理論最早出現于“文體”學中。曹丕 《典論·論文》按照文體寫作規范與特點的相似性,將八種文體劃分為四種類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②郭丹主編:《魏晉南北朝文論全編》,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頁。
曹丕以 “雅”“理”“實”“麗”對四類文體進行分類概括,簡潔而凝練。就所用范疇語匯來看,除 “麗”之外,其他三個范疇并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 “風格”范疇,這種“混雜”并列,某種程度上是對前代相關“藝術”類型劃分的延續,依然含有 “實用性”成分。但是,這一分類理論并不完全是從外部社會功能著眼,而是從不同文體自身寫作要求進行分類,提出了相應的評價標準或審美 (風格)要求,體現出較強的形式美傾向。尤其是他將文體兩兩歸類,已然認識到不同文體之間的共通性,具有一定進步意義。
其后,晉代陸機對不同文體作了更為細致的區分,《文賦》云:“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凄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③[西晉]陸機著,金濤聲點校:《陸機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頁。
不同于曹丕將每兩種文體歸為一類,以“單字”范疇對四類文體 (風格)進行簡括。陸機更側重對單一文體進行具體闡發,他采用極富形容性、審美性的 “五字”范疇語匯對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十種文體 “風格”進行分別概括,無論文體種類,還是辨析層次,都更顯細膩,表明理論家對風格類型的認知逐步走向深化。就所用范疇的構詞方式來看,陸機采用 “AB而CD”和 “AB以CD”兩種類型,前者出現7次,后者出現3次,突出了不同文體在功能、用途等主旨內容方面的要求,也體現出不同文體在辭采、聲情等表現形式方面的特點。當然,陸機的分類理論同樣也具有實用性目的,但陸機更側重于 “形式服務于內容”這個角度來區分不同文體的風格類型。
魏晉六朝時期,有關體式風格類型理論探討最為細致周全的是劉勰。他在 《文心雕龍》二十余篇文論中對包括:詩、樂府、賦、頌、贊、祝、盟、銘、箴、誄、碑、哀悼、雜文、諧、隱、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啟、議、對、書記等30多種文體作了研析,結合各種文體特定的功能用途,與儒家文化、社會事物、交際往來、儀式慶典等相聯系,對它們的含義、起源、發展、適用場合、寫作特點等作了細致深入的闡釋,其中不乏文體寫作特征及風格的論述。如 《明詩》篇區分四言、五言詩體,提出 “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的觀點,這一提法對后世詩歌創作與理論批評產生深遠影響,甚至成為歷代評價四言、五言詩作的風格標準。尤其是 《定勢》篇,劉勰一口氣對22種文體的風格類型及特點作了區分與概括:“是以括囊雜體,功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于明斷;史論序注,則師范于核要;箴銘碑誄,則體制于宏深;連珠七辭,則從事于巧艷: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
這種論述方式與曹丕、陸機一脈相承,是 “體式”風格類型論的延續與拓展。就所涉文體種類來看,劉勰將22種文體 (或四種或兩種)區分為六類,相較于曹丕 “八體四類”的簡略粗分,其風格類型更為豐富,相較于陸機 “十體十類”的具體分析,其類型化思想更為鮮明,表明劉勰對不同文體風格之間 “共性”特征的認識與思考更加深刻。
2.書論 “體式”風格類型
書論批評領域,也有關于 “體式”風格類型的著述。東漢許慎在 《說文解字·序》指出中國文字的象形特點,強調文字的功用的同時,對文字的六種造字方法和文字演變脈絡做了梳理,列舉秦書 “八體”,包括“大篆” “小篆” “刻符” “蟲書” “摹印”“署書”“殳書”及 “隸書”,還列舉了王莽攝政后命大司空甄豐等人校訂文字、改訂古文所形成的 “六書”—— “古文” “奇字”“篆書”“佐書”“繆篆”“鳥蟲書”,這是中國古代書體演變的結果,也是基于實用功能而形成的不同書體類型。
然而,魏晉六朝以來,文學藝術的發展走向自覺,人們對書體實用功能的重視程度逐漸減弱,轉而關注書體自身的審美特點,涌現出相關書論,如崔瑗的 《草書勢》、蔡邕的 《篆勢》、成公綏的 《隸書體》、索靖的《草書狀》、衛恒的 《四體書勢》等,皆以“書體”的 “勢”“體”“狀”直接命名,更多關注的是不同書體自身的形態展示與審美意趣,已然擺脫了實用功能的束縛。某種意義上,這些關于不同書體 “勢”“體”“狀”的審美描述,可視為早期書體風格類型理論的雛形。
3.畫論 “體式”風格類型
魏晉六朝時期,畫論批評領域沒有出現專門探討 “體式”風格的著述。相關言論主要著眼點,一方面側重于繪畫實用功能的宣揚,另一方面側重于具體畫家畫作的品鑒。如王延壽 《文考賦畫》強調繪畫應發揮 “惡以懲世,善以示后”①王延壽:《文考賦畫》,載潘運告主編:《漢魏六朝書畫論》,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97年版,第252頁。的教化功能,而發揮這樣的功能主要通過 “人物畫”來實現,顧愷之的 《論畫》《論畫人物》《魏晉勝流畫贊》等著述也主要是針對 “人物”繪畫進行品鑒。需要指出的是,這個時期受玄學影響,自然山水已然引起文人士大夫的關注,逐漸成為繪畫創作的表現對象。相關畫論如宗炳的《畫山水序》、王微的 《敘畫》等,都是關于“山水畫”的專論。
盡管這個時期的畫論批評較為零散,相關 “人物畫”或 “山水畫”專論只涉及某一體裁,尚不具備類型的意義,但至少具有某一類繪畫 “體式”風格的意義。表明此時畫論批評相關 “風格”問題的理論探討尚處起步階段。
4.詩論 “體式”風格類型
魏晉六朝時期,詩論批評獲得長足發展。除相關詩體的各種散論之外,最有代表性的是鐘嶸的 《詩品》,該作以 “體”論詩,將兩漢至齊梁間的五言詩詩人 (120人)和無名氏的 《古詩》分為上、中、下三品,其雖然沒有專門針對詩歌風格類型進行劃分,但作為中國藝術批評史上第一部以 “品”評詩的詩學專著,其中關涉大量詩人詩作風格的品評言論①如評古詩 “其體源出于 《國風》……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評陸機 “才高詞贍,舉體華美”,評謝靈運 “雜有景陽之體”等,參見[梁]鐘嶸著、曹旭集注:《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5、132、160頁。,在某種意義上,其也具有 “詩體”風格的意義。尤其是 《詩品》將風格品評與分級品第聯系在一起,將感性領悟納入理性批評中,這為后世理論家在此基礎上認識到風格類型的多樣性,進而從理論層面進行風格類型劃分,奠定了基礎,在中國古代藝術批評領域具有重要影響。
(二)審美風格類型
除了對門類藝術的 “體式”風格類型進行探討,這個時期最為突出、最為重要的風格類型理論是劉勰的 “八體”說,他在 《文心雕龍》 “體性”篇中,首次從宏觀層面對文學風格類型進行整體分類與審美概括:“若總其歸途: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
此處的 “體”,指的就是 “風格”,該理論 “是區分風格之始”②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42頁。。劉勰認識到風格的多樣性,將風格歸納為八種類型,并對每一種風格都做了具體規定與闡釋:
典雅者,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遠奧者,馥采曲文,經理玄宗者也;精約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醲采,煒燁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爍異采者也;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③[梁]劉勰:《文心雕龍·體性》,載詹瑛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4—1020頁。
很顯然,劉勰對風格類型的區分是比較純粹的風格類型理論。“八體”的設置,主要從內容與形式兩方面展開。其中 “典雅”與“遠奧”二體側重于內容主旨,其他 “六體”皆側重于形式表現。如,“精約”體現為字句簡練、剖析精細;“顯附”體現為文辭曉暢,切合事理;“繁縟”指內容繁復,辭采絢爛;“壯麗”指宏偉高超,措辭雄麗;“新奇”指摒棄傳統,追求新奇;“輕靡”指文辭浮華,內容淺薄。這些風格類型體現出劉勰對形式要素的重視。這一點十分關鍵,自先秦以來,藝術創作及理論批評的重心偏重于思想內容,而忽視形式表現。劉勰能認識到內容與形式對藝術創作的重要性,關注到形式表現對風格的影響,從審美角度來劃分風格類型、概括風格特點,使藝術風格獲得獨立存在的意義,實在是難能可貴。特別是劉勰將八種風格類型兩兩相對,認識到風格類型之間的聯系與對比。張少康認為 “劉勰之所以把風格分為八體與兩兩相對的四組,這是與他受《易經》思想的影響有關系的。風格組成上的八體與四對,即來自于 《易經》八卦的啟發。”④張少康:《文心雕龍新探》,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版,第115頁。王小盾甚至認為 《文心雕龍》是依據《周易》陰陽八卦理論建立風格類型體系的,并將八種風格與八卦作了一一對應:典雅—乾、遠奧—坤、精約—震、顯附—艮、繁縟—兌、壯麗—離、新奇—巽、輕靡—坎。⑤王小盾:《〈文心雕龍〉風格理論的 〈易〉學淵源——為王運熙老師80華誕而作》,《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5期。當然,這一假設不一定成立,但表明 “八體”類型論并非隨意設定,而是深受中國古代辯證思維影響的產物。“八體說”的提出,雖然只是針對文學風格類型進行劃分,卻在中國藝術風格理論體系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中國古代藝術風格類型理論真正 “確立”的標志,對后世各個門類藝術風格類型的劃分,產生了廣泛影響。
三、古代藝術風格類型理論的審美話語
風格類型理論是人類審美意識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站在審美立場上對藝術自身體貌與特色進行感悟、體驗的結果。通過對古代相關 “藝術”理論文獻考察發現,從藝術與非藝術的混雜,到單一門類藝術的分列,古人首先強調的是藝術的實用功能,至于藝術的 “審美”問題,則往往依附于其 “功能論”中。這一點在先秦兩漢時期體現得尤其明顯。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古人對藝術 “審美”的毫無覺察。恰恰相反,古人正是認識到了藝術的 “審美”價值,藝術才受到部落首領、君主貴族的重視與利用,將其視為治國安邦、思想教化的工具。可以說,在任何歷史階段,理論批評總是在倡導藝術的 “實用功能”的同時,伴隨著對藝術自身 “審美”價值的肯定。只是在不同歷史階段,由于社會主流思想、審美觀念不同,尤其是門類藝術發展成熟的高度不一,理論批評對藝術及風格類型的認知與評價呈現出鮮明的時代差異。
循著這個思路,探究中國古代藝術風格類型理論的早期形態,本文以魏晉六朝時期形成的一系列風格類型理論為基點向前追溯,力求從相關 “藝術”及其 “風格類型”理論的話語表述方式中發掘古人的看法、觀點及審美立場,是否能從藝術本體出發,基于高度成熟的創作成果與豐富的欣賞實踐,對藝術 (藝術家或作品)整體風貌與審美特色從理論層面進行概括,彰顯藝術自身的藝術魅力和審美價值,以此作為甄別風格理論話語的主要依據。
從 “萌芽”時期理論批評來看,盡管理論家始終將實用功利與社會功能作為評價藝術的根本原則,但也伴隨著他們對 “美”的感悟與追求。上古時期舜帝規范樂教,旨在通過詩、歌、聲、律、八音彼此和諧,培養年輕人的良好品格,實現 “神人以和”的“和美”境界。周代推行 “六藝”,充分認識到 “樂”的藝術感染力和審美價值。孔子論樂,倡導 “美善合一”,追求內容與形式的和諧統一;評 《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評《武》 “盡美矣,未盡善也”,不但不否定“美”,還對 “美”抱以欣賞態度;談及聞《韶》的審美感受,竟然發出 “三月不知肉味”的感嘆——可見孔子已被音樂自身的表現力和感染力所征服,已然產生對作品審美本質的深層認識。到荀子這里,對藝術表現及風格的認識進一步具體明晰,采用 “大麗”“統實”“廉制”“發猛”“清盡”等范疇語匯對 “聲樂之象”進行概括,并且認識到藝術的審美娛樂價值,多次強調 “樂者,樂也”,盡管尚未突破儒家政治道德框架的約束,但他對 “聲樂”風格類型的劃分,更多的是從欣賞角度來感知藝術自身特點,從中獲得豐富的審美體驗和精神愉悅。漢代揚雄區分 “賦”體類型雖以儒家道統思想為本,但他以 “麗”字概括 “賦”體風格,表明他對 “賦”這種文體自身審美性的認識與把握是十分準確的,這一點,可從大量的賦作文章中得以確證。
從 “確立”時期的理論批評來看,基于藝術自身審美價值的褒揚,遠遠超過對其外在實用功能的倡導,相關 “藝術”及其 “風格類型”的理論話語、概念范疇,較前代呈現出更為強烈的審美性。
一方面,風格類型理論所涉范疇語匯具有審美性。文論批評成熟較早,采用高度凝練的單字或雙字范疇概括文體風格較為多見,如曹丕以 “麗”概括詩賦風格,陸機以 “綺靡”“瀏亮”“纏綿”“溫潤”“清壯”“精微”“朗暢”“閑雅”“煒曄”等范疇概括詩、賦、誄、銘、箴、論、奏、說等文體風格;劉勰以 “雅潤”與 “清麗”對比四言詩與五言詩風格,以 “典雅”“清麗”“明斷”“宏深”“巧艷”等范疇將多種文體按照寫作要求及特點的相似性進行分類,甚至還從宏觀層面對文學風格類型進行整體概括,提出的“典雅” “遠奧” “精約” “顯附” “繁縟”“壯麗”“新奇”“輕靡”等,都是較為純粹的 “風格”范疇語匯。可見這個時期理論批評對藝術自身風格問題的重視,對形式美的主動追求與積極倡導。而且,這些極具審美性的范疇語匯是以不同文體或作品之間共性的寫作要求或風格標準為基礎進行歸類的,這表明魏晉六朝時期的理論家已然清晰地認識到風格的相通性與類型化,為后世風格類型理論話語、構詞范式樹立了典范。
另一方面,風格類型理論所涉意象比擬具有審美性。如書論批評,以書體演變為基礎,將筆畫線條的形態走勢作為區分書體風格類型的依據,采用 “意象比擬”方式描述書體風格特點,如 “或象龜文,或比龍鱗”(蔡邕 《篆勢》), “婉若銀鉤,漂若驚鸞”(索靖 《草書狀》)等,所謂美在 “勢”“狀”,美在 “意象”,鮮活生動地展現了不同書體的風貌與特色。又如詩論批評,鮑照對比謝靈運與顏延之詩作,區分出 “初發芙蓉,自然可愛”與 “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①[唐]李延壽:《南史·顏延之傳》,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586頁。兩種風格類型。這些話語通過創設意象,以批評者的審美眼光照亮了不同書體、詩作的風格特色,這是獨具特色的理論話語方式,對后世藝術理論批評產生了深遠影響。
需要特別關注的,還有這一時期相關作家、作品風格的品評言論,雖然只針對單一門類藝術,卻采用大量極富審美意味的范疇語匯。如顧愷之的 《魏晉勝流畫贊》中評《小列女》 “面如銀……作女子尤麗衣髻,……成其艷姿”,評 《伏羲神農》“有奇骨而兼美好”,評 《壯士》“有奔騰大勢”等;謝赫的 《古畫品錄》評陸綏 “體韻遒舉,風彩飄然”,評吳暕 “體法雅媚”等;南朝姚最的 《續畫品》評劉璞 “體韻精研”,評沈粲“筆跡調媚”等。袁昂的 《古今書評》評皇象書 “如歌聲繞梁,琴人舍徽”,評衛恒書“如插花美女,舞笑鏡臺”等。鐘嶸的 《詩品》評曹植 “骨氣奇高,詞采華茂”,評陸機 “才高詞贍,舉體華美”,評張華 “其體華艷”,等等。從中可以看出,此時的理論批評已然擺脫了各種功利思想的鉗制與實用功能的束縛,將注意力更多集中在對藝術家、藝術作品風格特色的贊美與審美價值的褒揚上。
結 語
綜上,中國古代藝術風格類型理論從先秦兩漢時期孕育萌芽,到魏晉六朝時期正式確立,總體上經歷了從模糊趨于鮮明、由外部實用功能轉向藝術自身審美價值研究的發展過程。早期社會作為綜合藝術的 “樂”,逐漸分化為具體的詩、樂、舞;為滿足不同實用功能的需求,又出現不同文體、書體、畫體等,藝術的樣態形式愈加豐富,風格類型也愈加多元。與此相應的理論批評,伴隨著“藝術”的分化逐漸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門類藝術實踐發展成熟次序不一,理論批評與實踐發展之間的不平衡,致使各門類藝術理論批評領域積累的藝術風格理論文獻呈現出較大差異。相對而言,魏晉六朝時期由于文學藝術的發展走向自覺,文學創作實踐的高度成熟,促使文論批評獲得長足發展,相關風格類型理論取得豐碩成果,形成了一定的規模體制,為研究風格類型理論提供了豐富直接的理論文獻;書論、畫論批評由于書畫藝術實踐仍處發展完善過程中,相關風格問題的理論探討還不夠深入,但理論批評者也認識到藝術自身的美以及風格問題,從 “體式”或書畫作家作品的品鑒中,仍可以發現與風格類型相關的理論話語或風格范疇。最為困難的是對魏晉六朝以前相關 “藝術”及其風格類型理論的挖掘,由于其時 “風格”概念尚未明晰,與 “藝術”相關批評言論大多零散、潛藏在非藝術的歷史典籍文獻有關 “樂”的批評話語之中,從而給研究者探索中國古代藝術風格類型理論早期形態帶來很大困難。更為重要的是,先秦兩漢時期相關 “藝術”批評,更多的是從功利角度對藝術的社會功能與實用價值進行衡量,而不是從無功利角度對藝術的自身特點與審美價值進行評價,即使有相關藝術品鑒的言論涉及美感,采用一些頗具形容性、審美性的范疇語匯對藝術表演及音聲特點進行描述品賞,也始終束縛于政治道德與倫理規范中,屬于 “功能論”的范疇。這恐怕也是目前研究領域忽視先秦兩漢時期 “風格”問題的主要原因。研究者很難從龐雜、模糊的言論中發現與 “風格”直接相關的文獻資料,對藝術自身特點及 “風格”問題進行研究,由此也造成古代風格類型理論研究的“不完整”,研究者往往將魏晉六朝時期作為研究起點,逐漸向后延展關涉唐、宋、元、明、清各個歷史時期,唯獨沒有先秦、兩漢時期。雖然有研究者指出,先秦時期理論批評中出現的 “文” “質” “美” “善” “哀”“樂”等概念, “可以看作風格類型論的萌芽”①吳承學:《中國古典文學風格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頁。,但對于 “萌芽”時期與 “藝術”相關的言論是否關涉 “風格類型”問題,至今沒有梳理清楚。正緣于此,本文基于理論文獻的發掘考察,結合門類藝術實踐發展史實,試圖對先秦兩漢至魏晉六朝有關 “藝術”及其風格類型理論由 “萌芽”到 “確立”這一過程進行回溯、梳理,力求對中國古代藝術風格類型理論的早期形態形成較為清晰的認識與理解,為彌補當前研究領域存在的缺失做一點基礎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