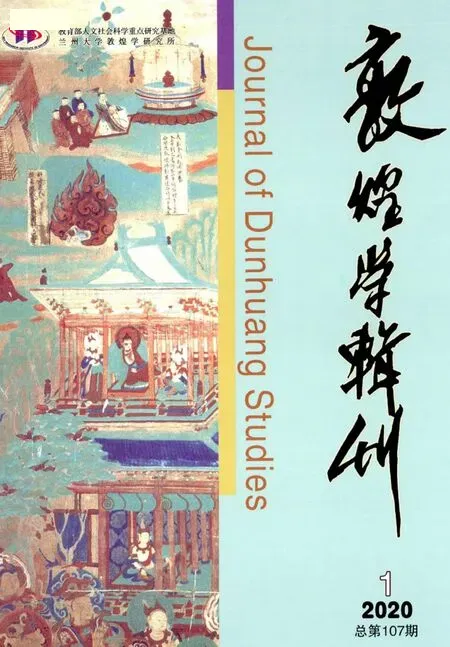莫高窟唐代 《維摩詰經變》中的帝王像及其冕服研究
趙燕林
(敦煌研究院 考古研究所,甘肅 敦煌 736200)
一、莫高窟唐代 《維摩詰經變》中的帝王像
莫高窟現存唐代 《維摩詰經變》共計32鋪,除漫漶不清的4鋪和唐初的7鋪舊式《維摩詰經變》之外,其余23鋪都以 “貞觀新樣”的 《維摩詰經變》 (后文簡稱 “新樣維摩變”)的形式呈現,①王中旭 《敦煌翟通窟 〈維摩變〉之貞觀新樣研究》,中山大學藝術史研究中心編 《藝術史研究》第14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69-397頁。在該經變文殊一側下部問疾隊伍的中心位置一般都繪制有一身身穿冕服的中原帝王像,這些帝王像多與傳為唐閻立本的 《歷代帝王圖》中的晉武帝司馬炎、魏文帝曹丕等穿戴冕旒的帝王像形象相似,此類帝王像清晰可辯者共存18鋪。②根據筆者調查,敦煌石窟中的唐代 《維摩變》全部繪制在莫高窟。據 《敦煌石窟內容總錄》統計,榆林窟晚唐第30窟中繪制有 《維摩變》,但經實地調查該窟及榆林窟其它唐代洞窟,均未發現該經變。霍熙亮整理 《安西榆林窟內容總錄》,敦煌研究院編 《敦煌石窟內容總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04-221頁;及其附錄 《維摩詰經變》部分,第295-296頁。此外,在同時期的 《涅槃經》《觀無量壽經》《金光明經》和 《地藏十王》變中也有繪制,但和 “維摩變”中的帝王像相比,這些經變中的帝王像不僅數量少而且形式簡單,僅可算作是一種象征或標志而已。而 “新樣維摩變”中的帝王像則繪制得寫實而精致,尤其是各時期不盡相同的冕服服制,更是值得關注。
根據前賢研究成果來看,學界對于敦煌帝王像的專題研究較為鮮見,大多關注于對220窟 “新樣維摩變”帝王像與 《歷代帝王圖》的對比討論,且多為介紹性文字。其中,討論最多者當屬段文杰先生,他曾極具見地的指出:“閻立本 《歷代帝王圖》中的晉武帝司馬炎、光武帝劉秀幾乎完全相同,所不同者 《維摩變》中之帝王圖盡管衣冠服飾與當時制度完全相符,卻不是一個具體帝王畫像。①段文杰 《創新以代雄——敦煌石窟初唐壁畫概觀》,中國壁畫全集編輯委員會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壁畫全集·敦煌5初唐》,沈陽:遼寧美術出版社,1989年,第14頁。此后,王中旭先生專文梳理了莫高窟第103、220、332、335窟中的 “新樣維摩變”,并論述了第220窟壁畫與貞觀年間長安流傳帝王圖像、蕃王使臣之間的關系。②王中旭 《敦煌翟通窟 〈維摩變〉之貞觀新樣研究》,第369-397頁。趙聲良先生則系統論述了唐代莫高窟帝王圖像與閻立本 《歷代帝王圖》帝王像的流傳情況。③趙聲良 《帝王圖與初唐人物畫》,《絲綢之路:圖像與歷史》,上海:東華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39-146頁。同時,葉貴良④葉貴良 《莫高窟220窟 〈帝王圖〉‘貂尾’大臣非中書信令、亦非右散騎常侍》,《敦煌學輯刊》2001年第1期,第22-25頁。、盛朝輝⑤盛朝暉 《也談莫高窟第220窟帝王圖 ‘貂尾’大臣之身份》,《敦煌學輯刊》2005年第2期,第77-84頁。、曹喆⑥曹喆 《莫高窟唐代壁畫維摩詰變中的官員服飾考證》,《敦煌研究》2007年第1期,第45-49頁。等人對此也有過不同的論述。這些研究成果的發布,都為我們系統梳理莫高窟唐代帝王像及相關歷史問題提供了可靠依據。此外,筆者在討論莫高窟第220窟帝王圖冕旒問題時,對該窟帝王像所著冕服的紀實屬性做了說明,并討論了此帝王像所著冕服可能為 《周禮》所載六冕之纟希冕,但對同期其他壁畫中的帝王圖像卻未涉及。⑦趙燕林 《莫高窟第220窟維摩詰經變帝王圖像研究》,《敦煌研究》2018年第6期,第20-31頁。故本文在前文的基礎上,就此問題進行進一步的討論。
經筆者調查,莫高窟唐代 “新樣維摩變”中的帝王像保存較好者共計18鋪。其中,初唐3鋪,盛唐2鋪,中唐7鋪,晚唐6鋪。其所繪位置、內容在各時期不盡相同,但其畫面形式卻始終是以文殊和維摩詰兩者對坐辯法的形式呈現的。從服制方面看,各時期帝王冕服服制亦有區別,既有穿戴無旒 “大裘冕”和 “皮弁”的情形,還有穿戴玄冕、纟希冕、袞冕的情況,形式較為復雜。為了梳理之便,現將莫高窟唐代帝王圖像所在洞窟號、所繪位置和冕旒數、服制等情況統計如下 (表1):

表1 莫高窟唐代 “新樣維摩變”中的帝王像統計表① 洞窟排列依據樊錦詩等人的洞窟時代分期研究成果羅列。樊錦詩、劉玉權 《敦煌莫高窟唐前期洞窟的分期》,樊錦詩、趙青蘭 《吐蕃占領時期莫高窟洞窟的分期研究》,《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43-181、182-210頁。
由上表可知,莫高窟唐代 “新樣維摩變”打破了隋代以來在西壁龕內、外兩側或上部繪制 《維摩詰經變》的格局,不僅品數增加,而且畫面內容變得更為復雜。恰如段文杰先生所論:“初唐第220窟維摩詰經變帝王圖中之帝王,頭戴冕旒,冕板前圓后方,前低后高,垂十二旈,兩側垂黈纊,著大袖青衣,白紗中單,方心曲領,大綬畫升龍,紅蔽膝,曲裙,黑地紅裳,笏頭赤舄,衣領十二章,兩肩繪日月,衣上遍飾山樹,袖端飾粉米等紋,形制文采與唐閻立本 ‘帝王圖’中之蜀主劉備、晉武帝司馬炎衣冠相同。”①季羨林 《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第210頁。其他帝王像也和第220窟帝王像大致相似,但其所著冕服服制都不相同。造成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我們推測可能與有唐一代各時期輿服制度的調整有著密切關系。
二、唐代冕服制度的調整
輿服是中國古代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古代帝王的 “為邦之道”,由此形成的禮樂典制——包括輿服——既被視作天下大治的標志,又被視作大治天下的手段。據閻步克先生研究, 《周禮》所載的 “六冕之制” (大裘冕、袞冕、鷩冕、毳冕、纟希冕、玄冕)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包括唐在內的各朝各代祭服的變遷。輿服最大的區別在于冕冠旒數和服裝紋章的多少,并以此區別尊卑貴賤,但很長時間以來,臣下的冕服也可以 “如王之服”。尤其是在 “視朝”和 “聽朔”的時候,君臣在服飾上難以區分,為了 “尊卑有差、貴賤有等”,突出帝王至高無上的地位,歷代都對輿服制度進行調整和更新,而有唐一代更為突出。②閻步克 《宗經、復古與尊君、實用 (上)——中古 〈周禮〉六冕制度的興衰變異》,《北京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閻步克 《宗經、復古與尊君、實用 (中、下)—— 〈周禮〉六冕制度的興衰變異》,《北京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2期。
唐朝立國,依循隋制。而隋代冕服制度乃采北齊之法,同時也受到北周冕服制度的影響。③《通典》記載:“隋采北齊之法……子男則毳冕。五品以上纟希冕,五品以上爵弁。”但并未敘及冕旒的情形。參 [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 《通典》卷57《禮典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604頁。北齊、北周冕服制度具有的 “君臣通用”特點,這一點在隋代冕服制度中得以延續,并直接影響到了唐初的冕服制度。唐初統治者注意到了因為 “古禮”可能造成的等級扭曲,遂于唐高祖武德七年 (624)推出了 “武德令”。但到了唐高宗顯慶元年(656),“巨勘前件令,是武德初撰,雖憑 《周禮》,理極未安”的矛盾暴露了出來。于是,長孫無忌、于志寧、許敬宗等大臣認為 “服制混亂”導致 “君臣不別”,并上書曰:
又檢 《新禮》,皇帝祭社稷繡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玄冕,三旒,衣無章。謹按令文是四品五品之服,此則三公亞獻,皆服袞衣,孤卿助祭,服毳及鷩,斯乃乘輿章數,同于大夫,君少臣多,殊為不可……請遵歷代故實,諸祭并用袞冕。①[后晉]劉昫等撰 《舊唐書》卷45《志第二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938-1939頁。
唐高宗隨即 “制可”,“自是,鷩冕已下,乘輿更不服之,……而令文囚循,竟不改削”。鷩冕以下諸冕,從此被皇帝擱置一旁,等于又回到隋煬帝大業冕制去了。②閻步克 《宗經、復古與尊君、實用 (下)—— 〈周禮〉六冕制度的興衰變異》,第95頁。即唐高宗時期皇帝不再穿戴毳、纟希、玄冕,即五、四、三旒的冕冠只有大臣在祭祀的時候穿戴了。這一狀況一直延續至唐玄宗開元十一年 (723)南郊,玄宗以 “大裘樸略,冕又無旒,既不可通用于寒暑,乃廢不用之”。 “自是,元正朝會,用袞冕及通天冠;大祭祀依 《郊特牲》,亦用袞冕。自余諸服,雖著在令文,不復施用”。③[宋]王溥撰 《唐會要》卷31《輿服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62頁。自此,“冕服只被看作是一種隆重的禮服”④孫機 《兩唐書輿 (車)服志校釋稿》,《中國古輿服論叢 (增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383頁。,冕服的使用范圍日益萎縮。到了唐文宗開成元年 (836)五月 “常服御宣政殿”,文宗僅著常服。可見這時連袞冕和通天冠也逐漸退出了實用的領域。⑤孫機 《兩唐書輿 (車)服志校釋稿》,第409頁。自此,唐代輿服制度經過不斷調整之后,帝王冕服已經失去原本的意義。
總的來看,有唐一代輿服制度屢有變遷,但基本都以 “武德令”和 “開元禮”為據。而 “武德令”服制冕旒以九、七、五、四、三為差, “開元禮”服制以九、七、六、五、四為差”。⑥閻步克 《宗經、復古與尊君、實用 (下)—— 〈周禮〉六冕制度的興衰變異》,第93頁。其不同點我們引用閻步克先生所作 “《周禮》鄭玄注與兩 《唐書》的冕旒級差表 (表2):

表2 閻步克先生所作 “《周禮》鄭玄注與兩 《唐書》的冕旒級差表”⑦ 閻步克 《宗經、復古與尊君、實用 (下)—— 〈周禮〉六冕制度的興衰變異》,第93頁。
由此表可知,《周禮》和新、舊 《唐書》中除大裘冕與袞冕所載冕旒數相同以外,鷩冕、毳冕、纟希冕和玄冕的旒數完全不同。故考察唐代帝王服制問題,需要關照 “武德令”和 “開元禮”的時效問題。據前文可知,大可將唐代服制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從唐朝建立的618年到 “武德令”頒布的624年為沿襲隋朝服制階段;第二,從 “武德令”推行的624年到 “開元禮”頒布的732年為 “武德令”服制階段;第三,從“開元禮”推行的732年到唐文宗開成元年 (836)五月 “常服御宣政殿”為 “開元禮”服制時期;第四,唐文宗開成元年五月直至唐結束為 “常服”服制時期。也由此可知,唐代輿服制度至少有過四種面貌,這不僅反映在唐代文獻中,還反映在這一時期的敦煌 《維摩詰經變》的帝王像中。但需要注意的是,安史之亂以后,敦煌一度為吐蕃和歸義軍節度使統治,這也是導致莫高窟唐代帝王圖像形式多樣的主要原因。因為不同的統治者在表現地位尊卑的帝王圖像時,無疑會注入自己的政治意志及愿望。
三、莫高窟唐代帝王像及其服制的變化
(一)初唐時期敦煌帝王像及其服制
一般來說,敦煌初唐時期為唐高祖建國到武則天退位這一段時期 (618-705年)。莫高窟第220、332、335窟屬于這一時期開鑿完成的洞窟,其中都繪制有 “新樣維摩變”,此三窟帝王像分別穿戴六、五、五旒冕冠 (圖1、2、3)。根據洞窟時代信息,三窟帝王冕服應該是依據 “武德令”服制繪制。但檢索 《舊唐書》等與武德令相關的文獻資料,其中沒有六旒冕冠的記述,卻有五旒纟希(繡)冕。我們推測,這一服制與初唐輿服制度不斷調整的歷史密切相關。

圖1 莫高窟第220窟帝王像(敦煌研究院提供)

圖2 莫高窟第332窟帝王像(敦煌研究院提供)

圖3 莫高窟第335窟帝王像 (敦煌研究院提供)
1.莫高窟第220窟開鑿完成于貞觀十六年 (642),其東壁 “新樣維摩變”帝王像是敦煌現知最早的帝王像,人物形象、藝術風格等方面都和傳為唐閻立本繪 《歷代帝王圖》晉武帝司馬炎像等帝王像都極為相似。但 《歷代帝王圖》中的晉武帝司馬炎等帝王穿戴十二旒袞冕,而第220窟帝王像卻穿戴六旒冕冠。根據貞觀十六年這一時代背景推斷,第220窟帝王像所著六旒冕冠系唐 “武德令”和 “開元禮”糾纏期間借鑒北齊、北周或隋初輿服制度的產物,而非前人所謂初唐帝王應著服制。①趙燕林 《莫高窟第220窟維摩詰經變帝王圖像研究》,第20-31頁。另據史睿先生考證,初唐第220窟 《維摩變》是現存隋代孫尚之新樣 《維摩變》的最早作品。②史睿 《隋唐法書屏風考——從莫高窟220窟維摩詰經變談起》,榮新江主編 《唐研究》第23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339-359頁。如果這一觀點成立,則該窟帝王冕服依隋制而來的說法應該是可信的。
2.莫高窟第335窟北壁 “新樣維摩變”繪制完成于圣歷年間 (698-699),③賀世哲 《從供養人題記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營建年代》,敦煌研究院編 《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94-236頁。其中帝王像穿戴五旒冕冠。據前文可知,武周冕服制度沿用 “武德令”之制,故檢 《舊唐書》可知,此一時期的五旒冕冠為天子所著 “纟希冕”。但有意思的是,該窟帝王像冕旒數雖然和第220窟旒數不同,但兩者服制一致,都為 “纟希冕”。可據此推測,第335窟帝王像應該是對第220窟帝王像的復制和移用,只是第335窟帝王像改用了武德服制,使得二者冕旒旒數發生變化。
3.第332窟建成于武周圣歷元年 (698),④賀世哲 《從供養人題記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營建年代》,第194-236頁。該窟北壁 “新樣維摩變”所繪帝王穿戴五旒冕冠,亦系 “武德令”之 “纟希冕”。根據原保存于該窟的 《李君莫高窟佛龕碑》碑文內容可知,該窟是時任 “大周沙州左玉鈐衛効谷府校尉”的李克讓修建的功德窟。有學者曾指出,第332窟是李克讓家族融入全國擁戴武周、崇信佛教熱潮的表現。⑤楊效俊 《王權、佛法、家族與敦煌的宗教空間——以莫高窟李氏家族所供養的第332、148窟為中心》,杜文玉主編 《唐史論叢》第28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19年,第259-273頁。如此,帝王像應該是嚴格按照當時服制而成的觀點便不難理解。
(二)盛唐時期敦煌帝王像及其服制
根據樊錦詩等先生的斷代分期研究,盛唐為李唐復辟到吐蕃攻陷敦煌一段時期(705-781年),這一時期敦煌石窟中繪制有 “新樣維摩變”的有莫高窟第68、103、194窟三窟。①樊錦詩、劉玉權 《敦煌莫高窟唐前期洞窟的分期》,第143-181頁。其中,第68窟畫面漫漶不清,帝王具體形象不得而知,在此不做推測。第103、194窟帝王像繪制為六、九旒冕冠的形象 (圖4、5)。
1.一般認為,盛唐第103窟 “新樣維摩變”所據粉本和初唐第220、335、332窟相同,且人物線條更為遒勁,風格更趨成熟。②李昀 《萬國衣冠拜冕旒——敦煌壁畫中的朝貢者形象》,中山大學藝術史研究中心編 《藝術史研究》第19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69-206頁。其中帝王像冕服和第220窟帝王像冕服服制完全一致,皆戴六旒冕冠。前文已論,“開元禮”頒行于唐開元二十年 (732),而此窟開鑿時代 “大致在中宗、睿宗、玄宗前期開元時期 (705-749年)”③樊錦詩、劉玉權 《敦煌莫高窟唐前期洞窟分期》,第171頁。,故我們推測此窟帝王像冕服服制應該是依據 “開元禮”而成,該窟最早繪制完成于 “開元禮”頒布之后,即唐開元二十年 (732)之后。

圖4 莫高窟第103窟帝王像(敦煌研究院提供)

圖5 莫高窟第194窟帝王像 (敦煌研究院提供)
2.盛唐第194窟開鑿時間,“上限早不過天寶,下限當晚不過沙州陷蕃的建中二年(781)”④樊錦詩、劉玉權 《敦煌莫高窟唐前期洞窟分期》,第181頁。。該窟 “新樣維摩變”中的帝王像頭戴九旒冕冠,著青衣纟熏裳。就其冕服細節來看,冕冠前排旒珠為綠色,后排為青色;青綠色相間的上衣,兩肩繪日月,兩袖間各繪 “星辰”、粉米和黻章,并暗飾青色山章;白色中單;腰間一綠色菱格紋大帶,正前方方格內青綠色間飾;大帶下方為紅色革帶,正前方緊扣鉤楪;左腰間佩劍,劍鐓末鑲一藍色寶石;左腰一青綠色相間的大綬,從革帶處自然垂于腳上。與前者帝王像對比來看,該窟帝王像粉本形式完全不同于初唐及盛唐第103諸窟。前文所論五窟帝王服制雖有不同,但衣裳顏色卻都為 “玄衣纟熏裳”,①《周禮》曰:“凡冕服皆玄衣纟熏裳”。即冕服上衣為 “玄色”,下裳為 “纟熏色”。[漢] 鄭玄注、[唐] 賈公彥疏 《周禮注疏》卷21《司服》,李學勤主編 《十三經注疏 (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551-552頁。而該窟帝王卻為 “青衣纟熏裳”。因此,該窟帝王應據新的粉本或應其它服制而成。《新唐書》載:
袞冕者,一品之服也。九旒,青綦為珠,貫三彩玉,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青纊充耳,寶飾角稽導。青衣纟熏裳,九章:龍、山、華蟲、火、宗彝在衣,藻、粉米、黼、黻在裳,皆絳為繡遍衣。白紗中單,黼領,青褾、襈、裾。朱襪,赤舄。革帶鉤楪,大帶,黻隨裳色。金寶玉飾劍鏢首,山玄玉佩。綠綟綬,綠質,綠、紫、黃、赤為純,長一丈八尺,廣九寸,二百四十首。效祀太尉攝事亦服之。②[宋]歐陽修、宋祁撰 《新唐書》卷24《車服志》,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19頁。
對比第194窟帝王像冕服和文獻資料來看,這一冕服和 《新唐書》載一品大臣所穿 “袞冕”服制一致,系 “效祀太尉攝事”之服,可能是 “開元禮”之后 “青衣纁裳”之 “袞冕”的寫照。因為該窟 “新樣維摩變”中的各國王子無論人物排列、方位或是選擇,均與晚唐的各國王子圖相似,但這一粉本卻不為隨后吐蕃統治者所采用,而在歸義軍統治時期則成為主流。這是因為,安史之亂以后,基于眾多原因,朝集制度逐漸崩壞,取而代之的是方鎮進奏院,元日朝會中諸州朝集使諸蕃客使共同構成的帝國秩序也隨之崩塌,政治理想化的意圖促成了該窟新型粉本的出現,其 《各國王子圖》不再寫實,而是用衣著華麗、隊伍龐大的 “各國王子”表現盛世 “王會圖”的政治意象,為一種政治祈愿。所以,盡管這種粉本的內容遠遠悖離實際情況,但恐怕依然是唐帝國政治現狀的寫實。③李昀 《萬國衣冠拜冕旒——敦煌壁畫中的朝貢者形象》,第169-206頁。由此我們推測,該窟頭戴九旒冕冠、著青衣纁裳的帝王像表現的正是安史之亂前后,唐王朝式微,地方政權勢力加強的反映。所以,“新樣維摩變”中本來的帝王像被更換成了節度使形象假設便成為了可能。
(三)吐蕃統治時期敦煌帝王像及其服制
敦煌吐蕃政權時期 (781-848年)的 “新樣維摩變”,最顯著的特征是吐蕃贊普進入到了各國王子圖的中心位置,這也是目前學界判斷吐蕃統治時期所開洞窟的主要依據。該時期共存帝王圖像8鋪,7鋪出現在 “新樣維摩變”中,1鋪出現在 《涅槃經變》中。此一時期 “新樣維摩變”中的帝王像,如第133、159、231、360窟中的帝王像分別穿戴四、三、三、四旒冕冠 (圖6、7、8、9);第236、237、359窟帝王像全部穿戴 “皮弁”(圖10、11、12),這也是這一時期帝王像的主要特點。而第158窟 《涅槃經變》中的帝王像穿戴3旒冕冠。

圖6 第133窟帝王像(敦煌研究院提供)

圖7 第159窟帝王像 (敦煌研究院提供)

圖8 第231窟帝王像(敦煌研究院提供)

圖9 第360窟帝王像 (敦煌研究院提供)

圖10 第236窟帝王像(敦煌研究院提供)

圖11 第237窟帝王像 (敦煌研究院提供)

圖12 第359窟帝王像 (敦煌研究院提供)
前文已敘,除初、盛唐時期的帝王冕服外,其它時代的帝王冕冠旒數可能只是一種象征或標志。故吐蕃統治時期的敦煌帝王像,已不再是按照唐朝服制而來,可能僅僅是作為對故有圖像粉本的借用或延伸。若依唐制,則三旒冕冠者為 《舊唐書》所載之“玄冕”,四旒者為 《舊唐書》所載之 “纟希 (繡)冕”。有意思的是,《新唐書》中沒有三、四旒冕冠的相關記述。
最為特殊的是,第236、237、359窟中帝王一改前代穿戴冕旒的傳統,代之而來的是 “皮弁”。 《周禮》謂: “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又 《新唐書》謂:“弁服者,朔日受朝之服也。以鹿皮為之,有攀以持發,十有二綦,玉簪導,絳紗衣,素裳,白玉雙佩,革帶之后有鞶囊,以盛小雙綬,白韈,烏皮履。”①[宋]歐陽修、宋祁撰 《新唐書》卷24《車服志》,第516頁。據此可知,無論哪種 “皮弁”,其都有君臣通用的特點,形制又都差別不大。所以第236、237、359窟中出現穿戴 “皮弁”的帝王圖像,一者是有意降低中原帝王身份;二者兼有提升對應吐蕃贊普身份的意愿,因為這一時期文殊一側的贊普形象變得更為突出。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帝王像雖然頭戴皮弁,卻所穿冕服皆 “青衣纁裳”。前文已論“青衣纁裳”者臣下穿戴之冕服。所以,吐蕃統治時期敦煌壁畫中穿戴皮弁冕服的帝王像,可能是依據第194窟帝王像形制而來。
如果我們將敦煌吐蕃時期的帝王像作一類比,則呈現出兩種面貌:一,穿戴冕冠的帝王圖像,如第133、159、231、360窟 “新樣維摩變”,以及第158窟 《涅槃經變》中的帝王像;二,穿戴 “皮弁”的帝王像,如第236、237、359窟。這樣一種變化應與其時吐蕃政權的統治密切相關。根據王中旭等先生的研究:“敦煌吐蕃時期的 《維摩變》新樣應出現在821-822年長慶會盟之后到848年之間,前后時間跨度不超過30年”,并認為第237、231、133、359窟贊普及隨從像繪制時代當在830年代中期至840時代早期之間;第360、159窟應繪制于840年代早期至848年。②王中旭 《贊普的威儀——試論敦煌突吐蕃時期贊普及隨從像的演進》, 《藝術設計研究》2012年第4期,第18-25頁。據此,我們可以根據這些帝王像服制的變化,大致可以推斷出這些壁畫繪制完成的前后時間關系。即穿戴四旒冕冠的第133和穿戴三旒冕冠的第159、231窟的繪制時代應早于穿戴皮弁帝王像的第236、237、359四窟,而最晚者當為穿戴四旒冕冠帝王像的第360窟,這一點基本和樊氏分期所論一致。③樊錦詩文認為第132窟屬于吐蕃早期洞窟,即8世紀80年代到8、9世紀之際;第237、359、360、159窟,以及第44、185窟屬于吐蕃晚期前段洞窟,即9世紀初至839年左右;第359窟屬于吐蕃晚期后段,即9世紀40年代。樊錦詩、趙青蘭 《吐蕃占領時期莫高窟洞窟分期研究》,敦煌研究院編 《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第182-210頁。
依上所論,吐蕃時期帝王冕服大致經歷了 “四旒——三旒——皮弁——四旒”這樣一種流轉程序,而這一過程卻為我們推斷各窟先后時代提供了重要線索。即第133窟屬于吐蕃早期洞窟 (其帝王像穿戴四旒冕冠),緊隨其后的則為繪制有穿戴三旒冕冠帝王像的第159、231和158窟,而繪制穿戴皮弁帝王像的第236、237、359窟的繪制完成時代可能稍晚。具體而論,其一,第360窟和第159窟圖像屬于成熟階段,但159窟時代略晚,④王中旭 《贊普的威儀——試論敦煌突吐蕃時期贊普及隨從像的演進》,第21頁。又第231窟 (陰嘉政窟)紀年顯示該窟開鑿于839年,此窟和第159、158窟帝王所著服制一致,故此三窟繪制時限應不會相差太遠。其二,第359窟中的帝王像所戴皮弁不同于第236、237窟的帝王所戴皮弁,其冠飾、服裝顏色幾乎全為褐色,而第236、237窟幾乎全部為黑色,且周圍侍從也不同于其他。再據樊氏分期,第359窟屬于吐蕃晚期后段,則第236、237二窟繪制時代應更為接近,應在第359窟之前。如此,大致可以梳理出各洞窟的前后時代關系。即第一期洞窟為第133窟;第二期洞窟為第159、231、158窟;第三期洞窟為第236、237、359窟;最后一期為第360窟。也由此可知這一圖像所內涵的不同尋常的地位和價值。
(四)張氏歸義軍統治時期敦煌帝王像及其服制
敦煌晚唐時期,實為張氏歸義軍統治時期 (851-907年)。這一時期共有10鋪“新樣維摩變”,其中第9、12、18、138、156、85窟帝王像保存較好 (圖13、14、15、16、17、18),第139、141、150窟帝王圖像損毀,即現存此一時期完整的帝王圖像共有6身。除第156窟帝王像穿戴四旒冕冠和第12窟帝王像穿戴不同于以往皮弁的冠冕外,其余3身全為無旒之大裘冕。

圖13 第9窟帝王像(敦煌研究院提供)

圖14 第12窟帝王像 (敦煌研究院提供)

圖15 第18窟帝王像 (敦煌研究院提供)

圖16 第138窟帝王像(敦煌研究院提供)

圖17 第156窟帝王像 (敦煌研究院提供)

圖18 第85窟帝王像 (敦煌研究院提供)
第156窟是敦煌首任歸義軍節度使張議潮的功德洞窟,完成時間大致在唐大中五年至大中十年間 (581-586)。①李國、沙武田 《莫高窟第156窟營建史再探》,《敦煌研究》2017年第5期,第55頁。其中所繪 “新樣維摩變”帝王像冕服和吐蕃第360窟一致,依然有吐蕃統治時期粉本的影響,但又突出了中原帝王的地位。這種變化,我們可以理解為這一時期已擺脫或減弱了吐蕃的影響,形成了具有敦煌歸義軍統治時期的繪畫風格。
在張氏功德窟的影響下,約862-867年間,歸義軍第二任都僧統翟法榮修建了第85窟。②賀世哲 《從供養人題記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營建年代》,第194-236頁。從繪畫形式上來看,該窟帝王像和第156窟帝王像極為相似,兩者可能使用了相同的粉本,只是第85窟帝王像冕冠旒數部分因損毀具體情況現不得而知。在隨后的咸通十年 (869)前后,敦煌望族索義辯主持營造了第12窟。③范泉 《莫高窟第12窟供養人題記、圖像新探》,《敦煌研究》2007年第4期,第86-90頁。而第12窟 “新樣維摩變”帝王像卻穿戴異于其他冕冠的黑色皮弁,其具體原因還得再行討論。
反觀同期其它洞窟,現存第9、18、138三窟 “新樣維摩變”帝王像全部穿戴無旒大裘冕。所謂大裘冕,其最大的特點是冕冠無旒,為諸冕中級別最高的冕服。 《周禮》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④[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 《周禮注疏》卷21《司服》,李學勤主編 《十三經注疏 (標點本)》,第549頁。新舊 《唐書》皆曰:“祀天地之服也。”⑤《舊唐書》曰:“祀天神地祗則服之。”([后晉]劉昫等撰 《舊唐書》卷45《輿服志》,第1936頁);《新唐書》曰:“祀天地之服也。……黑表,纁里,無旒,金飾玉簪導,組帶為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宋]歐陽修、宋祁撰 《新唐書》卷24《車服志》,第514頁)。但玄宗開元十一年冬 (713),玄宗以 “大裘樸略,冕又無旒,既不可通用于寒暑,乃廢不用之”。“自是,元正朝會,用袞冕及通天冠;大祭祀依 《郊特牲》,亦用袞冕。自余諸服,雖著在令文,不復施用。”⑥[宋]王溥撰 《唐會要》卷31《輿服上》,第662頁。因此早已退出唐代冕服舞臺的大裘冕,為何會在敦煌歸義軍時期重新使用,應該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我們推測,這一圖像在這一時期的出現,至少表明歸義軍政權在有意抬升與中原王朝的正朔地位之間的關系。
四、結語
唐朝前期是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發展的鼎盛期,亦是敦煌石窟發展的高峰期。唐朝中后期,其統治由盛轉衰,玄宗天寶十四載 (755)的 “安史之亂”是學界公認的分界線,而敦煌一般以吐蕃占領的建中二年 (781)為分界點,分唐朝中央政府直接控制時期 (武德初至建中二年,618-781年);吐蕃占領時期 (建中二年至大中二年,781-848年);張氏歸義軍統治時期 (851-907年)。而作為統治者象征或符號的帝王圖像,不可能隨意而作,根據筆者調查及比對相關文獻,可知有唐一代敦煌 “新樣維摩變”中的帝王圖像基本按照當時帝王形象或服制描繪而成,具有極高的歷史研究價值。
本文首先統計了唐代各時期帝王圖像的分布及形式、服制等情況。其次在分析現存18身帝王像的過程中,根據歷史文獻等資料對帝王服制的演變歷史做了進一步的分析。我們認為敦煌石窟中的唐代帝王圖像,不僅與敦煌歷史密切相關,而且具有嚴密的演進程序。
第一,初唐時期的帝王冕服皆為 《周禮》之 “纟希冕”。第220窟帝王六旒冕冠系唐初沿襲北周及隋代服制而成的 “纟希冕”。第332、335窟五旒冕冠為 “武德令”之天子“冕”。
第二,盛唐時期的帝王冕服應依據 “開元禮”而成,并沿襲了唐初以來的服制,最初沿用 “纟希冕”,后因為其他原因而改為袞冕。第103窟六旒之冕系 “開元禮”之“纟希冕”。第194窟帝王 “青衣纟熏裳”穿戴九旒袞冕,這不僅與玄宗 “諸祭并用袞冕”的史實相符,而且與 “安史之亂”后的軍鎮制度密切相關。
第三,吐蕃統治時期,帝王圖像一改前代穿戴 “六冕”的形式,首先出現了依“武德令”而來的四旒 “纟希(繡)冕”;接著改為了依 “武德令”而來的三旒 “玄冕”;接著全部改為 “六冕”之外的皮弁;最后又改為了四旒 “纟希(繡)冕”。這樣一種變化,筆者推測應與吐蕃嚴苛的統治不無關系。還有,通過對這一時期服制的類型分析,可以看出帝王服制的變化和洞窟繪制時代幾近吻合,更與其時歷史密不可分。
第四,張氏歸義軍時期,除咸通六年 (865)建成的第156窟帝王穿戴四旒 “纟希冕”和第2窟帝王穿戴皮弁外,其余如第9、118、138三窟帝王全部穿戴 “大裘冕”。這一變化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這與晚唐歸義軍政權既尊中原王朝為正朔,又刻意抬高自己統治地位的歷史息息相關。
總之,莫高窟唐代壁畫中的帝王像,是有唐一代歷史變遷的寫真。歷經初唐的發展,到盛唐的鼎盛,再到吐蕃 (中唐)的過渡,直至張氏歸義軍政權 (晚唐)的衰落,各時期的輿服制度伴隨著帝國政權的更迭而不斷調整。如果穿戴冕冠是華夏帝王的基本標志,那么吐蕃政權時期穿戴皮弁的中心人物和張氏歸義軍時期穿戴三、四旒冕冠的帝王形象可能就是地方政權的統治者的寫真,歸義軍后期穿戴無旒 “大裘冕”的帝王形象便是尊中原王朝為正朔的某種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