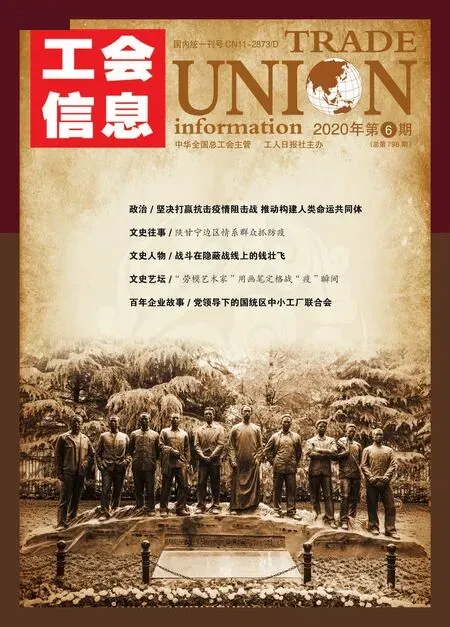曬一曬元代的“新詩”
◆文/南鐵英
今年是中國新詩創生100年。自1920年胡適出版新詩集《嘗試集》開始,100年來,中國的詩壇,涌現出大量寫新詩的詩人,郭沫若、徐志摩、聞一多、劉延陵、戴望舒、馮雪峰、謝冰心、林徽因、何其芳、艾青、馮至、臧克家、舒婷……自由奔放的詩歌表現形式,終于孕生出“鳳凰涅槃”“再別康橋”“死水”“水手”“雨巷”“大堰河的保姆”“致橡樹”等不同風格的代表性傳世之作。百多年前的新文化運動時期,胡適首倡文學改良運動,號召遠離文言文,讓大眾化的鮮活語言入文、入詩、入歌詞,就是從那時開始,中國的詩壇,迎來了去掉格律枷鎖、自由歌舞的時代。
讀者興許不知道,在六七百年前的元代,在中國的詩壇上,就曾出現過“新詩”,那就是元散曲。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曲)這種詩歌表現形式,脫胎于宋詞,但它突破了宋詞的格律與語言束縛,大量引入了民間白話,初具了新詩的風貌。下面,筆者就向讀者曬一曬元代的“新詩”。
宛如現代人寫的愛情詩
元散曲中的諸多小令和套曲,就詩歌的內容而言,有諷刺詩、愛情詩、感懷詩等等,其中,最能代表散曲作家“新詩”風格的,還是那些愛情詩。以下向讀者曬幾首散曲中的愛情詩——
賈固《紅繡鞋》(擷句)
當記得夜深沉,
人靜悄,
自來時。
來時節三兩句話,
去時節一篇詩。
記在人心窩兒里直到死。
賈固《醉高歌》(擷句)
黃河水流不盡心事,
中條山割不斷相思。
無名氏《塞鴻秋(二)》
愛他時似愛初生月,
喜他時似喜看梅梢月,
想他時道幾首西江月,
盼他時似盼辰鉤月。
當初意兒別,
今日相拋撇,
要相逢似水底撈明月。
無名氏《紅繡鞋 (二)》
裁剪下才郎名諱,
端詳了展轉傷悲。
把兩個字燈焰上燎成灰,
或擦在雙鬢角,
或畫著遠山眉,
則要我眼眼前常見你。
無名氏《寄生草》
有幾句知心話,
本待要訴與他。
對神前剪下青絲發,
背爺娘暗約在湖山下。
冷清清,
濕透凌波襪,
現將我院2016年6月到2017年6月的收治的66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將其平均分成兩組,觀察組和對照組分別為33例患者。觀察組有17例男性患者,16例女性患者,年齡在42-76歲之間,平均年齡為(54.6±1.7)歲,其中下壁梗死12例,廣泛前壁梗死7例,前間壁梗死14例;對照組有19例男性患者,14例女性患者,年齡在39-72歲之間,平均年齡為(48.7±2.1)歲,其中下壁梗死患者16例,廣泛前壁梗死9例,前間壁梗死8例。這其中已經排除藥物過敏患者、有感染類疾病的患者以及心、肝功能不正常的患者。將兩組患者進行對比,無明顯差異,不具備統計學意義(P>0.05),可以進行比較。
恰相逢和我意兒差。
不剌(音“辣”,違約)你不來時,
還我香羅帕。
無名氏《三番玉樓人》(擷句)
暗想他,
忒情雜,
等來家,
好生的歹斗咱。
我將那廝臉兒上不抓,
耳輪兒揪罷,
我問你昨夜宿誰家?
瞧一瞧,這些愛情詩是不是像是現代人所作?散曲中的這些愛情詩,是詩作者真摯情意的純天然流露,有的索性就拿起家常話入詩。這在講求嚴苛格律、注重文言表述、“崇典故、雜考據”的傳統詩壇,真的是有些離經叛道的味道。不過,從當代人的視角看,元代的“新詩”,既不離“經”也不叛“道”,而是發乎性情的率真表達。王國維先生就曾說過:元散曲“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者”(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確實如此。
散曲和徐志摩詩中的數字排比
再來曬一曬散曲小令作品中的口語化數字排比手法的運用,并和現代新詩代表性人物徐志摩的作品作一比較。
無名氏《雁兒落過》
一聚一離別,
一喜一傷悲,
一榻一身臥,
一生一夢里。
尋一伙相識,
他一會,
咱一會;
都一般相知,
吹一回,
唱一回。
在這首小令中,詩作者巧妙地運用數字“一”,采取排比的手法,將所要表達的人生感喟,通過“N個一”,層層遞進,層層深入,表現得淋漓盡致。再來看一看徐志摩《滬杭車中》的片段——
一卷煙,一片山,幾點云影;
一道水,一條橋,一支櫓聲;
一林松,一叢竹,紅葉紛紛。
徐志摩在《滬杭車中》所采用的數字排比手法,與元代無名氏所創作的小令,幾乎如出一轍。
散曲小令中的這種數字排比手法的運用,俯拾即是,這如徐再思《水仙子 夜雨》中有:
一聲梧葉一聲秋,
一點芭蕉一點愁,
三更歸夢三更后。
徐再思在《水仙子 春情》中,索性將全詩貫以數字:
九分恩愛九分憂,
兩處相思兩處愁,
十年迤逗十年受。
幾遍成幾遍休,
半點事半點慚羞。
三秋恨三秋感舊,
三春怨三春病酒,
一世害一世風流。
姑且不說小令中所表現的思想情緒是否過于消極,只看其對數字排比的運用,已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600多年后的詩人徐志摩,在《闊的海》一詩中,也幾乎玩起了通篇使用數字的“游戲”——
闊的海空的天我不需要,
我也不想放一只巨大的紙鷂
上天去捉弄四面八方的風;
我只要一分鐘,
我只要一點光,
我只要一條縫,
像一個小孩爬伏,
在一間暗屋的窗前,
望著西天邊不死的一條
縫,一點
光,一分鐘。
對比上述的詩,不知道是徐志摩借鑒了元代小令的數字排比手法,還是今古之人有著某種跨越歲月的心靈暗合。反正,600多年前的元代詩人,與600多年后的現代詩人,在運用口語化數字排比這一手法時,當真是“如出一轍”。
散曲諷刺詩和現代諷刺詩
散曲中的諷刺詩,與現代新詩中的諷刺詩,也有驚人相似之處。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以劉半農、劉大白、沈定一為代表的一批學人,在新詩創作中,探索了民歌詩體,強調新詩要向民謠學習。如沈定一創作的一首民歌體諷刺詩:
杭州城里一只狗,跑到鄉間作獅吼;
鄉人眼小肚中饑,官倉老鼠大如斗。
減租也,民開口;
軍隊也,民束手;
委員也,民逃走;
鐵索鐐銬攔在前,布告封條出其后,
豈是州官惡作劇,大戶人家不肯歇,
不肯歇,一畝田收一石租,
減租惡風開不得,入會人家斷煙炊。
這首諷刺詩以白話入文,針砭時弊,與散曲小令中的“民歌體”諷刺詩,有異曲同工之妙。舉一個元代無名氏創作的《朝天子 志感》:
不讀書有權,

徐志摩

沈定一
不識字有錢,
不曉事倒有人夸薦。
老天只恁(音“嫩”,那么)忒心偏,
賢和愚無分辨。
折挫英雄,
消磨良善,
越聰明越運蹇(音“簡”,不順利)。
志高如魯連(魯仲連,戰國齊國人,有計謀不肯做官),
德過如閔騫(閔子騫,孔子弟子),
依本分只落的人輕賤。
現代詩人沈定一與元代無名氏詩人的這兩首作品,皆采用白話來諷刺不良現實,何其相似乃爾,就語言與風格而言,兩首詩仿佛是同時代人所作。
讀者看過這些散曲作品后,是不是有一種感覺:原來在600多年前的元代,就已經出現了“新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