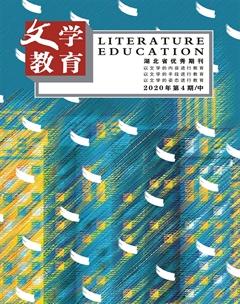沉默
“2020年2月24日”我掛斷電話,瞟了一眼日期。
不知不覺,疫情爆發已經一個多月了。自從爆發以來,父母越來越忙,經常早出晚歸。后來城封了,小區封了,每天一見的“傳統”也斷了。被“隔離”在奶奶家的我,已是半個多月沒見到他們了。
有時,會有零星的視頻電話打來。人沒變,但隔著一層屏幕,仿佛什么被切斷了一樣。草草地問候兩句,交代結束,又各忙各地去了。
我知道,不是我一個人在堅守。不時看到瘋傳的視頻中,總有那么一批人。他們下至嬰兒上至老人,都是身居后方卻一直守望著一線的人。說不上有多刻骨銘心,但就是放不下。
視頻太多,我很快就忘記了。一時的觸動轉瞬即逝,我找不出更多的內涵值得我去回憶。
從學校發的書來了,送不到家。拿不到,只好讓在外的父親送過來。“順便看下你”,我在電話里說。
夜幕降臨。車還沒到,父親的電話倒是提前一個接一個的打來。“還有10分鐘”“還有5分鐘”……本是定好了時間,兩邊卻都先慌了神。只是一邊催著,一邊應著。昨晚想了好久要帶的東西,出門卻不知道先拿什么好。
于是在一陣手忙腳亂中,匆匆地下了樓。外面仍是漆黑,稀稀疏疏的有路人走過。帶著口罩,人與人之間仿佛隔了一堵密不透風的墻。全副武裝之下,只剩下黑暗中格外明亮的眼睛一閃而過。
電話又響了好幾聲,我終于走到了大門。轉角一盞路燈,散著耀眼的白光。眼前的一片強光中,隱隱約約看到大門外佇立著一個人影,一動不動。
電話終于不響了,人影也漸漸清晰。我蹭著步子一步一步挪過去,去接父親身上大包小包的東西。幾個星期積累下來的點點滴滴的話,隔著一層口罩,一時竟說不出口。理論上親人之間久違的淚水,這時卻收得格外的緊。只是呆呆地立在半人高的停車欄的兩側,沒有想象中的擁抱,倒像是兩個平行世界的人在相互眺望。
“還好嗎?”父親打破了沉默。我點點頭,湊過身去接他遞過來的東西。遞完東西,他往后退,我們之間仍是一米的距離。
“照顧好自己。非常時期,不能天天來看你。自己要注意,不要感冒了。”父親簡單地交代了幾句話,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點頭。我不知道該說什么,我不知道能說什么。
又是幾秒的沉默與對視,他笑了。把手一揮,“好好學習,走了!”父親轉身,消失在寂靜的夜幕中。
父親應該是有很多話要說的。他身為國家公職人員,是最先一批上前線的人。年都沒過好,臘月三十就連夜往回趕。正月初一撂下一句:“你們要注意”,就上班去了。為了不打擾我和母親,他自己每天堅持騎自行車去上班。后來自行車壞了,沒處修,他就走。于是每天下午催他吃飯變成了常態。“你還在哪里啊?”“快了,快了,你們先吃”。一直催到我們都吃完后他才姍姍而回。就連吃飯,他也主動離我們遠遠地。“一線風險很大”,搬把椅子就往門邊挪……
然而人在某種壓力下,是真的說不出話來的。好像死守著什么一樣,深怕什么東西會順著言語漫溢出來。甚至只有眼神在流動,在傳遞對方未曾開口的萬語千言。他轉身別去,留給我的不是遺憾,反而是一種莫名的滿足。一路來,我知道他是愛我的。而今兩地分隔,我肯定他也一定有千言萬語想要對我訴說,但也許是怕給我增添不必要的煩惱,怕我分散了學習的精力,他選擇了沉默。我理解,于是默默告訴自己:“這就夠了”。
我開始懂得那些窗臺上孩子和老人無言的牽掛,也開始明白那些休息室里的父母無聲的惦念,更漸漸體悟到他們只對視一眼便心滿意足的真摯與深情。一切盡在不言中,這不僅是災難面前人最本能的情感流露方式,更是苦難面前人心最深處的明亮與堅強。我不再給他們扣上一頂“幼稚,脆弱,煽情”的帽子后轉身離開,我隱隱約約地體會到某種更深的含義——沒有機會脆弱,便默然地扛起自己的重擔,無言地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這是他們最堅定的支持。
我忽然明白,瞞著父母來到武漢漢口醫院的朱海秀護士面對鏡頭時,為什么會選擇轉身離開,只留下短短的一句“對不起”。因為一切深切的想念,都在這沉默中轉化為更加偉大的力量,那是兩個人、一家人、千萬人,面對疫情的恐嚇,面對人的本能的情感動搖,彼此支持,彼此寬慰,共同發出的最堅定最決絕的吶喊,此時無聲勝有聲。
“我們不能就這么完了”,這是平凡人的情感牽掛。“我們一定還有未來”,這是普通人的堅定信念。
早晨起來,父親和我又開始新一天的生活。突然發現昨天父親凌晨更新的朋友圈,是一首小詩,《相見歡》:“社區任務繁重,妻子值班忙碌,兒子高考在望。防疫鏖戰正酣,只好如此這般,誰無兒女情長?”扭頭向窗外看去,霧依舊很濃,看不到遠方。稀稀疏疏的陽光散落進來,深深淺淺的印在地上,像是在給人傳遞某種安慰。
我知道,不是我一個人在堅守,于是沉默地在紙上寫下:“眾志成城,共克時艱”。
爸爸,使命在先,望早日凱旋!
(作者介紹:陳元相,湖北省恩施高中2017級3班學生;指導教師:譚本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