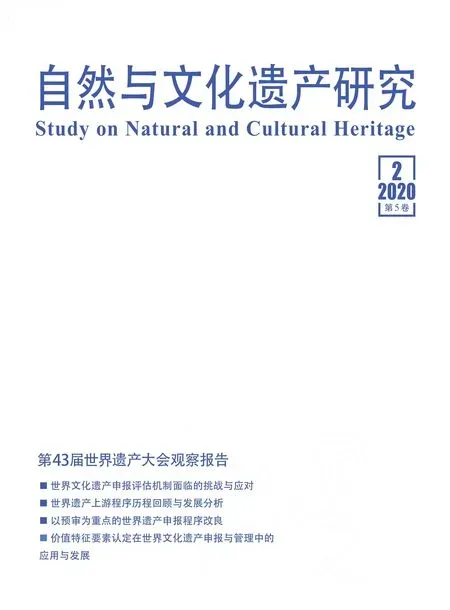價值特征要素認定在世界文化遺產申報與管理中的應用與發展
魏 青
(清源視野文化咨詢有限公司,北京 100101)
Aattributes,一般被譯為屬性,是世界遺產保護領域中的一個專業術語。它指的是一項世界遺產中承載突出普遍價值并使其得以顯現的要素,可能是物質實體,也可能是與物質遺產相關并對其物理形態產生影響的過程,比如形成獨特景觀的自然過程、農業過程、社會分工或文化行為[1]。無論它以物質或非物質形態存在,其核心一定是某種可被識別、感知的特征。正是這種特征將其與人們理解的遺產價值內涵緊密聯系起來。《實施世界遺產公約操作指南》(以下簡稱《操作指南》)在真實性評估中列舉的“形式與設計,材質,使用與功能,傳統、技術和管理體系,選址地點和環境……”,是這些特征可能的表現形式①005版《實施世界遺產公約操作指南》中第一次在真實性的段落中采用a t t r i b u t e s一詞表述相關概念。。識別和理解一項遺產中的attributes,及其之間的相互關系,對于理解突出普遍價值、真實性和完整性,并確保恰當的保護和管理機制都至關重要[1-2]。為了將attributes與一般認知中的遺產組成部分(element)、構成要素(component)或含義更寬泛的要素(feature,多用于自然遺產領域)相區別,本文將其譯為價值特征要素——以強調這一概念中要素、特征和價值之間的緊密關系。
價值特征要素的概念被融入世界遺產特別是文化遺產體系,經過了相當長的歷程,至今也尚未發展成熟。這伴隨著評估機構、締約國和遺產地管理者、在遺產大會上表決的各屆委員會國對這一概念和認定方法的探索,也伴隨著整個世界遺產體系應對正在危及世界遺產可信度的嚴峻挑戰中所做的一系列努力。
2019年,ICOMOS在新申報項目的評估報告中,以attributes為標題統一規范了對價值特征要素的梳理歸納,并將這段內容調整至總結突出普遍價值評估結論之前。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聯系近年來遺產大會決議頻繁修改咨詢機構意見的狀況,可以理解這與第三輪定期報告工作的新動態類似,是對世界遺產體系提出強化基于價值的保護工作邏輯這一關鍵任務的響應,咨詢機構試圖進一步完善申報這一源頭環節的技術細節。
本文以此變化為切入點,回顧價值特征要素認定在世界遺產體系中逐漸被使用、推廣和深化的過程,梳理締約國和遺產地、評估機構、委員會決策體系等各方的認知和運用狀態,評述其在世界遺產理念和方法發展中起到的積極作用,其概念和相關方法的成熟度,并對仍需探討的關鍵問題和亟待完善的重點工作提出建議。
1 ICOMOS評估報告對價值特征要素認定的關注
價值特征要素(attributes)在ICOMOS對申報項目評估報告中的使用,大致可追溯到2001年對奧地利和匈牙利聯合申報的新錫德爾湖與費爾特湖地區文化景觀②Fert/Neusiedlersee Cultural Landscape,2001年以標準v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評估報告中,論及該文化景觀中的獨特文化價值特征要素[3]。圖1統計了自2001年以來ICOMOS評估報告中價值特征要素從零星出現到頻繁使用的變化趨勢和使用方式。從一般性術語向專項評估內容,這一過程大致可被劃分為3個階段。
1.1 2001年至2009年價值特征概念的逐步引入
第一階段從2001年至2009年,是一個緩慢增長的過程。價值特征要素先在個別文化景觀類項目中被提及,逐漸擴展到其他類型。圖2的統計詳細闡述了這個“傳播”的過程。在具體語境中,也可以看出因文化景觀類型對遺產范疇的擴展、價值特征要素在探討價值內涵及其相關要素時的具體運用。突出的一點是,自然的價值特征要素(natural attributes)出現25次,在這9年的169次中占比接近15%,而“文化與自然的價值特征要素”(cultural and natural attributes)這樣更明確表達自然與文化融合的表述也在2007年之后出現了4次。在一些項目中,價值特征要素被明確用來指向一般性的構成要素難以對應或涵蓋的對象,如2003年巴西申報的里約熱內盧③該項目2003年申報時全名為Rio de Janeiro: Sugar Loaf, Tijuca Forest and the Botanical Garden,2012年更名為 Rio de Janeiro: Carioca Landscapes between the Mountain and the Sea,作為文化景觀類型,價值標準v、 vi被列入世界遺產。項目,19世紀景觀規劃的山林和植物園在宏觀尺度上賦予這座山海之間的城市獨特的景觀環境。這評估報告認為是重要的文化價值特征要素(significant cultural attributes)[4],該項目最終于2012年以“里約熱內盧:山與海之間的卡里奧卡景觀” 的名稱列入名錄。2009年法國申報的的“喀斯和塞文”項目,評估報告高度關注其農、牧混合系統與自然環境之間的融合形態,希望對這種田園牧歌式的價值特征要素(agro-pastoral attributes)進一步深入研究、認定并落實保護。最終該項目在此指引下調整完善,于2011年以“喀斯和塞文——地中海農牧文化景觀”的名稱列入。該項目評估報告共21次使用價值特征要素一詞,貫穿于比較研究、真實性完整性、突出普遍價值、遺產邊界、保護管理、監測各方面的評估內容[5]。除此之外,也有一些關鍵問題被涉及。如2008年對阿根廷申報的布宜諾斯艾利斯④該項目后來未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評估中提出如下疑問:一個仍在動態變化的文化景觀系統是否能夠通過詳細認定價值特征要素,從而對可允許的變化范疇作出清晰界定,并作為對是否具有OUV和對未來保護管理進行評判的關鍵依據[6]。

圖2 2001—2009年ICOMOS評估報告中價值特征要素(attributes)在不同類型遺產中的出現頻率(來源:作者自繪)
1.2 2009年至2018年對申報項目價值特征要素認定的關注
從2010年開始,這一術語在其他類型項目的評估中逐漸普及,但仍明顯集中在文化景觀類型。顯著的變化是在評估報告第三節判斷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結論后,出現以“價值特征要素描述”(Description of the attributes)為標題的段落。其內容是結合對價值標準、真實性完整性評估的結論,梳理歸納申報文本羅列的構成要素。在當年大部分突出普遍價值被ICOMOS認可項目⑤中國的嵩山-天地之中和塔吉克斯坦的Sarazm被ICOMOS評估具有突出普遍價值并推薦列入,但未梳理確認價值特征要素。的評估報告中都出現了這一段落。
2011年這一技術環節被應用到幾乎所有被推薦列入或建議補報(refer)項目中⑥蒙古的阿爾泰山脈巖畫群項目(petroglyphic complexes of the Mongolian Altai),ICOMOS認可突出普遍價值,但因保護管理問題建議退回重報(defer)。最終大會修改決議草案,該項目以ICOMOS認可的價值標準iii列入名錄。[7]。這可視為評估機構對推薦列入或有可能列入項目突出普遍價值載體的一種確認。然而,2010年后,也正是世界遺產大會新申報項目審議中,大會決議和咨詢機構建議之間分歧日益加劇的階段。越來越多咨詢機構對突出普遍價值提出質疑的項目在大會決議中被列入名錄。這些決議草案的修改過程總體是倉促而未經充分討論的。因此以這種方式被列入名錄的項目,不僅是突出普遍價值——“為什么”列入的問題得不到深入的推敲,作為認知突出普遍價值客觀基礎的價值特征要素——“是什么”的問題同樣無法在這個過程中被探討和檢驗。
1.3 2019年對申報項目價值特征要素認定評估的調整
2019年,ICOMOS評估報告中認定價值特征要素的段落生了新的明顯變化。段落被提前到價值標準、真實性完整性評估之后,突出普遍價值評估綜合結論之前,并以attributes命名。該段落的意義不再是確認遺產具有突出普遍價值后對其價值特征要素認定的認可,而是被納入突出普遍價值的評估。因此,幾乎所有申報項目的評估報告都出現這一段落。除梳理歸納外, ICOMOS還對某些項目提出問題或給出增減建議。(詳見本文第五節)
這一系列變化,也將價值特征要素(attributes)和feature、element、component等相近術語更清晰地區分開來。這些概念中,feature與attributes最接近,并在自然遺產領域被廣泛應用。在文化遺產領域,兩詞也經常通用。相對來說feature更多用來指較寬泛意義的“要素”;而attributes逐漸被更規范化地用于價值特征要素的分析、認定中。個別突出普遍價值被質疑的項目,ICOMOS在梳理歸納其價值特征要素時,會以attributes/features的方式將兩詞并用。component更常用來表達在物質形態方面可分辨的個體或群體構成要素。近年來,隨著系列遺產,文化線路等規模巨大、構成內容復雜的遺產越來越多,咨詢機構對申報遺產內容和構成關系的關注,component一詞的使用頻率明顯激增。element一詞相對意義更寬泛,報告談及任何尺度、類型的內容、元素時都可能用到,但也可能是在有更具體指向時被其他含義越來越明確的術語逐漸替代,elements的使用頻率不增反降。
2 世界遺產定期報告對價值特征要素認定的推動
2.1 第二輪定期報告對價值特征要素認定提出的要求和反饋結果
第一輪定期報告中并沒有與遺產價值特征認定相關的要求。但對第一輪工作的回顧中認識到早期列入遺產的突出普遍價值不清晰導致后續保護管理方面的困境。于是,世界遺產委員會敦促各締約國在執行第二輪定期報告之前,根據2005年更新的《操作指南》,完成突出普遍價值的回顧性聲明(rSOUV)⑦參見后文第三節內容。,同時提出通過回顧性清單(retrospective inventory) 加強基礎數據,包括遺產地理信息的辨認,遺產邊界和規范的地圖等[8]。這一任務在第二輪定期報告新調整的問卷內容中得到進一步落實,在遺產地填報問卷中突出普遍價值聲明部分,要求針對遺產地符合的每條價值標準,填寫對應的價值特征要素。
然而遺憾的是,第二輪定期報告中并未對什么是價值特征要素,以及如何認定作出進一步解釋。概念的模糊和技術要求的不明確,給各遺產地的填報造成了不小的困惑。即便從更熟悉世界遺產體系的歐洲國家的反饋看,都相當不理想。筆者選取了4個較有代表性的國家⑧分別選自從歐洲定期報告工作組織中劃分的4個區域——地中海、西歐、北歐及波羅的海和中東及東南歐。,統計它們在第二輪定期報告中對價值特征要素認定的反饋結果。如圖3所示,在應提交報告的89個文化遺產項目中⑨其中包括1項混合遺產。,只有25項提交了認定內容⑩4個國家中瑞典的反饋最為積極,全部提交;英國有一多半文化遺產沒有作出認定;意大利僅提交1項;波蘭的所有文化遺產地都沒有作出認定。。沒有作出認定的主要原因是該項目遞交給世界遺產委員會的回顧性突出普遍價值聲明仍在審議中,其他也有保護管理規劃尚在編制等原因。這說明這些締約國認同價值特征要素認定與突出普遍價值確認(甚至表述)有密切關系,需嚴謹的工作程序,這是合乎遺產保護邏輯的。同時也意味著,已列入名錄的大量世界遺產,其承載價值的要素不夠明確,難以據此作為依據對應新版《操作指南》要求,從表述上完善突出普遍價值聲明。這其中甚至有根據回顧性突出普遍價值聲明的調整,對曾經納入申報范圍的遺產要素進行調整的空間,并由定期報告的記錄成為未來的評判依據。但這種可能的調整顯然沒有像突出普遍價值聲明那樣被納入嚴格的審議程序。

圖3 第二輪定期報告歐洲部分國家對價值特征要素認定的反饋情況(來源:作者自繪)
從提交價值特征要素認定的案例分析可見,在認定方式方法上呈現出非常多樣的狀態。根據定期報告提出的要求,大致可以分為兩組(圖4)。

圖4 第二輪定期報告中歐洲部分遺產地價值特征認定的表述方式(來源:作者自繪)
一組是按定期報告要求對應價值標準認定,在案例中占大多數。其中又有3種具體方式。其一是直接對應每條價值標準羅列價值特征要素,另兩種分別從價值主題出發,如英國的卡萊納馮工業景觀[9],或構成要素結構關系出發,如英國的巨石陣[10]、斯塔德利皇家公園和噴泉修道院遺址[11],先明確價值主題或構成要素的歸類,再分別羅列具體內容,進而注明這些主題或要素類別支撐的價值標準。從效果來說,前一種方式雖能清晰確認每條價值標準獲得的支撐,但往往導致價值特征要素的表述被價值標準割裂,在對遺產地認知方面明顯不如后兩種方式有整體性和清晰的層次關系。同時,后兩種方式都呈現出一個主題或一組要素支撐多條價值標準,或多組內容支撐一條價值標準的交叉對應關系。
二組是未對應價值標準認定的案例,也有一部分采用按價值主題歸納組織,或按結構關系歸類的方式。瑞典的斯科斯累格加登公墓則代表了按真實性的評價指標(即價值特征要素的類型)進行認定的方式[12]。也有項目僅將要素進行簡單羅列,甚至只提供一小段綜述。

圖5 第二輪定期報告部分遺產地反饋的價值特征要素認定清晰度分析(來源:作者自繪)
在認定的清晰度方面,限于定期報告的形式,各項目的認定都以一段文字表述,深度和細節非常有限(圖5)。在認定的層次、結構清晰度方面,相對詳細的案例可以做到有層次,分類明確并能對各類特征要素進行概述或羅列主要內容。但也有相當多案例只有簡單羅列,沒有主次關系。在對特征的描述方面更加不清晰,三分之一多的案例基本未涉及對特征的表述,僅有對要素內容的羅列,很難從中看出和價值的聯系,即便其中有的已按價值標準整理歸類,有特征表述的也僅是概述性的。

圖6 英國巴斯古城遺產地管理規劃(2016—2020年)中對遺產價值特征要素的認定(節選)(來源:https://www.bathworldheritage.org.uk/management-plan)
當然,定期報告中的認定清晰度并不代表遺產地實際工作深度。例如英國的不少項目意識到定期報告表述方式的局限性,在報告中補充說明管理規劃中有更詳細的認定,并給出網址鏈接。比較典型的是巨石陣、巴斯古城等案例。圖6為巴斯古城遺產地管理規劃(2016—2022年)中認定的遺產價值要素,共分6組,分別是羅馬時代的遺址、溫泉、喬治王時代的城市規劃、喬治王時代的建筑、在山谷中被植被環繞的城市環境以及喬治王時代建筑折射的18世紀的社會雄心。尺度上從宏觀到具體,類型上包括物質與非物質[13]。事實上這6組價值特征要素是上一版規劃(2010—2016年)認定的。這一版進一步細化,列舉了每組要素中的具體內容,注明了每項要素呈現其特征的形式是形態與設計,還是材質,或功能、傳統、技術和管理體系、位置和環境、精神與感受等,每項要素可能以一種或多種形式傳達價值特征,清晰對應了真實性的評估要點。這顯然有利于為遺產管理確定更明確的目標、任務和標準。管理規劃中也對認定遺產價值特征要素的作用做出了解釋,“使這些要素得以被保護、管理和監測,并用來評估管理規劃的執行、相關規劃的部署、項目和干預計劃。價值特征要素比各個構成要素(components)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它包含著那些承載著突出普遍價值陳述中被認知價值的特征”[13]。應該說,英國巴斯古城遺產地管理規劃,是遺產地價值特征要素認定方法和管理銜接方面一個較為系統和邏輯清晰的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定期報告中類似英國巴斯古城這樣的填報方式,事實上是通過外部引用,解決定期報告表達形式對表達深度的限制。因此這些項目在報告中往往采取更為簡單概括方式(圖6)。但外部引用的依據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與報告中的概述保持一致,遺產地規劃不同版本間能否長期保持一致,可能出現的變化是否能得到必要和及時的審議,規劃中未經嚴格審議的這部分內容是否可以作為世界遺產體系監督、評估遺產地保護狀況的依據?第二輪定期報告相關工作并未給這一系列問題以明確的解答。
2.2 第三輪定期報告對價值特征要素認定的新要求
第三輪定期報告在對第二輪的總結反思后,于2018年正式啟動。認識到第二輪中的問題,在新一輪的準備過程中,專家組將價值特征要素認定作為一項核心任務(one of the core aims)提出[14]。新改版的問卷細化了對價值特征要素認定的要求,遺產地需歸納出不超過15項的價值特征要素,并分保存較好、受損、嚴重受損和已損失四級,逐項評估其保存狀況[15]。同時,配合第三輪定期報告,世界遺產中心將完善用于監測評估世界遺產保護管理狀況的4個分析數據集,其中之一即是由每個遺產地的價值特征要素、保存狀態和相關圖紙、描述及檔案記錄組成的數據集[16-17][11]其他3個數據集分別是:定期報告締約國問卷中采集的數據、遺產地問卷中采集的數據、影響因素數據集。。世界遺產委員會希望進一步強化以價值為核心的保護邏輯,建立一個信息更具體,遺產價值與保存狀態、影響因素之間聯系更緊密,可以長期跟蹤的認定、評估機制。細化落實價值特征要素認定成為其中一項重要舉措。
為幫助各遺產地更好地理解和填報相關內容,問卷援引《操作指南》《世界遺產申報籌備》等相關內容,對價值特征要素的概念做了長達一頁的說明,幾乎匯集了官方文件中所有相關內容。但限于引用文件本身的深度,這些說明仍只是概念上的,并沒有就具體操作給出細節說明,也沒有給出認定和填報內容的技術要求。說明中列舉的參考案例,全部是自然遺產,無一文化遺產。更突出的問題是,單一層級的填報形式和不超過15項的數量限制,沒有深入關注到價值特征要素認定可能的豐富層次和復雜關系,也沒有積極吸收第二輪定期報告中一些遺產地已經在成果中呈現的有益的技術方法和管理實踐的經驗。
在2019年世界遺產大會的邊會活動中,已經啟動填報的阿拉伯地區遺產地管理者們,也紛紛表達了在這一項填報中遇到的困惑。這些問題似乎只能在推行中逐步解決,最終能取得怎樣的效果,有待進一步觀察和評價。顯然,技術方面的改進更新并不簡單。而一旦價值特征要素的認定還需要通過下一輪定期報告繼續彌補,其見效周期可能會無比漫長。
3 《操作指南》中的價值特征要素認定相關內容
3.1 《操作指南》正文中與價值特征要素認定相關的內容
在2003年世界遺產委員會第六次特別會議針對《操作指南》修訂的討論中,專家們提出在附錄中應對一系列術語[12]被提及的術語包括:“conservation” and“ protection”;“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criteria”“ values”“attributes”“qualities”and“ characteristics”“management approach”“management system”“ management plan”and“ management and/or planning control”;and“ property”and“ site”.進行定義,并保持使用的一慣性。這其中就包含價值特征要素(attributes)[18]。在這之后2005年版的《操作指南》中,價值特征要素(attributes)首次出現,主要用在真實性、完整性和邊界劃定相關的表述中。具體內容詳見《操作指南》第82段、85段、100段、204段相關內容[19]。
從以上表述中可以理解,所謂價值特征要素,并不是簡單的物質或非物質載體,而是這些載體(或載體之間、載體中的某個部分)中某種可被感知的呈現價值的特征。對價值特征要素的認定,不僅是認定包含這些特征的某個物質或非物質對象,更重要的是識別它傳達價值的特征。這一概念的核心是一種因特征聯系起來的關系,對其認定和完整表述,也必須包括這個要素—特征—價值的關系,由此建立價值認定的基本邏輯關系。對邏輯關系的強調而不限于對要素類型的界定,使價值特征要素在世界遺產文化與自然、物質與非物質相互融合的過程中,可以很好地支持遺產價值和范疇的擴展,使遺產的形態日益豐富,呈現出越來越多的可能性和越來越強的包容性。
當然,這必須基于對邏輯關系準確且謹慎的運用。例如真實性中所涉及的價值特征要素類型,不能被簡單理解為一種評價指標,機械地套用在各種被認定為遺產構成要素的對象上。只有首先確認了承載價值的對象是通過哪種方式呈現的價值,才能針對這種方式呈現特征的準確性、可靠性進行評價。而特征必須是客觀明確的,相對穩定的(和不變的有所區別),這是可以從真實性的視角進行評判的基礎,否則會出現類似前文所述2008年布宜諾斯艾利斯申報項目中咨詢機構提出的質疑。
遺憾的是,2005年版《操作指南》并沒有完全按2003年會議討論的計劃,對價值特征要素從術語的角度給出完整的解釋。在2005年版《操作指南》的附件部分有一份術語的索引[13]這個術語索引保留到2011年版的《操作指南》,在之后的版本中未再出現。,列舉了100多個術語,其中也沒有“attributes”。盡管這個術語被應用在條款中,但仍被作為一個關鍵性術語給予足夠的重視。客觀上2005年版《操作指南》問世十幾年來,很多文化遺產領域的實踐者對這一概念的理解仍不夠清晰準確。
《操作指南》正文中與價值特征要素相關的內容在2005年之后的修訂中沒有重大的變化。后續的補充主要是2011年版《操作指南》第137段關于系列遺產的內容中特別提到應關注非物質形態的價值特征要素[20]。在2015年版《操作指南》第99段關于遺產邊界的總體要求中將原來的籠統表達“應完整呈現突出普遍價值和遺產的完整性和/或真實性”,進一步明確為“邊界的劃定應納入所有承載突出普遍價值的價值特征要素以確保遺產的完整性和/或真實性”[21]。
3.2 《操作指南》對申報文本要求中涉及價值特征要素的內容
在2005年版《操作指南》附件里對申報文本的要求中,只在第二章描述部分針對自然遺產提到應關注重要的物質形態的價值特征要素。在對第三章列入理由部分,雖然提出要編寫“建議的突出普遍價值聲明”,但并未明確涉及對價值特征要素的具體要求。
在2011年版的《操作指南》中,要求文本第三章開頭增加一節“簡要綜述”(brief synthesis),其中特別明確“也應包括體現其潛在的突出普遍價值并因此需要得到妥善保護管理和監測的價值特征要素的概述”。在對價值標準的闡述部分,也明確提出“并描述符合每項標準的相關價值特征要素。”在真實性聲明部分,特意摘錄了《操作指南》正文中對價值特征要素的說明。在保護與管理需求部分,提示組成保護管理框架的保護機制、管理系統和管理規劃,應以保護和保存承載突出普遍價值的價值特征要素為目標。此外,在第四章關于影響因素的內容中,在“負責任的旅游參觀”部分特別提到應關注“由參觀壓力和游客行為導致遺產劣化的可能形式,包括對非物質形態價值特征要素的影響”[22]。
這些對申報文本要求中與價值特征要素認定有關的內容自2011年版《操作指南》之后沒有再做調整。
從上述內容來看,雖然《操作指南》已經將價值特征要素作為一個相對明確的術語引入其中,并在多處對其涵義和重要性做了闡述,但總體是以較為零散的方式出現在其他重要概念和要求中,沒有將其突出為一個重要概念和技術環節,提出更完整清晰的要求。
3.3 《世界遺產申報籌備》對價值特征要素認定的闡述
相對更詳細解釋價值特征要素含義與工作方法的, 是UNESCO、ICCROM、ICOMOS 和IUCN合作出版的《世界遺產申報籌備》這一指導手冊。其中就價值特征要素的認定專門編寫了一個小節,對其核心概念做了一系列闡述,相關要點內容已整理在本文的開頭部分。這部分內容還強調了在申報中通過圖紙清晰認定價值特征要素的重要性,特別是對于有復雜層次(complex layering)的文化遺產項目來說,不僅能幫助理解價值特征要素間的關系,更能在識別矛盾與管理問題,在合理界定申報范圍等方面起到關鍵作用[23]。關注到價值特征要素認定與真實性評估的緊密關系,手冊在指導真實性評估的章節中,以烏干達的巴干達國王們的卡蘇比陵為例,列舉了該項遺產的價值特征要素,并依照《操作指南》對其真實性評估時應關注的問題做了解釋說明[24]。
應該說,指導手冊對價值特征要素相關概念和技術要點的解釋更為全面了。但相對于文化遺產的多樣性,開展價值特征要素認定工作可能采取的多種技術路線,并沒有在手冊中得以展開討論。《操作指南》中強調的對應價值標準的價值特征要素認定和指導手冊案例中從真實性評估角度進行認定,兩者之間的關系是什么,如何銜接?第二輪定期報告很多復雜案例給出的認定框架是否值得推薦?對不同類型、不同復雜度,不同文化環境中的項目,如何選取適合、有效的技術路線而不偏離基本原則?對這些實踐中可能存在的具體問題還沒有更為深入的探討。而案例的單一性,也容易導致手冊中的方式方法在推行中被簡單機械地效仿套用。
4 歷年世界遺產大會決議中涉及價值特征要素的內容
世界遺產大會決議中價值特征要素術語的出現頻率和使用方式,是反映這一概念在世界遺產委員會決策體系中被關注和運用的一個有表征意義的指標。和前文對ICOMOS評估報告的追溯一致,筆者回顧統計了自2001年開始歷年世界遺產大會決議中這一術語的出現和使用情況,共計549次。
從圖7的統計來看,在2005年《操作指南》改版之后,價值特征要素一詞開始零星見于大會議程7(保護狀況)和議程8(申報項目審議)環節的相關決議中。這一階段在保護狀況審議中的使用略占多數。使用頻率的明顯增長始于2010年,在之后幾年中集中在議程8的決議中。與前文對ICOMOS評估報告的統計對照,可以發現這和ICOMOS在這一年中開始對推薦項目的價值特征要素進行梳理有明顯的相關性。2012—2013年有一個明顯減少的過程,之后逐漸增長,議程7和議程8決議中使用頻率的關系也基本保持穩定。直到2019年,隨著ICOMOS在評估報告中對所有申報項目梳理價值特征要素,決議中提及總量和議程8決議在其中所占比例都明顯增長。
圖8統計了價值特征要素被提及時決議內容相關的主題。左邊的主題列表大致按照一個遺產項目從認定,到申報,再到列入后持續的保護管理階段梳理。總體來說,自2009年之后,價值特征要素的概念在各主題相關內容中開始普遍出現。而其中比較明顯的,在申報階段相關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完整性和真實性相關的主題中。特別是近年來涉及這方面的內容更為頻繁。而在保護管理階段,更集中涉及的主題是對遺產地各方面影響因素的評估、措施建議或要求。值得關注的是,一些新申報項目和已列入項目,相關決議中都探討到和其遺產認定相關的基本問題,這中情況在近幾年決議中保持著一定的頻度。

圖7 歷年世界遺產大會決議中價值特征要素(attributes)出現頻率的統計(來源:作者自繪)

圖8 歷年世界遺產大會決議中價值特征要素(attributes)出現頻率按相關主題統計(來源:作者自繪)
在被統計的549個記錄,共涉及254個遺產地。大部分被涉及的遺產地只在某一年決議的一兩個問題中涉及價值特征要素。圖9列出了有5條以上記錄的13處遺產地,總計108次,占總體記錄的20%。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遺產地集中在文化景觀和仍有人生活的歷史城鎮兩大類。可見這兩類遺產中,和價值特征要素相關的問題相對更為突出。圖9的下半部分對照分析了這些遺產地決議中提及價值特征要素的相關主題內容。

圖9 歷年大會決議中有5條以上價值特征要素(attributes)相關記錄遺產地統計分析(來源:作者自繪)
從決議產生年份來看,其中8處遺產為申報當年決議。原因主要是這些項目類型的特殊性,在如何理解認知其突出普遍價值和表現形式,判斷真實性和完整性,以及在此關系基礎上確定保護管理需求等問題上,需要更緊密地結合價值特征要素論述。比較典型的案例如中國的“西湖文化景觀”和英國的“湖區文化景觀”。2019年申報成功的意大利“科內利亞諾和瓦爾多比亞德內的普羅賽柯產地”是一項重報的文化景觀項目,參照ICOMOS意見對價值主題、標準和相應的價值特征要素做了大幅度的刪減調整,而同年申報對的印度“拉賈斯坦邦的齋普爾老城”則是申報文件中的價值特征要素認定引起了ICOMOS的困惑,盡管大會修改決議草案將其列入,但評估報告中提出的諸多完善相關工作的要求被保留在決議中[25]。
另一類遺產地則是在多年的決議中都頻繁的涉及價值特征要素相關問題。其中包括烏茲別克斯坦的“沙赫利蘇伯茲歷史中心”,英國的“利物浦”,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奧地利的“維也納歷史中心”等,都是歷史城鎮相關類型遺產地。其中最突出的是烏茲別克斯坦的“沙赫利蘇伯茲歷史中心”,在5年的決議中提及價值特征要素相關記錄19次。核心問題是其歷史城區中心遭受當地開發建設項目造成的難以挽回的損失,重要的價值特征要素之一——保存完好的歷史城市肌理,如中亞城鎮規劃具有的獨特特征、建于不同時期的歷史街區和傳統建筑被破壞[26]。
該項目于2016年被列入瀕危遺產名錄。因對損失性質的判斷,以及損失能否挽回等問題在咨詢機構、締約國及其盟友、各界大會委員會成員中各執一詞,使該項目在近幾年遺產大會中成為持續的爭論焦點[27]。咨詢機構一度建議將其除名,但決議草案在大會上未被通過。上述數據統計突出地顯現出這個項目相關問題長久未能解決的狀態。導致各方爭議而難有定論的根源之一,在于對其價值特征要素的界定沒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官方認定依據,因而締約國及其盟友可以在大會上以城區歷史建筑的總量作為評判主要依據,用量上損失的百分比去抵消在形態肌理特征上遭受的不可挽回的損失。該案例中另一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在這19條記錄中,有9次與“可恢復的(recoverable)價值特征要素”“恢復(recover)價值特征要素”(的相關行動)有關。這種具體建筑形成的城市肌理類型的價值特征要素,真實性的評價應該深入到哪個尺度,哪種程度的破壞或損失可被視為“可恢復的”,現有決議中顯現的態度似乎是模糊的。
5 2019申報文化遺產項目中的價值特征要素認定
2019年申報的文化遺產項目,包括混合遺產項目中的文化遺產部分,共計35項。筆者對照分析了除5個撤回項目外的30個項目的申報文件、評估報告和大會決議,可以比較清晰地看到價值特征要素的認定,在申報、評審和決議3個環節的狀態(圖10)。根據《操作指南》對申報文本的內容要求,本文對申報項目價值特征要素認定的分析主要針對申報文本第三章中3.1.a的簡要綜述、3.3建議的突出普遍價值聲明、3.1.d真實性評估和3.1.b對列入標準闡述中的相關內容,個別項目參考了比較研究中明確提出的梳理和認定價值特征要素的框架。根據價值特征要素認定應建立的申報內容與突出普遍價值間的關系,分析重點關注兩方面:一是對申報要素的界定——總體層次、歸類梳理是否清晰,各層次、類型構成要素中的主要內容是否清晰;二是對價值特征的表述——對應價值主題的總體特征是否清晰,各組成部分或各類要素的具體特征是否明確。
5.1 認定方式與表達的清晰度
從申報文本中對價值特征要素的梳理和表述方式看,大致可歸納為4種:以遺產自然的結構關系為主導,以價值主題為主導,以價值標準為主導,以及建立多維度的梳理框架,對價值特征要素與構成類型、價值主題或價值標準之間的關系進行交叉梳理。也有個別項目在這些章節的表述相當籠統,難以概括其邏輯方式。

圖10 2019年申報項目價值特征要素認定情況分析統計(來源:作者自繪)
以遺產自然的結構關系為主導是較為普遍的方式,共12項。由于其表述直接反映遺產在物質形態以及相關非物質要素上自然的組合和結構關系,因此總體上都能對要素類型作出清晰的層次分類,梳理各層次或類型中具體的內容。采用這種方式表述的挑戰在于對特征的描述。大部分項目在第三章的表述都只做到了對總體特征的概括,缺少能聯系到價值的明確的特征描述,對各類構成要素特征的表達更是被忽略的內容。少數案例做得非常出色。例如的英國的“卓瑞爾河岸天文臺”項目,在第三章的簡要綜述清晰列舉了從天文臺的景觀環境到最核心的射電天文望遠鏡,天文臺一系列重要的功能性建筑和附屬設施,以及早期科學設施的遺存遺跡等各類型要素的內容,并對每類要素的特征要點和價值內涵做了清晰的論述[28]。
意大利的“科內利亞諾和瓦爾多比亞德內的普羅賽柯產地”等項目則從價值主題對應的特征要素進行歸納,從“the hogback landscape” 賦予種植園的景觀基底特征,“ciglioni”這種培育種植方式呈現的農民的創造力,人與自然共同創造的馬賽克鑲嵌般的種植園大地景觀三方面梳理相關的物質與非物質價值特征要素[29]。顯然這種表述方式更利于突出要素特征與突出普遍價值之間的關系,準確理解要素被認定的原因,也利于明確保護和管理在遺產地的形態特征方面應達到的綜合效果。經過這樣的梳理之后,價值標準部分的論述則相當簡明扼要。
中國的“良渚古城遺址”[30]、俄羅斯的“普斯科夫學派教堂建筑”[31]等項目代表了以價值標準為主導梳理價值特征要素的方式。文本第三章的綜述相對簡短概括,詳細的價值特征要素認定出現在各條價值標準的論述中。這種方式對應了《操作指南》中提出的“描述符合每項標準的相關價值特征要素”這一要求。其優勢是能夠強有力地論述價值標準的選用理由。但很多情況下,價值標準關注的角度和遺產地價值主題的層次關系并不一定有很好的對應,特別是選取多條價值標準并按其排序論述時,容易導致從價值主題到特征表現的完整結構與層次關系被拆開,分散在各條價值標準的論證中。2019年申報項目中采用這種方式的并不多。
更為綜合的方式,是在價值特征要素和價值主題、價值標準之間建立一種更系統化的分析、對應框架。比較典型的如日本的“百舌鳥和古市古墳群”(圖11),美國的“弗蘭克·勞埃德·賴特的20世紀建筑作品”(圖12)這兩個項目。日本的古墳項目將其價值特征要素歸納為3方面:一是很多類型的古墳聚集在一起的整體形態特征;二是顯示這些古墳間鮮明層級關系的4種典型規劃布局形態;三是顯示出精心而獨特的葬禮儀式的各種考古證據,進而通過圖表方式闡述這3類價值特征要素對應價值標準iii、標準iv的具體特征,和這一特征在價值上的重要意義。美國賴特建筑作品的案例則是將價值特征要素歸納為3大方面和每個方面下的3個要點,然后對本次申報的8個建筑作品逐一明確在價值特征要素框架下對應呈現的具體特征。這一框架也在文本中用來對將來可能繼續申報的建筑作品做出評估和論述,為擴展申報奠定基礎。總體來說,這種方式能夠更清晰地闡述申報內容、其特征所反映的價值主題,以及價值主題與可能符合的價值標準之間的聯系,框架性的分析方式也更便于從要素的構成和價值特征雙向理解,掌握一個遺產項目的整體輪廓和結構層次。

圖11 日本“百舌鳥和古市古墳群”申報文本中對價值特征要素與價值標準對應關系的闡述(來源:http://whc.unesco.org/document/166325)

圖12 美國弗蘭克·勞埃德·賴特的20世紀建筑作品申報文本中對各建筑價值特征要素的梳理(來源:http://whc.unesco.org/document/170692)
5.2 價值特征要素的涵蓋范疇
2019年申報項目從類型上呈現出較為豐富的狀態,不僅包括傳統的紀念物、考古遺址、建筑群,也包括具有歷史城鎮特征的遺產地,大量主題多樣的文化景觀,并包括多項20世紀遺產、工業遺產甚至射電望遠鏡這樣的當代天文領域科技遺產。因此,這些項目認定的遺產價值特征要素在所涉及的范疇上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反映當前文化遺產類型多樣化的發展狀態。
圖13從兩個角度梳理了這些申報項目價值特征要素涵蓋的范疇。左側是這些項目在真實性評估中涉及的價值特征要素類型;右側是在價值特征要素中,除通常會關注的物質形態特征外涉及的內容。遺產地的類型按世界遺產公約中認定的基本類型和《操作指南》中陸續擴展的類型從上至下排列。

圖13 2019年申報項目認定的價值特征要素的范疇(來源:作者自繪)
左側在真實性評估中可見,形態和設計、材質、使用和功能、選址和環境仍是主要被識別的價值特征要素類型。但并不是所有項目在真實性評估中都涉及這些“指標”。說明不少項目會根據自己的價值特征要素從更有針對性的類型角度評估。這在文化景觀類型的項目中尤為突出,如意大利的“科內利亞諾和瓦爾多比亞德內的普羅賽柯產地”,澳大利亞的“布吉必姆文化景觀”等,只涉及這4項中的1項或2項。而這4項之外,視覺完整性已經比較多地出現在真實性評估中,如韓國的“韓國新儒學書院”、緬甸的“蒲甘”,巴林的“迪爾穆恩墓葬群”、阿爾巴尼亞的“奧赫里德地區自然與文化遺產”(擴展申報)等。右側在具體認定的價值特征要素中包括“空間聯系-視覺完整性”的遺產地所占比例則更為突出。同時,真實性評估中涉及非物質類型要素的遺產地絕不僅限于文化景觀、歷史城鎮等類型,管理、技術相關要素在工業類型的遺產項目中普遍被涉及,其他非物質方面的類型呈現明顯的多樣化,不限于《操作指南》給出的范疇。
右側價值特征要素認定中特別關注的類型中,不少項目都涉及個體構成尺度以下由局部反映的細節特征。例如阿爾巴尼亞的“奧赫里德地區自然與文化遺產”中強調的教堂遺址中印證時代和文化關聯性的馬賽克鋪地,“賴特建筑作品”等眾多建筑群項目中對建筑風格在細節方面的具體體現,中國“良渚古城遺址”等很多考古遺址中強調的細微的考古現象等。這表明價值特征要素在尺度層次上的豐富性,即便規模再大的遺產地,都可能有細微尺度上支撐核心價值的特征要素。與自然相關聯的要素,以及森林植被等要素在這一年的申報項目中也被較多涉及,不僅是文化景觀,遺址、建筑群、甚至具有紀念物性質的遺產地也認定相關價特征要素。這也鮮明地反映出當代世界遺產文化與自然融合的趨勢。同樣,眾多類型項目中對非物質遺產類型價值特征要素的認定,也反映了物質與非物質融合的趨勢。此外,5個遺址或復合型遺產地(sites)都涉及出土文物或館藏文物類型的價值特征要素。這些要素應如何被認定為不可移動遺產的一部分,在遺產邊界、要素清單的確定方面似乎仍有待深入探討。
5.3 ICOMOS對申報文件價值特征要素的整理歸納
如前文所述,2019年ICOMOS開始對申報項目做全面的價值特征要素梳理。這部分的內容以一段100~150字(英文字符數)的文字表述。ICOMOS首先要對出現在申報文件(文本及補充材料)各處、可以確認是在價值特征要素認定的內容上進行整理歸納。這是由于申報文本對價值特征要素認定的表述還不夠統一規范。如在對印度“齋普爾古城”的評估中評論道“申報文本沒有提供一套清晰明確的突出普遍價值特征要素認定,文本中多處出現了不同的價值特征要素清單,并在其他地方暗示了另外的價值特征要素”[32]。可想而知,ICOMOS的歸納并不是一項容易完成的工作。ICOMOS對各個項目的歸納程度也各不相同。多數項目這段評估約達180字,可以做到內容豐富而有層次;個別項目不足100字,有些如阿爾巴尼亞的“奧赫里德地區自然與文化遺產”,只有不到50字的概述。更特殊的例如對德國和捷克共同申報的“厄爾士/克魯什內山脈礦區”,直接評述“對如此大型且復雜的遺產地……很難在短短幾行內將這一系列遺產的所有價值特征要素表述清楚”,便略去了歸納整理內容,直接給出結論認可文本中認定的要素可以支撐突出普遍價值[33]。
除上述個案, ICOMOS在大部分項目中都做出了相當審慎的歸納整理。其成效主要表現在對要素層次的梳理和一些ICOMOS認為需要補充的內容。共有16個項目的價值特征要素在這一過程中被重新梳理了層次,其中13個項目被提出建議補充或刪減部分要素。其他有7個項目以梳理歸納為主,大都是沒有明確從價值特征要素角度做過系統梳理的項目。也有美國的“弗蘭克·勞埃德·賴特的20世紀建筑作品”、緬甸的“蒲甘”和意大利的“科內利亞諾和瓦爾多比亞德內的普羅賽柯產地”3個項目基本參照文本表述的層次和內容未做調整。
但另一方面,ICOMOS在這部分的工作突出對價值特征的表述。從圖11的對比來看,經過ICOMOS精煉的價值特征要素認定,在層次和內容認定上普遍有所提升,但在特征表述方面,無論是總體還是具體層面的,都更加概略甚至變得模糊。多個評估報告在這段文字中只是分層次羅列了要素內容。
5.4 大會決議中對價值特征要素的認定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大會決議中并不包含專門針對新列入遺產價值特征要素認定的確認,依據《操作指南》編寫的突出普遍價值聲明中的簡要綜述部分,是最接近價值特征要素認定結論的內容。而這段內容會遇到兩種情況。
一是該項目被咨詢機構推薦列入,決議草案由ICOMOS起草,其中突出普遍價值聲明中的簡要綜述會參照評估報告對價值特征要素的梳理結果,報告中提出的增減建議也會在決議的建議中被提及。這種情況下,申報、評估和決議環節能在價值特征要素認定上形成一個基本連續的鏈條。
二是大會修改決議草案,將咨詢機構不建議列入,甚至不認可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項目列入遺產名錄。這種情況下,評估報告沒有給出突出普遍價值聲明的草案,決議中這部分內容一般會參照申報文本中的聲明草案,并很少對其中的實質內容進行修改。于是,如圖11中所示,2019年6個修改決議草案列入名錄的項目里,決議中與價值特征要素相關的表述和評估報告意見能保持基本一致的,只有波蘭的“科舍米翁奇的史前條紋燧石礦區”一項[14]該項目在評估報告中突出普遍價值基本被認可,因完整性方面有缺失,評估報告對價值特征要素認定提出了補充建議,并建議該項目補報。,其他都與評估報告有明顯差異。因此,在大會上臨時修改決議列入的遺產項目,不僅是在價值論證的結論上跳過了專業審查,對價值依托的客觀事實的認定上同樣跳過了專業審查。
由于大會決議的行文體例,決議中突出普遍價值聲明部分的綜述文字向來傾向于綜合性的概述,ICOMOS所作的本已精煉概括的價值特征要素認定,在這里被進一步縮略簡化,在對價值特征要素表述上更加不清晰、不具體,幾乎無法作為價值特征要素認定的依據。但由于每個環節都可能發生的變化,無論申報文本、申報時的管理規劃,還是ICOMOS的評估報告,也都無法作為技術性附件,承擔起列入項目價值特征要素認定依據的作用。
6 結束語
價值特征要素,作為一個專業術語被引入世界遺產體系,特別是文化遺產部分,已有20年的歷史。這一概念建立起價值和遺產要素之間基于特征的緊密聯系,在世界遺產的發展過程中,特別是文化與自然、物質與非物質的融合過程中,擴展對遺產價值范疇、呈現形式的認知,并保持以價值為核心的保護邏輯,起到了重要作用。深入推動價值特征要素的認定,可以提升以價值為核心的遺產保護工作邏輯,保障世界遺產名錄的可信度。
但官方重要文件中對這一概念的定義和相關工作方法、技術要求的闡述尚不清晰,較為簡化和單一,還不足以有效應對當前世界遺產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很多有益的實踐經驗未被及時吸收借鑒。這導致目前參與世界遺產保護的各方,遺產地管理者、決策者,咨詢機構,遺產大會決策機制中的參與者,對這一概念和相關技術要求的理解認知呈現參差不齊和多樣化的狀態。特別是在遺產申報、評估和決議的一系列過程中,缺乏能夠將各環節成果統一連貫起來的操作規則和技術標準,導致價值特征要素認定無法切實起到加強以價值為核心保護邏輯的關鍵作用。通過定期報告去完善這些環節產生的問題,或許是一種解決途徑,但不可能很快取得收效,而每年新增項目積累的問題會造成越來越大的包袱,進一步加劇對世界遺產名錄可信度的挑戰。同樣基于從上游解決問題的策略,在世界遺產委員會和相關機構推動申報程序改革的同時,對價值特征要素認定相關概念和技術要求的完善和推廣也是亟待得到重視的關鍵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