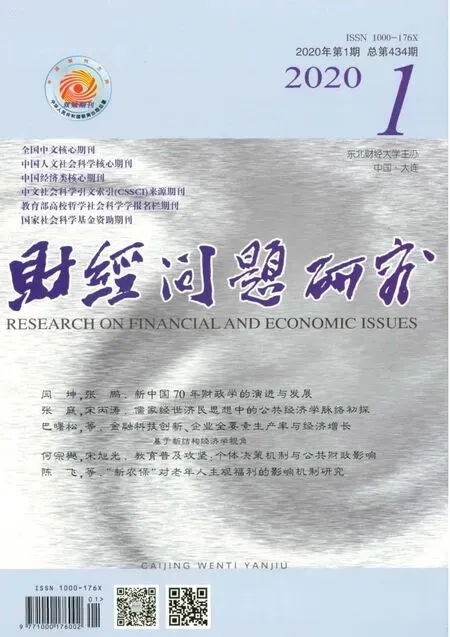中國的勞動力價格扭曲及其經濟影響
——基于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的研究
陳 沁,朱宏飛,樊瀟彥
(復旦大學 經濟學院,上海 200433)
一、問題的提出
在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換的關鍵時期,繼續深化供給側改革、優化要素市場配置效率是決定中國經濟長期健康發展的新動能。然而,要素資源配置效率不高的現實,嚴重束縛了當前中國經濟的活力[1]-[3]。尤其是在近年來人口紅利消耗殆盡、勞動力成本迅速上升的背景下,改善勞動力市場配置效率,對中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與高質量發展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4-5]。
改善勞動力市場的配置效率,首先需要科學測量勞動力價格的扭曲程度。Hsieh和Klenow[6]發現,勞動力價格扭曲使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損失了24.00%。與資本價格扭曲不同,勞動力價格扭曲隱藏在工資差異中,因存在勞動力異質性而難以度量。如果資本價格扭曲是資本的價格差異,那么勞動力價格扭曲就是相同能力勞動力的工資差異。在研究勞動力價格扭曲問題時會面臨這樣一個障礙:即使勞動力的教育程度、經驗等已觀測特征都相同,他們的能力差異仍然存在,而這部分未觀測能力難以被度量,導致無法計算出勞動力價格的扭曲程度。
既有文獻并未很好地測算勞動力價格扭曲,研究勞動力價格扭曲對經濟造成影響的文獻也相對較少。在傳統文獻中,工資殘差一般包含兩個部分:一是未觀測能力與能力價格的乘積,二是未觀測能力之外的差異,即勞動力價格扭曲。然而,由于勞動力價格扭曲難以從殘差中識別出來,以往的研究只能使用較強的假設來控制扭曲對工資的影響。例如,假設勞動力價格不包含任何扭曲[7],或假設勞動力價格僅包含一個不隨時間變化的扭曲[8]。然而事實并非如此。一些文獻已經發現:個人能力以外的“暫時性隨機誤差”可以解釋工資殘差變化的一半[9]-[11]。如果忽略這個部分,將高估工資殘差中未觀測能力的影響,并遺漏重要的扭曲信息。本文將放松這些嚴格假設,將工資殘差中的扭曲和能力部分區分開來,并測量勞動力價格扭曲的相對大小。
本文首次對中國的勞動力價格扭曲及其影響進行了定量分析。本文使用上海2011年外來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來識別勞動力市場的扭曲。該數據的最大優勢在于涵蓋了流動人口來滬前后的工作和工資信息。通過對個體來滬前最后一份工作的工資與來滬后第一份工作的工資進行差分,可以剔除該樣本未觀測的個人能力,從而找出省際間的勞動力價格扭曲差異。研究結果表明:發達省份,如北京、上海、廣東等,勞動力價格扭曲的程度相對較低,發達省份的工資也更能夠體現個人能力。這一結論也部分解釋了所謂的“逃回北上廣”現象。本文應用Hsieh和Klenow[6]的方法估計了勞動力價格扭曲對收入不平等、總產出和平均工資的影響。既有文獻指出,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中有80.00%—90.00%來自于勞動力價格扭曲的增大。但本文發現,在扭曲程度較高的省份,勞動力價格扭曲使得工資方差提高了15.58%—41.09%。并且,勞動力價格的扭曲也會加劇勞動力的錯配,造成效率損失。在扭曲程度較大的省份,總產出和平均工資分別下降了21.36%—34.88%。
二、文獻綜述
工資的決定因素一般包括兩個部分:已觀測能力、未觀測能力。前者包括受教育程度、工作經驗等已觀測特征,這些是目前文獻研究的主要部分。另外一部分特征無法被觀測到,稱之為未觀測能力,這部分特征構成了工資殘差,由于缺少數據難以識別。對工資進行分解的傳統文獻發現:工資方差中組間差異占30.00%左右,工資殘差占另外70.00%[12]。Katz[13]的工作也得到了類似結果:工資殘差的變動占1963—1965年美國工資總方差變動的75.00%。這一系列研究的共識是:在理解收入不平等的問題上,必須更關注工資殘差的水平和變化趨勢。但到目前為止,大部分文獻仍然集中于研究已觀測特征可解釋的工資組間差異,對工資殘差的研究仍然不多。

隨后,學界對工資殘差的研究沿襲了Juhn等[7]的假設。Chay和Lee[11]對工資殘差的分解為:εit=pteit+ωit,其中,εit為工資殘差,pt是未觀測能力的價格,eit為未觀測能力,ωit是一個隨機沖擊。Chay和Lee[11]的研究將ωit看作關鍵變量,假設其方差在不同人群中發生變化時,未觀測能力的價格變化會對工資殘差造成怎樣的影響。Lemieux[8]的研究采用了Chay和Lee[11]的假設,但同時假設ωit的方差并不隨時間變化。因此,工資殘差的變化主要分為兩部分:一是未觀測能力分布變化,這個變化是由已觀測特征結構變動導致的;二是未觀測能力的價格變化。Juhn等[7]與Lemieux[8]分別分解了各時期美國的收入不平等狀況,得到了不同的結論:前者認為造成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是未觀測能力的價格變化,而后者則認為未觀測能力分布的變化對收入不平等的貢獻更大。
基于以上研究方法,一些學者對中國的工資殘差進行了研究。Xing和Li[14]采用了Lemieux[8],DiNardo等[15]的方法研究了中國的工資殘差,使用中國家庭收入調查(CHIPS)數據研究了1995—2007年中國收入不平等變化中各因素占比,并認為中國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是未觀測能力的價格上升。Xing和Li[14]還進一步研究了城市特征與工資殘差變動之間的關系,發現私營企業對雇員未觀測能力的定價更高,因而國有企業占比降低會導致工資殘差的提高。Meng等[16]也認為導致工資殘差增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的變化。
技能偏向型技術變革(Skill-Biased Technical Change,SBTC)理論對工資殘差的擴大趨勢作出了解釋。該理論認為:偏向高技能的技術變革提高了勞動技能價格,而勞動技能價格則包括了未觀測能力,進一步提高了工資的組內差異。Acemoglu[17]認為,教育與未觀測能力的回報從長期看都會提高,其原因在于高教育水平勞動力供應增加后技術進步會更偏向于與技能互補。Ingram和Neumann[18]的研究發現,教育回報率的提高可以被不同種類技能回報的上升所解釋。Violante[19]指出,如果勞動力市場存在摩擦,未觀測能力占比相對較大的勞動力將更傾向與高技術互補,使教育回報率和未觀測能力的價格同時上升。Hornstein等[20]總結了SBTC理論的文獻認為,技術進步會同時提高已觀測能力與未觀測能力的回報。
在SBTC理論的框架下,不難作出這樣一個推論:如果未觀測能力與已觀測能力的價格同比例上升,那么工資殘差在收入不平等中的貢獻應當是恒定的。然而,實證結果并不符合這點。Card和Dinardo[21]的研究發現,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工資殘差在總收入不平等中的占比確實上升了,但在技術進步更快的20世紀90年代,該比例卻保持穩定。對此現象的一個解釋是:未觀測能力的價格包含了隨時間變化的勞動力價格扭曲,該因素抵消了技術進步的作用,這就導致最終的未觀測能力的價格并未像SBTC理論所預測的那樣變化。
事實上,很多文獻都已注意到價格扭曲的重要作用。Gottschalk等[9]、Moffitt和Gottschalk[10]與Chay和Lee[11]均發現,工資殘差中,隨機沖擊能夠解釋工資殘差上漲幅度的1/2。問題的關鍵是工資殘差中的“隨機沖擊”到底是什么?事實上,如果改變工資殘差的組成成分,假設工資殘差包含價格扭曲、且允許該扭曲隨時間變化,實證與理論的分歧便可彌合。
當價格扭曲替代“隨機沖擊”成為為觀測能力變化的成分時,可以分析勞動力價格扭曲會如何影響不平等和產出。Hsieh和Klenow[6]研究了要素價格的扭曲對企業分布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朱喜等[22]考慮了農業部門的勞動力價格扭曲,并發現中國產生剩余勞動力的重要原因正來自于東、西部相對于中部的較高勞動力價格扭曲。本文使用Hsieh和Klenow[6]的模型,研究勞動力價格扭曲對平均工資和產出的影響。
三、數據描述
在研究未觀測能力時,勞動經濟學中常用的多期面板數據可能并不合適,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在間隔較長的多期面板數據中,個人未觀測能力和已觀測特征的累計函數關系可能不再適用。Meng等[16]與Xing和Li[14]的研究表明,2000年中國高校擴招后,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顯著增加,這使得低教育水平人群的未觀測能力區間收縮而高教育水平人群的未觀測能力區間擴張。因此,用高校擴招前的數據來推斷高校擴招后的工資,可能會錯誤估計工資殘差的占比,對高技能人群來說會低估,而對低技能人群來說則有所高估。第二,暫時性隨機沖擊,或者說本文定義的勞動力價格扭曲,在長時期面板中可能會隨時間發生變化。在整個收入變化中,若幾個組成部分都發生變化,將無法在工資殘差變化中識別出勞動力價格扭曲。
為了解決以上問題,本文使用上海2011年外來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以下簡稱“上海數據”)。上海在2011年對全市外來流動人口進行了抽樣調查,這次調查訪問了23 517人,覆蓋所有16—60歲的外來人口。由于調查還涉及到與外來人口同住及不同住的家庭成員,因而調查數據實際提供了105 747人的信息。數據包含了外來人口的工作經歷,尤其是來滬前的最后一份工作和來滬后第一份工作的信息,包括收入、企業性質、職業、行業等。
由于包括了遷移前和遷移后的信息,對本研究而言,上海數據是一套唯一可用的數據。實際上,大部分同類研究僅能使用移民遷出地和遷入地的普查數據,很難將其在個人層面上進行匹配。使用上海數據,可以避免以往文獻中通過連接幾個時間間隔較長的截面來構造反事實工資的作法。這種作法可能會因為個人能力變化或高校擴招等原因錯誤估計工資殘差。由于來滬前最后一份工作與來滬后第一份工作對來滬前后狀態均為“就業”的人來說時間間隔較短,可以假定其未觀測能力沒有發生變化,因而其工資差異就完全來自于已觀測能力和未觀測能力的價格變化。通過對來滬前后兩份工作的工資進行回歸和差分,就可將工資殘差中已觀測能力和未觀測能力造成的影響消除,剩下的差異便是由兩地之間勞動力價格扭曲造成的。在數據處理中,保留了調查中標記為來滬前后都處于工作狀態的樣本,排除一些樣本較少(低于50人)的省份,總樣本量為6 882人,來自13個省份。表1列示了數據中來自各省份的流動人口數量及相應的部分人口統計信息。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外來人口經過多次遷移,本文使用外來人口來滬前最后一份工作的所在地作為來源地。

表1 來滬前后狀態都屬于“就業”的外來人口統計(來源地)
四、勞動力價格扭曲的估計
根據Mincer收入函數,工資主要由勞動力技能和工作經驗決定。基于此,本文假設個人工資由式(1)決定:
wagei,j,k=pj,kskilli+βj,k,1expi+βj,k,1dummyi+ωi,j,k
(1)
其中,i=1,2,…,Nj,j∈Θ,k=0,1。Nj代表來源j省份的來滬勞動力;Θ代表除上海外的30個省份;k代表外來人口屬于來滬前(0)或來滬后(1)。wagei,j,k代表來源于j省份的勞動力i在k狀態下的工資水平。skilli=(skilli,e,skilli,u)T是能力向量,包括已觀測能力和未觀測能力兩個部分,且相互正交。已觀測能力skilli,e由教育程度表示;未觀測的能力skilli,u指努力程度、組織能力等無法通過教育程度觀察到的能力。pj,k=(pj,k,e,pj,k,u)為來源于j省份的勞動力在來源地和上海能力的價格。pj,k同樣分為已觀測能力的價格pj,k,e與未觀測能力的價格pj,k,u。expi代表個人工作經驗,dummyi為時間啞變量,ω為殘差。
根據以往文獻,經驗與能力的回報可能并不一致,因而在公式中將expi與skilli區分開來。Jeong等[23]的研究發現與SBTC理論的觀點不一致,Jeong等[23]認為,隨著經驗供給量的增加,經驗的回報率會下降,而SBTC理論認為技能的回報應當是上升的。本文區別于以往文獻的關鍵變量是式(1)中的ω。由于所有能夠提高勞動生產效率的個人能力都已經用已觀測能力或未觀測能力囊括,ω是個人能力之外的工資差異。與通常意義上的工資殘差不同,它代表勞動力工資的扭曲,與個人的已觀測能力與未觀測能力都正交。根據Ingram和Neumann[18]與Hornstein等[20]文獻,已觀測能力與未觀測能力的價格相關性較高。不失一般性,在此假設式(2):
(2)
其中,j∈Θ。式(2)的含義是,在不同省份,已觀測能力的價格和未觀測能力的價格雖然會變化,但比值保持恒定。這個等式在直覺上也是成立的,這是因為,如果已觀測能力與未觀測能力都屬于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能力,只是前者能夠容易地被觀測到而后者不能,兩者在技術進步時與資本相結合的水平也會按相同的速度上升,兩者的比值就是必定相同的。
將式(1)中的skilli分為已觀測能力與未觀測能力兩部分,得到核心模型式(3)。該式區分了勞動力工資中的勞動力價格扭曲部分與未觀測能力部分,這是與傳統工資決定方程最大的區別。
wagei,j,k=pj,k,eskilli,e+βj,k,1expi+βj,k,2dummyi+pj,k,uskilli,u+ωi,j,k
(3)
分別在k等于0和1時對每一個來源省份j估計式(3),可得到來自j省份的外來人口在來滬前后的擬合工資,用實際工資減去擬合工資算出工資殘差。對每一個j依次計算來自該省份人口在來滬前和來滬后的工資殘差方差,將來滬前后的工資殘差方差相除,可得式(4):

(4)
在式(4)中,σj,k2(k=0,1)表示由式(3)估計出的同一批人口在來源地j及來滬后的工資殘差方差,由已觀測能力方差、未觀測能力的方差加上已觀測能力和未觀測能力的協方差組成,且由于已觀測能力和未觀測能力相互正交,兩者間的協方差為零,第一個等號成立。σu2為來自ji省份的外來人口的未觀測能力方差。由于流動人口在來滬后獲得第一份工作與來滬前最后一份工作的時間間隔很短,可認為其未觀測能力未變化,因而式(4)第二個等號成立。σj,k,ω2(k=0,1)是ωi,j,k的方差,即人口遷移前及遷移后的工資扭曲方差。式(4)中的ηj,k=σj,k,ω2/(pj,k,u2σu2+σj,k,ω2)(k=0,1)表示來自j的勞動力的工資扭曲方差占工資殘差總方差之比。與Juhn等[7]等文獻相同,式(4)的含義是,在勞動力來滬后的工資殘差中去除價格扭曲后,剩下部分的占比應當等于來滬后所面臨的能力價格的比值。


(5)


從表2可以看到,安徽、北京、福建等地的勞動力價格扭曲程度相對上海較低,其他省份的勞動力價格扭曲程度相對上海更高,湖南、重慶、江西、江蘇、浙江與上海之間存在顯著程度在10%以下的差異。山東的殘差分布的方差較大,雖然其扭曲程度較高,但其分布也較寬。如果在第一步中將山東工資殘差分布進行5%截尾,山東與上海扭曲差異的顯著程度便提高到10%以下。安徽與四川的扭曲程度與北京、上海、廣東、福建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差異。原因在于,這兩個省份的勞動力在來滬后未觀測能力所解釋的部分占比的下降速度比工資殘差縮小得更快。根據Hornstein等[20],已觀測能力和未觀測能力的價格同步變化。然而與其他省份來源的外來人口不同的是,安徽、四川兩個省份流動人口來滬后的教育回報反而出現明顯下降:從安徽到上海的人口的教育回報從5.20%減少至4.00%、從四川到上海的人口的教育回報從7.00%減少至5.70%。這一現象可能與其具體分布情況或從事職業有關,導致某省份勞動力價格扭曲增大或縮小的原因可能比想象的更復雜。

表2 不同省份勞動力市場的相對扭曲程度
注:該表格的結果并未控制個人的職業、所屬行業與公司性質等啞變量。即使控制以上特征變量,也不會影響結構的排序。
Altonji和Pierret[24]指出,雇主在難以識別個人未觀測能力時更有可能只根據已觀測特征來為勞動力確定價格。該機制會導致流動人口在流入地首次工作的工資殘差偏小。如果該機制成立,那么隨著外來人口來滬時間的增加,未觀測能力在工資決定中起到的作用更大,這會使工資殘差的方差增大。如果不同時期來滬人口的能力分布相同,那么2010年之前來滬人口的工資殘差應當大于2011年的工資殘差。
因此,分別對2010年和 2011年來滬的2 058名外來人口進行檢驗,結果表明,2010年來滬人口的工資殘差和2011年來滬人口的工資殘差并沒有顯著差異。將檢驗擴大至2001—2010年也能得到類似的檢驗結果。基于這一結果,并沒有證據能夠表明外來人口在上海第一份工作工資的殘差會偏低。事實上,即使第一份工作的工資殘差確實偏低,只要其未觀測能力進入殘差的速度與來源省份無關,那么各省份勞動力市場相對扭曲程度的估計和排序也不會受到影響。這個結論也進一步證實了之前的結論。
五、勞動力價格扭曲的影響
(一)勞動力價格扭曲對總產出的影響
勞動力價格扭曲可能會造成勞動力的錯配,降低總產出。使用Hsieh和Klenow[6]的方法,假設j省份的總產出Yj由產出為Ys,j的Sj個行業生成。式(6)描述了總產出生成過程。式(7)描述了所有行業實現利潤最大化情形下的價格關系。

(6)
Ps,jYs,j=θs,jPjYj
(7)

(8)
每種產品的產量是資本和勞動的Cobb-Douglas函數如式(9)所示:
Ysi,j=Asi,jKsi,jαs,jLsi,j1-αs,j
(9)
Lsi,j與Ksi,j分別表示在j省份s行業的i企業所使用的勞動力和資本。與Hsieh和Klenow[6]引入要素價格扭曲的方法類似,本文在利潤函數中引入勞動力價格扭曲,如式(10)所示:(1)參考Hsieh和Klenow[6]的公式設計。此公式與下文的式(11)都采用了與Hsieh和Klenow[6]相似的推理方法。
πsi,j=psi,jYsi,j-w(1+τLsi,j)Lsi,j-RKsi,j
(10)
psi,j代表產品價格,πsi,j代表單位產品利潤。w為單位勞動力價格,R為單位資本的價格。τLsi,j為真實工資偏離市場工資的程度。在工資偏離時,該企業的勞動力會發生錯配,此時企業的邊際勞動產出不等于w,而是w(1+τLsi,j)。以上海為基準計算其他省份的扭曲方差var(τLsi,j)。
將式(8)與式(9)的產出加總,可得j省份s行業的總產出Ys,j如式(11)所示:
(11)
將式(11)中的行業全要素生產率提取出來,可以算出各個行業全要素生產率與勞動力價格扭曲的關系如式(12)所示:
(12)

(13)

結合以上作法與參數設置,能夠從式(13)中算出勞動力價格扭曲對各省份總產出具體的影響程度,結果如表3所示。在產品價格被標準化的前提下,各省份平均工資與總產出之比是給定的,勞動力價格扭曲對總產出的影響就與對平均工資的影響相同。

表3 各省份與上海的勞動力價格扭曲差距導致的產出(平均工資)損失程度 單位:%
根據表3,由于勞動力價格扭曲程度相對較高,山東、江蘇、重慶、湖南、江西的總產出與平均工資降低了21.36%—34.88%。勞動力價格扭曲的意義非常重要,其不僅會造成資源錯配,導致總產出的效率損失,還是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
(二)勞動力價格扭曲對收入方差的影響
勞動力價格扭曲會帶來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以往的研究發現:工資殘差的擴大,而非教育、經驗等已觀測特征能夠解釋中國城鎮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逐年上升的80.00%—90.00% 。Meng等[16]發現,工資殘差的擴大可以解釋中國男性收入對數1988—2007年總方差上升的91.00%。Xing和Li[14]使用類似的數據,發現工資殘差可以解釋1995—2007年城鎮工資方差擴大的78.00%。這類文獻主要從時間維度來分析工資殘差的貢獻,而本文已經證明殘差中的重要部分是勞動力價格扭曲,那么使用表2結果,可以分析在空間維度上,由于不同省份勞動力的價格扭曲差異造成工資殘差擴大,進而使得收入不平等的比例。
圖1展示了各省份的工資總方差進行分解結果。與Gottschalk等[9]、Moffitt和Gottschalk[10]、Chay和Lee[11]的結論一致,勞動力價格扭曲差異在收入不平等中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而這部分差異原本會被解釋為未觀測能力的差別。在勞動力價格扭曲程度顯著高于上海的七個省份中,勞動力價格扭曲可以解釋收入方差的15.58%—41.09%。

圖1 各省份勞動力價格扭曲的分解
六、結 論
本文使用上海2011年外來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度量了中國各省份的勞動力價格扭曲程度。沿襲Hsieh和Klenow[6]的模型,對勞動力價格扭曲造成的宏觀影響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表明:北京、福建、上海、廣東等省份的勞動力價格扭曲程度相對較低,湖南、重慶、江西、江蘇和浙江等省份的勞動力價格扭曲程度相對較高;勞動力價格扭曲在一些省份可以解釋高達41.09%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并且導致總產出和平均工資水平降低了21.36%—34.88%。本文的結論可以為制定矯正勞動力市場扭曲的相關政策提供理論支撐。
本文的邊際貢獻主要有兩點:第一,相比既有文獻,本文相對科學地測算了中國的勞動力價格扭曲。勞動力價格扭曲是工資殘差的關鍵組成部分,代表了勞動力市場對勞動力的定價錯誤,對于不平等研究和資源錯配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第二,本文使用流動人口來滬前后的工資數據,解決了傳統文獻中研究勞動力價格扭曲時存在的固有問題。一方面,在以往有關工資殘差的研究里,無法區分工資殘差中未觀測的能力部分與勞動力價格扭曲,而以往的研究假設往往過于嚴格,如假定“沒有勞動力價格扭曲”或“只有恒定勞動力價格扭曲”,會高估未觀測能力的大小。另一方面,已觀測特征在不同時期可能不同,在使用長時間截面生成反事實工資時可能會出現問題。以上操作使得勞動力能力價格研究中技能偏向型技術變革理論的預測與實證結果之間產生了矛盾:前者認為,未觀測能力的價格與已觀測能力的價格應當有較高的相關性,而后者認為,兩者有時會呈現無關,甚至相反的趨勢。本文的研究彌合了理論文獻與實證文獻的鴻溝。
本文也存在一些未來可繼續研究的內容:第一,考慮數據可得性問題,本文使用的樣本量偏少,能夠計算勞動力價格扭曲的省份較少。第二,本文主要定義并初步測算了勞動力價格扭曲,并沒有挖掘扭曲產生的原因。盡管如此,本文還是為相關文獻提供了新的角度,在不平等和資源誤置方面,勞動力價格扭曲將有待進一步更加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