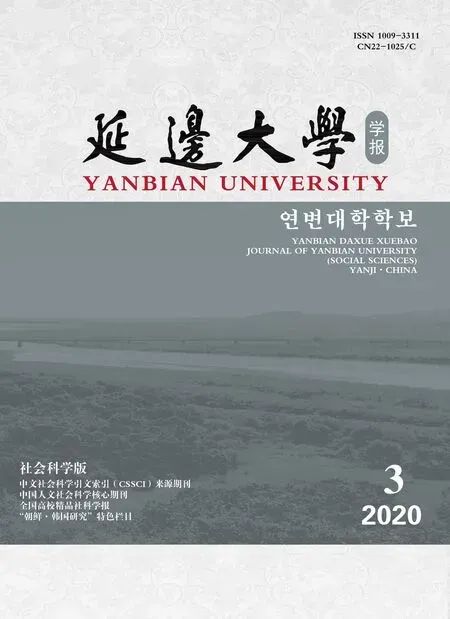中國朝鮮族抗日歌曲《游擊隊進行曲》淺析
李智淵 崔玉花
美國歷史學家杰里·本特利指出:“從人類種群出現的那一天開始,跨文化碰撞就成為了全球史的固定特征。”(1)[美]杰里·本特利著:《簡明新全球史》,魏風蓮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序言第3頁。中國朝鮮族自朝鮮半島遷移而來,在定居與繁衍、發展的過程中,通過與其他民族文化的碰撞和融合,逐漸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特點。在音樂文化方面,朝鮮族基于自身文化所具備的諸多傳統要素,結合其在各個特定的歷史時代的發展階段,經歷了審美與創作的本土化進程。“音樂作為語言是一種典型的社會和文化的產物,它所敘說的話語、表達的思想、引發的感情、體現的意識、刻畫的心理都是在一個特定社會和文化環境中發生和作用的。”(2)洛秦:《音樂中的文化與文化中的音樂》,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0年,第12頁。抗日歌曲作為中國朝鮮族歌曲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是民族藝術情感與時代、歷史精神相結合的文化產物,具有鮮明的民族音樂本土化的烙印,而《游擊隊進行曲》則是東北地區傳唱最為廣泛、最典型的中國朝鮮族抗日歌曲之一。本文對中國朝鮮族抗日歌曲《游擊隊進行曲》的音樂淵源、音樂節奏的傳承與變化、歌詞的韻律特征、傳播的社會音樂基礎等進行研究,進而考察中國朝鮮族抗日歌曲創作的時代特征、傳播的社會音樂基礎以及在與外來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體現的混雜性。
一、中國朝鮮族抗日歌曲《游擊隊進行曲》的音樂淵源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朝鮮族是最早參與抗戰的少數民族之一,他們與其他兄弟民族并肩作戰,積極參與打擊日本帝國主義、爭取民族解放的抗戰歷程,為民族解放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音樂作為“語言”主要是作用于人們的情感交流。“交流的信息傳遞方式可以是直接的,但更多的是不直接的。”(3)洛秦:《音樂中的文化與文化中的音樂》,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0年,第12頁。在抗日戰爭這一特定的環境里,抗日歌曲傳遞的交流信息顯然是直接的,并“給予人們行為外向型指導”,抗日歌曲矯健、挺拔的旋律和富有號召力的歌詞,其效應是顯現和明確的。在抗日戰爭時期,涌現出很多能夠充分調動廣大軍民群眾的抗戰熱情和必勝決心的中國朝鮮族抗日歌曲。中國朝鮮族抗日歌曲的創作主要以1930年為界,分為前、后兩個階段:1930年以前的作品主要圍繞民族主義思想進行創作和普及,1930年以后的作品則進一步結合共產主義理想進行創作和普及抗日歌曲。(4)中國朝鮮族音樂研究會:《中國朝鮮族音樂文化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22頁。這些抗日歌曲不僅在苦難期撫慰了中國朝鮮族人民的傷痛,更鼓舞了抗日民眾的斗志,堅定了抗戰必勝的信念,在他們心中燃起了希望之光,是抗日民眾的精神力量、是鼓舞士氣的號角和迎接勝利的旗幟。不少中國朝鮮族抗日歌曲和獨立軍歌還被譯成漢語,在中國的其他地區廣為傳唱。
《游擊隊進行曲》是東北地區抗日歌曲中最具有典型性、最為廣泛傳唱的中國朝鮮族抗日歌曲,也是20世紀30年代革命歌曲中最具傳統行進歌曲特征的作品之一。它是一首在艱苦的武裝斗爭行程中創作并傳唱,表現了面對任何難關和考驗都不屈不撓的革命斗爭精神的革命歌曲。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東北抗日武裝斗爭經歷了三個時期,即抗日游擊隊時期、東北人民革命軍時期和東北抗日聯軍時期。就當時延邊四縣(延吉、和龍、汪清、琿春)而言,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前的抗日武裝力量被稱為反日游擊隊、工農游擊隊或者紅色游擊隊,此后則被稱為抗日游擊隊。(5)李光仁:《八一軍旗下的朝鮮族官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44頁。延邊抗日游擊隊成員主要以中國朝鮮族為主,他們高唱《游擊隊進行曲》鼓舞士氣,抱著必勝的信念打擊日本帝國主義。可以說這首歌曲在振奮人心、團結隊伍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關于《游擊隊進行曲》的產生,學界也經歷了一段探索階段。1995年,金德俊在《寶貴的文化遺產——抗日歌謠》一文中提出,《游擊隊進行曲》是1933年由一位普通抗日戰士作詞,旋律是由歐洲歌曲發展而來的戰歌,而且是朝鮮民族風格濃郁的進行曲。(6)金德俊:《藝術論文集》,延吉:東北朝鮮民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99頁。2005年出版的《20世紀中國朝鮮族音樂文化》和2010年出版的《中國朝鮮族音樂文化史》中則記載,這是一首由獨立軍《勇進歌》改編而來的曲子。1933年,一位不知名的普通抗日戰士將朝鮮語歌詞填寫進《勇進歌》的旋律中,由此產生了這首《游擊隊進行曲》。而《勇進歌》是一首富有朝鮮民族風格的優秀作品,但作曲者不詳,認為可能是由外國旋律改編成朝鮮民族風格,若是中國朝鮮族民族固有的曲子,肯定是由具有很高音樂素養的作曲家創作的旋律。(7)中國朝鮮族音樂研究會:《中國朝鮮族音樂文化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27頁。2016年出版的《解放前中國朝鮮族歌謠研究》一書中,記載了作者在《日本歌謠集(1868-1926)》里找到了《游擊隊進行曲》的旋律出處。《游擊隊進行曲》是由1908年(日本明治四十一年)創作的《時裝節(ハイカラ節)》改編而來的,并且在延吉縣光成中學1914年使用的《最新唱歌集》中,找到了學堂樂歌《前進》的旋律與《時裝節(ハイカラ節)》的旋律幾乎一致,只是整個作品的節奏型發生了變化。(8)崔玉花:《解放前中國朝鮮族歌謠研究》,首爾:國學資料園出版社,2016年,第205-206頁。
由此可見,《游擊隊進行曲》的旋律是來自1908年創作的日本歌曲《時裝節》。1914年學堂樂歌《前進》第一次改編了《時裝節》的旋律,并重新填詞創作成《前進》。之后獨立軍軍歌《勇進歌》、抗日歌曲《游擊隊進行曲》都是在改編旋律的基礎上填詞傳唱的。《勇進歌》既是20世紀10年代至2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獨立軍軍歌,也是最廣為傳唱、最具影響力的抗日歌曲之一。因此,在其基礎上改編而來的《游擊隊進行曲》的旋律是眾所周知的音調,此后很快在抗日部隊中得以廣泛普及和推廣。
二、中國朝鮮族抗日歌曲《游擊隊進行曲》的音樂節奏傳承與變化
如上所述,中國朝鮮族抗日歌曲《游擊隊進行曲》、獨立軍軍歌《勇進歌》、學堂樂歌(9)學堂樂歌是20世紀初期在新式學校音樂課程中大量傳唱的一些原創歌曲。它是一種選曲填詞的歌曲,起初多是歸國的留學生用日本和歐美的曲調填詞,后來用民間小曲或新創曲調。《前進》三首歌曲的旋律是幾乎相同的,它們都源自日本歌曲《時裝節》,但在節奏上進行了一定的改編。



中國朝鮮族抗日歌曲和學堂樂歌中極少使用傳統音樂的復合3拍子形態,這與2拍子、3拍子、4拍子等短單位拍子的簡單、易記等特征分不開。另外,與緩慢、柔軟、律動的音樂相比,當時的朝鮮族更迫切地需要有節奏、有魄力、有強烈情緒的音樂。由于時代和民族情緒的需要,中國朝鮮族抗日歌曲的拍子形態吸收并繼承了學堂樂歌既有躍動性又有氣魄和力量的拍子形態。20世紀10年代到20年代,大部分中國朝鮮族學校都在傳唱《前進》,正因為有了這樣的旋律音調基礎,再填寫上《游擊隊進行曲》《勇進歌》等歌詞后,更容易被人們廣為傳唱。節奏變化后的歌曲旋律表現出了輕快、有力的特征,能夠使人聯想起嘹亮的沖鋒號和戰斗的勝利,真實地表現出了抗日部隊的堅強性格。
三、中國朝鮮族抗日歌曲《游擊隊進行曲》的歌詞與韻律特征
歌曲是由詩歌和旋律結合而成的,是融合文學與音樂的綜合藝術。文學和音樂的融合,意味著歌詞應與旋律在曲調、節奏、形式等方面做到有機統一。也就是說,兩者不僅要在思想和情緒色彩上相符,而且語言的音調節奏、抑揚頓挫等也要與旋律高度吻合。(10)[朝]金俊奎:《名曲創作的思想美學要求及其實踐方法》,平壤:藝術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173頁。
抗日歌曲的歌詞帶有明確的主題傾向,即激發和提高抗日戰士們和民眾們對抗日斗爭的堅強信心和不屈精神。歌詞形式繼承了7·5調類的韻律特性,表現出了歌詞語言的混和特性。中國朝鮮族歌曲的韻律具有如下特征:以歌曲的7·5調韻律為基礎,顯示出繼承傳統民歌節拍3音步的近代詩歌特征,同時結合帶有一定周期進行反復的音數律,從而形成反復的律調,表現為規則性和律動性,并賦予情緒變化等。8·5調和6·5調是以7·5調為基礎,通過一定音節數的增減形成的韻律,因此,可以認為8·5調和6·5調是7·5調的變形。在現成的旋律中填上新詞的歌曲,意味著歌詞是以歌曲旋律為前提而創作的,形式上大多從屬于旋律,而且節拍簡潔、詞匯通俗,能夠激發許多詞作者的參與熱情。
中國朝鮮族抗日歌曲《游擊隊進行曲》、學堂樂歌《前進》和獨立軍軍歌《勇進歌》等,都是8·5調。例如:
同志們呀 時刻準備 手中的武裝
帝國主義 侵略強盜 堅決消滅它
前進前進 奮勇前進 勇敢又頑強
流血犧牲 寧死千萬次 英勇殺仇敵
——抗日歌曲《游擊隊進行曲》(1933年)
往后事情 不用考慮 一心向前進
前進前進 生龍活虎 勇往直前時
青年們呀 精氣十足 奮發更圖強
向著目標前進前進 文明富強行
——學堂樂歌《前進》(20世紀10年代)
白頭山下 廣袤無際 滿洲大平原
到處都是 抗日聯軍 馳騁的戰場
排列成行 步伐整齊 一心向前進
朝氣蓬勃 邁向大步 莊嚴又悲壯
——《勇進歌》(20世紀20-30年代)
當時,由于東北抗日游擊區極其缺乏掌握近代音樂理論與創作能力的音樂家,因此,大部分歌曲都是在俄羅斯歌曲、日本歌曲、中國民歌以及傳統民歌旋律的基礎上重新填寫歌詞,使用7·5調及其變形8·5調和6·5調等創作而成,這種情況其實就是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結果。
奴才棍噶扎勒參他們一直與哈薩克交戰至十月,陸續在哈薩克游牧地搶奪駝、馬、牛、羊等牲畜,分給城內外所有官員和士兵食用。馬、牛等牲畜備用于百姓的騎乘、運輸等。
四、中國朝鮮族抗日歌曲《游擊隊進行曲》的社會音樂基礎
隨著朝鮮移民及其人口聚居地的劇增,教育、新聞、文學和藝術等文化活動也蓬勃發展起來。1906年李相卨開設了“瑞甸書塾”,中國朝鮮族的先民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寧肯自己餓著也為子女辦教育”,有錢出錢、沒錢出力,朝鮮族辦起了教育機構,朝鮮族聚居地區的學校也如雨后春筍般拔地而起。以“民族重興”和反日為教育理念的學校,將音樂課作為積極培養和強化民族意識的教育手段。而學堂樂歌既具有啟蒙性和民族性,同時因其通俗易懂的歌詞和簡潔振奮的旋律,也很容易普及。
20世紀10年代至20年代,這些歌曲在朝鮮族學校被廣為傳唱。在既有的旋律和音調的基礎上,填寫諸如《前進》一類的歌詞,便于廣大人民群眾傳唱,從而使抗日歌曲植根于朝鮮族社會的肥沃土壤中。由于學堂樂歌的廣泛傳播,抗日歌曲的旋律在群眾中已經耳熟能詳,為熟悉的歌謠填加歌詞給了他們耳目一新的感覺和更為親切的感覺。雖然抗日歌曲是出自于抗日游擊區,但其傳播之迅速、范圍之廣泛,離不開它在朝鮮族群眾中的音樂基礎。另一方面,這也說明這些歌曲符合朝鮮族群眾的審美情趣和愉悅需求。
軍歌是戰爭時期最為重要和有效的精神武器。當時,盡管中國朝鮮族在中國東北地區展開了聲勢浩大的反日武裝斗爭,但是其物質基礎或各種條件都是極其有限和惡劣的,為了更加有效地開展反日武裝斗爭,必須吸引更多的人參與其中,必須依靠強大的精神力量。這時就需要通過軍歌宣傳愛國心,喚醒國民性。軍歌是中國朝鮮族抗日武裝斗爭中不可或缺的聲音。
東北三省的獨立軍陣營認識到了軍歌的必要性,高級干部們便開始親自創作歌詞。軍歌的主題意識是宣揚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復仇之心,振奮抗戰士氣,以及表達對故土的懷念等。但是當時受沒有作曲家的時代局限,其旋律只能依賴于外國樂曲。不管這些軍歌對外國音樂旋律進行了怎樣的修改,音樂語言有多么不成熟,但這些都“不重要”,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的那樣,“無論歌詞多么陳舊,曲子多么平凡,唱國歌時都能體會到同步性”。(11)[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韓]尹衡淑譯,首爾:羅南出版社,2007年,第188頁。
當時具有代表性的軍歌有《勇進歌》《獨立軍悼念歌》《革命軍進行曲》《前進歌》《勝利進行曲》等。當時的軍歌,在音樂方面主要是吸收外來音樂和中國其他地方音樂等,其中有許多歌曲是以日本率先接受后經日本式重構的西洋音樂旋律為基礎而創作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一是因為由朝鮮族親自作曲的歌曲不多;二是因為隨著近代化的開始,許多日本歌曲已經流入到朝鮮,使朝鮮民眾都十分熟悉;三是因為人們在歌曲傳唱時,可能不清楚是否是日本歌曲而被動接受。當時把創作的歌詞借外來歌曲配曲的旋律來演唱,其特征是歌詞一般都是由教育者或獨立斗士們創作而成的,其意識傾向反映了移民和定居之痛、民族啟蒙志向、民族自強意識等。同時,最重要的是這些軍歌作為激勵獨立軍戰士們的戰斗士氣、宣傳愛國獨立思想的重要武器,一直到1945年抗戰結束依舊被廣為傳唱。
五、中國朝鮮族抗日歌曲《游擊隊進行曲》的混雜性
據文獻考證,借用《時裝節》旋律進行填詞的抗日歌曲不只是《游擊隊進行曲》,此外還有《勇進歌》《五月進行曲》《無產革命曲》《勞動者之歌》《走向革命戰場》等。在上述歌曲中,傳唱于20世紀10年代至20年代反日獨立軍內部的《勇進歌》贊頌了李舜臣、安重根等先烈的赫赫戰功,表達了緊隨先烈、英勇殺敵的意志。其他歌曲則是傳唱于20世紀30年代的抗日游擊隊時期,大部分表達了打倒侵略者、建設革命政權的強烈意愿。此外,一些歌曲也表達了窮苦百姓和勞動者們齊心協力推翻不平等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打倒資產階級、共創無產階級政權的理想。這些讓人耳熟能詳、被群眾所熟知的抗日歌曲旋律,因填上了新詞,給人們以嶄新的感受。
“占有”一詞一般指為了自己獨自使用,不經許可而占為己有。“占有”一詞也指接受某種形態的文化資本,并使該文化資本與原所有者為敵的行動。“再占有”是指通過變更某符號所在的脈絡,使該符號發揮其他符號的作用,或者帶有其他意義的行為。(12)[美]Joseph Childers,Gary Hentzi著:《現代文學與文化批評詞典》,[韓]黃宗淵譯,首爾:文學街坊出版社,2003年,第75-76頁。朝鮮族未經作者神長瞭月的“同意”,便將《時裝節》改為符合當時朝鮮族民族情緒的《前進》《勇進歌》《游擊隊進行曲》等抗日歌曲并廣泛傳播,而這樣的“前進”正是給日軍帶來落敗的沖鋒號角。
當代著名的后殖民理論家霍米·巴巴對“混雜性”所具有的文化政治學的激進性進行解釋時主張:“對抗殖民地權威的過程中產生土著傳統的變化與轉移,這一事實體現出互文性的不確定性與后殖民主義對權利與知識的支配關系的斗爭的深度關聯。在此神圣的權力語言在轉為土著符號的過程中產生斷裂,在支配的實踐中主人的語言就會帶有混雜性。”(13)[美]霍米·巴巴:《文化的地位》,[韓]羅炳哲譯,首爾:昭明出版社,2005年,第84-85頁。
霍米·巴巴在此關注的是《圣經》(支配敘事)的翻譯、變異、置換的過程,但我們可以用這一理論解釋支配階級的文本——《時裝節》在被支配階級的反殖民斗爭中的混雜性。可以說當時的日語是強者的語言,朝鮮族語言是弱者的語言,而《游擊隊進行曲》則是帶有混雜性與反諷性的又一案例。但無論如何用對方的表象體系顛覆對方,都會引起反諷的雙面性效應。在當時的社會生活環境中,朝鮮族群體很大程度上在心理上和身體上都受到壓抑。通過這種音樂可以使其身心得到宣泄,心靈上也得到慰藉。“文化身份產生于矛盾和含混地帶,混雜不但去除了模式化的想象和疆界,而且其所產生的中間地帶造就了具有多元想象與對抗策略的第三空間。在混雜中,異質性的文化彼此交織與交錯,釋放出新的能量并產生新的意義。”(14)程賀:《全球化傳播語境下的文化混雜性問題研究》,博士學位論文,武漢大學,2013年,第59頁。
音樂作為一種情感交流的“語言”,用聲音傳遞人的喜、怒、哀、樂等情感。氣勢磅礴、鏗鏘有力的音樂節奏,能夠讓人在視覺上產生影像,將音樂所描繪的畫面生動、形象地展現在人們眼前,并能夠振奮人心、喚起人們的激情與勇氣。比起文字符號,聲音符號更容易被理解和呼喚人類情感。因此,在混雜中“釋放出新能量”的抗日歌曲,在當時特定的環境下傳播得最快、最廣泛。
劉勰在《文心雕龍·樂府》中也對音樂進行了論述:“夫樂本心術,故響浹肌髓,先王慎焉,務塞淫濫。敷訓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動八風。”(15)劉勰:《文心雕龍·樂府》,https://so.gushiwen.org/guwen/bookv_4022.aspx。他認為音樂是表現人內心世界的一種方法,其影響遍布在生活的各處,而且可以深入人的骨髓之中,因此,可以感天地、動鬼神、美教化、厚人倫,由此可見音樂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有多深。
中國朝鮮族的抗日歌曲,在多數情況下固守了傳統曲調節奏,但并不故步自封,而是根據自身的需求進行一定的改變,這使其具有了特定的社會觀念和時代烙印。經過調整音高、節拍、調式、節奏等充分反映出當時特殊歷史時代的精神和歷史氛圍,可以說是在傳統觀念指導下的美學接受。
外來音樂文化一方面滿足了當時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也對當時聽眾的文化心理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另一方面,作曲家們也順應了時代的需要,借用了更多外來的音樂元素,并將這些音調、節奏與中國朝鮮族人民傳統的音樂元素糅合在一起,形成了風格獨特的中國朝鮮族抗日歌曲。
六、結語
抗日歌曲《游擊隊進行曲》是中國朝鮮族以靈活性和實用性原則對待外來文化的產物,也是特定時代下的必然產物,其吸收了日本的音樂元素,用近代音樂理念詮釋了傳統的音樂節奏,創造了全新的音樂形式。中國朝鮮族抗日歌曲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通過吸收融合外來文化,完成本民族的音樂創作。這是中國朝鮮族傳統藝術與外來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實現了中國朝鮮族近代歌曲從接受到創新的轉型。抗日歌曲是中國朝鮮族歌曲形成的重要基礎之一。
音樂是朝鮮族形成和發展過程中重要的歷史文化產物。作為文化遺產的一部分,我們可以從中發掘出時代的氣息和歷史的脈絡。混雜性是藝術的生命,中國朝鮮族歌曲也不例外地利用混雜性進行改編。在激烈的獨立斗爭和抗日革命斗爭時期,藝人和民族斗士在創作初期,也借用了中國其他地方、日本、西方的歌曲旋律。創作這些歌曲并不是為追求藝術的自律性,而是為了宣傳救國。從這一點來看,中國朝鮮族歌曲經歷了符合時代審美的藝術革新、轉換和產生的過程。由此可以充分看出中國朝鮮族歌曲創作者們的開放性文化意識和藝術創作態度,從而也使中國朝鮮族歌曲具有了更深層的價值。
中國朝鮮族是通過移居后逐漸與中國的其他民族融合,并逐漸由最初的朝鮮人轉變成為中國的少數民族之一的,因此,中國朝鮮族歌曲是帶有混雜性的新文化的產物。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僅僅是離散的人群,所有的人都經歷著文化的混雜性。因此,對于中國朝鮮族歌曲的研究,需要從文學史、音樂史、移民史、交流史、美學史、文化史等多方位視角和方法論入手進行研究。探究中國朝鮮族歌曲在其形成過程中對多元文化的接受以及本土化進程,是有待進一步探索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