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故事》:殘忍而溫柔的親密關系
魯冬旭
從情節上看,《婚姻故事》似乎改叫《離婚故事》更為合適。演員妮可(斯佳麗·約翰森飾)和導演查理(亞當·斯基飾)曾是一對恩愛的夫妻。許多說不清道不明的微妙感受讓他們漸行漸遠,最終兩人決定離婚。兩個真誠、有趣、不在乎錢財的“文藝青年”本來打算好聚好散,誰知一場徹底撕破臉的離婚訴訟大戰還是不可避免地打響了。
離婚是導演諾亞·鮑姆巴赫特別偏愛的一個主題。他此前的半自傳性作品《魷魚與鯨》取材于他小時候父母離婚的經歷,這部《婚姻故事》則取材于他自己的離婚經歷。很多人說這部電影是“婚姻勸退指南”,其實電影的基調是溫柔且極富感情的,許多場景都帶著一種“我愛過你,我從不后悔”的動人濾鏡,但溫情并不妨礙本片的清醒。本片的主題不是控訴婚姻的可怕,而是探討婚姻中的權力關系。
不管我們多么不想承認這個事實,都不能否認,任何親密關系歸根結底都逃不開話語權的博弈。
在影片所描述的親密關系中,妮可是弱勢的一方。這也許是因為她在見到查理兩秒鐘后就愛上了他;也許是因為當時她更想結婚,而查理并不那么想結婚;也許是因為她是女人,而社會對女人,特別是親密關系里的女人(也就是妻子和母親)的要求總是比對男人的要求多一些。如同影片中女律師所說:“他們容易犯錯,我們因此愛他們,但人們絕不會接受女人有同樣的感受,無論從生理上還是精神上……所以你必須完美。查理是個混蛋也沒有關系,人們永遠會用不同且更高的標準來要求你。糟透了,但就是這么回事。”
在親密關系中,一旦有了強勢方和弱勢方,就有了忽視和壓迫。弱勢方的愿望往往不被重視——夫妻倆可以為了查理的工作去哥本哈根生活半年,卻不能為了妮可的工作去洛杉磯一年;弱勢方的聲音不被聽見——盡管妮可很想當導演,可查理的回答永遠是“下一部”;弱勢方長期被要求無條件付出,且所有的犧牲都被視作理所當然——查理覺得妮可為他導演的戲做演員天經地義,還覺得妮可的片酬當然應該用來投資他的戲劇公司;強勢方的意志會自動成為已達成的協議,而弱勢方的愿望永遠只能停留在討論階段。更可氣的是,強勢方完全意識不到自己這套赤裸裸的雙重標準。正如妮可對查理所說:“你和你的自私融為一體,你甚至都分辨不出那是自私。”
遺憾的是,權力關系里的弱勢方若想爭取權益,從來只有一條路——拔刀相向。妮可這樣做了,準確地說,是她的女律師代表她這樣做了。我們總是要求親密關系必須是溫情的、為對方著想的,因此在拔刀相向的那一刻,這段關系必然也就結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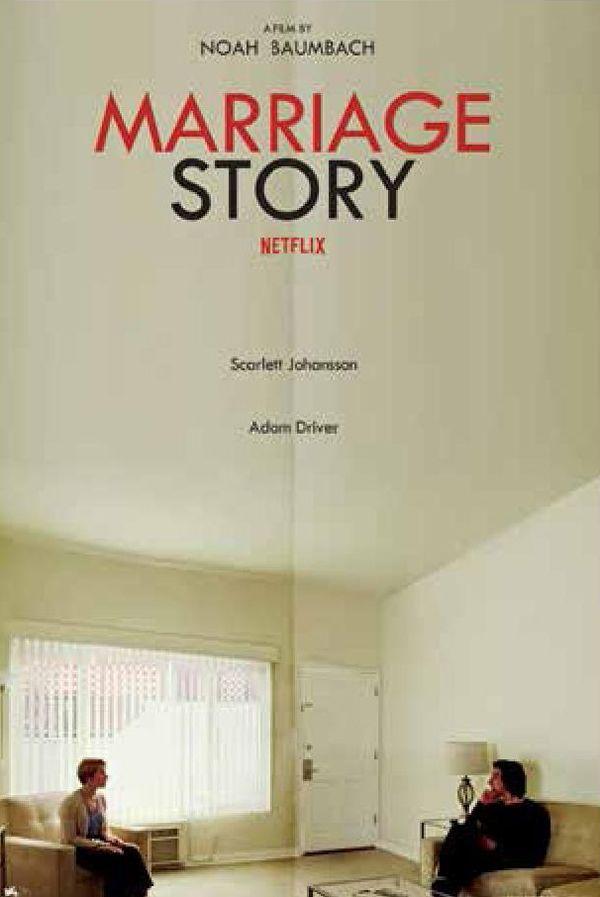
離婚戰役打響時,查理最初的反應是驚愕和不解,他覺得妮可不近人情。查理的律師在法庭上質問妮可的律師:“你怎么可以使用雙重標準?”女律師答:“為什么不可以?”有的觀眾看到這里會覺得這個女人令人厭惡,可真相是,她說得完全正確,而且她的方法也許是唯一的解決辦法。當強勢方在親密關系內用雙重標準對待自己和別人時,他又何曾問過自己“你怎么可以這樣”。
問題就在于,在親密關系里,強勢方永遠不會大發慈悲地主動解決弱勢方的困境。妮可只有要求離婚,只有劍拔弩張地刺痛對方,才能得到她想要的東西。最后,查理決定搬到洛杉磯住一年,妮可實現了她并不過分的愿望。可是為了實現這一點,他們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價:婚姻破裂,雙方撕扯到遍體鱗傷,還要支付兩份天價的律師費賬單。
也許我們會覺得這一切本來都可以避免:如果查理能重視—下對方的愿望,夫妻倆就不至于感情破裂;如果決定離婚后雙方能坐下來好好談,矛盾就不至于升級為昂貴且丑陋的訴訟大戰。但從權力關系的角度看,這些“如果”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在親密關系中,弱勢方不可能靠溫和的抗爭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拿出武器是唯一的選擇。離婚的丑陋不在于兩個曾經相愛的人如今惡語相向,而在于揭掉了親密關系的“皮”以后,婚姻關系就是這么不堪。
親密關系的殘忍之處,還在于我們往往把人生的不完美、內心的黑洞都“甩鍋”給一段我們不再滿意的關系。查理說妮可是利用他逃離洛杉磯,說妮可明明自己選擇了這種生活,卻把對自身選擇的不滿怪罪于婚姻。查理說:“你那時很幸福,你只是現在判定那時不幸福。”妮可說因為婚姻,她放棄了電影,放棄了洛杉磯,放棄了導演夢。查理說因為婚姻,他放棄了青春,放棄了自由,放棄了豐富的情愛生活。他們說的都完全正確,也都相當錯誤。親密關系永遠意味著放棄一部分自我,這不可避免,但“因為婚姻,我才沒能如何”的說辭大可不必。人生的不完美有其更本質的原因,那是每個人都只能獨自面對的東西。不肯承認自己的失敗,把婚姻當作擋箭牌,往往只是自欺欺人的軟弱之舉。
而親密關系的溫柔之處,也許都在查理的那首歌里:“它使我們擺脫了孤獨,它使我們找到了活著的感覺。”當一切過去,沒有必要再“判定自己那時不幸福”時,我們會發自內心地承認——我們曾經是幸福的。
于是,當查理讀到那封遲到的信時,當妮可彎腰給查理系鞋帶時,我們忘記了前兩個小時的丑陋,在眼淚和微笑中原諒了一切。因為誰也不能否認——他們曾深愛過對方。
愛,殘忍也溫柔,但它畢竟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