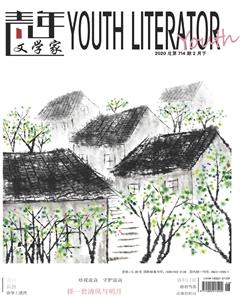創傷與成長
李媛媛
摘? 要:美國當代女作家伊麗莎白·斯特勞特的小說《我的名字是露西·巴頓》,通過回溯主人公童年到成年的人生經歷,描繪了復雜的親情關系,揭示了童年心理創傷給人們帶來的痛苦與影響。本文以創傷理論為視角,從逃避創傷、直面創傷、重審創傷、撫平創傷四個層面對主人公的心理歷程進行了解讀,力求揭示小說中的創傷與成長主題,探討創傷治愈的過程,期望為現代人在積極治愈心理創傷方面提供借鑒與啟示。
關鍵詞:《我的名字是露西·巴頓》;創傷;治愈創傷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06-0-02
創傷(trauma)來源于希臘語,19世紀末弗洛伊德等精神分析家開始對創傷理論進行科學系統的研究。二戰之后,創傷的研究進一步深化,尤其是越南戰爭造成的“戰后神經癥”更加引起了專家學者的關注。20世紀90年代是創傷研究的黃金時代,涌現出了一大批重要研究者和著作。美國學者凱西·卡魯斯在著作《沉默的經驗:創傷,敘事和歷史》中將創傷定義為對于突如其來的、災難性事件的一種無法回避的經歷,其中對于這一事件的反映往往是延宕的、無法控制的,并且通過幻覺或其它侵入的方式反復出現。[1]隨著創傷研究的范圍和對象不斷擴大,創傷理論開始從心理學、精神分析學滲入到社會學、文學等人文學科的總體研究上來。
伊麗莎白·斯特勞特,美國當代女作家。1998年出版長篇處女作《艾米與伊莎貝爾》,獲《洛杉磯時報》最佳首作獎及《芝加哥論壇報》中心文學獎,并入選橘子獎短名單及筆會/福克納獎。2006年出版《與我同在》,登上全美暢銷榜,入選美國獨立書商協會選書。第三部作品《奧麗芙·基特里奇》獲美國普利策小說獎。《我的名字是露西·巴頓》是她的第五部小說,入選2016布克文學獎長名單。
這是一部以女主人公露西·巴頓為第一人稱敘述者的傳記體小說。露西的童年生活在貧窮、虐待、孤獨中。露西拼命讀書,憑借優秀的成績上了大學,嫁給了來自中產階級的丈夫,后來成為一名小說家,然而階級躍升卻不能抹平兒時的創傷。一次手術后,露西巴頓處于緩慢而艱難的康復過程中,丈夫不愿到醫院陪伴,多年未見的母親來到她身邊。陪護時,母女談起過去,終于能夠溫和地交流,也觸發了露西童年的種種往事與回憶。在傷疤重新掀開的過程中,露西學會了直面一切,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露西也體會到了親情的盤根錯節,是痛苦之源,也是愛之源。深埋的傷口透入了溫暖的陽光,露西終于達成了自我和解,勇敢宣告“我的名字是露西·巴頓”。在創傷理論視角下,露西與母親病床前五天短暫的相守,展現了露西逃避創傷、直面創傷、重視創傷、撫平創傷的心理歷程,也揭示了只有勇于接受創傷、改變自己、接納新生活,才能治愈創傷,從過往的經歷中找到意義,獲得前行成長的力量。
一、逃避創傷
露西的父親曾經在參戰時失手殺死無辜的人,形成了扭曲的性格,對家人苛刻,有暴力傾向。母親在艱難的生活中變得易怒、不會表達愛。在二戰后美國國力上升的繁榮時代,一家五口冬天付不起暖氣費,孩子們在蛋糕店門前垃圾箱找東西吃,在學校受到同學的排斥與欺凌,一家人掙扎在社會底層。童年的貧窮、虐待、孤獨在露西心中留下創傷的記憶。露西拼命讀書,逃離原生家庭的窘迫困境,卻始終避不開童年的創傷。
因無人照看,還沒到上學年齡的露西有時被父親鎖在骯臟的卡車里。一次天黑了,蜷縮在車里的孩子發現緊鎖的車廂里有一條長長的褐色大蛇,她尖叫呼喊,哭泣著敲打著車窗,直到幾乎不能呼吸。從此,“卡車”、“蛇”成為誘發露西創傷回憶、極力避免的詞匯,甚至在母親閑聊時無意中提到“蛇”,都讓她害怕得幾乎要跳起。多年后在紐約地鐵里,孩子的哭泣都能使她聯想到自己兒時絕望的哭喊,讓她感到不安,難以忍受。露西童年中其他的悲慘經歷并沒有吐露太多,她把這些創傷與虐待統稱為“這種事”,她在極力回避,沒有勇氣說出,當她聽說其他人有相似的成長經歷時,她恐懼地渾身起雞皮疙瘩。
二、直面創傷
逃避創傷并不能擺脫心理上的痛苦,要想撫平創傷,必須直面創傷,接納不完美的人生,不完美的自我。在母親陪護的五個日夜里,在與母親的閑聊中,露西童年的一幕幕又與她重新聯系起來,雖然露西仍然不愿面對,但她已能鼓起勇氣主動說出“有時我會記起那輛卡車”。
出院后,露西將自己的童年經歷,婚姻生活和所有不愿提及的經歷寫下來向心理醫生訴說,此時她已成功邁出了最艱難的一步。當露西想要把自己的童年經歷以及與父母、女兒、丈夫的關系向他人傾訴時,當她企圖尋找理解和表達時,她已經做到了揭開傷疤,面對創傷,直面內心,不回避,不粉飾。而在直面一切的過程中,她也體會到了親情的愛恨交錯,體會到了人性與生活的復雜性。
三、重審創傷
朱迪思·赫爾曼指出,創傷不能獨自面對,只有在關系中才有恢復的可能,會因另一個人的慷慨、善意和寬容而感到與他的聯系由此開始與外部世界重新建立聯系。[2]在露西病中最脆弱無助時,多年不見的,從未出過遠門,從未坐過飛機的母親千里迢迢趕來,坐在了她的床邊,一天24小時衣不解帶的陪護著她,沒有睡過一個完整覺。這讓心中極度渴望母愛的露西倍感幸福欣喜。然而當醫生告知露西出現腸梗阻,需要立即手術時,母親卻突然提出要回家,匆忙返鄉。露西不明白母親為何突然離開。后來在露西母親臨終前,露西返鄉守在病床前,母親含淚要求露西離開,為自己保留死亡的尊嚴,以免女兒與自己在生命最后一程陷入痛苦的牽絆。此時露西懂得了母親的那種愛。其實母愛一直都在,只是不善表達,也拒絕表達。露西問母親“媽媽你愛我嗎”,母親先是阻止她問這個問題,然后只會不斷重復“傻孩子”,露西知道母親說不出口,閉上眼睛問母親,母親也只是說“當你閉上眼睛的時候”。雖然“我愛你”這三個字始終沒有說出口,但母親的心露西感受得到,這已經讓她無限歡喜。
露西父母因為她嫁給了德國人而不接受她的婚事,沒有出席她的婚禮,然而在露西的女兒出生后,露西從紐約打電話給父母時,母親說她早就夢到了,她已經知道露西生了個女兒,就是不知道名字而已。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母親對女兒的感情只是說不出,再度回憶起往事,露西感覺到了那份牽掛。
露西父親脾氣暴躁、性格扭曲,兒時會把她鎖進卡車不管不問,但露西還記得父親將她抱出卡車時,手掌在腦后的溫暖。她回憶起小時候和父親出門,在她渴望要糖蘋果時會買給她,在她買到后不想吃時自己吃掉,沒有責備她。她想起兒時,父親因露西哥哥穿女裝而大發雷霆,讓他游街示眾,帶給兒子一生的心理陰影與傷害,然而當天晚上父親又像抱著嬰兒一樣,抱著受了驚嚇的兒子一起哭泣低語。當露西回憶往事,重新審視傷口,她感受到了痛苦中的溫暖,恨中的愛意。那盤根錯節的親情,是她恨之源,愛之源,痛苦之源,也是力量之源。
四、撫平創傷
生病期間母親突然到來,多年未被提起的小名再度被叫起,露西的心溫暖而充盈,深埋心中的傷口在悄悄愈合。而在露西父親臨終前,那個多年來對女兒冷漠排斥的老人,握著露西的手熱淚盈眶地說“露西,你一直都是個好孩子”。那一刻父女間的傷痕已經抹平。
從住院到出院后的日子里,露西重新審視了童年的創傷、與父母相處中的生活點滴,她感受到了復雜的家庭關系中流淌的愛。她將自己的童年經歷以及與父母、女兒、丈夫的關系作為素材寫進自己的書中,露西的寫作導師在看過她關于童年和住院日子經歷的文稿之后曾說,“虐待,多么愚蠢的詞啊,不要為你的作品辯解,你知道,這是一部關于愛的故事……不完美,因為我們的愛都不完美”。愛,即使不完美,依然是打開封閉的內心世界的一把鑰匙,是受傷心靈復原的一劑良藥,幫助受傷者建立對自我的認識,獲得前行的信心。此時的露西更好的認清了自我,體會到了人與人之間復雜的感情,堅定了未來前行的方向,走出了創傷,收獲了創傷后的成長。
小說細膩平緩地敘述著露西的人生經歷以及她逃避創傷、直面創傷、重審創傷、撫平創傷的心理歷程,平靜的敘述中淺淺地投進了時代的側影。二戰以及越戰對家庭的摧殘,艾滋病肆虐的紐約,911事件,階級歧視,既有個人心理創傷也體現了集體心理創傷。創傷事件對受創者的影響如同躲藏在海底的怪獸,時常浮出水面,啃食受傷者的心靈。只有當我們徹底認識它,接納它,才能最終擺脫陰影的折磨,治愈創傷,實現心靈的成長。莫拉維·賈拉魯丁·魯米有這樣的詩句“傷口是光進入你內心的地方。”為何有人在傷痛中一蹶不振,有人卻會自我療愈并含笑前行?因為有些人在受傷后,依舊追尋“光”,讓“光”透過傷口進入內心,把人生照亮。史蒂芬·約瑟夫博士認為,創傷后成長的關鍵在于我們對創傷的理解。當我們從過往的經歷中尋找到意義,它就能給我們帶來前行的力量。[3]人生在世,總會遭遇艱難與磨難,我們要承擔起自己心理康復的責任,留心積極的變化,把自己引向恢復和成長之途。
在成長中受傷,也在傷痛中成長。雖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幸能夠主宰自己命運,但每個人都有選擇用何種姿態去面對命運的自由。這也是這本《我的名字是露西·巴頓》帶給我們的思考。
參考文獻:
[1]Caruth, Cathy.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2]Herman, Judith Lewis.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M]. New York: Basic Books,1992.
[3]史蒂芬·約瑟夫. 殺不死我的必使我強大:創傷后成長心理學[M].青涂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6.
[4]Elizabeth Strout. My Name is Lucy Barton [M]. Great Britain: Viking,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