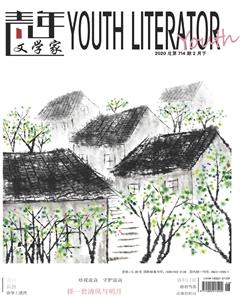魏晉風度
雷旭寧
摘? 要:魏晉南北朝是我國思想文化嬗變的關鍵時期,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環便是魏晉風度,這種迥異于兩漢的行事風格和思想風貌,由魏晉名士們不斷發揚,為中國文化的發展增添了一抹異彩。本文對魏晉風度的產生做簡要梳理,主要以阮籍和陶淵明為例,闡述其對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產生的一些解構與創造。
關鍵詞:魏晉風度;阮籍;陶淵明;創造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06-0-01
一、兩漢經學的式微與士人生活的破壞
經學是儒學在兩漢占統治地位的形態,東漢末,隨著帝國崩潰,它的影響不斷削弱,儒家的倫理道德準則已失去普遍的約束力。[1]士人們得到某種意義上的解脫,文化不再只是朝廷進行倫理教化的工具。人們對人生意義、價值的思索,都不可避免的開啟新的一頁。
思想解封的源頭是穩定的消失,建安伊始至衣冠南渡,中國大地上政局持續動蕩,對于士人來說,大一統下的晉升渠道和生存環境消失了,百姓流離失所,餓殍遍野,士族和高層文人也難得幸免。如建安二十二年的一場瘟疫,帶走了建安七子中的五位,曹植的《說疫氣》中記錄到:“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到了西晉,司馬氏出于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和自身合法性的維護,對身處文化主導位置、表達悖逆王朝主體價值觀的士人進行屠殺。參與軍政的文人也多半不得善終。文化精英們進一步失去安全感。當時許多名士,如何晏、嵇康、陸機、陸云、潘岳、謝靈運等人,都不免被卷入政治斗爭的漩渦中。他們一批一批的被送上刑場。魏晉士人面臨的是全方位的桎梏。
二、士人對傳統的解構與創造
在這種實實在在的危險下,魏晉士人的第一步是對儒學的反叛,尤其是其核心的“禮教”,時代令人失望,人就不免轉向對自身的關注,重視自身的價值,產生的是行為瀟灑不羈的名士;在自身上面找到虛無,產生的是玩弄邏輯和概念的玄學。嵇康就自稱其“非湯武而薄周孔,”從根底否定禮教的正統性和合法性,“竹林七賢”代表了衰世亂世,命運捉摸不定,志向難以實現,對死亡的思考和人生意義的質疑便應運而生,魏晉名士,如嵇康、阮籍、陸機等人的作品,都發出了一種對于人生無常、歲月易逝的感嘆。如阮籍《詠懷》八十二首:“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我們可以看到,從經學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的士人們,發現了自我,產生了一種對人世執著追求的蒼涼之感。
這一時期,受社會推崇的這類名士,他們既沒有顯赫的功勛,也沒有可稱道的節操,卻以其個體人格本身,成為人們的理想和榜樣。
魏晉士人的第二步是對思想的重新解讀和對文學的創新,兩漢文學思想重功利。當時的詩學,實際上是政治學和神學,文學既是宮廷玩物也是經學附庸。到了魏晉,文學地位產生變化,魯迅說:“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最早看重文學的曹丕也說:“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非功利、重抒情,這時期的詩歌擺脫了漢代詩歌那種“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功利主義詩歌的影響。文體上,五言詩體確立成熟。
三、阮籍與陶潛
眾多魏晉名士中,阮籍和陶潛兩人的成就最高,風格亦有所不同,作為魏晉風度兩個維度的代表可以說非常恰當。[2]
阮籍是受莊子思想影響很深的人,他也向往于一個精神自由翱翔與無何有之鄉、與道一體的人生境界,但是又無法實行。但他內心卻是無比苦悶與彷徨,既有是非之心卻又不能訴說,他其實有濟世之志,曾經嘆息過“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這樣的話,他還有諸多怪誕之舉,比如獨自駕車到林中大哭。這樣的心境對他的文學創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也是他的詩作中的一大特點,把心中的哀傷用曲折而強烈地抒發出來,深沉美麗。
他以隱晦曲折的方式對黑暗、腐敗的現實,表現了深沉的憂憤和不滿,阮籍的懷古詩即是隱晦方面的代表:
愿登太華山,上與松子游。漁父知世患,乘流泛輕舟。(《詠懷·其三十二》)
愿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詠懷·其八》)
人情有感慨。蕩漾焉能排。揮涕懷哀傷。辛酸誰語哉。(《詠懷·其三十七》)
另一個人格化的理想代表是陶潛,與阮籍相似的地方在于,陶淵明也是一個政治斗爭的回避者。他雖沒有阮籍那樣高的政治地位,但他的家世和少年抱負都讓他與政治產生了聯系。陶淵明卻十分自覺地從政治中退出來,將精神的慰藉寄托在田園生活中的飲酒、讀書、作詩上。陶淵明更看重精神的自由,不以心為形役,不讓精神的需求服從于物質的追求,追求在人與自然和諧的相處中得到寧靜和歸屬感。
當然,陶淵明在物質和精神二者難以得兼時,也流露出物質困乏的艱難和苦惱,但是他決不愿為了物質的享樂而犧牲精神的獨立和自由。他在田園和勞作中找到了歸宿和寄托,他把自漢末以來的人的覺醒提到了一個遠遠超出同時代人的高度,達到了一種尋求更深沉的人生態度和精神境界的高度。
而陶淵明這種精神境界和寄情與田園之間的處世態度,使得他的文學作品表現出一種情味極濃的沖淡之美。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飲酒》)
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酬劉柴桑》)
阮籍和陶淵明在魏晉時期,之所以能成為兩個人格理想化的代表,就在于他們分別創造出了兩種不同的境界。在我看來,阮籍和陶潛都在回避丑惡的現實環境,但前者只是在逃離中郁悶,后者則在逃離中找到了一片新的樂園。阮籍憂憤無端,慷慨人氣;陶淵明超然世外,平淡沖和,他們都以深刻的形態表現出士人們的理想追求和魏晉風度。
注釋:
[1]羅宗強,《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M].北京:中華書局,2016.97頁.
[2]李澤厚,《美的歷程》[M].北京:三聯書店;2014,1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