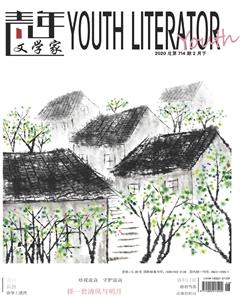我家老屋
王桂新
我久久地站在老屋前,用靈魂感知它,冥冥中傳來(lái)一聲嘆息。四十多年了,我不曾細(xì)致的讀它了。“少小離家老大回”,當(dāng)我終于可以靜靜站在它面前,用心聽它時(shí),它卻老去了,老得都站不起來(lái),認(rèn)不出我了。靜默中的無(wú)言,心有著撕碎的痛。
老屋有著悠久的歷史,七十多年前,爺爺奶奶帶著父親姑姑,到這水草豐盈的葦塘邊分戶另過,依塘傍水建了這三間房。當(dāng)時(shí)所建的是低矮的茅草房屋,后來(lái)翻建成三間泥瓦房子,這低矮的老屋,在我眼里勝過高大氣派的洋房。老屋最有特色是窗戶,只有在古裝戲里才能見到的窗,木欞把窗子分割成多個(gè)小方塊,下半是死的,開窗時(shí)要把上半抬起,用鉤子鉤住,這樣的窗子很有優(yōu)勢(shì),不用擔(dān)心孩子玩耍掉到窗外,窗紙是由毛頭紙糊的,窗紙上涂上豆油(防止刮風(fēng)下雨濕破窗紙),后來(lái)陸續(xù)換上了塑料或玻璃。記憶中的東小間草棚子是倉(cāng)庫(kù),永遠(yuǎn)是黑漆漆的,棚頂是裸露的木椽子,縱橫交錯(cuò),從一頭搭到另一頭,足有五米長(zhǎng)。都說歲月無(wú)痕,可那黝黑的椽子,卻記載著歲月的深深足跡。
小時(shí)候,老屋是我的天堂,房邊潺潺流水,清澈照人,溪上的獨(dú)木橋通向南葦塘邊小菜園,一幅小橋流水人家的嫻靜畫卷。誰(shuí)說“水至清則無(wú)魚”?那條小溪里不知生了多少魚,站在塘邊會(huì)看到成群的魚在游動(dòng),那些公分長(zhǎng)的小精靈,在水里自由舒展著,搖擺的尾部曾讓年少的我有了不盡的夢(mèng),何時(shí)我也能如魚般游著呢,長(zhǎng)大后每次看到水里的游魚都會(huì)問自己,它們快樂嗎?可惜莊老先生走了,沒人會(huì)告訴我。有時(shí)會(huì)坐在塘邊石頭上,把腳放進(jìn)水里,一動(dòng)不動(dòng),一會(huì)兒魚兒就會(huì)圍在腳周,不時(shí)咬上一口,酥癢的感覺轉(zhuǎn)瞬即逝,但不敢久放,塘里有種俗稱肉馬鳀(水蛭)的水生物會(huì)沿腳心鉆進(jìn)人體,那不時(shí)彎扭的身體會(huì)讓我怕蛇一樣怕它,實(shí)在忍不住時(shí),會(huì)和小哥哥們?cè)谔吝叺乃堇镉门钃启~過癮,那也不能一心撈魚,還要擔(dān)心水蛇的偷襲。可憐那些離開生命本源的小魚小蝦小蝌蚪,不是死在瓶里,就是成了雞鴨的美食。
最喜歡晚上全家圍坐在堂屋油燈下,媽媽、姐姐們棉紡線,爸爸蹲在地上編筐,爺爺抽著旱煙袋,撫著胡須講故事,那時(shí)的家鄉(xiāng)沒有電視,電燈,連收音機(jī)都沒有,更別說玩英雄聯(lián)盟和吃雞了。當(dāng)然最開心的只能就是聽爺爺講故事了。爺爺?shù)木使适露剂粼谕砩洗禑艉笾v。爺爺講故事現(xiàn)在想來(lái)就是胡編的故事或者沒由來(lái)的故事吧。爺爺只上過幾天私塾,但知道的卻不少,經(jīng)歷的也多,當(dāng)過風(fēng)水先生,會(huì)泥瓦匠手藝,治扭傷正筋骨,樣樣在行,他總能把一切編進(jìn)故事里,哄著我們玩。記得有一次講聊齋,嚇得我們把頭蒙在被子里,還是不肯讓爺爺停下,半夜里睜開眼睛看著沒有窗簾的窗戶,擔(dān)心鬼來(lái)了。在爺爺?shù)淖炖铮抑懒巳龂?guó),西游記,知道了忠奸,更知道了做人應(yīng)該本份。爺爺沒直接教育過我們,但那種潛移默化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
每年最盼望的日子就是過年,過年不僅能穿上新衣服,還可以吃到很多平時(shí)吃不到的東西,最重要的是可以有機(jī)會(huì)打著紅燈籠,在道邊空地上放上幾只撿來(lái)的小洋鞭,感受一下家過年的氣氛,但這種待遇不是時(shí)常能有的,我的記憶中也只有幾次。老家過年有些老習(xí)俗,這種習(xí)俗對(duì)我來(lái)說很神秘,臘月二十九那天爺爺就會(huì)在廳堂的北面掛好家譜,把那些身著古裝的先人們請(qǐng)到家里,好吃好喝擺滿案前,晚上吃年夜飯時(shí),先由爺爺端一碗餃子,叩完頭,再把餃子放到幾案上,請(qǐng)先人品嘗,然后家里男人依次叩頭,從煮餃子開始一直到吃完飯,不到不得已是不準(zhǔn)說話的。平時(shí)慈愛的爺爺,變得格外嚴(yán)肅,我們這些小的更是一聲不敢不吭,只感覺一種肅穆裹著我,那一刻仿佛失去了童心。
如今的老屋只留下些許記憶,曾經(jīng)的“故事”追隨爺爺而去,童年的快樂也灑落在老屋的泥土里。我不知道另一個(gè)世界的爺爺、奶奶是否會(huì)記起老屋,還有老屋旁邊的那株空心大槐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