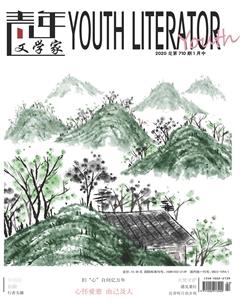回歸自然:生態(tài)后現(xiàn)代視角下再讀《詠水仙》
摘? 要:本文以生態(tài)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為基礎(chǔ),對英國十九世紀(jì)浪漫主義作家華茲華斯的詩作《詠水仙》進(jìn)行分析,得到應(yīng)對現(xiàn)代性危機(jī)生態(tài)性的啟示。
關(guān)鍵詞:華茲華斯;生態(tài)后現(xiàn)代主義;《詠水仙》
作者簡介:張若涵(1995.8-),女,漢族,遼寧大連人,在校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學(xué)。
[中圖分類號(hào)]:I106?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2-2139(2020)-02--02
引言(緒論):
華茲華斯作為英國杰出浪漫主義詩人之一,早年與柯勒律治及騷塞兩人一同隱居在英國西北部的湖區(qū),并稱為“湖畔派”詩人。他們是英國文學(xué)史上最早采用浪漫主義風(fēng)格進(jìn)行創(chuàng)作的作家群體。華茲華斯作為他們中的一員,相當(dāng)熱愛大自然,并且十分厭惡資本主義制度下所謂的城市文明。華茲華斯對工業(yè)社會(huì)充滿了斥拒,他認(rèn)為工業(yè)社會(huì)處處充斥著對人性的壓抑。華茲華斯認(rèn)為科技高速發(fā)展會(huì)導(dǎo)致人與自然的對立,人的精神與肉體亦會(huì)被分離,故他對“二元論”背景下西方人價(jià)值觀產(chǎn)生了嚴(yán)重質(zhì)疑。這些充分的表明華茲華斯在人與生態(tài)及自然關(guān)系中的預(yù)見性,以及他與同時(shí)代文學(xué)藝術(shù)家理念上的不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其創(chuàng)作中流露著與斯普瑞特奈克別無二致的思想意識(shí),那便是生態(tài)后現(xiàn)代主義。
本文以生態(tài)后現(xiàn)代主義為基礎(chǔ),對華茲華斯《詠水仙》一詩進(jìn)行解讀,以期待得到對現(xiàn)代性危機(jī)更加理性的認(rèn)知與應(yīng)對。
一.
十八世紀(jì)六十年代英國第一臺(tái)蒸汽機(jī)的運(yùn)轉(zhuǎn)帶動(dòng)著人類走進(jìn)工業(yè)文明時(shí)代。人類以空前的規(guī)模和速度從大自然攫取物質(zhì)財(cái)富。時(shí)至今日,科技更是以令人炫目的速度,提升著的人類的生活質(zhì)量和水平。但是與此同時(shí),我們的生存環(huán)境也在被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破壞力摧毀。有些破壞可以挽回,有些卻覆水難收。嚴(yán)重的環(huán)境污染問題迫使人們思考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關(guān)鍵命題。擺在人們面前的“要金山銀山,還是綠水青山”的這個(gè)抉擇,亟待人們作答。現(xiàn)代性并沒有給人們帶來“和平的世界”或者“自由的世界”,相反帶來的是環(huán)境污染、世界的毀滅、核威脅等,這讓人們的理想破滅,生存的意義消失。那么,重新審視生存方式的追尋成了一個(gè)大課題。生態(tài)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應(yīng)運(yùn)而生。
在上世紀(jì)九十年代 末,查倫·斯普瑞特奈克在《真實(shí)之復(fù)興:極度現(xiàn)代的世界中的身體、自然和地方》(1997)一書中深刻地分析了現(xiàn)代性危機(jī),對其外在表現(xiàn)的十一種形態(tài)進(jìn)行了批判。她主張不應(yīng)該把經(jīng)濟(jì)因素作為社會(huì)的核心焦點(diǎn)和驅(qū)動(dòng)力量來操控社會(huì)的一切,拒絕把人異化為“經(jīng)濟(jì)人”的做法。斯普瑞特奈克指出:“現(xiàn)代生活允諾人們可以脫離變幻莫測的身體、脫離自然的限制以及脫離對地方的鄉(xiāng)土聯(lián)系”[3](p2)。按照現(xiàn)代世界觀,“身體被看成一臺(tái)生物機(jī)器,自然界僅僅被看作是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的外殼,地方觀念成了世界主義者眼中的未開化之物”[3](p2)。日復(fù)一日,人們深受這種世界觀的毒害。生態(tài)后現(xiàn)代主義則認(rèn)為,“身體”是“統(tǒng)一的身心”,“自然”是“與我們的身體密不可分”的“物理環(huán)境”,“地方”是“生物區(qū)域,是社區(qū)和個(gè)人得以舒展的物理場所”。[3](p5)
關(guān)于“身體”,斯普瑞特奈克指出,在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里人被視為一種機(jī)器,與自然作斗爭 ,這種“新鮮”的世界觀割裂了人與自然之間原本的和諧,促使人從自然中分離出來,進(jìn)而與自然形成對立。實(shí)際上,人的生命是由各種因素以一種微妙的力量平衡進(jìn)而產(chǎn)生的產(chǎn)物,它是一個(gè)動(dòng)態(tài)的系統(tǒng),對自己內(nèi)部及外部的世界都非常的敏感,每一個(gè)身心都是獨(dú)一無二的,每一個(gè)身心都與周圍的整體環(huán)境相協(xié)調(diào)。關(guān)于“自然”她認(rèn)為自然本質(zhì)上是與人相互貫通的有機(jī)整體,自然是鮮活的,它并不是人類所壓榨的對象,而是我們?nèi)祟愃蕾嚨募覉@,人本與自然同生共存。關(guān)于“地方”她指出人與“地方”密不可分,人時(shí)刻與“地方”所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地方”是社會(huì)、文化及生態(tài)相融合的場所,“地方”給人帶來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然而,現(xiàn)代人脫離了可以給予他們心靈滋養(yǎng)的地方,生活在混凝土筑成的森林里,惶惶不可終日,度過這看似真實(shí)實(shí)則罔矣的生活。
二.
華茲華斯生逢18世紀(jì)末期,此時(shí)英法兩國資產(chǎn)階級(jí)革命及第一次工業(yè)革命正高潮迭起,他滿懷抱負(fù)投入法國大革命,但隨著大革命失敗,他的關(guān)注點(diǎn)也從“人的世界”轉(zhuǎn)移到“自然的世界”,他逐漸接受以盧梭為代表,主張“泛神論”思想。他認(rèn)為上帝并不是在遙遠(yuǎn)的天國,而是在自然中,自然中上帝以及他的神性無處不在。華茲華斯要回到自然中去,從自然中尋找理性從而補(bǔ)救被工業(yè)文明所割裂的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恢復(fù)人與自然相協(xié)調(diào)的狀態(tài)。他看到科學(xué)技術(shù)的廣泛運(yùn)用對自然和社會(huì)所帶來的破壞,就此為突破口,以詩為器,表達(dá)出自己對自然的斥拒。
《詠水仙》一詩源于華茲華斯的回憶,兩年前一次訪友歸來,途徑高巴羅公園時(shí)偶遇湖邊大叢水仙花盛綻綺麗之景。這首詩語言精練,通俗易懂,充分體現(xiàn)出華茲華斯禮敬自然,欣賞記憶的詩歌特點(diǎn)。
在詩的開篇,詩人將自己比作一朵孤獨(dú)的流云,飄蕩于山谷之上,開篇色彩暗淡,“我”是一朵灰暗的流云,飄浮在空中,將整個(gè)場景都淡化,從側(cè)面體現(xiàn)出“我”當(dāng)時(shí)悶悶不樂,行動(dòng)漫無目的。實(shí)際上,這里寫出了詩人對社會(huì)的真實(shí)感受:在工業(yè)文明所帶來的丑陋的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中,那高傲而又純潔的靈魂只能郁郁寡歡。但緊隨其后兩行話鋒一轉(zhuǎn),“我”忽然之間發(fā)現(xiàn)一大片水仙盛開,場景立刻變得歡快有力,凸顯出詩人初見水仙的欣喜。隨著詩歌節(jié)奏的明顯加快,整體畫面出現(xiàn)一種動(dòng)態(tài)的快感,無論是在措辭上,還是在語氣上。與開頭二句相比,“我”是靜止的,后來出場的水仙一躍成為全場的焦點(diǎn),吸引了無數(shù)讀者目光。“水仙”的出現(xiàn)使得詩人那陰郁的內(nèi)心也有了陽光照射進(jìn)來,以“水仙花”為代表的大自然正是射進(jìn)詩人那空洞內(nèi)心的裂縫中的陽光,讓詩人那顆飽經(jīng)工業(yè)社會(huì)丑惡現(xiàn)實(shí)所摧殘的心靈得以滋養(yǎng)。第二節(jié)詩人繼續(xù)用擬人及比喻等修辭方法由近及遠(yuǎn)的描摹著一望無盡的水仙。它們多如天空中的星,沿著海岸向前延伸,一眼望去,猶有萬朵,隨風(fēng)起舞,婀娜多姿。詩人筆下的“水仙”此時(shí)完全占據(jù)了主角的位置,當(dāng)然此時(shí)“水仙”代表了自然的精華,是自然靈魂的美妙表現(xiàn)。
第三節(jié)中,詩人運(yùn)用了對比的寫作手法,將粼粼湖波與水仙花那曼妙的舞姿進(jìn)行對比,進(jìn)一步闡明了連湖水的漣漪都不及水仙花那舞姿。隨后詩人筆鋒再次轉(zhuǎn)換,“水仙花”此時(shí)已經(jīng)不再普通,它成為了我的 旅伴,成為了 幫助“我”走出孤寂與哀傷的老師。前三節(jié)里不難看出,在那個(gè)資本主義迅猛發(fā)展的年代,在那個(gè)物欲橫流,人性泯滅,的年代,“水仙”作為自然的代表,永遠(yuǎn)快樂,永遠(yuǎn)自在,并不會(huì)因?yàn)椤拔摇北瘋瘋八伞笔亲匀慌c理性的象征,也不難看出,詩人極力強(qiáng)調(diào)回歸自然,斥拒工業(yè)文明的思想。
第四節(jié),也就是最后一節(jié)里,每當(dāng)詩人獨(dú)處于臥室之中,每每感到孤獨(dú)之時(shí),只要一想到水仙花,便會(huì)感到歡欣鼓舞,此時(shí)水仙花已經(jīng)化身自然中歡樂的精靈,它不僅是詩人的精神導(dǎo)師,更是世間萬物的快樂源泉和精神導(dǎo)師。詩人將自己孤傲高潔的靈魂和以水仙花為代表的大自然的歡快、美好和淡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詩人看來,只有在大自然中才能尋找安慰,尋找人性最后歸宿的情懷;只有大自然才能夠撫慰人的心靈創(chuàng)傷,使人得到真正的幸福。這首詩雖然是在歌頌水仙,但同時(shí)也是詩人自己內(nèi)心的抒發(fā)和感情的自然流露。
華茲華斯在大自然中成長起來,山河大川 便是他童年最好的玩伴,他們相互浸染,他的身心便也和諧地同大自然相融。這樣的成長環(huán)境使他深信,和諧且健康的身心由自然孕育,所以重回自然,重回“地方”,遠(yuǎn)離喧囂又不真實(shí)的現(xiàn)代生活,讓身心得以放松。這一點(diǎn)雖與斯普瑞特奈克隔閡幾世但也不謀而合。
三.結(jié)語
華茲華斯用詩歌表達(dá)出了人類與自然相融合這種觀點(diǎn)。他把自然作為精神的安慰,為了取得主體與客體、人與自然、意識(shí)與無意識(shí)之間的重新協(xié)調(diào)的努力。由此可以看出,華茲華斯描寫的自然不是簡單的生活情趣,也不是被人類控制的從屬,而是人類幸福生活的源泉。這是一種先進(jìn)而充滿生態(tài)性的啟示,對未來有著積極深遠(yuǎn)的影響。
參考文獻(xiàn):
[1]張秀梅.抗拒現(xiàn)代:再讀華茲華斯[J].《廊坊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7 (4) :35-39.
[2]肖霞.華茲華斯《我孤獨(dú)地漫游,像一朵云》淺析[J].徐州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0,(4).
[3]查倫·斯普瑞特奈可.真實(shí)之復(fù)興:極度現(xiàn)代的世界中的身體、自然和地方[M].張妮妮,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